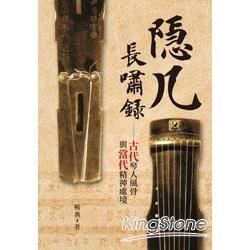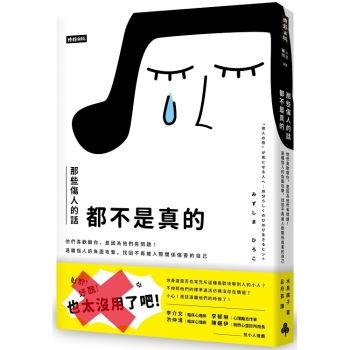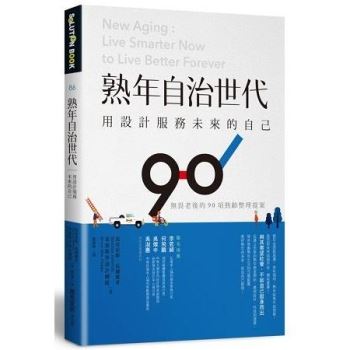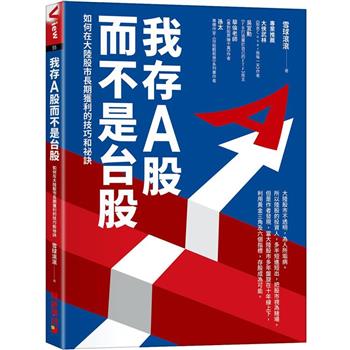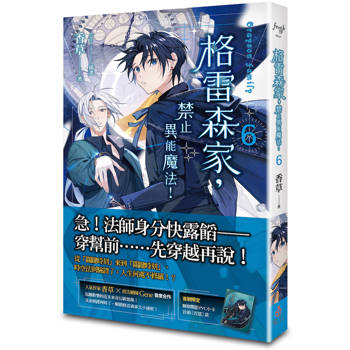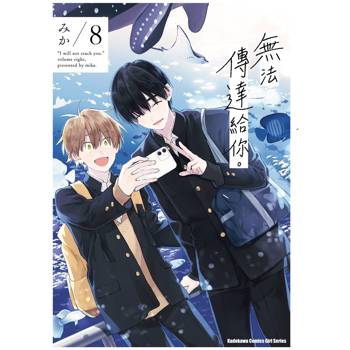音樂是文化藝術中的一種巔峰之物,而古琴又是中國音樂與群藝之首,是金字塔的塔尖,而不是地基。若要深刻理解這門藝術,必須充分懂得它的地基和土壤裡博大之所藏:這就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乃至全世界一切博覽旁通的文化。 琴作為最古老的中國藝術,它也不可避免地帶有犧牲的烙印。 只是它在表達對大自然與人性的愛時,能偶爾忘卻這一烙印,為中國士大夫知識份子,文人或學人們暫時找到一個療傷的角落。 古琴也是一個悖論,一個具有「自我犧牲」的文化象徵。因琴之為物,如刀在手,譬如古根,可藥可毒。藥者養生延年,補瀉雌雄;毒者貪多失衡,引頸自割。在世界藝術史上,因迷戀藝術本身之美而導致悲劇的事件實在太多了。美都是危險的。哪怕是所謂的澹泊之美。就像曾有人所云「古書有毒」一樣。在歷代琴史與琴人中,一直也都有各種各樣的走火入魔者。 中國古代的人嘗「隱几而坐,仰天長嘯」。但靜心的方式很多,何必彈琴?當然有人說,只要通過持之以恆的練琴,就能獲得靜心。沒錯,但你要是原本心就不靜,輾轉反側,見人如鬼,彈琴又有何用呢?那只能讓你更鬧心,也未可知。所謂秉性難移,出問題的往往只是人本身,而不是琴。古琴太無辜了,它只是一件樂器,不是一件醫療器械。一個人若真靜心了,真有定性了,即便是去殺人放火,大愛大恨,激蕩狂狷,也會泰然自若,靜如止水。說白了,即琴因人變,而不是人因琴變。琴的完成,也絕不是靠幾個人的喧囂就能造就的。那需要靠整個歷史、文明與思想來傳承、甚至要靠多元的資訊刺激和新理念的灌溉、靠具體的實踐和反抗來驗證,最後再大浪淘沙,披肝瀝膽,並對剩下來的東西有所思、有所化、有所得,才能窺其於萬一罷。 作者楊典自小接觸東、西方的音樂與樂器,因著對古琴的熱愛,在古琴領域中鑽研多年,不僅成為在中國大街上開設琴館的第一人,亦藉由持續的教學、講座、演出、錄製古琴演奏光碟與出書,和大家分享這個中國音樂與群藝之首——古琴。
作者簡介:
楊典(1972-) 大陸作家、古琴家、畫家。 已出版作品: 隨筆集:《狂禪:「無門關」鏡詮》、《孤絕花》、《肉體的文學史》、《打坐》。 短篇小說集 《鬼斧集:異端小說、頹廢故事與古史傳奇》。 詩集《花與反骨》、《禁詩》及古琴演奏專輯(雙CD)《移燈就坐》等。 古琴師承虞山派著名琴家吳文光先生。
章節試閱
不久前有學生已經對我說,看到我的繪畫與文學作品太多,而關於古琴音樂方面的東西似乎比較少。在這裏我不得不解釋:一來是過去琴學文章已很多,《琴殉》初版時也出過不少。我又不太喜歡說口水話,所以沒有正經的琴學文章,就很少會放在網上。其次,我是多職業,文學寫作、編劇與繪畫佔用的時間也很多,古琴雖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但也遠不是全部。不過由於朋友的提醒,我會注意到這個問題。畢竟古琴教學不能只在上課的那一個小時糾正技巧、講琴譜和音樂處理,更多的還有對傳統文化、琴、音樂和世界藝術,現代社會和古今歷史的關係、以及我個人思想中對古琴的認識。這些都應該是教學的一部分。雖然中國人中韓愈《師說》之毒比較深,所謂「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但我從來不覺得導師的意義就在於「專攻」二字。恰恰相反,一個好的導師應該影響給學生的是更多別的東西。至於教授古琴領域中的東西,本來就是作為導師分內之事,不存在專攻與特權的問題。 當前的問題是,除演奏外,很多古琴教師根本就沒有更多的東西教給學生。是學生不需要嗎?不是,是老師本來很貧乏罷了。 一年教學十來個曲子之後,所謂的老師們說完指法,講完琴史和廣陵散那點故事,談談演奏裏的竅門,再吹噓一下對琴界的瞭解和某些老頭的鳥事,就再也沒什麼可說的了。從師學琴的普遍現象是,除專業學生外,其他學生在略知一二,管窺全豹之後,大多即開始自己打譜、遊學、尋名師、找突破、甚至對此藝術開始猜疑或放棄……而新的老師也一樣給的有限,膚淺,讓大多數人更加失望。有些人還能斷續堅持,有些人則掛琴封書,逐漸淡忘。這本不是大家最初求學時所期望的結果,更不是老師願意看到的結果。業餘學琴者能堅持到五年以上的,只有十分之一。但為什麼會這樣呢? 學琴的人朝三暮四不認真,這很正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對大多數人來說,學琴只是一種休閒方式,並非要專業化藝術化,更不想變成壓力。但是怎麼有的人就能堅持下來並自得其樂呢? 問題自然不全在學琴者,大部分還是在教琴的人。 琴家陳雷激曾經笑對我說,說他以後要開一個古琴「教師班」,就教這些目前在教琴的老師怎麼彈琴。陳雷激說的只是演奏方面。我認為他的想法很對,而且還要更擴大:真正關鍵的是要教這些漫天蝗蟲一樣多的古琴老師怎麼教學——尤其在當教學告一段落之後,當「專攻」領域內的事情進入假期之後,該怎麼影響學生對藝術與文化本身的認識與吸收。有些人跟了好的琴家,一學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半輩子。真的是古琴本身有那麼多東西可學嗎?不完全是。閣譜三千,難道每一首曲子你都能給學生講解?就是能,這也是可笑的。學做原子彈也有畢業的時候。況且藝術這東西,從來就不需要一般意義上的「老師」。歷史上沒有一個好的藝術家是靠老師「教」出來的。誰知道嵇康、郭楚望、朱權、嚴天池或張孔山等的老師究竟是誰呢?當然,他們肯定也有老師,很多藝術家都有所謂「師承」,哪怕是無師自通的天才也需要「不師古人師造化」,向大自然學習也是在拜師。既然是有師,這就對導師本身的水平與智慧提出了一種考驗。你在思想上的,人格魅力上,文化與行為上的,都會被求學的人提出質問。天才可能不會來找你。而找你的人裏面也未必就完全沒有具備天才潛力的人。那麼,曲子學完後,你用什麼影響他們呢?減字譜嗎?流派風格嗎?指法和名氣嗎?演奏技巧嗎?進門是老師,出門是路人嗎?簡單的亦師亦友以便於隨時喝酒吃肉侃大山嗎?……恐怕都不是。音樂是文化藝術中的一種巔峰之物,而古琴又是中國音樂與群藝之首,是金字塔的塔尖,而不是地基。但是要深刻理解這門藝術,則必需充分懂得它的地基和土壤裏博大之所藏:這就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乃至全世界一切博覽旁通的文化。古琴好比中醫學,琴師好比醫師,學琴者好比病人,漫長的教琴好比看病——那是一個長期調整演奏、琴學與藝術乃至生活方式不平衡的過程。而龐大的中西歷史文化和思想體系,無數的藝術現象和作品,就好像埋藏在萬物與大地下的藥材,你只有對所有的草藥,礦物藥和陰陽四時五行變化有深刻瞭解,對學琴者的精神和弊病進行適當的望聞問切,引導與灌輸,才能夠讓其從無到有,練氣化神,使本來虛弱的琴音樂在他們手中逐漸健康起來。
不久前有學生已經對我說,看到我的繪畫與文學作品太多,而關於古琴音樂方面的東西似乎比較少。在這裏我不得不解釋:一來是過去琴學文章已很多,《琴殉》初版時也出過不少。我又不太喜歡說口水話,所以沒有正經的琴學文章,就很少會放在網上。其次,我是多職業,文學寫作、編劇與繪畫佔用的時間也很多,古琴雖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但也遠不是全部。不過由於朋友的提醒,我會注意到這個問題。畢竟古琴教學不能只在上課的那一個小時糾正技巧、講琴譜和音樂處理,更多的還有對傳統文化、琴、音樂和世界藝術,現代社會和古今歷史的關係、以及我個人...
作者序
冬去春來,時至立秋,眨眼又過了一年。自吾古琴演奏光碟《移燈就坐》發行後,關注本書的人更日益多起來。記得八年前,本書第一次在琴界內部流傳時,曾是用的繁體字版:因書中牽涉到不少古琴減字譜和異體字,用簡體字頗難傳意。後隨虞山派宗師吳文光先生學琴,提耳立雪,對琴之理解也漸漸有所演變,而本書亦在反省中逐年增加內容,直至最終出版。惜大陸正式出版物,皆禁止用繁體字,故不得已而為之。且大陸版還刪節了部分所謂「敏感的文字」。而繁體字本是漢語正統,說真話和出版作者原文,才能有效體現書的意義,這是我一貫的認知。這次有幸,由臺灣秀威蔡登山先生應允,再次出插圖本繁體字版,讓我仿佛又回到了此書第一次出現在琴館,於隆冬時節如古人「隱幾而坐,仰天長嘯」,卻令許多琴學師友激動的景象和難忘的日子。去年本書第三版面世時,因時間倉促,未將寫浙派琴家姚公白先生之《老鬼》一篇收入,甚為遺憾。這次自然補入書中,也算是為姚師當年曾幫我校對本書做一個交代罷。弦波鼓浪,太音橫流,迅雷風烈必變,如今琴壇之喧囂浮躁,早已今非昔比。然少年狷介往事不再,而文字與琴音猶存,此即為人生大幸之事也。其餘皆為多言了。特此為記。
冬去春來,時至立秋,眨眼又過了一年。自吾古琴演奏光碟《移燈就坐》發行後,關注本書的人更日益多起來。記得八年前,本書第一次在琴界內部流傳時,曾是用的繁體字版:因書中牽涉到不少古琴減字譜和異體字,用簡體字頗難傳意。後隨虞山派宗師吳文光先生學琴,提耳立雪,對琴之理解也漸漸有所演變,而本書亦在反省中逐年增加內容,直至最終出版。惜大陸正式出版物,皆禁止用繁體字,故不得已而為之。且大陸版還刪節了部分所謂「敏感的文字」。而繁體字本是漢語正統,說真話和出版作者原文,才能有效體現書的意義,這是我一貫的認知。這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