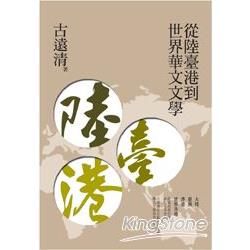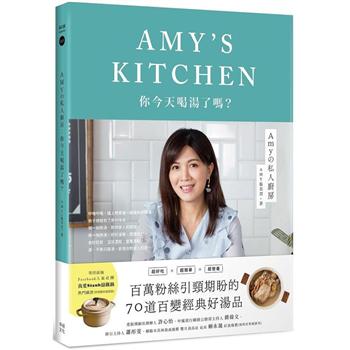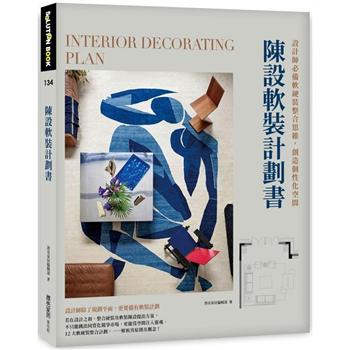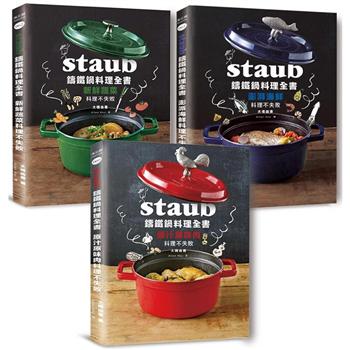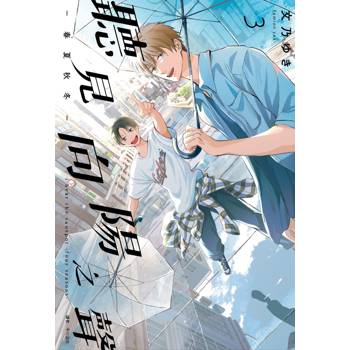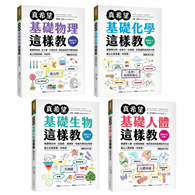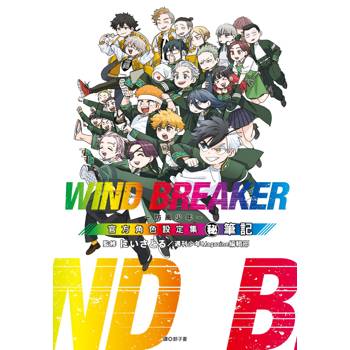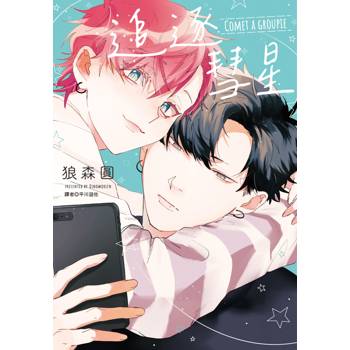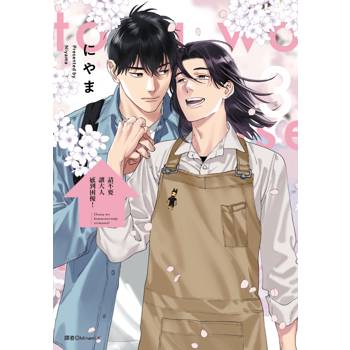自序
對《從陸台港到世界華文文學》這個書名,也許有朋友會持異議:世界華文文學雖然有一些成分和臺灣文學接近,如臺灣赴美作家白先勇、葉維廉、於梨華等人的作品和海外華文文學有交叉之處,可把香港文學和臺灣文學放在一起就不合適,因為「臺灣文學和香港文學的距離一直很遠,彼此陌生,彼此瞧不起。」在筆者看來,臺灣文學與香港文學其性質比大陸文學更接近:兩者一直在淡化乃至沒有約束創作自由的文藝政策,出版商業化和自由度均比大陸高,另還有余光中、葉維廉、蔣芸這些臺灣作家加盟香港文學。至於說大陸文學和臺灣文學是「各自獨立」的存在,其實這獨立系相對而言。不管臺灣文學如何具有獨立性,它與大陸文學仍有共同的對話空間。如果臺灣文學不能與大陸文學對話,或大陸文學不能與臺灣文學交流,那這近三十年來的兩岸文人互登作品,互出文集,互評作品,互通詩藝,互相來訪,互相競爭,那就成了竹籃打水一場空了。兩岸文壇的「三通」, 是大家共同期待的。比如大陸學者首次為臺灣新詩寫史,儘管有諸多失誤,但不可否認,其開臺灣詩史研究之先河的意義,是有目共睹的。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文訊》雜誌社才會動員眾多詩人、詩評家參加「臺灣現代詩史研討會」。此次會議所結下的碩果《臺灣現代詩史論》,正「代表著本土研究勢力(對大陸學者)的反彈」。
有位朋友認為,作家的文章一定是他本人過往歷史的積淀和結晶,其成功經驗在深藏不露或秘不示人的出書秘訣裡。我不是「深藏不露」之人,那就從實招來我兩次與「秀威」相遇,進而相識、相知的經過吧。鑒於第一本書《古遠清文藝爭鳴集》的出版我已在別的地方談到過,現在只說這本書——那時我因拙著《臺灣當代新詩史》與臺北幾位詩評家發生論爭,並在臺北出版的《傳記文學》以及香港《文匯報》接連刊載了幾篇近兩萬字的長文,正愁著沒有機會結集出版,恰逢上海文藝出版社在滬上主辦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國際研討會,碰到一位多年的老友答應幫我「做媒」。在他牽線搭橋下,想不到我這本書以及《古遠清文藝爭鳴集》很快和「秀威」成交「嫁」出了去。中間雖然有波折(原稿近四○萬字,現壓縮了一半),但在他人看來仍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啊。通常是從容不迫地出書,寫作是不疾不徐的節奏,這裡自有一份慎密心思在其中,而現在不能再「不疾不徐」了。機緣重要啊,在這個兩岸文壇「三通」已實現但出書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的時代!
兩岸文壇的「三通」,不僅充分體現在筆者和臺灣詩壇的爭鳴上,還體現在筆者與彼岸出版界的互動上。我已在海內外出版過二十多本書,這十年來幾乎在寶島每年出一本,且從不是自費出書,有人認為這是因為我知名度高的緣故,有人則認為我神通廣大,其實這一切都是錯誤的猜測。那怕到了這把年紀,我從不隱瞞自己出書的「歷險記」。長期以來,我一直在和大陸眾多出版社或打「游擊戰」,或打「遭遇戰」,均因大陸出版體制的限制容不下我研究的敏感題材。而在境外,出版高度自由化,從沒有報「專題審批」的程式,更不亂刪亂改作者的文章,這就是臺灣出版自由之可貴。
《從陸台港到世界華文文學》係我新世紀以來研究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的結晶。從《北大中文系的簡史》到柳忠秧的《嶺南歌》,從澳洲心水到泰國的夢凌,從臺灣的林明理到香港的林幸謙,林林總總,寫了海內外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多位。但我沒滿足於個案研究,還有《二十一世紀世界華文文學的前沿理論問題》、《學院作家現象與二十世紀臺灣文學》這樣的宏觀論述。所有這一切,均得力於世界華文作家的耕耘,及文壇友人的催促和媒體的支持,我的文章才能源不斷生產出來。我衷心希望明年有個好收成。
二○一一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