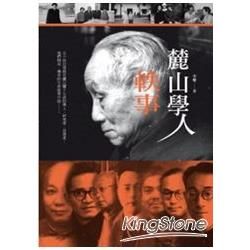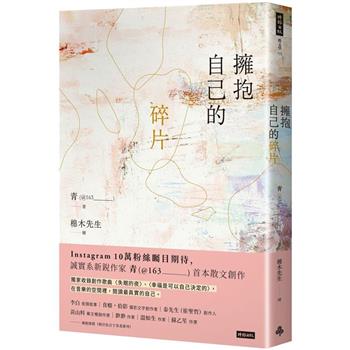序
1945年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後,搬遷到外地避難的各大中學校和文化團體陸續遷回長沙,一大批老中青知識份子雲集名城,雲集嶽麓山下,這裡又成了人文薈萃之區。這批知識份子親身遭受過外國強盜的蹂躪,飽嚐顛沛流離、饑寒交迫的困苦,領略過封建獨裁統治者的橫暴,大家都希望國富民強,要求開創一個沒有戰亂、沒有饑餓、沒有迫害的新的時代,新的生活,並為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掀起追求民主、自由、溫飽的鬥爭高潮。
我和本書的作者李蟠(筆名李鶴齡)教授是在這一高潮中邂逅相識的。以後我倆也和長沙一帶的其他廣大知識份子一樣,接受新的洗禮,有如季羨林先生〈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一文中所說:「懷著絕對虔誠的心情,嚮往光明,嚮往進步,覺得自己真正站起來了……全心全意投入造神運動……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對自己則認真進行思想改造……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得懵懵懂懂……然而涅槃難望,苦海無邊……通過無數次的運動,直到十年浩劫……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誠之心真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了。改革開放以後,自己的腦袋才裂開了一點縫,覺今是而昨非。」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後期,我從北方回到嶽麓山下休養,與一別四十餘年的鶴齡教授比屋而居,時相過從。兩個「裂開了一點縫」的腦袋,兩顆「覺今是而昨非」的心,有說不盡的話。從古今中外的興衰成敗,賢愚不肖,到當年嚮往光明,嚮往進步的老中青知識份子的命運和我們自己的經歷,無所不談。燈前月下,秋夕春朝,我們常相對欷噓,相對憤懣,相對熱血沸騰。
教授在嶽麓山下執教、生活五十餘年,對嶽麓山下的許多往事比我熟悉。我在外地闖蕩了幾十年,對故鄉的人和事已經很陌生了,發言權自然不如鶴齡兄大,所以常是聽者。不過我聽得很專心,很認真,像一個很用功的小學生。打那以後,我再去讀魯迅的名著《野草》,特別是其中的〈失掉的好地獄〉一文的時候,便覺得好懂多了。魯迅先生那精湛的思想,犀利的目光,那非常強烈的憤懣,震撼我的心靈,使我難以平息心靈深處的驚濤駭浪。
現在教授已將在嶽麓山下和我談過的一些往事記錄成集,名曰《麓山學人軼事》,據實走筆,不加粉飾。我想,在諛詞盈耳、謊話連篇的迷霧中為子孫後代留一點點歷史的真實,自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善舉。縱然只是罄竹難書中的一葉,滄海橫流中的一粟,對後之來哲以史為鑒,大約不無裨益吧!當然來哲們怎麼想,那也還是個變數,不是我們管得了的。
作為一個整體來說,知識份子是人類文化知識的載體,是人類的腦袋,是從事複雜勞動的勞動者,是社會第一生產力的代表。沒有知識份子,社會便不能進步,民族便不能振興,國家便不能強盛。虐殺知識份子就是虐殺民族的生機,雖有利於愚民政策的貫徹,有利於封建專制獨裁統治的延續,而其毒害社會、毒害人民之禍是非常深遠,非常劇烈的。古今中外的興衰成敗早已證明瞭這個並不是怎麼深奧難懂的真理。即使是在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其知識份子的命運也不見得比嶽麓山下那一大批知識份子的命運悲慘。這是我們中國的悲哀,一個時代的悲哀!
知識份子不是敷在獸皮上的毛。野獸怕冷時,可以用毛來保溫;燥熱時,可以把它掉光;瘙癢時,可以在粗糙的樹幹上或石頭上擦蹭以快意,一大片一大片地將它磨掉,在所不惜。然而,虐殺知識份子遠不是蹭掉皮上的一層毛。知識份子的命運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這不是個人恩怨問題,不是個人情緒問題,而是關係到天下興亡、生民死活的大問題。如果還不肯認識這個問題,那仍然是很危險的。
教授來信囑我寫序。記得魯迅曾驚詫於向秀的〈懷舊賦〉怎麼寫得那麼短,剛開始就結束了。我這篇序卻早已大大超過了〈懷舊賦〉的篇幅,該打烊了。自己也不知所云。
2009年5月陶俊新於青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