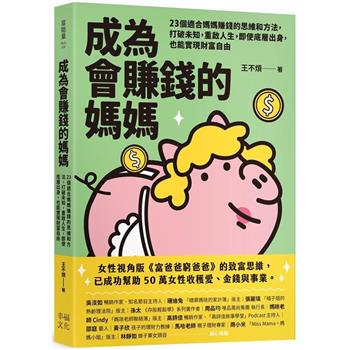【第十二章 澎湖從軍記】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濟和輪」載我們這批山東流亡學校的學生到澎湖。
船航行四天三夜後終抵達目的地。大家從渾渾噩噩中醒來,聚在甲板上指手劃腳。
向東方看,晨曦佈滿天際;向海裡看,一片水域平靜而深邃;向南方看,浮在海上的漁翁島魑魅魍魎,仍是黑漆漆的一片。
天大亮時,我們看見漁夫搖著一葉葉的小舟,向我們船的方向來,當漁船到達我們船的正下方時,方弄清楚這些漁民是前來兜生意的。船上載的貨是:香煙,酒,香蕉,花生糖及小魚乾。
我們一路流亡,早已囊空如洗,剩下的僅是有限的幾件衣服及棉被。常識告訴我們台灣四季如春,留一條毛毯,幾件單衣就已夠了,於是乎,有的同學把一路攜帶來的棉被,棉襖及棉褲以幾斤香蕉的代價與漁民們交換。
在船上等了一個上午,直到下午四時左右,方准我們離船上岸。
大家被領到內垵小學的操場上集合,然後,分配至日軍留下來的營房內居住。
稍做安頓,我們即迫不及待的到外邊走走。收進眼簾的是寸草不生的砂礫地,不但見不著有任何的農作物,連一棵像樣的樹也沒看見,僅外垵燈塔亮眼,既厚實又高聳。
最初那幾天,穿便衣的接待人員對我們若即若離,後來態度有些改變:客套中有堅持的一面,最後,顯示出﹁令﹂出必行的一副嘴臉,擠眉弄眼之間暗示他們就是我們的長官,命運已經注定,編入軍隊勢不可免。
在被編入軍隊之前做了一次篩選。
他們宣佈十七歲以上的站左邊;十七歲以下的站右邊。因為那時我正是虛歲十七實歲十六,我欣喜若狂的走向右邊的隊伍,但當我走到右邊快要入列時,一位身強體壯的傢伙突然竄到我的面前,疾言厲色的對我說:「你不行!你不行!」一把就把我拉了個趔趄,同時,扭著我的胳膊把我押向左邊。就是這樣,我被編入軍隊。過了幾日,我被調往「青年教導大隊」三中隊,駐紮在竹篙灣。
又過了些時日,從馬公傳來的消息說,召集去澎湖防衛司令部那裡的流亡學生,其編入軍隊的過程比我更慘。
李振清司令官及三十九師師長韓鳳儀將他們圈在澎湖防衛司令部的操場裡,四周圍架上機槍,韓鳳儀鐵青著面孔向學生宣佈:「歡迎大家來到澎湖,不過國家正處於危機存亡之秋,救國比讀書重要。」接著又說:「今日就是你們報效國家的良機,當兵是光榮的,相信你們不會拒絕!」霎時,怨聲四起,有幾位學生在列裡大聲抗議:「我們不要當兵,我們要讀書!我們不要當兵,我們要讀書!」
執行任務的幹部,要學生以高矮個子排列,來回在隊伍裡穿梭,拿著繩子量學生身高,以步槍高度為標準,與槍同高的一律編入軍隊,即使年齡十三,四歲,只要高度夠了,身體健康,也一律要當兵。
強制執行的結果,引起學生更激烈的抗議。為收殺雞儆猴,士兵向天空放空槍,有兩位學生遭刺刀穿刺受了重傷,也有幾位被子彈打中腿及屁股,此時大家亂成一團,哭著說:「我們不反對受軍事訓練,但我們也要受文科教育!」他們根本不理會學生的哭訴,並在眾校長們,師長們等的眾目睽睽之下,強迫學生脫下了學生服,換上了軍裝。
這個事件後被稱為「七一三事件」。
竹篙灣位於漁翁島的西端,地形變化多端:丘陵與谷地交錯,海岸上分佈著陡峭的山崖與奇異地珊瑚石洞,海水在珊瑚洞下涵澹澎湃,發出曠古的聲響。民宅大都建築在砂礫地上,圍以珊瑚石砌起來的牆。
綜合而論,漁翁島雖是荒島但卻是軍事重地,也是訓練野戰的好地方。
我們就在此先實施基本教練,後實行野戰演習,所遭受到的身體上之痛苦還能忍受,最使人受不了的是精神上的磨難。
大多數的幹部不僅識不了幾個大字,且說話粗魯,行動跋扈,再加上不懂如何帶「學生兵」,致在互動關係上每況愈下,我們表面上服從,內心裡反叛,但是,這種態度那能逃過老幹部的「法眼」?他們開始實施打罵教育,一邊打一邊罵:「你真活老百姓一個!」或者罵:「你不高興,對吧?你不高興你挨揍,我不高興我揍人!」
「青年教導大隊」的部隊設在小池角,距離我們的營區有四十分鐘的路程,週一得去參加例行的週會及聽韓斌隊長的訓話,間或有政工人員前來分析國際局勢。
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來漁翁島視察時,我們也得趕到小池角隊部聽他訓話。他原屬龐炳勳的雜牌部隊,因緣際會由一位小小的副官竄升至副旅長,旅長,副師長,三十九師的師長,副軍長,四十軍軍長,抗日戰爭中,很僥倖的打過一,兩次勝仗,最後,在河南安陽縣被共軍俘虜,釋放後,收拾了剩下的殘兵敗將撤退到台灣,因其忠心於國府,獲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賞識,再給他一次試用機會,任其為澎湖防衛司令。
他所受的文科教育有限,鬧出來的笑話無算,掛在他嘴上的老生常談是「十粒花生米抵一粒雞蛋!」因此,他要我們多吃花生米,不要吸煙。因肚子裡沒多少墨水的關係,說出來的話俗不可耐,一句話裡常有「這是」怎麼長及「這是」怎麼短。
在「學生兵」中流傳許多有關他的笑話。
有一則是這樣的:某次,他講話後,亢奮之餘領著大家呼口號,前面幾個口號喊得尚稱順利,後面的一個原為:「國父精神不死!」不料喊成:「國父不死!」此四字一出,引起一陣愕視。
他意會到了遺漏了兩個字,立即補正:「還有精神!」
他面相憨厚,老總統就是喜歡這種效忠型的將軍,有一次前來澎湖視察時,李司令對他表現的忠誠度已到了登峰造極的境地,當他被問及對時局的感想時,他竟答:
「報告總統,俺沒啥感想,俺就是你的小毛驢,你要俺往哪裡拉,俺就往哪裡拉!」
那時伙食費每人多少已不復記憶,反正在吃的方面已到了最壞的程度。
一個班十幾個人,蹲在地上圍住一臉盆的南瓜湯,其上漂浮著的是數滴油星及幾片白花花的肥豬肉。吃的是糙米飯,裡面有外殼,還摻著砂子,吃在嘴裡嘎叭,嘎叭的作響。怕吃不飽,學會了打衝鋒的技倆:「先填個半碗,吃完後再跑回去盛滿滿地一碗。」
我因為個子小排在班的倒數第二名,故以二等兵支薪,大約每月支領舊台幣七元五角左右。那時我奇饞無比,一旦領到茶色的薪水袋,撒腿就向低矮的小鋪子裡跑,買幾塊花生糖打牙祭。
抓「匪諜」的消息甚囂塵上,夜晚躺在床上,總覺得營房中鬼影幢幢。翌日起床,發現有一,兩位同學從人間蒸發,追問之下,所得到的答覆千篇一律:「他已調到另外一個單位去了」。「寧願錯殺一百,不能放走一個!」是那時常聽到的警語。
陸陸續續傳來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及二分校校長鄒鑑被逮捕的消息。
他們二位校長反對以這種方式將學生編入軍隊,更反對以這種方式摧殘年幼的學生,寫信到處求援,又邀約山東省教育廳廳長徐軼千下部隊挑十六歲以下的學生。這些舉措,激怒了三十九師的師長韓鳳儀。一方面誣指他們「破壞建軍」,另一分面在他們頭上扣「匪諜」的帽子,極欲置他們於死地。
張校長被誣指為:「匪膠東地區執行委員」;鄒校長則為:「匪煙台市黨部委員兼匪煙台市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任」。
扣人帽子容易,證據難尋。
為人陰險的韓鳳儀,為了要保住自己有官無兵的師長地位,乃唆使其黨羽李復生不惜以任何的手段向學生﹁詐取證據﹂。學生若不從,則以不許睡覺、吊打、過電、灌水、滾珊瑚石等刑逼供。其中尤以劉廷功所寫之詩,最能傳神:「身在牆前臂在後/雙手反綁墜石頭/石割兩肋鮮血流/三八刺刀腿上抽/痙攣麻木無知覺/兩眼模糊赴幽州/一桶涼水頭上灌/醒來變成黑腿囚。」
「調」來的學生在這些酷刑的威脅下,要什麼樣的口供,就有什麼樣的口供,可說到了予取予求的地步,除此,為招供的合法化,他們要求不懂法律的十幾歲孩子在口供上簽名或按手印。
證據取得後,台北保安司令部,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馬場町將兩位校長執行死刑,行刑時,有五位學生(原為六位,因有一位名叫王子彞者,病死在獄中)亦以「匪諜」罪名陪葬,最小者僅十九歲。
這兩位校長及五位學生雖是冤死,但還是經過白色恐怖時期的一個形式上的軍法審判,最心狠手辣的手段是把他們認為是「匪諜」的十幾名學生,用漁船載至澎湖外海,裝入麻袋,綴以石塊,拋到船外,任其墜入海底溺斃,名之謂:「拋錨」,其餘約五十餘名「匪諜」學生編為「新生隊」,嚴加監控。
死的死,亡的亡,管訓的管訓,編入部隊的也好過不到哪裡去,整人的技倆變本加厲。其中包括要你在地上學烏龜爬,把雙手放在後腦袋瓜上兩腿彎曲學青蛙跳,在烈陽下全副武裝圍著操場跑五千公尺。
基本教練時,立正姿勢的要領是:頭要正,腰要直,抬頭,挺胸,收下巴等,自以為各種要求已經做到了位,卻冷不防的從你的背後踹你的腿,你若能挺得住尚好,否則,冷嘲熱諷辱罵你:「真活老百姓一個!真活老百姓一個!」美其名是訓練你的服從性,實際上暗藏著整人的玄機。
最苦的事莫過於﹁那半天文科教育﹂不可得的困境,不僅是荒廢了學業,就連過去所學的那一丁點兒也淡出了腦袋,想到這裡,我的淚水就又沿著腮幫子落下來了。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從二等兵到教授:馬忠良回憶錄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69 |
歷史 |
$ 299 |
中文書 |
$ 299 |
文學家 |
$ 306 |
作家傳記 |
$ 306 |
社會人文 |
電子書 |
$ 340 |
人物傳記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從二等兵到教授:馬忠良回憶錄
成功大學教授、《海鷗詩刊》發行人馬忠良回憶一生,六歲即因盧溝橋事件爆發而回山東陵縣避難,此後歷經國共抗戰,先是淪為山東流亡學生,後被攔截徵召為二等兵,1949隨國府遷台,發憤讀書,終成大學教授,化育莘莘學子。書中記載斑斑可考,真實反映大時代下的人物血淚。
作者簡介:
馬忠良,
1932年生,山東省陵縣人,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1971年美國奧立岡大學教育碩士,1978年美國南伊利諾州立大學教育博士。
自1985年起先後任成大外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訓導長、學務長、教育研究所所長。2000年創辦立德管理學院應用英語系,並兼該校學務長,2006年曾受聘該校講座教授。
曾擔任《海鷗詩刊》發行人,出版詩集《冬季以望遠鏡賞鳥》乙冊,專著兩冊。
章節試閱
【第十二章 澎湖從軍記】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濟和輪」載我們這批山東流亡學校的學生到澎湖。
船航行四天三夜後終抵達目的地。大家從渾渾噩噩中醒來,聚在甲板上指手劃腳。
向東方看,晨曦佈滿天際;向海裡看,一片水域平靜而深邃;向南方看,浮在海上的漁翁島魑魅魍魎,仍是黑漆漆的一片。
天大亮時,我們看見漁夫搖著一葉葉的小舟,向我們船的方向來,當漁船到達我們船的正下方時,方弄清楚這些漁民是前來兜生意的。船上載的貨是:香煙,酒,香蕉,花生糖及小魚乾。
我們一路流亡,早已囊空如洗,剩下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濟和輪」載我們這批山東流亡學校的學生到澎湖。
船航行四天三夜後終抵達目的地。大家從渾渾噩噩中醒來,聚在甲板上指手劃腳。
向東方看,晨曦佈滿天際;向海裡看,一片水域平靜而深邃;向南方看,浮在海上的漁翁島魑魅魍魎,仍是黑漆漆的一片。
天大亮時,我們看見漁夫搖著一葉葉的小舟,向我們船的方向來,當漁船到達我們船的正下方時,方弄清楚這些漁民是前來兜生意的。船上載的貨是:香煙,酒,香蕉,花生糖及小魚乾。
我們一路流亡,早已囊空如洗,剩下的...
»看全部
作者序
【後記】
二○○九年,我把在成大的兼任辭掉,正式過退休生活。此時,我已七十八歲,想起老來無依的不方便,不得不赴美國與我的一對兒女同住,但是,每年我們還是回台南我們那老房子裡住一段時間,會一會親友,見一見鄰居,也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在健康許可之下,間或去大陸旅遊,訪問,也有可能去南京看姐姐,到濟南看小妹及至牡丹江看我的弟媳淑敏。
總括我的一生,平凡至極,與我同一時代的人,有的所受的苦比我更大、更多。由他們來寫自傳,更具標竿意義。但是,在美國常被人問起:「當年,你是如何離開大陸的?」我常苦笑...
二○○九年,我把在成大的兼任辭掉,正式過退休生活。此時,我已七十八歲,想起老來無依的不方便,不得不赴美國與我的一對兒女同住,但是,每年我們還是回台南我們那老房子裡住一段時間,會一會親友,見一見鄰居,也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在健康許可之下,間或去大陸旅遊,訪問,也有可能去南京看姐姐,到濟南看小妹及至牡丹江看我的弟媳淑敏。
總括我的一生,平凡至極,與我同一時代的人,有的所受的苦比我更大、更多。由他們來寫自傳,更具標竿意義。但是,在美國常被人問起:「當年,你是如何離開大陸的?」我常苦笑...
»看全部
目錄
第 一 章 考古的聖地──陵縣
第 二 章 綽號小迷糊
第 三 章 小學時代
第 四 章 中學時代
第 五 章 五人行
第 六 章 青島賣鞋記
第 七 章 上海!上海!
第 八 章 長安鎮風雲
第 九 章 龍游行
第 十 章 「閩道難」
第 十一 章 濟和輪上
第 十二 章 澎湖從軍記
第 十三 章 死去活來
第 十四 章 軍中的文藝夥伴
第 十五 章 成功嶺上
第 十六 章 台中事件
第 十七 章 醫院春秋
第 十八 章 李平伯的智慧
第 十九 章 外雙溪
第 二十 章 大學之路
第二十一章 大學生...
第 二 章 綽號小迷糊
第 三 章 小學時代
第 四 章 中學時代
第 五 章 五人行
第 六 章 青島賣鞋記
第 七 章 上海!上海!
第 八 章 長安鎮風雲
第 九 章 龍游行
第 十 章 「閩道難」
第 十一 章 濟和輪上
第 十二 章 澎湖從軍記
第 十三 章 死去活來
第 十四 章 軍中的文藝夥伴
第 十五 章 成功嶺上
第 十六 章 台中事件
第 十七 章 醫院春秋
第 十八 章 李平伯的智慧
第 十九 章 外雙溪
第 二十 章 大學之路
第二十一章 大學生...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馬忠良
- 出版社: 新銳文創 出版日期:2012-08-05 ISBN/ISSN:978986609494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2頁
- 類別: 中文書> 傳記> 文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