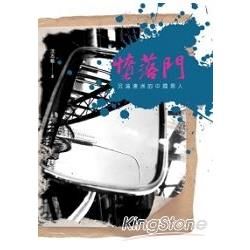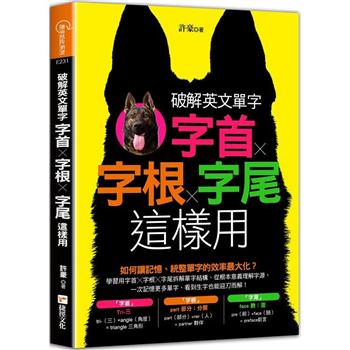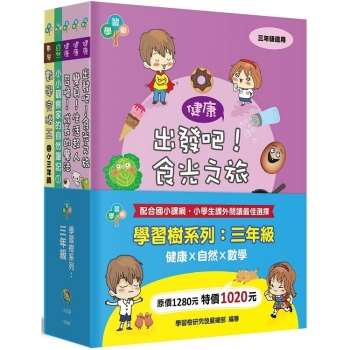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墮落門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73 |
小說 |
$ 308 |
中文現代文學 |
$ 343 |
小說 |
$ 343 |
小說 |
$ 351 |
小說 |
$ 351 |
現代小說 |
$ 351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390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墮落門
老謝出了國,老謝變成了黑民,老謝又被關進移民局的大牢,老謝搖身一變拿到了澳洲永久居留。
老謝結過婚,老謝又不得不離了婚。
老謝是一個平凡的人,而老謝卻偏偏要走不平凡的路,平凡和不平凡就像兩個雞蛋碰撞,蛋殼碎了,流出一堆粘糊糊的蛋清和蛋黃,這就是老謝的人生悲喜劇。
滾圓的雞蛋有點浪漫主義色彩,就像每個人的心裡都藏著一份浪漫主義的情懷;吃在嘴裡的雞蛋,卻是一股兒現實主義的味道。但雞蛋畢竟是雞蛋,雖然不是大魚大肉,和米飯菜蔬還是有點區別的。
老謝也一樣。老謝是生活在現代的人,但是按照現代人的標準,老謝又是即將過去的人,和新生代隔著八九條代溝,他想跳也跳不過去。可是老謝不死心,他還要無休無止地想望將來。
老謝在國外混的並不怎麼樣,卻一心想混出個人模狗樣,於是,為了滿足老謝的要求,上帝讓老謝莫名其妙地發了財,讓他衣錦還鄉光宗耀祖了一會,回到澳洲,老謝又糊裡糊塗破了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