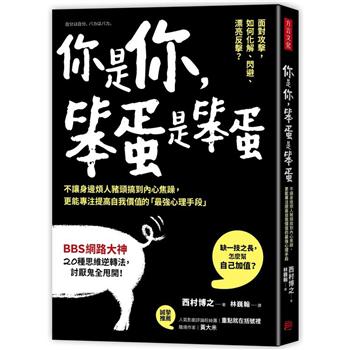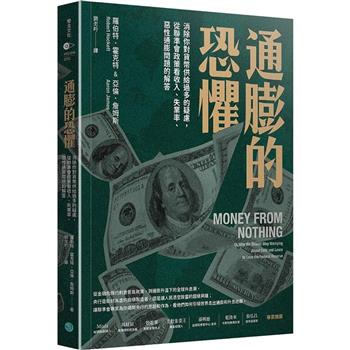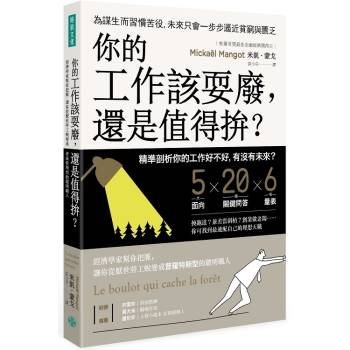推薦序
碧眼裡的日本
讀伊恩.布魯瑪的書別有趣味,起碼一是讀外國人怎麼看日本,再是讀西方的外國人看日本跟我們有甚麼不同,開卷有益。
布魯瑪是荷蘭人,說得更精當,乃父荷蘭人,母親是英國人,他們的國家近代與東方世界有密切關涉。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於海牙。一九七○年進萊頓大學讀中國歷史與文學,那時候的中國正在搞文化大革命,酷似煉獄。一九七一年,風貌有如拿破崙的寺山修司率領「天井棧敷」劇團在阿姆斯特丹演出《鴉片戰爭》,觀看之後,布魯瑪覺得「毛澤東版『亞洲式專制』含有訴求於清教徒的東西,而寺山所展現的日本則是長達幾世紀的吸引『放蕩者』、令『傳教士』喟嘆的那種『官能的東方』現代版」,興趣遂轉向日本,可以說寺山修司這個文藝怪才對布魯瑪的人生有重大影響。一九七五年至七七年在日本大學藝術系留學,專攻日本電影,這或許與伯父做電影導演不無關係。之後在東京從事攝影、寫作、電影導演,撰寫電影評論,並參加過唐十郎的劇團「狀況劇場」。一九八○年離開日本,正式步入新聞行,文化是當行本色,筆鋒更轉向社會政治,正如他日後自道:「作為一個批評家,我不只論說書本或電影,也一直寫時代的思想及事件」。二○○三年以後當大學教授,執筆執教兩擅場。二○○八年榮獲伊拉斯謨獎。通曉多種語言,見多識廣。比社會學的傅高義、文學的唐納德.金晚一代,與日本成為經濟大國以後出道的日本研究家同樣,有留學日本、與日本人結婚的履歷,而獨具的特色是真心喜愛日本的通俗文化,藉以展示並解析日本自畫像。
所謂通俗文化,即電影、漫畫、戲劇、讀物等,與纖巧、優雅的形式相比,屬於日本文化的另一面,也就是下位文化,或曰亞文化,是歐美世界幾無所知的。當然不應被輕蔑,但它淺俗,帶有暴力性,每每是病態的。通俗文化中的英雄或壞蛋是大眾性、集體性想像的產物,表現日本人一種典型,並形成國家或民族的認同。這正如約翰.韋恩所扮演的角色幾乎在美國不存在,但那是美國人的願望,被當作美國人的典型。如果說太平洋戰爭結束之際論說日本的經典《菊花與劍》基本是堆砌事例,勾勒日本人形象,那麼,布魯瑪的這本《鏡像下的日本人》則主要從神話、傳說中發掘日本人的原型。雖然歷史上時有變化,但日本人自己創造的最初的原型仍然活現在通俗文化當中。
布魯瑪於一九八四年出版此書,很多讀者應該還記得,就在一九八○年,如日中天的明星山口百惠把麥克風放在舞台上,跟人氣比她差N個數量級的演員三浦友和結婚,息影家庭。布魯瑪把這類事例與古代神話,以及十一世紀的《源氏物語》,十七世紀的《好色一代女》,乃至谷崎潤一郎的戀母小說等貫通一氣,揭示日本女人的母性與娼性諸相。溝口健二、今村昌平的電影,好些電視劇、漫畫,更被他順手拈來佐證自說。豈止西方人,連與之為鄰的我們亞洲人也常覺得日本所有的女人都是母親,而男人都是兒子,這種男人與女人的關係被布魯瑪追溯到天照大神和她的弟弟須佐之男那裡。男人,即便是硬派的非常男人,「總是還有一位最終的強者……那最甜美、最溫順、最和藹的生物……他自己的妻子,大和之母」(見正文二三一頁)。女人被崇拜為母親之神,可一旦剝下母親的假面,就變成可怕的惡靈。
潘乃德在《菊花與劍》一書中揭示日本人的二重性:「向來愛搞些天真爛漫的樂趣,以此聞名,如賞玩櫻花、月亮、菊花、初雪,在家裡掛個籠子聽蟲兒歌唱,吟詠和歌或俳句,擺弄院子,埋頭於插花、茶道。這樣的樂趣不像是抱有揣揣不安與反抗心的國民的行狀。」賞花詠俳之類是日本人的雅的一面,現實生活當中便呈現出一派「和氣」,而截然相反的另一面,即「揣揣不安與反抗心」,則通過酒宴上的胡鬧、漫畫中的血腥暴力、海報上被捆綁的裸女來宣洩。「和氣」,布魯瑪視之為日本人的核心,如同「教養」之於英國人,「文化」之於法國人,並非生來與俱,而是傳統秩序所強加的,是堂而皇之的表面原則。不健全的時而荒唐的趣味貫穿於通俗文化,是被強制服從嚴格的限制重重的正常規則的直接結果。從社會壓抑下唯一的解放是遊戲,壓抑越強,遊戲越荒唐。可以在空想中肆無忌憚地使用暴力,使暴力行動在現實中得到抑制,彬彬有禮,秩序正常。對於空想的暴力,日本人不是用道德,而是以純粹的審美來判斷。「邪惡的人也可以成為英雄,只要他的行為,無論是謀殺與否,有某種的風格,只要他看起來很棒。」(見正文二九六頁)
布魯瑪說過,也許在日本人看來他並沒有寫出新東西,但至少提供了新視點。日本位於歐亞大陸的盡頭,是從外側觀察除了日本之外的整個世界的最理想位置。而學習外國文化,不能給本國文化帶來新視角也就沒有意義,例如他看到,日本眾神跟我們人一樣有弱點,比基督教的三位一體更富有人性。很多住在日本的西方人搖擺於愛與憎的兩極之間,陷於一種精神性暈船。他們每每憧憬放蕩而來,風情閱盡之後卻變作傳教士,要把自己所丟棄的那套道德強加給東方人。布魯瑪住在日本時往往跟「日本是獨特的」這種日本文化論同調,但了解了亞洲其他地方,後來又回到歐洲,重新學習,便發現了自己的錯誤。日本人和外國人都相信日本是獨特的國度,在文化、經濟、政治方面,這種認識使日本孤立,而且是七十多年前日本走上不光彩道路的起點。文化的不同是存在的,也影響到人們的行動,但總是用文化的不同來說明政治的、經濟的制度,那麼,布魯瑪認為,文化相異的各國最終就只有三個選擇:或者對方像我們這樣,或者我們像對方那樣,或者抵制與對方貿易,兵戎相見。
布魯瑪解說文化,卻不容許隨便拿文化作擋箭牌,以開脫歷史的責任。他指出,日本人特別固執於文化是「欠缺政治」的結果。日本還遺留著冷戰結構,甚至仍籠罩在二次大戰的陰影之下,政治家、知識人迄今熱衷於議論日本在二次大戰中的作用。陰鬱的官僚統治著日本,雖然造成了某種安定,卻也使公然論爭的政治絕跡。在沒有政治的社會,日本人論、日本文化論代替政治,甚囂塵上。
宣示或張揚自己的文化,哪個國家、民族甚或地方都不無此心態,以日本為甚。他們總是忙於把外來文化加以本地化,創造自己的傳統,好似商場裡常見的情景,有走樣的洋食,有變味的中華菜餚,賣和食的要頭纏抹額,身穿印有店名的短外掛,吆喝兜售,似乎非此則無法認知。日本人不大有亞洲一員的感覺,其背景未必在於江戶三百年鎖國,倒像是日本人長年處於中國文化的陰影之下而形成的歷史情結,被美國炮艦敲開了國門之後,又唯恐歐美把自己跟中國及亞洲當作一回事。日本人愛看外人談論自己,不大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意思,他們確認並賞玩自己的與眾不同,為外人不可能理解而自鳴得意,從而更堅定島國根性。那些一知半解的日本論只會被當作電視的搞笑節目。但蔑視東方或厭惡西方均非「文明衝突」,而是破壞性的「思想衝突」。在很多場合,所謂亞洲價值觀其實是日本價值觀的變種,為避免這種尷尬,有人便煞費苦心,求助於所謂儒教,舊的或新的。
倘若時至今日才驚豔於《菊花與劍》,恐怕是難以真正了解日本的。當下倫敦書店裡擺著布魯瑪的著述。他並無批判日本之意,但取材於「低俗文化」,便像是與日本國拼命樹立「高雅文化」唱反調。近年來日本政府終於認識到漫畫動畫片之類乃日本最具獨創性文化,大力振興,推向世界,這就要躬身感謝布魯瑪才是。一雙碧眼所映現的日本或許會偏藍,有的景象更鮮明,有的反而模糊了。筆下恣意汪洋,令人眼花繚亂的感觀也時而漫沒了點睛之處。有關日本的著述,除了此書,布魯瑪還出版有《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日譯本《戰爭的記憶:日本人與德國人》)、《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 Love and War in East and West》(日譯本《伊恩.布魯瑪的日本探訪:從村上春樹到廣島》以及與人合著的《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日譯本《反西洋思想》)。就日本人的心態來說,最在意的仍然是歐美人說他們甚麼了。
李長聲
前言
曾經在某個星期天的午後,年老的阿姨問我在讀什麼?我回答說,一本日本小說。她想:「太離奇了!那些人的感覺一定和我們的大不相同,這對你怎麼會有任何意義呢?」像我阿姨一樣,許多人依然覺得難以置信,日本人不只是製造電晶體的奇特傢伙,對許多事情的感受,竟然也和我們相同。因為日本人的書寫方式從右至左,他們想當然爾地認為,日本人的感受也必定如此。
或許是在事情的表面上看起來極為不同,而且極度地自相矛盾,所以日本激起許多外國人突發的衝動,藉著文字來表達他們所受到的文化震撼,在回到家鄉後,向那些心存懷疑的同胞解釋他們在鏡子後面所看到的東西。如此一來,經常產生出如同「藍眼珠觀點下的日本」這類半調子的意見,可是,它卻似乎讓日本人感到愉快。日本人欣賞外國人對他們的注意,同時也確認了他們那安樂的狹隘想法,意即外國人不可能瞭解他們。
關於日本,陳腔濫調是很難避免的,因為它們似乎讓日本人和外國人雙方都感到最為舒坦。不過,這本書企圖描繪出一張日本人心目中的自己以及希望中的自己的畫像。很自然地,它將包括不少過去幾個時代所建立起來的文化性的老生常談。不過,首先這是一本有關想像的書,有時候,想像屬於個別的藝術家,他們除了為自己,從不會假裝是為他人而發表的。我將它們包含在內,因為它們呈現了某些比自身更廣泛的東西,而這些東西也告訴了我們有關孕育出它們的這個文化。
無論如何,我應該多提供一些更流行、更有集體想像力的作品,例如電影、漫畫、戲劇和書籍等,因為它們能迎合最多數人品味,所以也經常是最低的公約數。雖然這些通常不會是最佳的藝術作品──當然也不致於淪落到令人鄙視的地步──可是,這些東西卻經常透露出它們所訴諸的群眾為何。因此,比起那些西方人所熟悉的、纖細的、精鍊形式的日本文化,我將更多的空間奉獻給該文化中屬於比較猥褻、暴力以及經常是病態的部分。
把幻想從真實中分離,往往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在某個意義上,人們的渴望乃是現實的一部份。當然,即使最廉價的通俗文化與真實世界也有關連。如果它不是鏡中之像,至少也是它的反射。固然只有少許的美國人真正喜歡約翰.韋恩,但卻有很多人想成為約翰.韋恩,這個現象倒是值得注意的。英雄不會就從天上掉下來,他們大部分都是自家生產出來的。
我為這本書所選擇當作例子的英雄、惡棍和普通人,我認為他們呈現了日本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要素。他們在神話和傳說中扮演主角,同時還保有著民族的特性。不管怎樣,務必請放在心上的是,擁有代表性的事物,並不意味日本人就是特殊的。雖然幻想的表現方式通常存在著國與國之間的差異,但幻想本身卻是相同的。
即使多數的男女主角似乎只反映了他們本身的時代(或者年紀),但每個人都有著像他們一樣傑出的前輩。在眾多主角當中,有些共通的地方──某些個性突出於幾乎每個文化之中──但也有些類型則不斷地彈回無盡的轉世輪迴中,而且還貫穿了整個文化。
因此,我以日本第一位神祇做為開端。畢竟,天皇與主要的氏族一度被認為是神祇直接的後裔,這一點很特別。此外,正如同傳奇的編年史所描述的一樣,日本神祇似乎是非常人性化的。事實上,正因為如此的人性化,以致於許多日本人的特性,不論是想像或者真實的,都可以回溯到祂們身上。
本書的前半部有關女人,後半部則關於男人。在許多社會裡,女人所扮演的傳統角色被粗略地分成兩種:母親與娼妓。這兩個角色在日本都極為重要,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共通的。儘管她們的角色是社會性的,但也許區分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嚴格。當然,這兩種身分都是男人的幻想所塑造出來的。
夾在男人與女人之間的一個章節,則是有關第三性,也就是男人扮演女人和女人反串男人。雖然在目前的世界裡異性裝扮癖已逐漸走向沒落,但是在日本的戲劇中,反串卻依然是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文化上的性別角色也被定義得最清楚。
在男人的章節裡,大量的篇幅專門用於分析日本流氓,也就是「雅酷殺」【1】的傳統世界。原因是,這個幻想的世界構成了一個幾近完美的、日本社會的小宇宙。
如果在研究其他文化的時候,卻沒有學習到我們自己文化裡的任何東西,那就沒有意義了。據說,日本是個理想的地方,因為從她這裡,我們可以觀察世界的其他地方。由於座落於亞洲最邊緣地區,我們可以瞭解為什麼往往我們好像是從外面觀看這個世界一樣。
儘管通訊技術、大量的旅遊和其他事物均有著非凡的發展,而且這些成就應該有助於創造一個地球村,可是在許多方面,日本卻是現代世界裡最寂寞、最孤立的一員。在西方,如果在我們幸福的無知之下,常常會發現日本人很奇怪,那麼大多數的亞洲人也會有同樣的感受。
誠然,部分的原因是由於地理因素。就像位於北海上的英國一樣,海洋不但在心理上,也在物質上,把日本隔開在亞細亞大陸之外:日本人不覺得他們真正屬於亞洲的一部份。可是,他們也不覺得真正屬於任何事情的一部份。他們喜歡認為自己是獨特的,一種無疑是經過江戶時代約三百年實質上的與世隔絕之後所強化的心情。
有時,日本的確讓人感覺像是愛麗絲鏡中奇遇【2】的另一側。無論如何,這只是一個錯覺,它不會比廣為外國人和日本人所相信的事實更重要。因此,以「外人」【3】(按字面是指外面的人)的身分居住在日本,意味著是一個不斷被仔細檢查的怪人。這結果也使得外人不得不仔細檢查自己。這樣會很容易導致一個常見的謬誤,亦即凡是日本人認為是真的,外國人卻可能不認為是這樣,反之亦然。在日本人和外國人的想法中,兩者是如此地相互排斥,甚至有些科學家還認為他們可以證明此一事實【4】。最異乎尋常的,但也是唯一的例子,是備受推崇的角田博士宣稱,事實上,日本人有著不同和全然獨特的腦子。
我不同意日本人的獨特性這樣的迷思。相反的,由於她的長期孤立,日本保留了在我們自己的歷史過程中許多已經失去的、隱藏的或者改變得無法辨識的東西。在表面上,今天的日本似乎是個相當先進而且比衰退的英國還現代化的國家,但是,在內裡,她在許多方面更接近歐洲中古時代,也就是在基督教掃除異教徒信仰遺跡之前的那個時期。
日本的神祇似乎比基督教的三位一體更加人性化,因為祂們分享了我們人類的弱點而讓我更容易接受祂們。這樣的接受,是日本社會中最令人愉快且突出的特色,我相信,那是最值得西方人學習的課題。然而此事與神祕主義或者較高的智慧無關,也不只是取決於佛教徒消極順從的狀況,這可以是好壞參半的。當然,它不是更好或更壞的問題;就只是接受人性的本然,卸下在西方世界那些能夠而且經常限制人生的道德偏見。
因此,當本書裡的男女主角告訴我們某些有關創造他們的這個文化時,如果我們很誠實地觀察他們,他們將告訴我們更多有關我們自己的事情。
伊恩.布魯瑪,一九八三
《鏡像下的日本人》編輯手札
記得多年前在金馬影展看過一部考驗觀眾忍受暴力程度的片子:三池崇史導演的《殺手阿一》,在影展的簡介上就這麼大喇喇的寫著要挑戰你的感官,那時對於自己忍受人性黑暗面的程度也頗有想探究的意味。我一直相信那種未被釋放的野性,積壓下來反而會造成內傷,那倒不如先面對並且去思索它,後來還寫過一首詩〈狂暴鎮壓〉,就是對這種感觸的想法。類似的,以前學生時代曾有同學說過,去看一些動作片之後,往往體內就像充滿了力量,彷彿自己也可以像片中的主角一般無所不能。可見得電影的感染力,可以透過感官的刺激傳送到我們身上。
通俗文化這樣的功能,我向來深信不疑,或許它扮演著一個疏導的作用。但把這種功能發揮到極致的,恐怕非日本人莫屬,無論是漫畫、電影、文學、舞台劇、色情片或是電視,這種極致化已誇張到和一般日本人的生活處於兩極端的地步。明明是彬彬有禮、層級有序、和善自然,甚至不太敢表達自己主觀意見的日本人,但在國家、民族、公司、家族這樣的大社群壓迫下,每個人都只能默默扮演小螺絲釘的角色,於是壓抑的人生出口,就展現在通俗文化的想像世界裡,幾乎是把禁忌一層層的撥開探究,務必要把感官推展到忍耐度的極限為止。
聽說大島渚的《感官世界》當年在台灣上演時,最後女主角阿部定割下男人性器的一幕,許多觀眾奪門而出,對這種變態場面無法忍受的情形,我不知道日本戲院上映時是否也有同樣情況。不過多年後,我們依舊看到許多作品,繼續挑戰著社會禁忌的反射神經,像是前述的《殺手阿一》或是《大逃殺》(金馬影展引進時譯為《生存遊戲》,比較能一語道破電影主題),也有電視版的《失樂園》要挑戰電視尺度,即使引來衛道人士批判和社會的爭論,卻反而因為話題的渲染作用而吸引更多的觀眾。更不用說日本出產的龐大A片,以及漫畫中各式BL情節,或是像前幾年池上遼一的暴力美學作品《聖堂教父》也曾風靡一時。
這樣的作品在文學之中也處處可見,川端康成的《睡美人》描述一個讓女子服藥後進入睡眠的妓院,妓院服侍的對象是富有的老人,這些女子一方面有如沉睡的女神,另方面又令老人們得以馳騁各式幻想;谷崎潤一郎的《瘋癲老人日記》中,一位瘋狂愛戀媳婦美足的老人,甚至希望死後能在墓前放上媳婦的腳模型。於是病態而怪誕的色情和暴力,成了我們對日本精緻文化之外不能忘卻的另一個印象。而且只要是平日的行為得宜,就算是在街道上、公開的報章雜誌、漫畫或影片販賣店內公然購買和觀看這類產品,也都是見怪不怪的場面,甚至是日常生活的正常樣貌,布魯瑪形容說:「只要維持等級制度、禮節和得體的「立前」〔指外觀、公開的姿態和事情的原則〕,那麼沮喪的公司人員可以閱讀被綁住的女人的圖片,愛看多少就看多少。」
這種推展到極致的感官文化是否反過來影響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也許是個值得討論的大議題。但布魯瑪這本《鏡像下的日本人》倒不是從影響的層面來談,也不是要歸究或指責日本人,他反而是試圖解釋造就日本人這樣文化性格的起因,這也許和他所學有關。布魯瑪是荷蘭人,早期他在萊頓大學所讀的是中國與日本文學,後來雖成為知名的評論家和作家,但他曾在日本居住了七年,於東京的日本大學藝術學部就讀時是專攻日本電影,因此對日本的通俗文化較為關注。
他認為日本文化性格的源起,從日本的神話就可以現端倪,因為我們最常聽到的「天照大神」,其實絕不像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阿波羅那樣,光聽到「天照」二字就理所當然的以為祂是男性,其實祂是位女性,而且常常為了祂到處惹亂子的弟弟須佐之男收拾善後。於是天照大神這種母性、包容的慈愛精神,就成了日本神話中最重要的原型。反映到通俗文化層面,日本的女性不論她身為哪種角色(母親、妻子、女兒,甚至妓女),但要都展現出母性的精神與意味。相對的,男人的角色就像個孩子,反映在通俗文化上的角色,無論是無用的老爹、電影《男人真命苦》中漂泊的寅次郎,或是浪人武士和流氓,都有任性的一面,也有一般日本人所沒有表現出來的性格。以宮本武藏那樣的獨行俠來說,對於唯唯諾諾而不敢發出個人感言的日本人而言簡直是不可能存在的人物,這種虛幻的人物因為心嚮往之,所以成為了通俗文化中常見的主角。
本書的前半部談女性角色,後半部則是談男性角色,中間還夾有一章談第三性。我們熟知的寶塚歌舞團或是小時候看的漫畫《凡爾賽玫瑰》中女伴男裝的奧斯卡,都是最典型的角色。那種介於男女之間的中性美,或說是在男性中找不出的秀氣之美,都像是不食人間煙火或現實中找不出的人物。歌舞伎大師?東玉三郎扮演的女性,是同屬女性的女演員絕沒有的味道和唯妙唯肖。這種脫離現實的鏡中人物,就是令日本人為之瘋狂的角色,也是壓抑生活中可以尋求出口和慰藉但又虛幻而短暫的角色。
布魯瑪這樣特殊的西方觀察角度,李長聲先生在推薦序〈碧眼裡的日本〉中形容的貼切:「一雙碧眼所映現的日本或許會偏藍,有的景象更鮮明,有的反而模糊了。」至於是鮮明還是模糊,留待讀者自行研讀後再來判斷。不過這本書卻很受西方讀者的歡迎,藍燈書屋在2000年舉辦的「美國圖書博覽會」中,除了宣布編輯委員會選出的本世紀百大最佳英文非小說之外,也開放了網路的讀者票選,布魯瑪《鏡像下的日本人》即屬讀者票選的百大之列。本書最初出版於1984年,英國版書名是《A Japanese Mirror》,後來的美國版書名則是《Behind the Mask》(面具下的日本人),還有一個長長的副書名:On Sexual Demons, Sacred Mothers, Transvestites, Gangsters and Other Japanese Cultural Heroes,直譯成中文就是:「有關熱衷於性的人、神聖的母親、異性裝扮者、流氓和其他日本文化的主角」,副書名即在點出我們熟知的日本文化角色。而中文版的副書名:「永恆的母親、無用的老爹、惡女、第三性、賣春術、硬派、流氓」,則決定直接採用書中的部分章名,意義相同,都希望反應出一般人映象中的日本通俗文化角色。
另外要談一談中文版編輯上的一些小插曲。原書中附有許多電影劇照和漫畫,但因為版權取得不易,無法一一得到授權,但為了豐富內容,並為作者的文字佐證,於是想到找找看販售圖庫的公司,但後來又覺得牽涉到色情或暴力的圖片,只怕圖庫公司也不會有這類圖片。不過查詢之後倒是出乎意外,發現竟然有日本的情色咖啡館和土耳其浴的照片,這是否正呼應前述的,這些圖片已是日本一般生活中的常態,所以能找到這些圖片,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
不過找圖時我可是小心翼翼,深怕別人以為我上班時在偷看色情照片。而且圖片還得送回英國的原出版社去審查,我把選中的圖傳給版權部的同事,同事再傳給負責交涉的版權代理公司回報給英國,結果經手圖片的兩位小姐都與我有同樣的感受,臉紅心跳之餘還外加害怕有人看到。不過我終究還是不夠小心,即使在電腦螢幕上把圖縮到最小,仍然被突然出現在我身邊的同事給嚇到,急忙快速按掉畫面,但是當場不動聲色的這位同事,事後仍承認她看到了。嗯…只能說人性如此,對這樣的禁忌圖片仍是非常敏感的吧!
比起日本,台灣相對上既保守且自律的多,所以書一上市,就有書店自動把書用透明封套給封起來了,可見得我們的尺度比起日本,確實大大有別,還無法達到那種公然展示又若無其事的地步。不過還是要強調一下,本書並不是要宣揚日本文化的色情與暴力,而是解釋其來由,是以「理解」的角度去切入。這種虛幻之鏡反射的觀點,也將中文版的封面帶往這個方向設計,藉由類似底片的效果呈現出一種虛像的不真實意味。
布魯瑪談東西方文化的作品很多,光是談到日本的書還有許多本:《創造日本:1853-1964年》(Inventing Japan: 1853-1964)、《傳教士與自由思想者》(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日本人的刺青》(Japanese Tattoo)、《罪惡的代價:日本與德國的戰爭記憶》(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關於此書,昆布兄曾有一文〈罪惡的工價:一個荷蘭人的觀點〉)。其他作品還有《阿姆斯特丹的謀殺:電影人梵古之死與寬容的限制》(Murder in Amsterdam: The Death of Theo van Gogh and the Limits of Tolerance),《伏爾泰的椰子》(Voltaire's Coconuts,本書曾入圍歐威爾獎的最後決選名單)、《惡的要素:從洛杉磯到北京的中國叛民》(Bad Elements: Chinese Rebels from Los Angeles to Beijing),以及與馬格利特合著的《西方主義:敵人眼中的西方》(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等等,就不一一列舉了。
文∕主編 歐陽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