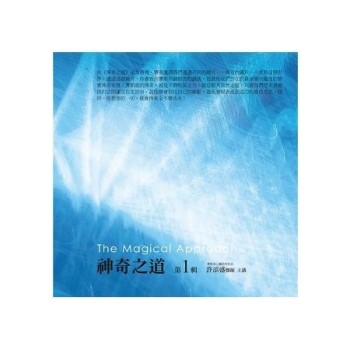推薦序
上窮碧落下黃泉,吸死人手又何妨
舉世聞名的華裔刑事鑑識科學大師李昌鈺博士曾在一場演講中說:「這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是靠犯罪維生的。」他這麼說,倒不是指地球是個罪惡的淵藪,犯罪人口的比率高到如此嚇人。他補充說:「除了罪犯本身,警察、司法機關、武器製造商……也都是靠著犯罪維生。」的確如此,如果這世界沒有人犯罪,司法、警察機關自然無用武之地,甚至那些寫犯罪、推理小說的作家,都無下筆題材。如此看來,這世界能夠存在,還真的跟犯罪脫離不了關係。罪行的存在,是不是一種必要之惡?我不敢說。但是,每個善良的公民,都想讓犯罪者在法律面前低頭,這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從古到今,包青天的故事一直是通俗小說及連續劇中的常勝軍,自不足為怪。
猶記得小時候,每到了八點檔連續劇時段,一家大小圍著電視,就等著黑面包拯喊出那一聲低沈又悠長的:「鍘~~~~~~~~~~」,那可真是大快人心啊!只是,包拯鐵面無私,斷案如神,從不冤枉好人,亦不縱放壞人,這種劇情,真的只有在小說和連續劇中才會出現。在現實生活中,誰有做或沒做某件壞事,除了天知、地知、犯罪者知之外,誰都不知。我認識一位法官,為官清廉,辦案認真,嫉惡如仇,對於犯罪者從來不稍假辭色。但他晚年時,卻開始吃齋唸佛。問他原因,他很沈痛的說,縱然如他這麼用心辦案,但他也不敢斷言,被他判決有罪的被告之中,究竟有沒有人是冤枉的。這種不確定的壓力,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積累在他心中,成了不可承受之重。他無法消解這種罪惡感,最後,只好靠宗教的力量尋求慰藉。這位法官的心情,我相信,一定也是很多辦案人員心中的寫照。
其實,隨著文明的進步,隨著民主化的發展,人權的觀念也逐漸加深在每一位公民心中。「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的觀念,在今天的社會也萬萬不能被接受,但要求辦案人員「寧可錯放一百,不可錯殺一人」,似乎又違背大部分的國民情感。安居樂業的老百姓想的是,「能不能百發百中?不錯殺也不錯放?」這種理想的境界,對所有的偵審人員來說,一定有「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的期盼。而在現實社會中,偵查手段及技術的日新月異,的確讓這個目標距離我們又近了一些。我還記得,二十年前跑新聞時,在某分局看到警方逮到一名性侵害嫌犯。自然,這嫌犯是抵死不認的。
於是乎,警方把他拖到地下室,一陣敲敲打打後,見他還是不肯招供,又看到我在旁,於是喊道:「小范,幫我壓他的腳。」我正狐疑他要做啥時,只見他已經提起一壺大水壺,作勢要對他灌水逼供。這嫌犯大概之前也嚐過灌水的滋味,一看刑警舉起水壺,心防馬上瓦解,立即哭著說:「我承認!我承認!是我幹的!是我幹的!」事後,這名刑警還很得意的對著目瞪口呆的我說:「什麼叫科學辦案?這就叫科學辦案!有做沒做,一壺水灌下去,馬上就知道。」自此之後,我就常常笑說,警方每次破案時發佈的新聞稿都說:「經曉以大義後,嫌犯坦承不諱。」其實,那根本就是「灌水刑求,曉以大義」嘛!二十年後的今天,警方是不是還在用那套傳統的「科學辦案」方式來發現真實?因為我已脫離了第一線的採訪生涯,自然不敢斷言。但肯定的是,這二十年來,刑事鑑識科學的發展,在台灣有非常長足的進步,「讓證據說話」,不再只是句口號,這對於人權的保障,以及對於案件的正確性,一定都有非常正面的影響。說到刑事鑑識科學的引進,我個人認為,李昌鈺博士仍要居首功。記得在十餘年前,吳東明擔任調查局局長時,在一次跨國性的反毒會議中,他向新聞界介紹了他的高中好友李昌鈺博士。當時,李博士已經是名聞國際的鑑識學大師,但在資訊封閉的台灣,認識他的人畢竟不多。那在次會議中,吳東明告訴大家,他決定敦聘李昌鈺博士為調查局的科技總顧問,並協助調查局發展DNA實驗室。
那時,所有的記者們都還不知道DNA實驗室對於辦案單位會有如何重大的影響及協助,但到了今日,靠著DNA無可置疑的精準性來確定或排除一個人是否涉及犯罪,卻也是人人皆耳熟能詳的常識了。之後,台灣警察大學出身的李昌鈺不能厚此薄彼,也被警方延聘為科技總顧問,並且也為刑事警察局建立了DNA實驗室,至此,國內的科學辦案基礎,總算初成。爾後,李博士更大方的同意警方、調查局不定期派員到他位於美國康乃狄克州的實驗室,跟著他學習刑事鑑識的專業技能,經過十幾年的培育,國內目前第一流的刑事鑑識人員,幾乎都是他的徒子徒孫。在我粗淺的認知中,刑事鑑識科學是一門包羅非常廣泛,而且又頗具意義的學科。要學好刑事鑑識,必須要有物理(彈道鑑定、血跡噴濺痕)、化學(火藥成分分析、血跡反應)、藥學(毒物反應)、解剖學(屍體鑑定)等方面的修維,又要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細密心思,更要耐得住寂寞。因為,每次辦案時,趴在地上找微物證據的,都是鑑識人員,但每次破案時,站著接受表揚的,卻都是偵查人員。如果鑑識人員不能把工作當成一種興趣,誰願意成天與死人、屍臭為伍?誰願意開口閉口和同儕聊的話題都是:「某某屍體上的蛆已經有幾公分長,所以應該已經死亡幾天了。」我們應該為這群辛苦且默默無名的鑑識人員致敬。
從李昌鈺博士、楊日松法醫、翁景惠、程曉桂科長以及更多更多的無名英雄,因為有他們,我們才能大聲的說,在科學證據下,再狡滑的犯罪也得低頭。近年來,坊間出版過不少與刑事鑑識科學有關的書,連電視推出的CSI影集,都成了熱門節目,但電視講究效果,部分劇情可能與事實有違,要了解真相、內幕與其中的甘苦,仍要看當事人現身說法才更為準確。戴娜.柯曼的《千萬別吸死人的手》,就是一本能達到這樣效果的書。更特別的是,柯曼的文筆非常輕鬆幽默,書中又儘量避免讓人望而生畏的學術專有名詞,因此,閱讀起來應該不致產生任何負擔。唯一要考慮的是,應該要避免邊吃飯邊看這本書(我就有這種壞習慣),否則,如果看到哪段情節,讓你忍不住噴飯,或是讓妳差一點反胃,那可得後果自負。
最後,還是想談一下書名。以前跑新聞時,法醫楊日松偶而會向我們表演他的絕技。他會伸出指頭沾一沾屍體上的屍水,再放入口中嚐嚐,然後,就可以很精準的告訴我們,這屍體已經死亡多久了。每一個菜鳥記者見狀,無不嚇得魂飛魄散,覺得楊大法醫未免也太誇張了吧?事後,我們才知,楊博士沾屍水的指頭,是食指,但放入口中的指頭,是中指。可是,在我們都嚇傻的當兒,是沒人能分辨得清他的手法的。至於他推斷死者的死亡時間,自然不是憑著嚐屍水得出的結果,而是依靠他長年的經驗,從屍首腐敗的程度推斷得知。至於在這本《千萬別吸死人的手》,作者是不是比楊日松博士更大膽,不只嚐屍水,而是連死人的手都吸吮下去?這黑色幽默的謎底,就要由各位讀者自己去發掘了。
范立達(新聞評論人)
前言
去年我回到了活人的世界,先是把制服交回去,然後拍掉鞋跟上的渣(也就是那些身分不詳的死者體組織),也將法院的傳票都整理起來。表面上我還是請育嬰假,但早在這十二週的空檔之前,我心裡已經明白我不會再回到這崗位上了。因此,我在假期開始之前,就先將自己的東西都收拾好,也很感謝同事主動幫忙,將還沒收走的東西打包好放在我桌子底下。之所以感謝他們,是因為我不喜歡道別,我只想偷偷摸摸回去,把要交還的東西放好,把自己的東西帶走,之後趁沒人發現之前趕快逃出去。
計畫進行地挺理想,星期五凌晨兩點鐘,我知道這時候實驗室一定忙得不可開交,趁此機會將要交還的東西擺在主管桌上,這包括了制服、防身噴霧器、行為及現場調查手冊、幾把鑰匙、生化危險裝備包、呼吸口罩、橡膠靴,以及識別證。在辦公室中我不免注意到主管的月曆上,三月七日那一天標著大大的一行字:「戴娜歸隊」,於是覺得喉嚨一哽、眼眶刺痛,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真的這樣做了,我要離開這裡,不會再回來了。
我把識別證拿起來,最後一次看著上面自己的相片。過去十年裡頭,每天我用沾了指紋粉的手去碰它,所以顏色褪得很厲害;加上識別證要遞給保全幾百次,照片中我的臉上都生出一堆皺褶了。就算沒有褪色、沒有起皺,這照片還是拍得很差勁,不過回想起拍照的那天早上,我卻又忍不住露出了微笑。那天我熬夜加班,只因為一件持刀殺人案,那是個下雨的晚上,有個婦人先拿了鍋子在丈夫頭上狠狠一敲,隨後又用刀戳了他,起因是丈夫抱怨她的魚煎得太難吃。行兇之後,婦人將鍋子從陽台丟出去,所以我還記得自己那夜冒雨在外頭拍照,照的就是鍋子、抹油刀、還有灑在杜鵑花叢間的魚肉。之後拍識別證的照片,我氣色自然好不起來,只能安慰自己一切都是因為全身濕透又沾滿油煙,還帶著魚腥味呢。看過以後,我將識別證又塞回制服底下。
回到實驗室的職員區,我把座位上自己的名牌取走,也將郵箱上的名條撕下來。郵箱裡頭有什麼我懶得看,如果有什麼重要的東西應該就轉寄到家裡了,所以我把剩下的個人物品收好以後,關上電燈,離開這地方。
電梯並不遠,但我繞了一段路,去看看證物處理室。房間裡頭很暗,十一層樓底下的街燈投進一點光芒照在煙燻箱上,我把行李先放在證物桌,走到窗邊看看外頭。這世界看似寧靜祥和,諷刺的是那些光怪陸離的事件、兇殘暴力的犯罪都要在這房間裡頭才找得到。
我在暖爐那邊坐下,看著這間實驗室一片黑,回數自己生命中有多少小時花在這四面牆壁包圍的空間。我就這樣坐在黑暗中,沈思了好一段時間,很難相信打從我初次步入犯罪實驗室以來,十年的歲月就這樣溜走了。當年的我沒什麼經驗,只是一心想多學習,無法想像現在的我,在這間實驗室的非警方調查員中已經資格最老,警方探員也只有一位年資比我更長。我並不後悔自己花在這裡的一分一秒,我覺得遺憾的是不應該將工作當成生命的唯一重心,造成我的生活與這份工作太過難以分割。幾年以前有一位槍彈鑑識員曾經告訴我:我對這個地方的愛,會遠大於這個地方對我的愛。他說的對,我有點遺憾自己沒聽進去,在感情上我隸屬於這個單位,但實際上我畢竟只是團隊中的一員,而不管我離開與否,實驗室依舊要繼續運作,想到這點,不免令人心頭一痛。
離開實驗室的決定也並非一昭一夕,這件事情我反覆考慮了一年,但直到我跟丈夫鮑伯從瓜地馬拉帶著兒子回來,我終於意識到自己必須重新評估生命中的輕重次序,我不能再做大夜班、不能排班、也不能永無止盡地加班。我希望聖誕節是跟真的聖誕樹度過,而不是看著一個死人掛在聖誕樹上成了吊飾;我也希望感恩節點心上的紅莓醬,以後不會再使我聯想到一團一團的血塊;甚至是七月四日國慶日的煙火,在我腦海也是出意外之後炸死圍觀群眾的慘狀。我不要把「這個人的直腸得刷一刷」或者「幫我把保險套從馬桶鉤出來」這種話當成家常便飯。我想要的是所謂的正常生活。
多年以前,我走上這條路之前,我媽媽不是很介意我做什麼工作,只希望我上班會穿得體面一點。我爸覺得只要有人肯出錢雇用我都好,而我哥還曾經對上帝做過祈禱式,希望祂就隨便賜給我一份工作吧。我自己呢?我想要跟死人混在一起。
所以我跑去被人全身綁著,坐在一張像電椅的東西上。桌子對面有個粗魯無理的胖女人看著一台很老舊、一直吐出圖表的機器。我非常想要成為非警務身分的犯罪調查員,這是我最想做的一份工作,但是這個求職過程真是永無止盡,花了一年的時間,通過評議審查、體能測驗、身家調查,最後還要面對這台混帳機器跟精神狀況檢查
我會對死人有興趣,其實是我父母的錯。我父親原本是警察,後來轉行去當消防員,他後來覺得我們在巴爾的摩這種犯罪率很高的地方念公立學校,最後大概也會變壞,所以一九七二年我們全家就搬到郊區去。這樣子是避開了街頭混混,不過也就少了市區才有的東西,像是游泳池、社區公園、便利商店之類,搬家之後認識新朋友,一群小孩子的消遣不外乎在樹叢裡比賽抓甲蟲,時間太多就會進樹林去找女巫、找一百萬年前半猴半人那些生物遺留下來的東西,而我們找到了牠們的骨頭跟小動物的遺體,以為這證明了人類的祖先是肉食動物。我把猿人骨頭壓在床墊底下,就這麼與它睡了快一年,終於有一天我爸覺得我房間老是有臭味,費了一番功夫才找出來,看樣子那骨頭上還留了一點肉屑吧。
上了高中,朋友都有了新的嗜好,但我卻不同。有一次週五下午我媽媽下班回家,看見鍋子冒著煙,還以為是我做了晚餐,但是一打開不沾鍋的蓋子看到的是經過解剖後煮熟的六隻貓屍體。後來我試著解釋:我要幫忙同學,把貓屍先蒸熟,才可以剔除軟組織,下週一生理構造課程上大家才能夠觀察骨骼,但氣炸的老媽當然聽不進去,還聲稱要叫人帶著拘束衣過來,把我包在又冷又濕的白布條裡面,帶去鋪滿泡棉的房間關起來。我媽還叫我把東西帶去碼頭給爸爸看,好讓老爸知道我幹了什麼好事。我爸看過之後拼命搖頭,說以後煮螃蟹吃的話大概會是滿嘴甲醛的的味道。週末想要清鍋子,但是貓黏住了掰不開,我媽狠狠地瞪著我,之後我也成為全班笑柄,因為老師後來說我們從課本的圖片觀察骨骼構造就可以了。
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我決定自己將來的工作內容,要跟屍體、骨頭、或者國家地理雜誌報導的「沼人」這類東西為伍,於是告訴家人我想要念考古學,但我媽可是一點都不開心。她提醒我:考古學要到處挖掘,把自己弄得髒兮兮,而且不能穿得漂漂亮亮。隔年秋天,我陰錯陽差地進了聯合紀念醫院的護理學院,開始幫老人家插尿管,這裡的課程很棒,但大概就是太棒了,所以我從第一天就很確定我一點兒也不想念,頭幾個月對我來說就是一連串的敏感度測試,我衝出課堂的次數應該在醫院地板可以看到痕跡吧,所以差不多只學會怎樣幫死人刮鬍子就輟學了。
離開護理學院後,未來的方向卻明確了起來。我果然還是念了考古,畢業之後不到一個月就找到現場技術員(俗稱鏟子工人)工作,這一點令我老媽頗吃驚。過了幾年,我回到校園進修法醫學,立定志向成為犯罪現場調查員,就算為此必須給人綁在椅子上問些莫名其妙的問題也在所不惜。
我眼神空洞地看著牆壁,等著操作機器的人問我下一個問題。她好幾次吼我說不要亂動,但我覺得自己根本一根筋也沒跳過,更不用說壓力大得全身緊繃,連深呼吸也不行呢,我曾經被罵過這樣子會使血液中含氧過多,結果我一道歉又被罵。但仔細一想,這就是為什麼胖女人腰間還要有武器,我猜她不喜歡的受試者應該都會一肚子怨氣走出去吧,實際上恫嚇在這個測驗中是很重要的一環,我只要乖乖照著這遊戲規則走下去就沒問題。想到這兒,我的思路又被打斷,「除了剛剛提過的以外,妳有沒有偷過東西?」這女人聲音乾扁單調,實在很難討人開心。
我沈默了一下,思考這個問題。我的心跳得很快,連脈搏聲都聽得到。先前我才承認我「無意中」拿過以前同事的筆啦、便條紙啦、修正液這一類東西,測驗官眼睛在機器跟我臉上來來回回,正在等待我的答案。「沒有。」我講得斬釘截鐵。
測驗官盯著我一陣子之後,用一枝簽字筆在紙上畫了一堆圓圈跟叉叉,造成我心跳更快、手也抖了起來。我很擔心這在那台笨機器上代表我說謊,我餘光一瞥發現她竊笑著搖搖頭,她有這種反應顯然也是知道我在偷看她。
我哥跟我還小的時候,父母就一直強調做人要端正,不然耶穌基督會在我們的靈魂上劃上黑色記號,我們不知道黑色的記號累積太多會有什麼後果,但人類也就是因為這種無知所以感到害怕。星期天下午大家會去教堂告解,因為這麼做可以洗滌我們的魂魄、重拾我們的清白,我對於上帝的懲罰、對於黑色印記也很害怕,所以一直品行端正,確實沒有做出什麼會失去工作資格的事情,連一些小奸小惡也沒有。
這種測驗過程,我也去其他兩間警局做過,之後就等著他們的篩選結果。面試了三間,希望至少有一間願意收留我,而就在這種信心全失、覺得自己渺小得有如螞蟻的情況下,我等待對方提出最後一個問題,結果這個問題確實成為我踏上犯罪現場調查員這條路的前兆。那女人用最嚴肅的聲音開口問我:「妳有沒有跟雞發生過性行為?」
啊啊啊?我有沒有聽錯?我花了一點時間整理邏輯、思考雞這種生物,尤其不明白雞要怎麼用才好?看樣子我回家的路上一定還會繼續思考這個問題,而且我當下覺得拿不到工作也無所謂了,要我乖乖地回答有或沒有根本不可能吧。於是我模仿起面試官那種嚴肅乾扁的語調說:「我說不定有跟些臭男人上過床,但是相信我,我絕對沒有跟雞做過。」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三日,我踏進警署訓練學院,心中以為這是踏進新事業的大門,殊不知這門後頭根本是個新世界,跟我已知的生活截然不同。
之後十年我在美國人熟知的九一一號碼後頭,有人打來說電視裡出現外星人,也有人報警希望處理掉環城高路上的袋鼠。在這個不一樣的宇宙裡,會看到女人帶著香菸出沒在一些難以想像的地點,男人可能因為無法維持勃起而叫救護車,家中養的寵物可能不是貓狗而是豬或者其他怪東西,還有人會在家裡鋪了油布的地上打算烤雞肉吃。在這新天地之中死人可能手裡還拿著披薩盒子,屍體給人丟在「死巷」、「請勿亂丟垃圾」的號誌下面,而我當然怎樣也沒想過有一天自己嘴裡會伸進死人的指頭,或者走一走會給死人壓頂。這些事情在電視上看不到、在小說裡讀不到,說真的要瞎掰都不是這麼容易吧!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這些在餐桌上不能說的故事,把電視關上,聽我親口告訴你「真相」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