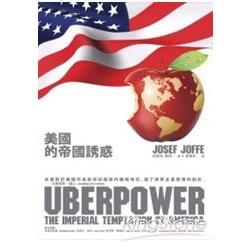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美國的帝國誘惑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5 |
二手中文書 |
$ 211 |
西方歷史 |
$ 288 |
國際關係 |
$ 288 |
西方歷史 |
$ 288 |
社會人文 |
$ 298 |
博雅書屋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內容簡介:
本書輕鬆地將軍事史融合進外交分析當中,
然後提供大家對美國近年來國際處境變化的重要觀察。
作者認為,美國已經成為(同時亦將繼續是)自古羅馬帝國以來最強大的一個國家,
由此他一方面企圖說明這個單一強權所負擔的重責大任,
同時強調小布希政府的外交政策並無助於維繫美國的領導地位。
相對於許多歐洲學者,本書作者並未「唱衰」美國霸權,
而是透過追溯歐洲與全世界新反美主義興起的根源,
去分析其前因後果。正如作者所展現的,
基於其無可匹敵的巨大能力,再加上其權力與正當性間的裂縫愈形擴大,
以及它所將面臨之無可避免的帝國化誘惑,因此美國其實並不安全。
歷史告訴我們,權力將促使反權力的成長。因此,美國這個超級強權將如何避免重蹈覆轍,
可說是許多人當前的關注焦點所在。無論如何,
作者認為,由於沒有其他國家(中國、歐洲或俄羅斯)能擔負起建構全球秩序的重任,
因此美國仍應該儘可能去選擇睿智的政策,來完成其歷史使命。
本書特色:
本書輕鬆地將軍事史融合進外交分析當中,
然後提供大家對美國近年來國際處境變化的重要觀察。
作者認為,美國已經成為(同時亦將繼續是)自古羅馬帝國以來最強大的一個國家,
由此他一方面企圖說明這個單一強權所負擔的重責大任,
同時強調小布希政府的外交政策並無助於維繫美國的領導地位。
相對於許多歐洲學者,本書作者並未「唱衰」美國霸權,
而是透過追溯歐洲與全世界新反美主義興起的根源,去分析其前因後果。
正如作者所展現的,基於其無可匹敵的巨大能力,
再加上其權力與正當性間的裂縫愈形擴大,
以及它所將面臨之無可避免的帝國化誘惑,因此美國其實並不安全。
歷史告訴我們,權力將促使反權力的成長。
因此,美國這個超級強權將如何避免重蹈覆轍,
可說是許多人當前的關注焦點所在。
無論如何,作者認為,
由於沒有其他國家(中國、歐洲或俄羅斯)能擔負起建構全球秩序的重任,
因此美國仍應該儘可能去選擇睿智的政策,來完成其歷史使命。
作者簡介:
約瑟夫.喬飛(Josef Joffe)
曾就讀於史瓦茲摩爾與哈佛大學,並取得政府學博士學位,
作品散見於「外交事務季刊」(Foreign Affairs)、「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與「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等期刊,自二○○○年起擔任「時代雜誌」(Die Zeit)發行人兼編輯,並為二○○五年創刊之「美國利益」(American Interest)期刊創始編輯委員。他曾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哈佛大學與史丹福大學等校教授國際關係與美國外交政策等課程,並擔任過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與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
譯者簡介:
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兼全球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專長主要為國際關係史、東亞區域研究與中國外交政策。著有專書十餘冊,主要包括:
《中國外交史新論》
《西洋外交史》
《李鴻章與清季中國外交》
《兩岸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
《政治啥玩意》
《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
《民主的全球旅程》
另有中英文學術論文上百篇。
第一章
未完成的世界
一個帝國之死
兩極體系及其遊戲規則
第二章
被鬆綁的超級強權
「責無旁貸的國家」
超強政治
制衡大國先生
第三章
反美主義的興起
反美主義的復活
反美主義的意涵
政策性反美主義與問題本質
伊斯蘭世界的反美主義
歐洲的反美主義
第四章
美國主義的興起
無處不在的美國
魅力誘人的美國
現代化的領航者
作為超級國家的美國
第五章
超強大戰略之歷史模式分析
英國式平衡的原則
英國式平衡的手段
英國式平衡的問題
俾斯麥同盟的背景
俾斯...
- 作者: 約瑟夫‧喬飛
- 出版社: 博雅 出版日期:2011-11-24 ISBN/ISSN:978986609829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2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西方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