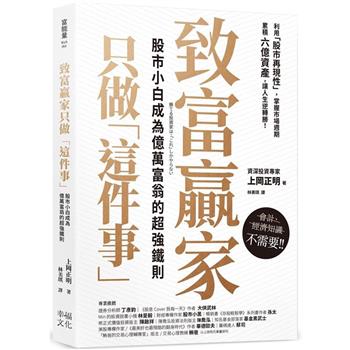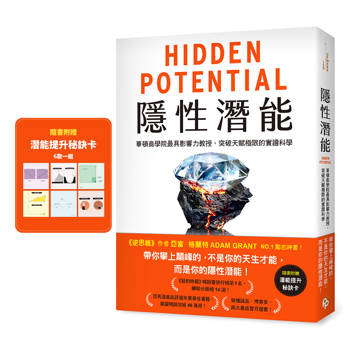代序
唐沙波印象∕記重慶市中華食文化研究會會長 唐沙波
在重慶,唐沙波是個文人,也是個名人,用毛新宇的話來說:唐沙波是飲食界的文人,文人中的飲食家。此話不假,唐沙波是重慶電視台《食在中國》欄目的製片人、重慶中華食文化研究會的會長、重慶飲食文化研究家、美食家、飲食評論家……
飲食文化,是一個廣博而浩翰的領域,既要追溯飲食的起源,又要明了飲食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演變發展,更要知道飲食史上重要的著述及作者。在這方面,唐沙波是當之無愧的大家了。他熟知中國飲食史,兼有深厚的古典文學基礎,使他在古人晦澀的記述中游刃有餘地抓住精髓。在這方面,唐沙波說過一句十分中肯的話:「文人與飲食,淵源十分微妙深沉。不能說文人最好吃,而是文人吃了最愛說,且說得中肯,精妙,雋永。」也就是說,文人更好寫作,如林洪的《山家清供》、李漁的《閒情偶寄》、袁枚的《隨園食單》,蘇軾、陸游的飲食見解等,他們的真知灼見或切身體會,付諸筆端,才有了中國飲食史上文人的飲食烹蝕著述,這些都是散落於歷史長河中的珍珠,史海覓珠,也就掌握了打開飲食奧秘的鑰匙。
讀唐沙波的飲食文章,你會驚異於他知識的廣博與剖析之精妙。一篇《味道四川》,將四川的歷史淵源及演變,風土人情及氣候,飲食發展及文化名人,淋漓盡致地以飲食串聯起來,叫人讀來拍案叫絕。對川味的特色與烹蝕之道,也有獨到的見解。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是歷代文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唐沙波的飲食文章,大都寫得舒緩從容,樸實卻又張弛有度,娓娓敘述中沒有大起大落的情節或故事,卻能抓住讀者心扉,使你欲罷不能非得讀下去。為文者,難的是在不波不瀾的描寫中靠語言和情感的揚抑吸引人,這就是功力。
唐沙波的飲食文化研究,始於上個世紀八○年代初,先是在《重慶日報》,後轉到重慶電視台,見證了重慶改革開放以來,飲食領域蓬勃發展的全過程。他能如數家珍地說出現今重慶餐飲界的一些巨頭,當初是如何從一兩張桌的街頭小店發展而來。這也使他結識了不少重慶餐飲界的老板和國內數得上名號的廚界大師,當然也品嘗了不少大師親手烹製的佳肴美味。用他的話來說,最得意的是品嘗了川菜中的「滿漢全席」。可以想象,上百種川菜中的精品,由特級大師親手烹製,琳琅滿目地擺在面前,未動筷已陶醉了。
正是由於他是重慶餐飲業發展的見證人和參與者,對於重慶餐飲業,唐沙波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凡是涉及重慶餐飲業發展之事,不論親疏,他都是傾注全力給予積極的支持與扶持。他對飲食行業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更有一種超然的遠見。前些年他到重慶一遠郊地採訪,到一家餐廳就餐,他見這家餐廳十分紅火,經營者有管理經營謀略,就建議這家企業到重慶發展,老守在這小地方成不了氣候。經營者聽從了他的建議。現今,這家企業如同一匹高速馳騁的黑馬,短短幾年已發展了四家超級大店並成為重慶餐飲界執牛耳者。
他的無私,他的學識,使不少餐飲老板,在創立一款菜品,或新開一個店面時,都要請他去品嘗,或與他商量,徵求他的意見。對此,他總是熱情相助,絲毫無保留。特別是在重慶提出打造美食之都後,他更是身體力行,積極推動這項工作。食文化研究會專門開會研究這項工作,積極倡導餐飲行業推行標準化、規範化管理,為打造美食之都奠定堅實的基礎。
唐沙波最大的心願,是看到重慶餐飲行業名師崢嶸,名菜薈萃,兩江三岸名店林立,成為西部地區乃至全世界名符其實的美食之都。
唐沙波好讀書,購書成了他生活中的一大樂趣,幾乎是隔個三五天,他就要購買一大摞書。可以說凡是飲食文化方面的書,他都有,包括各類飲食史書典籍。在常人眼裡,這麼多書,未必能夠一一看完。但當你對飲食方面的某個典故不明白,或某件事記不清拿不準時,請教於他,他立即就能說出出處,並馬上將這方面的書找出來,一一堆在你面前,讓你不得不驚嘆他超常的記憶和善於讀書了。
唐沙波有個心願,將中國文學史上從先秦到明清,浩瀚的詩詞曲賦及野史、掌故、史、志中,整理出有關美食的詩篇妙文,編一套叢書。並將其分類為飲酒、飲食、果蔬、典故、節日節氣、飲茶等幾個方面。現已經著手這一工作,編至宋詩了。這套叢書如若完成,可說是飲食研究史上的一大創舉,必定會受到飲食研究者的歡迎。
唐沙波還有個心願,在重慶創辦飲食烹飪大學,就叫中國食文化大學,研究學習系統中國飲食烹任史,中國各朝各代飲食變遷及發展,以及全國幾大菜系的形成、變遷和發展,認真研究中國乃至世界飲食發展走向,為重慶、為中國培養更多的飲食烹飪人才。然而這個願望的實現只好留與有志的來者了。
現在,唐沙波正在積極籌辦《食海》雜誌。創辦一本飲食文化方面的雜誌,是唐沙波多年的願望,也是飲食文化事業發展所需要的,為此,多次開會研究,並自費出過兩期試刊,分送有關行業和部門,廣泛徵求不同階層不同行業的意見。可以預見,雜誌若創辦成功,一定不負眾望,成為飲食領域裡的一朵瑰麗奇葩。
盧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