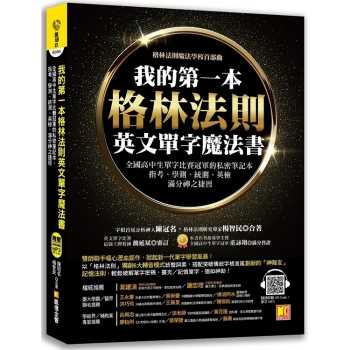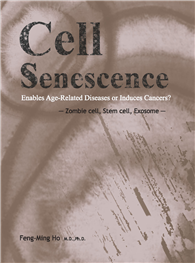建築和人一樣,
首先要真誠,要真實,
然後還要盡量做到親切和讓人喜歡。
萊特的草原風格成為二十世紀美國住宅建築設計的基礎。他設計的作品以本質的深刻理解和以形式與細節的相互烘托為主旨。他看到自然界的結構存在著類似的關係,而將他的作品稱為「有機建築」。
萊特在空間中充分考慮到人的存在,考慮建築與環境的有機結合。他提倡建築形式多樣化,較早地否定了風行世界國際式方盒子建築形式,給後來的美國建築思潮和世界各國的建築發展以深刻的藝術上的啟發。
萊特是二十世紀建築界的浪漫主義者和田園詩人。紐約古根漢美術館、落水山莊、鳳凰城西塔里森建築學校,均是建築師萊特的作品,除了美國的建築之外,更可在日本帝國飯店殘蹟的明治村中見到他的痕跡,這也在旅遊上蔚為一股風潮。可見萊特的影響力,他更為舉世公認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四大建築師之一,也被譽為當代建築界的先驅。本書選擇十五篇萊特最有影響力、最發人深省和最具持久魅力的著作,它們是萊特在1900年至1930年代所寫的文章,他的文章就和建築作品一樣,在歐洲和美國產生巨大影響,影響了現代建築的發展歷程。
坊間有關萊特的書多半談論他的建築作品,或是他與梅瑪之間的愛情故事,而這本書卻從萊特對建築的想法出發,對學建築及一般人來說是非常值得閱讀的一本書,透過這本書可以更加了解萊特,更加了解這個在一九九一年被美國建築師學會稱之為「最偉大的美國建築師」對建築的執著。
作者簡介:
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
生於一八六七年,卒於一九五九年,享年九十一歲。他是舉世公認的二十世紀偉大的建築師、藝術家和思想家,更是現代建築的創始人。與勒•柯比意、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沃爾特•格羅佩斯並列為世界四大建築師,更被譽為當代建築界的先驅之一。
萊特設計了超過1000個建築設計,他相信建築的設計應該達到人類與環境之間的合諧,稱之為「有機建築」的哲學。有機建築最佳的實例便是萊特所設計的落水山莊(1935年),曾被稱許為「美國史上最偉大的建築物」。
在萊特超過70年的建築師生涯中,設計了一系列各式建築,包括辦公室、教堂、摩天大樓、旅館和博物館,另外,還包含許多室內物品的設計,如傢俱、花窗玻璃。萊特一生著作二十本書與許多文章,並且是一位受歡迎的講者。
譯者簡介:
于潼
畢業於北京大學英語系,現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攻讀英語文學專業博士學位,譯著有《建築之夢》、《圖案之於建築》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系名譽教授 孫全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管理學系所專任副教授暨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邱詠婷
元智大學 藝術與設計系專任副教授暨系主任 阮慶岳
聯合推薦
如果今天是如同文藝復興的時代,那麼萊特就是二十世紀的米開朗基羅。
──國際知名建築師Eero Saarinen
路易斯•康、埃羅•沙里寧、貝聿銘、菲利浦•約翰遜都不能與他相比,即使上述這些人加在一起,他們在建築藝術上所具有的影響,也比不過萊特不尋常的七十二個年頭的建築職業生涯所造成的巨大影響。
──美國著名建築評論家Paul Goldberger
名人推薦: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系名譽教授 孫全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管理學系所專任副教授暨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邱詠婷
元智大學 藝術與設計系專任副教授暨系主任 阮慶岳
聯合推薦
如果今天是如同文藝復興的時代,那麼萊特就是二十世紀的米開朗基羅。
──國際知名建築師Eero Saarinen
路易斯•康、埃羅•沙里寧、貝聿銘、菲利浦•約翰遜都不能與他相比,即使上述這些人加在一起,他們在建築藝術上所具有的影響,也比不過萊特不尋常的七十二個年頭的建築職業生涯所造成的巨大影響。
──美國著名建築評論家Pa...
章節試閱
法蘭克.洛伊.萊特出生於一八六七年,當時安德魯.詹森擔任總統,美國收購了阿拉斯加,而在建築界,歷史折衷主義占有統治性的地位。他逝世於一九五九年,享年九十一歲,那時的美國總統是德懷特.大衛.艾森豪,蘇聯的「露娜一號」探測器到達了月球,而「現代主義」成了建築的同義詞。萊特出生在維多利亞時代,一生經歷了「快樂的九○年代」、「咆哮的二○年代」、經濟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並體驗了原子時代以及冷戰。一八六七年美國內戰剛剛結束兩年,而一九五九年電腦時代已經初現端倪。
萊特的職業生涯也特別長而富有變化。他負責的第一項工程就是威斯康辛州斯普林格林的聯合小教堂(Unity Chapel),該建築於一八八六年由芝加哥的建築師約瑟夫.L.希爾斯比為羅伊德.瓊斯家族設計,這個家族人丁非常興旺,萊特的母親就來自其中的一支。逝世前一周,他仍然待在這座建築附近,那時距他的第一份監督工程已經過去了差不多七十三年的時光。萊特的職業生涯比當時美國人的平均壽命還要長。
最初他選擇避開維多利亞式的折衷主義,而在職業生涯結束之前很長時間內,他都堅定地反對「現代主義」。儘管一直逆時代的流行而動,萊特卻是位異常多產的建築家。在他主持修建的近五百座各式風格的建築中,超過四百座至今仍然屹立,這個數字稍稍多於他設計的所有建築總數的一半。在他已完成和未實際建造的作品中,為中產階級和中上層階級客戶所設計的獨門獨戶家庭住房約占四分之三,這個比例在世界知名的建築師作品中可謂相當高,除非是為了富豪,這些建築師通常會避開設計家居這種盈利相對較小、又屬勞動密集型的項目。
萊特出生在威斯康辛州 Richland Center 的一個農莊,位於麥迪森以西五十英里。在愛荷華州、麻塞諸塞州以及羅德島居住過一段時間後,全家在一八七八年、萊特十一歲的時候,搬到了麥迪森。他曾經利用暑期在洛伊.瓊斯的農場工作,在那裡,他曾經一定為蜿蜒流過樹木、覆蓋綠色植被和淺黃色石灰岩相互映襯的威斯康辛河之美景而感到震撼。他在麥迪森度過初中和高中時光。儘管沒能從高中畢業,他仍然於一八八六年一月被威斯康辛大學以就讀「理科」課程的「特別學生」的名義錄取。他的學業成績其實並不突出,在畫法幾何與繪圖課上只得到「平均分」,也只有這兩門課程在他為期一年的大學生涯中留下了成績記載。
也許是因為他父母一八八五年離婚所帶來的經濟上困難,萊特一八八六年的春季和秋季學期在艾倫.D.考諾威教授的建築辦公室裡任職,並於同年夏季為在斯普林格林的希爾斯比(Silsbee)工作。也許他對建築的熱情是這兩個人點燃的。還有可能跟至親一起居住─比如他的母親,他的父親已經離開了麥迪森─萊特不再需要生活上的支援,他尋求職位只是因為他對建築的熱愛已經開始顯現而已。無論哪種猜測是對的,他還是在一二月從大學退學。一八八七年年初,他已經在芝加哥以繪圖員的身分為希爾斯比工作。
隨後他換過一次工作,然後,於一八八八年年初與丹柯瑪.阿德勒(DankmarAdler)和路易士.沙利文(Louis Sullivan)簽署合約,這兩個人的雇員人數在一八八六至一八九○年設計龐大的芝加哥會堂大樓(Auditorium Building)時達到頂峰。在接下來的五年中,萊特從繪圖員升職為首席繪圖員,並成為沙利文的門徒和知心朋友,負責公司承辦的一系列住宅工程,同時也照看其他類型的建築工程。也許正是因為沙利文和萊特變得如此親密─前者找到了自己從未有過的「兒子」般的人物,後者得到了一種可以做為替代者的「父親」─當兩個人因為萊特的雇用合約產生分歧時,情況看起來好像成了個人恩怨,至少在沙利文看來是這樣的。他覺得自己遭到背叛,於是解僱了萊特,而萊特則很快在一八九三年建立了自己的辦公室。
在接下來的八年裡,他設計了一批工藝精良、細節精湛的建築,它們大多數是具有獨特外形的房屋,慢慢地但又確實地─僅僅是在人們回顧過去時(這是個實驗的階段;萊特還沒有決定使用哪種建築語言)─演變成為了「草原城鎮中的一個家(A Home in a Prairie Town)」,這種新型房屋很快就為他帶來了聲望,這在一九○一年《婦女家庭雜誌》(Ladies Home Journal)二月號中有所描述。我們正是從這期雜誌的文章名中得到類似「草原房屋」、「草原學校」和「草原時期」等詞語。
「我將整所房子的規模壓縮……」他後來在《我的自傳》中寫道:「牆壁現在從地面上的一個……洩水臺開始,這看起來很像在建築物下面加了一個矮平臺……其頂端停留在二層窗沿的位置,這讓臥室通過一串連續的窗子連接起來,其上方則是具有較緩坡度的懸垂式屋頂和寬屋簷。」「中西部北方的氣候異常惡劣……,我為整個結構加上一種保護性的、遮蔽性的屋頂……屋頂的下面是平的,通常使用淺色,以造成一種反射光來柔和地照亮樓上的房間。懸垂的屋頂有兩個好處:能有遮蔽作用、保護牆壁……同時又能完成這種對光的反射……房子開始與地面有了聯繫,」他解釋說:「成為草原上一道自然的風景。」
他接著寫道:「建築的外觀主要是根據內部的需要而設計的。」他拒絕使用自己認為是「盒子邊上嵌盒子,或是盒子裡套盒子的建築設計」而重新做出如下定義:「整個底層是一個完整的房間,將廚房分隔出來做為一種實驗室,僕人們的臥室和生活區則與廚房一面相接……然後,為了不同的家居目的,我將大房間的不同部分隔開使用,比如餐廳、閱讀室、客廳等。」(他只在樓上保留了做為臥室的「盒子間」)「天花板……」他繼續寫道:「透過對水平的灰泥板子進行下調的反覆方式將其控制在窗子之上,並和房間的天花板漆成一種顏色」,這具有突出親密感和完整性的效果,房間中窗子和門楣處綿延不斷的裝飾線將所有因素聯繫在一起,更加強了親密感和整體性。充實感和留白感、垂直因素和水準因素都在這種整體性設計中得到體現,這其中也包括了家具、設備、玻璃美術製品和景觀美化。
在接下來的八年中,萊特以草原風格設計一百五十多處結構迥異的建築。他的作品從不缺少客戶,因為它們獲得的評價都很高,銷路也很好;他總是受邀演講或寫文章,並且還逐漸確立了國際性的聲望。但是在一九○九年九月,萊特的生活和事業卻急轉直下。一九○四年,他在伊利諾州橡樹園為愛德溫.H(Edwin H)和梅瑪.布斯威克.錢尼(Mamah Borthwick Cheney)設計了一處房屋,萊特從一八八九年起一直和妻子凱薩琳居住在該地─他們就是於當年步入結婚殿堂。這四個人成了朋友,當地的人都知道他們不分彼此,是一個融洽的四人組合。錢尼一家有四個孩子,而萊特家有六個孩子。但是在一九○九年九月,萊特和布斯威克偷偷在紐約見面,並轉往柏林,這個變故對少數人之外的所有人來說都是既突然又毫無徵兆的,他們讓自己的朋友、橡樹園,還有整個建築世界都為之震驚。就是這時出了大亂。
一九一○年十一月,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名為《西部建築師》的雜誌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其中描述了業界的反應,也反映了公眾的意見。該文章指出,當類似事件發生時,「美國和外國的建築師們……有權將這種灰暗的陰謀稱為『氣質問題』。(但是)如果我們率直而恰當地看待這件事,這種能夠讓一個男人帶著他人的妻子穿梭於歐洲首都城市間的氣質只能被認為是對道德缺失的最為卑劣的掩飾。
所謂的氣質問題就是道德敗壞的另一種說法。」怪不得萊特會於一九一四年聲稱:在任何可取的特徵中,「很不幸地,公平競爭(Fair Play)的精神在編輯之間太少見了。」梅瑪在歐洲大陸度過了一年,又在橡樹園花了一年時間,仍未能順利解決配偶和孩子之間的問題─她於一九一一年四月離婚,但凱薩琳這邊卻一直堅持到一九二二年才肯讓步─萊特和梅瑪於一九一一年決定要永遠一起住在威斯康辛州的斯普林格林。在那裡,萊特已經將塔里埃森(Taliesin)建造為他們的家和自己的設計工作室。儘管兩人受到嚴正的批評,被認為是「在罪惡中」生活,並為社會所孤立,但萊特和梅瑪卻過著一種互相激發靈感的生活;梅瑪翻譯了瑞典女權主義者艾倫.凱(Ellen Key)的著作,而萊特繼續進行建築方面的實踐─儘管與他在一九○五到一九○九年間接受的任務相比,從一九一○年到一九一四年,數量減少了五○%左右。到了一九一四年,來自社會方面的敵意已經逐漸消退,兩人似乎已經通過命運的考驗,可以過著正常的生活了,但就在這時,萊特卻經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打擊。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四日,他正在監督芝加哥一座房屋的建造工程,而梅瑪.布斯威克則正在和來看望她的兩個孩子、他們的一位朋友以及五個塔里埃森工匠一起共進午餐。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另外一個傭人在餐廳的窗子底下用汽油點燃了灌木,並鎖上了唯一的門,等在那裡,用短柄小斧砍死屋裡頭想要逃出來的人們。塔里埃森的大部分化為灰燼,梅瑪和其他六個人(包括她的兩個孩子)在這場災難中喪生。
萊特崩潰了。他在當地報紙上發表悼念文章,並在自己二十八年前建造的聯合小教堂內的洛伊.瓊斯家族墓地對面將梅瑪埋葬。幸運的是他毫髮無傷,他當時正負責兩處大工程,即芝加哥的米德威公園(Midway Gardens, 八月十四日他就是前往這項工程的現場),以及為東京帝國飯店進行初步設計,但是他最想做的卻是重建塔里埃森。「我將為曾經居住其中、熱愛這個地方的人們的不朽靈魂而重建塔里埃森」,他寫道:「我仍將居住在那裡,那裡仍會是我的家。」
但是他這種渴求在未來擁有寧靜生活和創造性工作的希望馬上就破滅了。一方面是因為他沒有辦法獨自生活,因為他生活中需要一個女人,至少可以這樣說,接下來的十五年他的人生充滿了暴風驟雨。在梅瑪死後不久,他就邀請發來感人弔唁的米利安.諾埃爾(Miriam Noel)來塔里埃森進行參觀。儘管性格明顯不合,他們卻斷斷續續地在一起生活了八年,其間爭吵不斷。然而,兩人卻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選擇結婚,並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分居、一九二七年離婚。因為財務和產業問題,也包括對塔里埃森的所有權─米利安投資了重建工程─惹來了看似永無終止的訴訟和法庭傳票,這時萊特有時無法去工作室工作,一九二五年的一場電氣火災更是讓他不得不將其重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他遇見了奧爾加.米蘭諾芙(OlgaMilanoff),並於次年的二月讓她搬進塔里埃森,成為她第二個孩子的父親─這已經是他的第七個孩子─孩子出生時還沒到一九二五年年底,這促使米利安提出「離間夫妻感情」的訴訟。儘管與米利安.諾埃爾的法律糾紛一直拖到一九三○年,萊特還是在一九二八年法律允許的情況下與奧爾奇瓦娜(Olgivanna,她現在對自己的稱呼)結婚,終於找到自己從一九一四年即開始追求的寧靜。他們的婚姻一直持續到他離開人世。
所有的這些人和事都被大肆報導,對萊特的生涯造成嚴重的損害。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只主持建造了二十九座建築,平均每年三座,這比他草原時期的業績少很多,也比他與梅瑪在一起的時候要少。但是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五年,已經降到了只有六座建築,其中有兩座是他為自己而建,一座是為親戚建造。他確實於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二年之間在日本待了四十個月,監建帝國飯店,同時大蕭條也限制了建築的發展,有些可能成為他客戶的人也是因為這段時間而卻步,他們並不太公正地認為一個無法處理好自己家庭情況的男人也不具備足夠的職業能力。結果,在「咆哮的二○年代」,當其他建築師的事業都繁榮發展的時候,萊特卻無事可做,但比較諷刺的是,在大蕭條時期最為嚴重的階段,當其他建築師手頭拮据時,他卻獲得了重生。
這其中包括三項獲得媒體大肆宣傳的工程:世界著名的落泉山莊(Fallingwater,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在賓夕法尼亞州熊奔(溪)(Bear Run),為愛德格.J.考夫曼設計的奢華鄉村小屋,在威斯康辛州拉辛(Racine)設計的嬌生公司行政大樓(Johnson Wax Administrative Building,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以及在威斯康辛州韋斯特摩爾蘭德(現在的麥迪森)設計的赫伯特.雅各住宅(Herbert Jacobs Residence,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這通常被認為是他的第一座「美國風(Usonian)」房子。從那時開始,除了在二戰期間,萊特的建築事業一直都興旺發達。他人生最後的十三或十四年是他一生中最具創造性的時期。
萊特的兒子約翰寫道,隨著梅瑪的死,她帶給他的 「存在於他心中的溫柔而可愛的東西也隨著死了……」儘管這些「東西」很難被確定,但其結果非常明顯。洛伊.瓊斯家族的箴言就是「違背世界潮流的真理」,在為梅瑪寫悼詞的時候,萊特就提到了這句話,儘管受到別人的詛咒、被社會所孤立,「我們卻坦率而真誠地生活著……我們還試圖幫助別人……為了他們自己的理想……我們所涉及的那種﹃自由﹄比遵守習俗要困難得多……很少有人敢於嘗試它。」
「妳們這些擁有愛的執照的夫人們,」他勸告道,「祈禱妳們可以像梅瑪.布斯威克一樣去愛、像她一樣被愛吧!你們這些有女兒的父母們─如果你們投入自己女兒的生命並達到跟這個可愛女人一樣的高度,你們就該滿意了。」除非我們意識到,當下就是我們生命中最為重要的時刻,「否則我們就會發現,如果有了愛和真情,這種珍貴的『當下』本可以變得多麼美好,那就非常痛苦了,我們的心就碎了。」
梅瑪.布斯威克是萊特一生的摯愛,即使在他與其他女人生活時也是如此。他們兩人就代表了「違背世界潮流的真理」這句箴言,當他們在斯普林格林的境況稍稍好轉時,他開始認為,兩人不顧世俗要求的生活實際上可以被接受、有可能被人欣賞,並可能成為解放他人的一種模範。但是她被謀殺了,這意味著異常艱難的十四個年頭的開始,讓他相信自己的希望落空了。和奧爾奇瓦娜之間的平靜生活也沒有讓他停止相信只有他自己─他自己一個人─象徵著「違背世界潮流的真理」。難道梅瑪的命運沒有證明,兩個人一起挑戰社會常規會讓獲得懲罰的機會也加倍嗎?
在某種層面上,這個「真理」是建築方面的。在哥德式建築時期結束後,萊特曾經反覆說(就像本書中的文章可以體現的一樣),只有他和路易士.沙利文才知道建築必須具有「有機性」才能真實可信。所有其他東西在社會和文化方面都是不恰當的。在美國,「有機建築」從意義上講就是「民主性建築」,因為民主從根本上來講就是這個國家的基本特徵。因此,任何不民主的東西就不是有機的,反過來也是如此,到了二十世紀二○年代晚期,這在他心中就意味著不是他自己設計的任何東西。這些概念並不是一直體現在萊特的思想中,但是經過二十世紀前二十年的經歷和磨難之後,它們變得清晰起來,常常被他重複,有時甚至讓讀者和聽眾覺得有些困擾。
這些文章揭示了他寫作風格的變化,本來他的文字就不是很流暢或者精美,但是現在卻愈來愈隨意,句法很容易引起人們的誤解,這讓他的文章和意思更難理解,有時竟非常難懂。並不是萊特刻意如此,顯然他更願意將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相反地,他這種特殊的文風顯示了一種自我中心主義,當剝去他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的文章中所使用的文學性、詩意的引用和例證之後,這個事實就更為明顯了。歌德、席勒、雨果、卡萊爾,還有其他那些為他的文章增色的人物都消失了。人們甚至會懷疑,萊特是不是不再閱讀了?又或者是,他認為自己已經是最好的權威了?
在一九一四年之前,他將自己的非常規性建築做為對同行的一種挑戰,讓他們重新思考自己為社會的利益做了些什麼,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二○年代,他利用這種建築來確立自己在一個失去希望的行業中的優越地位。在一九一四年之前,他的文章是為了透過一種相當直率的方式解釋自己的工作,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二○年代晚期,這種清楚的解釋讓給了一種文學上的唯我論。其中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本書中有關美國風房屋的文章,以及他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自然建築》(The Natural House)一書。該書是為想要建造房子的人所寫的一本易懂的使用手冊,其中包括了如何建造房屋,以及應該在這過程中以什麼為目標等內容。到了二十世紀二○年代晚期,從根本來看,他的設計和作品─以及他那種愈來愈花俏、隨心所欲、瀟灑又不合傳統的生活方式─對他來說都代表了他認為與自己天才相符的那種放蕩不羈,無論他自己是否意識到這些。這麼說並不是要批評他,而是試圖說明,在他心中,「違背世界潮流的真理」已經成為自己最好的庇護所,是他對在過去可怕的十五年來一直排斥他、詛咒他的社會的最後一道防線,在他的心裡這十五年已經成為他的整個人生。
當然,以上大部分都是一種猜測。萊特的生涯並沒有以輝煌的方式結束,大大小小的訂單並沒有從世界各個角落湧來。他在概念上、技術上和創作方面的創新雖然對建築史來說是關鍵性的貢獻,但是在今天對人們的認識來說仍然發揮作用─在當今時代,環境方面敏感的選址、材料和形式都比過去都更為必要。建築師對整個社會負有主要的責任─這是他作品中相當重要的一種資訊,本書中的文章體現出來的資訊也不僅僅局限於環境方面。
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他對於個人主義的深厚熱情,他主張每個人都有責任不顧輿論的壓力做回自己,但心中應保有社會和諧這個目標。同樣重要的還有他的另外一種主張─他並不主張一種掠奪成性、最終會帶來肆無忌憚的集權個人主義,而是主張每個人都有義務以民主原則的名義對其進行抵抗。做為當代的傑弗遜式的民主黨人,萊特花了很多時間批評政府和企業壟斷行為,認為這不可避免地會破壞個人自由。有些時候無論他的自我表達有多麼不成功,他的這些觀點就將他與大多數建築師區分開來,現在仍然如此。
法蘭克.洛伊.萊特出生於一八六七年,當時安德魯.詹森擔任總統,美國收購了阿拉斯加,而在建築界,歷史折衷主義占有統治性的地位。他逝世於一九五九年,享年九十一歲,那時的美國總統是德懷特.大衛.艾森豪,蘇聯的「露娜一號」探測器到達了月球,而「現代主義」成了建築的同義詞。萊特出生在維多利亞時代,一生經歷了「快樂的九○年代」、「咆哮的二○年代」、經濟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並體驗了原子時代以及冷戰。一八六七年美國內戰剛剛結束兩年,而一九五九年電腦時代已經初現端倪。
萊特的職業生涯也特別長而富有變化。他負責的...
推薦序
萊特的建築大夢與我們的未完成夢想
邱詠婷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管理學系所專任副教授、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總還記得當年拜訪萊特在鳳凰城的建築的震撼,朝聖般的參訪,看到我們對建築所有的想望,與自然的觀析與材料基地的結合,建築最第二自然的居所(dwelling)實體詮釋,是任何建築系學生的建築啟蒙。
這個大夢飄洋過海的移植到大西洋的另一頭,成為一個價值與信念,對自然的信念,對材料結構的自然狀態,所有的經驗,在落水山莊中,被看見被推崇。
姑且不論萊特的社會階級屬性,大樓,藝廊,別墅,旅館,別墅他是多產的,他的作品型式是多元的。大部分服務中產階級的家屋設計,理念卻是社會性的公共的,在每一個作品中,他企圖在原有的假設中,突破,改變,對工作的看法,對家的想像,與城市設計的想像,所以他改變的,不只是一種人,是一個城市的風景,一種觀看的方式,他更是環境多樣性的先驅者。然而他的局限性與企圖,在他的草原建築理論與美國郊區化和無盡的都市擴張問題,預言性的加速了美國城市之死亡,讓美國城市在夜晚成為危城,讓高速公路通勤成為上班族的日常生活,再現的,也是美國郊區的私有化的真實寫照,也因此改變了美國都市地景的死亡,這一個人的狂想,與現今郊區化的荒繆規劃現實即使萊特再富有想像力,都超出他的想像範圍。
而我們如何重返他的建築之夢學習,放在台灣,是精神嗎?是理念嗎?成為一個可實踐可參考的夢想而不是白日夢,畢竟再現的不該只是一盞燈或是平面圖,或火爐,作為不想量產,不相信現代主義模組化的美國建築師,所相信的美式個人自由與手感工藝,和永續環境,留給社會的除了草原式建築和有機建築的理念,最後竟讓後代基金會操作成為後現代消費社會下最有行銷概念與另類多產的建築師,正因為其多樣性,而出現我們對他的復刻版的生活型態。必須面對的是建築師再偉大,仍是社會經濟框架下的產物。
反骨建築設計
如同師徒制已經一去不復返,材料的地方性已成傳說,而自然早在全球化下成為奇觀,連萊特燈具都是美國商場上的熱賣品項,可消費而且無須等待,我們如何在網路年代仍對那美國藝術工藝大師學習,而所做的夢是現實可築構的夢想而不是,如白日夢虛幻的喃喃自語。
本書是萊特的自傳式書寫與其論述,討論的除了對建築的思考,環境與社會的關懷和世界觀,在不同層次企圖提出問題表達想法解決問題,也將讓我們看到從建築專業出發的夢想與困境。這對建築設計的同學是有助益的,不再只看圖片的型式模仿,也不再以單一簡單設計論述為對一建築理論的理解,而是透過他文本,得以從中反芻,並觀看一位建築師的養成過程中所遭遇的與其論述的轉化與盲點,包括與人相處的模式,資金和業主等問題,不再將建築師神格化某種程度讓專業者可以開始與其對話。透過此文本必須重新詮釋和閱讀,他所謂草原建築是在美國社會原子家庭的興起與其對家的渴望等脈絡下,得以被接受與建構。作為建築師的養成,更將連結他對專業的熱愛如何連結他感情歷程中的挫折和最終建築如何成為他個人的救贖與啟迪。他對建築,城市,社會輿論的看法,如何透過論述去發聲,實踐,翻轉與改變。唯有不斷的詮釋與思辨,我們才可定位萊特,作為建築師,老闆和環境主義者,如何被蓋棺論定。他是成功的建築師還是位失敗的規劃思想家? 窺視出他論述的盲點,因為時而自我的與偏頗所展現的平凡,得以讓我們看到曙光與建築規畫限制,他呼應的美國民主主義,讓我們看到設計伸展個人理想與發展出的建築型式,然而他所堅信的第二自然的社區規劃卻也讓我們深刻體會美國城市的死亡。這個建築大夢,即使生平備受批判與議論,但世人終究會給與萊特在建築史上該有的地位。而我們身在亞洲的台灣的建築學習又該是甚麼?
台灣版的沉淪與沉溺
經歷了社區營造,在文化創意產業成為另一波的空間改造關鍵字,都市更新與都市規劃讓草原式建築成為中產階級不可能或幾乎不合法的夢。而農村條例也讓建築師成為建商的白手套。年輕的建築師的困境沒有減少,熱情卻逐漸下降。無法奢侈的討論如何看到窗外更美好的風景,屬於自然環境融和的設計建造的創意成為遙不可及的夢。像等比例模型,我們僅能從暫時性的華麗樣品屋窺視我們短暫的萊特式白日夢與他本人所唾棄的風格。在地性與有機性已是主流價值卻無法被實踐的悲哀。台灣社會有無對應都市更新的建築型式,建築師的白日夢在哪?而真正改變的又是哪一個階級族群與群眾,我們的中產階級,將可擁有的家可以是甚麼圖像?新的辦公室圖書館藝廊是揭示企業的理念還是回到工作的新義涵或是人真正的體驗與自然土地的關係?
萊特展現了面對輿論壓力,面對師徒同業同事的回憶錄式警言反而可以給予我們一些建築職場的警惕。萊特是由媒體所吹捧但已也必須承受於公開輿論的壓力;師徒制的美好傳統卻也必須忍受人事的繁雜甚至專業的情感的背叛,也就是說,即使他的作品是非凡的,他經歷的生命過程與挫折與我們一樣是入世的。也唯有透過他的文本,即使斷裂,我們得以學習,而非片面山寨。反觀台灣建築,客觀評論極少,建築師被神格化或自我神格的書寫多於討論其困境,間接鉗制了真正想走進建築專業的年輕建築師設計師,因為看不到全貌或被蒙蔽。多少帶著夢想進來,卻失望離開的學子。在學習過程中,把這些看不到的真相不予討論並擱置。耽溺於美學型式與意識形態爭辯的學界,在此萊特的看似魯莽言論就顯得真誠許多,至少與他的整個創新思維與不想跟別人一樣的特質是一致的。值得我們藉由他來審視台灣在此專業養成與生涯規劃的缺失。
平凡與非凡
這本跳脫出咖啡桌上的圖像書的建築美學耽溺,在其並不精準的書寫中,翻譯出的是萊特作為非凡建築師的平凡。希望給與讀者的是一個專業對改變社會的無限想望鍾愛與最終的失望與明顯心情上沮喪和軟弱,也因為他的平凡歷程與壯志未果,我們再看他的建築作品,將更能領悟並看到其非凡的建築美學成就。至今,無人能及!
作為建築師,他對市場是不屑一顧的,然而在他生後,他的基金會卻將他變成最有市場性的建築師,遠遠超出他的想像。不僅在大賣場可看到他的複刻版燈或授權的手製工藝椅,連他的平面圖都是可從美國超市購買的藍圖。某種程度,他的民主思維,在後現代消費社會下反而是貼近市場的。
猶記得自己更年輕時朝聖般的參訪了鳳凰城Taliesn萊特的冬季居所與工作室,體會感動於他對於空間居所的呈現,只能意會,文字無法申論,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機乎過低的入口,而導覽員也有所解釋。一是萊特本身不高,所以他覺得開口越小越可感受進門後空間之遼闊。也就是說空間的魔法在於巧妙的創造層次與對比,不在實際坪數。他所運用的幾個建築設計手法,深深影響的,不只是中產階級,不只再美國本土而昰飄洋過海,已移植到許多亞洲建築人身上,將哲學思維空間化,結構與自然的和諧互相尊重等,對家的渴望與詮釋並實踐給予真實空間體驗。他在城市與鄉村,家與商業空間,有機建築與自然環境的尊重他的作品給予不同地景不同詮釋,而他的論述,將夢想成為真實!自己的建築養成與逃離,公民社會的關懷,包括師徒制的教學,也都曾深深受其影響。對與錯,不再是對他建築美學的耽溺,而昰將其文本重新與自己的專業對話與自我生命歷程深刻的省思!
空間詩學
萊特最動人的語言,仍是建築語彙,每個空間每個人每塊基地都有其獨特性有機性和詩意,小至燈具桌子椅子大到房子的外觀都有其特殊性與設計思考的可能,因此無可取代,都須量身訂做,這聽起來與現代國際風格背道而馳卻可相抗衡的思維與設計,終就讓這為反骨天才,不僅確立其無可取代的建築地位,也讓我們篤定這就是建築恆久不變的,永恆之道!
萊特的建築大夢與我們的未完成夢想
邱詠婷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管理學系所專任副教授、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總還記得當年拜訪萊特在鳳凰城的建築的震撼,朝聖般的參訪,看到我們對建築所有的想望,與自然的觀析與材料基地的結合,建築最第二自然的居所(dwelling)實體詮釋,是任何建築系學生的建築啟蒙。
這個大夢飄洋過海的移植到大西洋的另一頭,成為一個價值與信念,對自然的信念,對材料結構的自然狀態,所有的經驗,在落水山莊中,被看見被推崇。
姑且不論萊特的社會階級屬性,大樓,藝廊,別墅,旅館,別墅他是多產的...
作者序
法蘭克.洛伊.萊特出生於一八六七年,當時安德魯.詹森擔任總統,美國收購了阿拉斯加,而在建築界,歷史折衷主義占有統治性的地位。他逝世於一九五九年,享年九十一歲,那時的美國總統是德懷特.大衛.艾森豪,蘇聯的「露娜一號」探測器到達了月球,而「現代主義」成了建築的同義詞。萊特出生在維多利亞時代,一生經歷了「快樂的九○年代」、「咆哮的二○年代」、經濟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並體驗了原子時代以及冷戰。一八六七年美國內戰剛剛結束兩年,而一九五九年電腦時代已經初現端倪。
萊特的職業生涯也特別長而富有變化。他負責的第一項工程就是威斯康辛州斯普林格林的聯合小教堂(Unity Chapel),該建築於一八八六年由芝加哥的建築師約瑟夫.L.希爾斯比為羅伊德.瓊斯家族設計,這個家族人丁非常興旺,萊特的母親就來自其中的一支。逝世前一周,他仍然待在這座建築附近,那時距他的第一份監督工程已經過去了差不多七十三年的時光。萊特的職業生涯比當時美國人的平均壽命還要長。
最初他選擇避開維多利亞式的折衷主義,而在職業生涯結束之前很長時間內,他都堅定地反對「現代主義」。儘管一直逆時代的流行而動,萊特卻是位異常多產的建築家。在他主持修建的近五百座各式風格的建築中,超過四百座至今仍然屹立,這個數字稍稍多於他設計的所有建築總數的一半。在他已完成和未實際建造的作品中,為中產階級和中上層階級客戶所設計的獨門獨戶家庭住房約占四分之三,這個比例在世界知名的建築師作品中可謂相當高,除非是為了富豪,這些建築師通常會避開設計家居這種盈利相對較小、又屬勞動密集型的項目。
萊特出生在威斯康辛州 Richland Center 的一個農莊,位於麥迪森以西五十英里。在愛荷華州、麻塞諸塞州以及羅德島居住過一段時間後,全家在一八七八年、萊特十一歲的時候,搬到了麥迪森。他曾經利用暑期在洛伊.瓊斯的農場工作,在那裡,他曾經一定為蜿蜒流過樹木、覆蓋綠色植被和淺黃色石灰岩相互映襯的威斯康辛河之美景而感到震撼。他在麥迪森度過初中和高中時光。儘管沒能從高中畢業,他仍然於一八八六年一月被威斯康辛大學以就讀「理科」課程的「特別學生」的名義錄取。他的學業成績其實並不突出,在畫法幾何與繪圖課上只得到「平均分」,也只有這兩門課程在他為期一年的大學生涯中留下了成績記載。
也許是因為他父母一八八五年離婚所帶來的經濟上困難,萊特一八八六年的春季和秋季學期在艾倫.D.考諾威教授的建築辦公室裡任職,並於同年夏季為在斯普林格林的希爾斯比(Silsbee)工作。也許他對建築的熱情是這兩個人點燃的。還有可能跟至親一起居住─比如他的母親,他的父親已經離開了麥迪森─萊特不再需要生活上的支援,他尋求職位只是因為他對建築的熱愛已經開始顯現而已。無論哪種猜測是對的,他還是在一二月從大學退學。一八八七年年初,他已經在芝加哥以繪圖員的身分為希爾斯比工作。
隨後他換過一次工作,然後,於一八八八年年初與丹柯瑪.阿德勒(DankmarAdler)和路易士.沙利文(Louis Sullivan)簽署合約,這兩個人的雇員人數在一八八六至一八九○年設計龐大的芝加哥會堂大樓(Auditorium Building)時達到頂峰。在接下來的五年中,萊特從繪圖員升職為首席繪圖員,並成為沙利文的門徒和知心朋友,負責公司承辦的一系列住宅工程,同時也照看其他類型的建築工程。也許正是因為沙利文和萊特變得如此親密─前者找到了自己從未有過的「兒子」般的人物,後者得到了一種可以做為替代者的「父親」─當兩個人因為萊特的雇用合約產生分歧時,情況看起來好像成了個人恩怨,至少在沙利文看來是這樣的。他覺得自己遭到背叛,於是解僱了萊特,而萊特則很快在一八九三年建立了自己的辦公室。
在接下來的八年裡,他設計了一批工藝精良、細節精湛的建築,它們大多數是具有獨特外形的房屋,慢慢地但又確實地─僅僅是在人們回顧過去時(這是個實驗的階段;萊特還沒有決定使用哪種建築語言)─演變成為了「草原城鎮中的一個家(A Home in a Prairie Town)」,這種新型房屋很快就為他帶來了聲望,這在一九○一年《婦女家庭雜誌》(Ladies Home Journal)二月號中有所描述。我們正是從這期雜誌的文章名中得到類似「草原房屋」、「草原學校」和「草原時期」等詞語。
「我將整所房子的規模壓縮……」他後來在《我的自傳》中寫道:「牆壁現在從地面上的一個……洩水臺開始,這看起來很像在建築物下面加了一個矮平臺……其頂端停留在二層窗沿的位置,這讓臥室通過一串連續的窗子連接起來,其上方則是具有較緩坡度的懸垂式屋頂和寬屋簷。」「中西部北方的氣候異常惡劣……,我為整個結構加上一種保護性的、遮蔽性的屋頂……屋頂的下面是平的,通常使用淺色,以造成一種反射光來柔和地照亮樓上的房間。懸垂的屋頂有兩個好處:能有遮蔽作用、保護牆壁……同時又能完成這種對光的反射……房子開始與地面有了聯繫,」他解釋說:「成為草原上一道自然的風景。」
他接著寫道:「建築的外觀主要是根據內部的需要而設計的。」他拒絕使用自己認為是「盒子邊上嵌盒子,或是盒子裡套盒子的建築設計」而重新做出如下定義:「整個底層是一個完整的房間,將廚房分隔出來做為一種實驗室,僕人們的臥室和生活區則與廚房一面相接……然後,為了不同的家居目的,我將大房間的不同部分隔開使用,比如餐廳、閱讀室、客廳等。」(他只在樓上保留了做為臥室的「盒子間」)「天花板……」他繼續寫道:「透過對水平的灰泥板子進行下調的反覆方式將其控制在窗子之上,並和房間的天花板漆成一種顏色」,這具有突出親密感和完整性的效果,房間中窗子和門楣處綿延不斷的裝飾線將所有因素聯繫在一起,更加強了親密感和整體性。充實感和留白感、垂直因素和水準因素都在這種整體性設計中得到體現,這其中也包括了家具、設備、玻璃美術製品和景觀美化。
在接下來的八年中,萊特以草原風格設計一百五十多處結構迥異的建築。他的作品從不缺少客戶,因為它們獲得的評價都很高,銷路也很好;他總是受邀演講或寫文章,並且還逐漸確立了國際性的聲望。但是在一九○九年九月,萊特的生活和事業卻急轉直下。一九○四年,他在伊利諾州橡樹園為愛德溫.H(Edwin H)和梅瑪.布斯威克.錢尼(Mamah Borthwick Cheney)設計了一處房屋,萊特從一八八九年起一直和妻子凱薩琳居住在該地─他們就是於當年步入結婚殿堂。這四個人成了朋友,當地的人都知道他們不分彼此,是一個融洽的四人組合。錢尼一家有四個孩子,而萊特家有六個孩子。但是在一九○九年九月,萊特和布斯威克偷偷在紐約見面,並轉往柏林,這個變故對少數人之外的所有人來說都是既突然又毫無徵兆的,他們讓自己的朋友、橡樹園,還有整個建築世界都為之震驚。就是這時出了大亂。
一九一○年十一月,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名為《西部建築師》的雜誌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其中描述了業界的反應,也反映了公眾的意見。該文章指出,當類似事件發生時,「美國和外國的建築師們……有權將這種灰暗的陰謀稱為『氣質問題』。(但是)如果我們率直而恰當地看待這件事,這種能夠讓一個男人帶著他人的妻子穿梭於歐洲首都城市間的氣質只能被認為是對道德缺失的最為卑劣的掩飾。
所謂的氣質問題就是道德敗壞的另一種說法。」怪不得萊特會於一九一四年聲稱:在任何可取的特徵中,「很不幸地,公平競爭(Fair Play)的精神在編輯之間太少見了。」梅瑪在歐洲大陸度過了一年,又在橡樹園花了一年時間,仍未能順利解決配偶和孩子之間的問題─她於一九一一年四月離婚,但凱薩琳這邊卻一直堅持到一九二二年才肯讓步─萊特和梅瑪於一九一一年決定要永遠一起住在威斯康辛州的斯普林格林。在那裡,萊特已經將塔里埃森(Taliesin)建造為他們的家和自己的設計工作室。儘管兩人受到嚴正的批評,被認為是「在罪惡中」生活,並為社會所孤立,但萊特和梅瑪卻過著一種互相激發靈感的生活;梅瑪翻譯了瑞典女權主義者艾倫.凱(Ellen Key)的著作,而萊特繼續進行建築方面的實踐─儘管與他在一九○五到一九○九年間接受的任務相比,從一九一○年到一九一四年,數量減少了五○%左右。到了一九一四年,來自社會方面的敵意已經逐漸消退,兩人似乎已經通過命運的考驗,可以過著正常的生活了,但就在這時,萊特卻經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打擊。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四日,他正在監督芝加哥一座房屋的建造工程,而梅瑪.布斯威克則正在和來看望她的兩個孩子、他們的一位朋友以及五個塔里埃森工匠一起共進午餐。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另外一個傭人在餐廳的窗子底下用汽油點燃了灌木,並鎖上了唯一的門,等在那裡,用短柄小斧砍死屋裡頭想要逃出來的人們。塔里埃森的大部分化為灰燼,梅瑪和其他六個人(包括她的兩個孩子)在這場災難中喪生。
萊特崩潰了。他在當地報紙上發表悼念文章,並在自己二十八年前建造的聯合小教堂內的洛伊.瓊斯家族墓地對面將梅瑪埋葬。幸運的是他毫髮無傷,他當時正負責兩處大工程,即芝加哥的米德威公園(Midway Gardens, 八月十四日他就是前往這項工程的現場),以及為東京帝國飯店進行初步設計,但是他最想做的卻是重建塔里埃森。「我將為曾經居住其中、熱愛這個地方的人們的不朽靈魂而重建塔里埃森」,他寫道:「我仍將居住在那裡,那裡仍會是我的家。」
但是他這種渴求在未來擁有寧靜生活和創造性工作的希望馬上就破滅了。一方面是因為他沒有辦法獨自生活,因為他生活中需要一個女人,至少可以這樣說,接下來的十五年他的人生充滿了暴風驟雨。在梅瑪死後不久,他就邀請發來感人弔唁的米利安.諾埃爾(Miriam Noel)來塔里埃森進行參觀。儘管性格明顯不合,他們卻斷斷續續地在一起生活了八年,其間爭吵不斷。然而,兩人卻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選擇結婚,並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分居、一九二七年離婚。因為財務和產業問題,也包括對塔里埃森的所有權─米利安投資了重建工程─惹來了看似永無終止的訴訟和法庭傳票,這時萊特有時無法去工作室工作,一九二五年的一場電氣火災更是讓他不得不將其重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他遇見了奧爾加.米蘭諾芙(OlgaMilanoff),並於次年的二月讓她搬進塔里埃森,成為她第二個孩子的父親─這已經是他的第七個孩子─孩子出生時還沒到一九二五年年底,這促使米利安提出「離間夫妻感情」的訴訟。儘管與米利安.諾埃爾的法律糾紛一直拖到一九三○年,萊特還是在一九二八年法律允許的情況下與奧爾奇瓦娜(Olgivanna,她現在對自己的稱呼)結婚,終於找到自己從一九一四年即開始追求的寧靜。他們的婚姻一直持續到他離開人世。
所有的這些人和事都被大肆報導,對萊特的生涯造成嚴重的損害。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只主持建造了二十九座建築,平均每年三座,這比他草原時期的業績少很多,也比他與梅瑪在一起的時候要少。但是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五年,已經降到了只有六座建築,其中有兩座是他為自己而建,一座是為親戚建造。他確實於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二年之間在日本待了四十個月,監建帝國飯店,同時大蕭條也限制了建築的發展,有些可能成為他客戶的人也是因為這段時間而卻步,他們並不太公正地認為一個無法處理好自己家庭情況的男人也不具備足夠的職業能力。結果,在「咆哮的二○年代」,當其他建築師的事業都繁榮發展的時候,萊特卻無事可做,但比較諷刺的是,在大蕭條時期最為嚴重的階段,當其他建築師手頭拮据時,他卻獲得了重生。
這其中包括三項獲得媒體大肆宣傳的工程:世界著名的落泉山莊(Fallingwater,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在賓夕法尼亞州熊奔(溪)(Bear Run),為愛德格.J.考夫曼設計的奢華鄉村小屋,在威斯康辛州拉辛(Racine)設計的嬌生公司行政大樓(Johnson Wax Administrative Building,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以及在威斯康辛州韋斯特摩爾蘭德(現在的麥迪森)設計的赫伯特.雅各住宅(Herbert Jacobs Residence,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這通常被認為是他的第一座「美國風(Usonian)」房子。從那時開始,除了在二戰期間,萊特的建築事業一直都興旺發達。他人生最後的十三或十四年是他一生中最具創造性的時期。
萊特的兒子約翰寫道,隨著梅瑪的死,她帶給他的 「存在於他心中的溫柔而可愛的東西也隨著死了……」儘管這些「東西」很難被確定,但其結果非常明顯。洛伊.瓊斯家族的箴言就是「違背世界潮流的真理」,在為梅瑪寫悼詞的時候,萊特就提到了這句話,儘管受到別人的詛咒、被社會所孤立,「我們卻坦率而真誠地生活著……我們還試圖幫助別人……為了他們自己的理想……我們所涉及的那種﹃自由﹄比遵守習俗要困難得多……很少有人敢於嘗試它。」
「妳們這些擁有愛的執照的夫人們,」他勸告道,「祈禱妳們可以像梅瑪.布斯威克一樣去愛、像她一樣被愛吧!你們這些有女兒的父母們─如果你們投入自己女兒的生命並達到跟這個可愛女人一樣的高度,你們就該滿意了。」除非我們意識到,當下就是我們生命中最為重要的時刻,「否則我們就會發現,如果有了愛和真情,這種珍貴的『當下』本可以變得多麼美好,那就非常痛苦了,我們的心就碎了。」
梅瑪.布斯威克是萊特一生的摯愛,即使在他與其他女人生活時也是如此。他們兩人就代表了「違背世界潮流的真理」這句箴言,當他們在斯普林格林的境況稍稍好轉時,他開始認為,兩人不顧世俗要求的生活實際上可以被接受、有可能被人欣賞,並可能成為解放他人的一種模範。但是她被謀殺了,這意味著異常艱難的十四個年頭的開始,讓他相信自己的希望落空了。和奧爾奇瓦娜之間的平靜生活也沒有讓他停止相信只有他自己─他自己一個人─象徵著「違背世界潮流的真理」。難道梅瑪的命運沒有證明,兩個人一起挑戰社會常規會讓獲得懲罰的機會也加倍嗎?
在某種層面上,這個「真理」是建築方面的。在哥德式建築時期結束後,萊特曾經反覆說(就像本書中的文章可以體現的一樣),只有他和路易士.沙利文才知道建築必須具有「有機性」才能真實可信。所有其他東西在社會和文化方面都是不恰當的。在美國,「有機建築」從意義上講就是「民主性建築」,因為民主從根本上來講就是這個國家的基本特徵。因此,任何不民主的東西就不是有機的,反過來也是如此,到了二十世紀二○年代晚期,這在他心中就意味著不是他自己設計的任何東西。這些概念並不是一直體現在萊特的思想中,但是經過二十世紀前二十年的經歷和磨難之後,它們變得清晰起來,常常被他重複,有時甚至讓讀者和聽眾覺得有些困擾。
這些文章揭示了他寫作風格的變化,本來他的文字就不是很流暢或者精美,但是現在卻愈來愈隨意,句法很容易引起人們的誤解,這讓他的文章和意思更難理解,有時竟非常難懂。並不是萊特刻意如此,顯然他更願意將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相反地,他這種特殊的文風顯示了一種自我中心主義,當剝去他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的文章中所使用的文學性、詩意的引用和例證之後,這個事實就更為明顯了。歌德、席勒、雨果、卡萊爾,還有其他那些為他的文章增色的人物都消失了。人們甚至會懷疑,萊特是不是不再閱讀了?又或者是,他認為自己已經是最好的權威了?
在一九一四年之前,他將自己的非常規性建築做為對同行的一種挑戰,讓他們重新思考自己為社會的利益做了些什麼,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二○年代,他利用這種建築來確立自己在一個失去希望的行業中的優越地位。在一九一四年之前,他的文章是為了透過一種相當直率的方式解釋自己的工作,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二○年代晚期,這種清楚的解釋讓給了一種文學上的唯我論。其中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本書中有關美國風房屋的文章,以及他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自然建築》(The Natural House)一書。該書是為想要建造房子的人所寫的一本易懂的使用手冊,其中包括了如何建造房屋,以及應該在這過程中以什麼為目標等內容。到了二十世紀二○年代晚期,從根本來看,他的設計和作品─以及他那種愈來愈花俏、隨心所欲、瀟灑又不合傳統的生活方式─對他來說都代表了他認為與自己天才相符的那種放蕩不羈,無論他自己是否意識到這些。這麼說並不是要批評他,而是試圖說明,在他心中,「違背世界潮流的真理」已經成為自己最好的庇護所,是他對在過去可怕的十五年來一直排斥他、詛咒他的社會的最後一道防線,在他的心裡這十五年已經成為他的整個人生。
當然,以上大部分都是一種猜測。萊特的生涯並沒有以輝煌的方式結束,大大小小的訂單並沒有從世界各個角落湧來。他在概念上、技術上和創作方面的創新雖然對建築史來說是關鍵性的貢獻,但是在今天對人們的認識來說仍然發揮作用─在當今時代,環境方面敏感的選址、材料和形式都比過去都更為必要。建築師對整個社會負有主要的責任─這是他作品中相當重要的一種資訊,本書中的文章體現出來的資訊也不僅僅局限於環境方面。
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他對於個人主義的深厚熱情,他主張每個人都有責任不顧輿論的壓力做回自己,但心中應保有社會和諧這個目標。同樣重要的還有他的另外一種主張─他並不主張一種掠奪成性、最終會帶來肆無忌憚的集權個人主義,而是主張每個人都有義務以民主原則的名義對其進行抵抗。做為當代的傑弗遜式的民主黨人,萊特花了很多時間批評政府和企業壟斷行為,認為這不可避免地會破壞個人自由。有些時候無論他的自我表達有多麼不成功,他的這些觀點就將他與大多數建築師區分開來,現在仍然如此。
法蘭克.洛伊.萊特出生於一八六七年,當時安德魯.詹森擔任總統,美國收購了阿拉斯加,而在建築界,歷史折衷主義占有統治性的地位。他逝世於一九五九年,享年九十一歲,那時的美國總統是德懷特.大衛.艾森豪,蘇聯的「露娜一號」探測器到達了月球,而「現代主義」成了建築的同義詞。萊特出生在維多利亞時代,一生經歷了「快樂的九○年代」、「咆哮的二○年代」、經濟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並體驗了原子時代以及冷戰。一八六七年美國內戰剛剛結束兩年,而一九五九年電腦時代已經初現端倪。
萊特的職業生涯也特別長而富有變化。他負責的...
目錄
推薦序-擇善固執、堅持原則的建築師(孫全文)
推薦序-我的靈魂有翅膀(阮慶岳)
推薦序-萊特的建築大夢與我們的未完成夢想(邱詠婷)
導言
為了建築(一)
為了建築(二)
為了建築:東京新帝國飯店
機器的藝術和工藝
拉金公司行政新大樓
研究與已完成的建築
日本木刻版畫:一種詮釋
裝飾的道德標準
廣畝城市:一種新的社區規畫
美國住宅建築物體系
美國風住宅
國際風格
路易斯.沙利文
建築師
受獎演說
推薦序-擇善固執、堅持原則的建築師(孫全文)
推薦序-我的靈魂有翅膀(阮慶岳)
推薦序-萊特的建築大夢與我們的未完成夢想(邱詠婷)
導言
為了建築(一)
為了建築(二)
為了建築:東京新帝國飯店
機器的藝術和工藝
拉金公司行政新大樓
研究與已完成的建築
日本木刻版畫:一種詮釋
裝飾的道德標準
廣畝城市:一種新的社區規畫
美國住宅建築物體系
美國風住宅
國際風格
路易斯.沙利文
建築師
受獎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