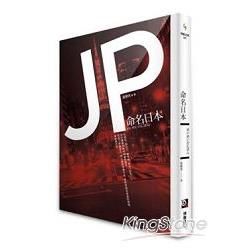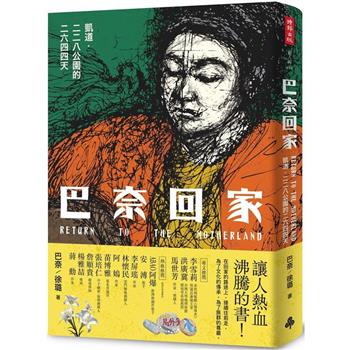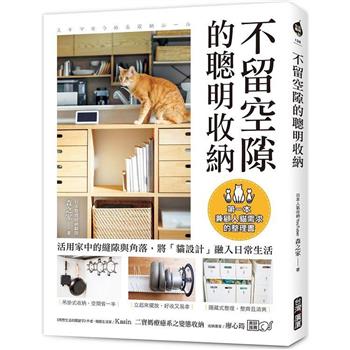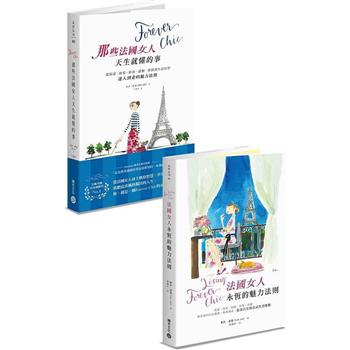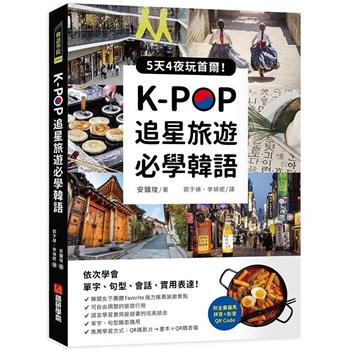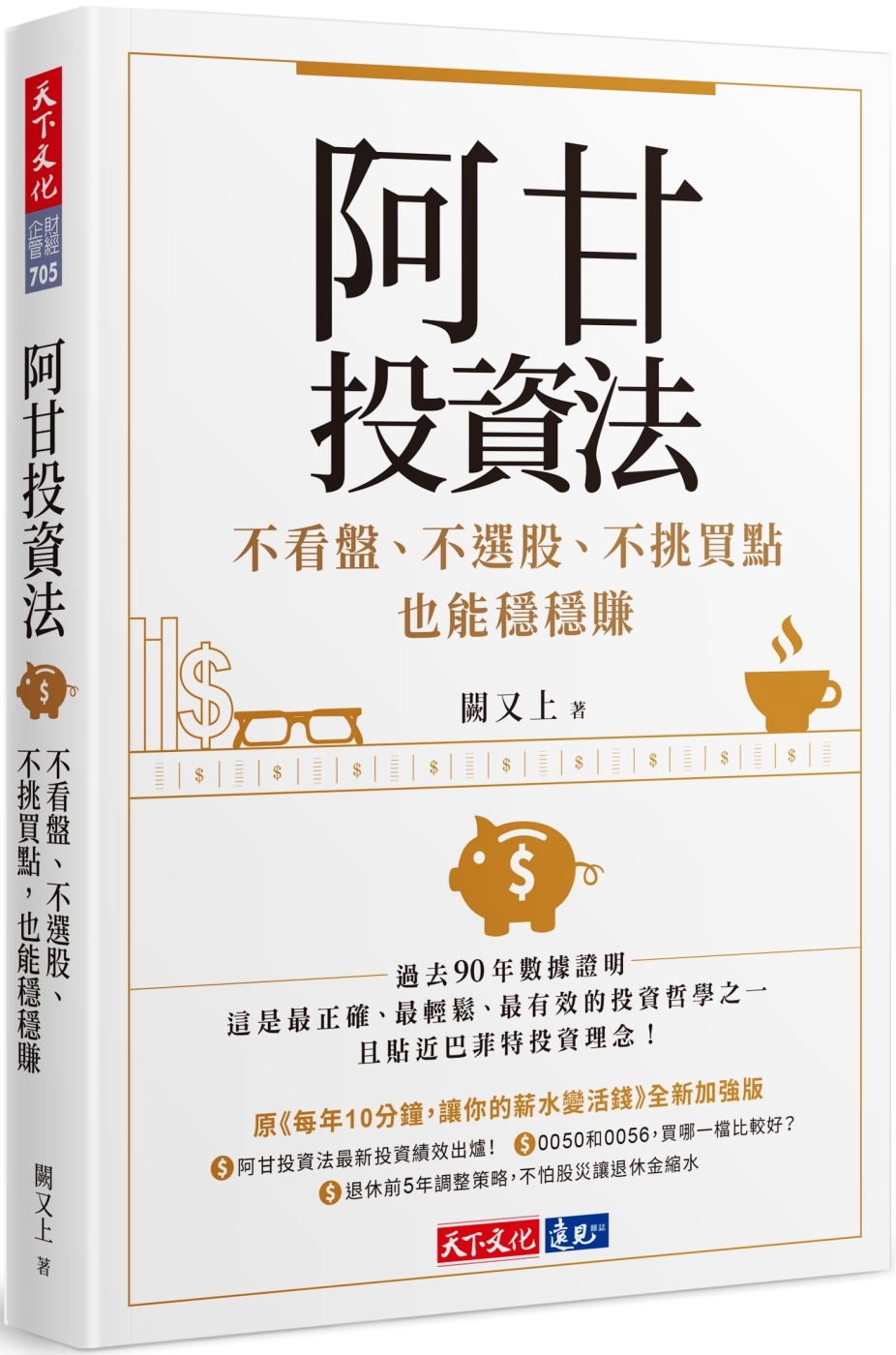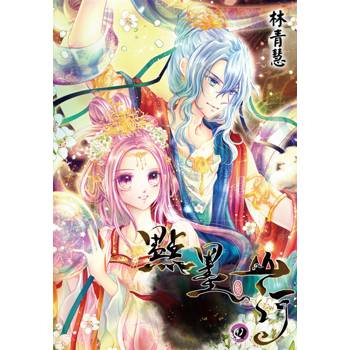導言
離陸的思想與著陸的思想
(I)為甚麼你不需要一本關於日本流行文化的讀物
湯禎兆上一本《整形日本》,不知不覺已經整了日本第4版。我想原因很簡單,因為不懂日文而仍想稍為認真點去閱讀日本的讀者,在香港(或許在台灣沒有那麼糟糕),要是不看湯先生的書,真的沒有太多選擇。
為甚麼呢?
原因可能是我們有太多販賣日本的專家,他們一天到晚對你說,日本社會是這樣的,日本文化又是那樣的。而妙在除了一些看似是他們知道,而我們不知道的所謂最新流行資訊外,這類文字與資料,並沒有甚麼可供我們思想的滋味與營養。很多人以為,走進自己不懂卻以為很容易掌握的文化問題,就能隨便寫寫。連日文書也沒有多讀幾本,就能充當日本專家的時代,閱讀這類文化趣談,根本沒有任何供人思考的營養—更糟糕的是,直接享受各類日本文化作品,遠比閱讀這類評論更為有趣。實情是很多人認為,只要曾在日本住過幾年甚或幾個月,就能在異地隨便書寫現時日本現況的介紹和分析。反正用中文書寫日本,日本是否真的如此,從來不會有日本人走出來指責。
長期生活在這種文化氛圍的人,長大了一心去日本尋找東洋俊男美女,追逐最新潮流,體會真實日本,結果焦頭爛額。對日本人產生了奇妙的心理情意結,抱著虛弱的心靈回來之後,能販賣的頂多是日本電視節目與雜誌的最新資訊。這樣一來對日本以至本地社會,就有更多看不順眼的地方。一般旅遊雜誌提供的資料,還能教導遊客到適當的地方購物玩樂,可是這種文化評論,讀之無味,不但棄之不可惜,亦無循環再造之必要。
可是我們依然在寫,你依然在讀,《整形日本》印了幾版還是在賣。
為甚麼呢?
這是因為我們打從開始只是自說自話,只看到自己心目中的日本。
我們(包括香港、台灣、中國大陸、亞洲等地、以至全世界的人)想像一個日本出來,然後只會看到自己認識的部分。湯先生自己說,上一冊《整形日本》銷路好,正因這種寫作策略:拉雜一大堆不同種類的抽象理論、讀書心得、最新資訊、個人體會、意見散文。於是乎,不同種類的讀者自會選擇他們各自看得懂的內容去看,各自拼湊出心目中的日本。
奇怪的是,我們會以為自己認識了真正的日本。我們受到十多二十年的強逼填鴨教育,因為習慣,讀一本書的時候,只會Underline自己看得明的句子,嘗試瞭解自己早已明白的內容。奇妙的是,我們讀一本課外書的目的,其實應該是去讀一些自己看不明的內容,這樣才能學習新的東西,自我才能改變。
可是我們依然會選擇地閱覽自己看得明的部分,更會認為這部分才是真正的日本。我們忽略了這個幾乎是自欺欺人的遊戲本質:我們生活在大量日本流行資訊的年代,充滿大量由各類日本專家與媒體過濾及創作關於日本的知識。我們成長在這種文化環境下,就會選擇性地閱讀自己看得明的內容。
去新宿走走就會知道。大量香港台灣遊客充塞在街道、店舖,但從來不會出現在紀伊國屋書店的三樓或以上樓層。好奇心強一些的遊客可能順道到一樓走一個圈,會看日本雜誌的到二樓逛逛,至於三樓或以上的各色日本書本,由於遊客都嚷著「我都不懂日文」,而從來不走上去看看。那麼,在港台文化背景生活的我們,所體會與認識的日本是多麼的有限,不待明言。我們所體會到的日本,跟日本人自己所生產的日本,兩者之間有道不可逾愈的牆。
這樣一來,為了彌補,我們生產更多的日本專家,為我們提供更多最新日本流行文化資訊,而這些專家與我們這類讀者,就更沉醉於自己認識的部分去選擇性地閱讀,結果強化了更多對日本的無謂與無責任想像,造就了一場偉大的對日精神自瀆文化戰爭。
結果是,為了彌補心理缺憾,我們強化了另外一些想像,譬如對日本侵略戰爭的道德控訴。政論專家與讀者,不斷生產與消費日本二戰時的惡行知識,強化大家的道德情操。而奇怪的是當今香港與台灣的大部分讀者,既沒有戰爭體驗,也沒有受到甚麼國家愛國宣傳,反而不斷去消費這類分析。日本人也不會閱讀用中文寫成的道德控訴,那麼我們有沒有想過,講這些故事的目的,其實是甚麼?
對的,這些都是我們不斷在販賣「日本」這兩個字的各種後果。筆者有位背負日本姓氏的老師說,在他教授的大學日本文化概論課上,當學生得知他其實是美國人,而非100%日本人之後,竟在課程檢討的問卷上寫上「不是純正日本人的老師,教的日本大概不夠真實」,令老師哭笑不得。這種心態當然可以理解:因為原來連大學教授,都跟旺角熟食中心內平民食店的「沖繩餃子」一樣,都是只有名字是日本的─ 顧客當然覺得被騙錢。原因是,叫「日本餃子」、「日本珍珠米」實在太普通了。就如速食店標明是「秋田小町米」的米飯漢堡一樣,我們販賣與消費「日本」的時候要求愈來愈高,於是乎,我們要求更陌生的日本。
二十多年來,一個社會愈是以日本作為招徠,我們愈追求更真實與更精緻化的日本。同時,我們先入為主對日本的想像,已經自動為我們選擇既定對日本的看法。愈多人在參與這種想像真實日本的遊戲,為了追求更真的日本去消費,我們就愈是想像更假的日本。
我們遺漏了一個問題沒有問:我們為甚麼想知道日本的事情?
(II)為甚麼你需要這本解說日本的普及文化讀物
那麼,這本書有何與別不同的地方,值得你購買呢?
如果這本書的內容你早已知道,那根本不值得你買。去年我曾為上冊《整形日本》作評,說:與日本社會與文化有關的大學導修課,我聲明不可抄引此書。理由是上日本社會課的大學生,有指定參考書不好好讀,隨便拿些坊間書本,譬如「日本人的性格」、「日本大不同」一類東西,來填塞學期報告。上幾個月拿功課來看,我發覺情況更壞,因為他們連坊間書本也不翻了。
理由呢?
在香港、台灣,關於日本的資訊實在太多了。報紙的、雜誌的、電視的、網上的、朋輩的。每天香港報紙娛樂版,例必有連日本人也不知道是誰的日本明星之水著照片與緋聞消息,而評論版就不難找到可能連外交部也覺得煩厭的日本政治評論。香港的各類旅遊、飲食、購物、潮流裝扮雜誌,內容緊貼日本不在話下,甚至連日本也難以得知的情報,在香港與台灣卻俯拾皆是。電視節目或明或暗的整形日本,其實我懷疑類似的飲食或者旅遊雜誌的表達手法與形式,根本就是在八、九十年代抄自日本的。從八十年代A-Club雜誌的讀者,投訴香港電視台隨意增減日本卡通的主題曲,到控訴本地劇集偷用動畫的背景音樂作為配樂─ 無論自覺或不自覺,我們已經完全生活在日本的影響之下。年輕一代根本不需要任何參考書,就能堆填一份充滿資料,而缺乏靈魂的關於日本社會功課來。理由是,他們本身,就是一本日本普及文化的參考書,不假外求。
既然人人能當日本專家,何苦再繼續整形日本?
這是因為我們想像日本,同理,日本人也能想像自己、命名日本。因為日本,原本只是一個名字而已。
讀者或許聽過以全球化一類的概念去談類似文化現象的方法。這些論調,其實假設了日本文化是一種既成的傳統或者價值,能輸出外地讓各國消費。可是,如果打從開始文化就是各種想像的產物,會隨時代而變化,那就根本不存在任何固定與不變的日本文化在全世界流動。我們喜歡吃的日式牛肉飯,在明治維新以前就不存在,因為那時候除了沒有日本人吃牛肉,連日本人的概念也未有。所謂的日本料理,根本就是對應「洋食」而應運而生的概念。現代意義的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並不存在。因此,我們所消費的,不是甚麼固有的日本文化,而只是「日本」這個字而已。日本人所生產的,也就是「日本」這個招牌了。不同的人群再因應自己的時代需要,把各色各類的想像內容,貼到這些招牌之下。
在這個大招牌之下,包含著更多不同的字詞。透過使用這些流行字眼與概念,讓大家能想像自己身處的環境,替自己找到適當的位置。最終,人們還能面對轉變,依然一起生活在同一個叫日本的共同體之中,成為日本人。我們的目的,正是分析不同的人群如何使用這些字詞,認知與感受他們如何安身立命。
作者所探討的,正是在九十年代後,這類字詞在日本社會出現的原因,還有這類想像背後所帶出的意義。本書以《命名日本》為題,不光是為好奇的讀者,提供消費這些東瀛字眼的部首索引。在日本語境之外看過去的好處是,我們反倒能更清楚地觀察由各種字眼所帶動的潮流。用中文書寫與分析日本,不代表我們對日本有任何影響,但起碼令我們在閱讀日本人用自己語言所書寫的作品,能比他們更加敏感。一般讀者可能不諳日文,而就算懂,如上所述,困在各地語境的讀者,依然會按照自己對日本的理解而有所選取,未必能直接理解當地各類人群所認同的架構。作者曾說,他所做的,莫過於替外地的讀者群,大量地閱讀我們平常不會主動拿上手的日文書籍,做翻譯與整合的工作。
讀者從目錄就能抽出本書探討日本社會的各種關鍵詞彙:人妻、女子鐵道迷、女子高生、主婦、悠長假期、落水狗、化妝狂、巨乳、購物狂、腐女子、老頭、武士道、足球、寅次郎、欺凌、百貨公司、感淚、郊外、文壇、御宅族、M型社會、AV等等。知道這些字詞的意思,並不單為追趕潮流。這其實是為讀者提供認識日本社會當地語境的新線索,讓大家考察日本人在過去二十年,如何透過創作新的詞彙與概念去面對社會不安,重新認識自己及他們身處的環境。
透過瞭解日本社會這些新興字詞與概念,我們或多或少能夠感受到這個群體在面對環境改變的時候,如何不斷摸索自己與社會的未來。《命名日本》承繼前著的精神,在廣泛的普及文化光譜中,找出各種不同有趣的蛛絲馬跡,整理出一般香港與台灣讀者也能趣味盎然地享受的一眾小故事來。
本書介紹的這類關鍵詞,在九十年代至今於日本消費與使用的同時,讀者仍須留意這些字詞與概念,其實是在不同年代發明的。雖然有這幾年新造的(譬如M型社會、腐女子),與在九十年代不安境況下誕生的關鍵詞(譬如悠長假期),但也有在高度經濟成長下(譬如購物狂與欺凌),以至大正時代所產生的字詞(譬如主婦、郊外與百貨公司)。考究這些概念在甚麼年代與社會背景下產生,解釋這些字詞的意義,能夠給我們一個系譜,為明日本現代社會是如何成立的。
當局者迷,日本文壇本身並未注意到他們自身如何製作、販賣與消費這些字詞,更何況日本的出版業與作者群,正是不斷生產這類概念去為當代日本社會整形。事實上,作者在《文壇偶像暢銷構造攻略》一文中,也觸及九十年代初日本出版業的泡沫問題。縱使大量水準參差的作者與出版商胡亂出版,各類書本很多時候也能賣個滿堂紅。可是,隨之出現的日本經濟泡沫爆破,出版業繼而凋落,加上九十年代打後的經濟與社會困境,正正刺激了出版社、學者、作家、傳媒與讀者群,售賣與消費不同的當代社會與文化分析書籍,試圖為自己的不明朗的未來摸索一個可能的新方向。社會整體的不安,令日本讀者與作者更急切需要某些關鍵詞,去掌握這個變動與不安的時代。
在日本九十年代的出版與社會背景下,我們當能瞭解世界各地對日本普及文化的追捧,終究是因為這些作品,其實有令人共鳴與感動的質素,而這些令人心動的普及文化作品,其實正是日本社會不安的反映。困境令人思考,各種文藝作品與為社會把脈的書籍,正好是不幸時代的象徵。
不同類型的人群,透過這類概念表達日常生活中的感覺與感情,包括歡喜、無奈、希望、挫折、苦痛與樂趣。我們的目的還是瞭解人本身,如何被困在這個社會—也就是自己—所製作的各種概念與神話之中,又如何嘗試替自己多找些可能性。
事實上,這本書絕對有好的理由去問關於日本的情況。透過理解他者如何面對改變中的環境而安身立命,至少為我們提供一種知性的刺激去為自己的境況想像。
人會對外在的世界與文化嚮往,而日本恰如香港與台灣兩地的月亮,對照自身社會的文化衛星。令人徘徊的日本,是我們對他者的神往,令人能脫離自己生活的種種限制。這是一種離陸的思想,一種心靈的開發。
可是,一旦種種虛妄層層疊疊,造就了各種心靈扭曲與消費洪流,導致了不同人群之間的癡心妄想、妒忌與猜疑。這是一種失控的思想,一種心靈的閉塞。
我們至今(包括文化界、學術界這類生產虛偽知識的元兇)還未看到問題的本質:我們為甚麼問關於日本的事情?日本人又是如何想像日本與自己出來的?
作者說過:「所以凡事都有不同的可能性,在乎我們想去認識哪一面的日本─而不是在想像日本。」《命名日本》嘗試面對這些問題。這本書,提供一種思想離陸的想像與心靈開發的期許。
2007年9月於CR本社
題目名稱借自見田宗介《現代日本的感覺與思想》(1995講談社學術文庫)其中一個章節的標題
如果我跟湯先生有任何共同點的話,那是雖然我倆都不大願意承認我們是甚麼日本專家,但我有信心保證,我跟湯先生所販賣的所謂「日本知識」都是有背後的經驗支持:書本、生活、各類文化產品的感動和經過腦袋處理的思想產物。是為本書的良心品質的保證。
張彧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專攻日本社會史)
序言
讀《命名日本》
看到香港少男少女狂迷日本漫畫、動畫、電視片集、日劇、流行曲,目睹女孩子扮起lolita通街走、聽到人說電車男他也把電車男掛在口邊的青年聲音,我常常思索,他們真的懂得日本次文化的深層含意有多少?
沒關係,孩子玩玩罷了,不必認真!有人說我一講到日本,就嫌嚴肅過了頭。也許是。那已經是四十年前的心結了。
1968年,左舜生老師約我跟他一同去日本,去看看明治維新百年紀念,了解這個中國死敵與強鄰,有些甚麼「作動」。我沒有去,因為工作時間不容許自由閒蕩,也因為窮。我只好留在香港努力讀許多有關日本的書,可是,能讀到的都是很硬的材料,好像總鑽不進日本人的社會和大和民族的心靈。
1973年,我終於到了左舜生老師口中「可怕、可愛、可恨」的日本。不過,我選「錯」了地方。京都一年,我一頭栽進了古典優雅、洛陽唐風的和式生活,腳步隨著川端康成《古都》的四季游移,我心目皆忙於遙接古風的文化品味中,竟全然體察不到「可怕可恨」,也遠離現代日本的形體活動,更遑論社會文化觀照了。
一年過後,我赤貧如洗,回到香港。儘管一年中,我學不到左老師想我學的東西,但日本人的執著與認真從事,無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裡的研究風氣,或巴士司機珍而重之戴上一塵不染白手套才開車的態度,都令我難以忘懷。
但說到底,一年日本生活,我並不因此認識日本這個國家。
往後的日子,東洋風幾乎不擇方向吹襲香江,中日關係也日益頻繁而張弛互動,我們不能不好好解讀大和民族。日本流行文化正盛,社會問題複雜變化也大,這該是最理想的解讀切入點,可惜,我都不懂得。
九十年代初,湯禎兆告訴我他要去東京讀書。我說很好!
先岔開一筆說說,我在中文系任教二十多年,發現有些中文程度很好,創作力強的學生,其實並不適宜讀中文系,湯禎兆是其中一個。他觀察力分析力都很強,課堂上,總有自己的看法,通常他一講,道理通透,有時也非一般人能接受。我手頭藏有他當年一篇文稿《某天,又一個大學生自殺了— 給林奕華》,開頭一句是「自殺是一種創作」,內裡文字揮灑不羈,思想另類,這種學生,中文系的規行矩步,如何縛得住?我不知道他到東京去學甚麼,但,在東京,現代日本全貌當可鉅細靡遺,對靈活的浪遊者來說,自有一番參透。所以,我說很好。
1992年年底,他回到香港,從他寫的文章中,我慢慢讀到他一年日本的觀察與感受,半工半讀的生涯,把他的目光磨得更銳利。
《俗物圖鑑》、《亂步東洋》、《AV現場》,他深化理解當代日本的某些層面,只是他講的那些文化,我不大感興趣。(湯禎兆還以為我不會看《AV現場》,他實在小看了我!)直到《整形日本》出版,我才以學習的態度去細讀了。「湯禎兆對日本流行文化追得貼,看得透,最要緊是把問題大而化之,小而中的。理論不是沒有,卻處處滲在實例中。」讀後我寫下了以上的看法。
一天,湯禎兆打電話來,他的《命名日本》要出版了,問我可不可以寫篇序,我沒有猶疑,答應了。
從書稿中,可見他選定了一些日本社會比較值得探討的論題:兩性處境、教育體系變化衍生的問題、消費文化的模式衍化等等。我不是尋求甚麼文化研究理論根據,但書中所載的觀察,校正了無數我對當今日本的認知。
三十多年來,日本已抵抗不住各種變異風浪,起了變化。例如老化銀髮族的遭遇與《恍惚的人》原來早有一段距離。我一直十分佩服的日本國民教育,近十多年也無法穩持了,青少年問題困擾著日本,且看政府如何重新起步改造國民質素。只有「男女社會地位不平等」這一項,是歷史宿命,看來甚麼女權主義,仍起不了作用,日本女性多大膽婚前性愛、狂購物化妝,到頭來還是回家當「人妻」,受盡委屈,這與我三十年前所見並無不同。
《命名日本》,與《整形日本》配套可成解讀日本的手邊書。左舜生老師以經驗學問教導我認識日本的可怕可恨,湯禎兆以新知識與分析引導我從新角度觀察今天的日本,那已經不再是愛恨的纏繞,而是知己知彼的進程。
盧瑋鑾(小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2007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