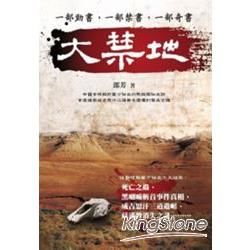一部勁書,一部禁書,一部奇書
中國首部關於蒙古秘史的懸疑探秘史詩
首度揭密成吉思汗三道著名遺囑的驚天玄機;
強勢破解蒙古秘史十大謎案的勁書。
《大禁地》是一部「禁書」,更是一部「奇書」,已完全脫離了傳統懸疑文學的寫作套路,它試圖破解「成吉思汗的三道神秘遺囑」、薩滿教的「一切皆傳自天語」、只聞其名、未見其面的「死亡之蟲」、黑喇嘛「斬首事件」的真相……《大禁地》更是一部「勁書」,它有西部風格的粗獷豪放、跌宕起伏的情節設置、糾結繁複的兒女情長、波詭雲譎的勾心鬥角、險死還生的喋血惡戰……
作者簡介
郎芳
女,現居北京。被譽為「中國懸疑小說天后」,「內地女性文化懸疑第一人」。以詭異文風、超常想像力、無可比擬的故事情節設置、以及深厚文化底蘊笑傲華語文壇。是中國懸疑文壇現如今最為炙手可熱的實力派作家之一,也是媒體報導最多的作家之一,每本作品均具有極高的口碑與收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