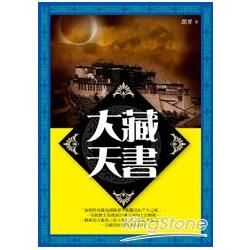「揭密所有藏地探險都不敢觸及的千年之秘」,「一卷被唐玄奘遺落於通天河的上古佛經,一個牽連古藏地三座王權你死我活的不殺之秘,一位絕世紅顏的淒涼歸宿」
古老的藏地歷史上,古精絕國、古象雄國的突然消失,一直是一個謎。據說,這是歷史上最大的陰謀,而陰謀的主角,竟是象雄國的一個女人。
到底是為了愛情、權勢、還是報復?
沒有人知道這位絕世紅顏的下場,只知道她最後曾現身於蘇毗王子的「天宮」。而蘇毗,則是當時藏地歷史上最為輝煌的女國。
千年以後,這個秘密被偶然揭破,這個「偶然」來自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一個夜晚:一則關於「喜馬拉雅野人」的新聞突然爆炸,真假難辨,於是,一群充滿好奇心的年輕人組成了探險隊,想一探野人真身。誰也沒有想到,雪線以上等待他們的,卻是一場慘烈的大屠殺……。
而事實上,這支探險隊的組成,同樣是一個陰謀。它的任務,是要找到千年之前蘇毗女國所遺留下來的一個秘密,這個秘密,跟當年唐玄奘西天取經時,遺落在通天河的一卷絕世經書有關……。
作者簡介
郎芳
女,現居北京。被譽為「中國懸疑小說天后」,「內地女性文化懸疑第一人」。以詭異文風、超常想像力、無可比擬的故事情節設置、以及深厚文化底蘊笑傲華語文壇。是中國懸疑文壇現如今最為炙手可熱的實力派作家之一,也是媒體報導最多的作家之一,每本作品均具有極高的口碑與收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