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名症候群:個人與群體的面向
楊照 新新聞副社長兼總主筆
前言
十多年前,差不多同一個時間,我有機會接觸到台灣政界三位重要人士──當時的李登輝總統、許信良、以及陳水扁。這三個人,構成清楚的對比。
李登輝對什麼話題都充滿興趣,鮮明對照陳水扁對什麼話題,除了現實政治以外,都沒有興趣。跟李登輝聊天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你提起任何題目,不管是歷史、文學、音樂還是水利工程,李登輝都會興致勃勃地開始炫燿他的知識,熱情地擺出指導者的姿態來。不過相比之下,跟陳水扁聊天是一件更困難的事,因為你講的任何東西,他通通不懂,他會用客氣、籠統的方式不斷認同回應,然而,表面的禮貌無論如何無法掩飾事實│他聽不進去你在講什麼。
陳水扁和許信良構成另外一組對比。我沒有看過比許信良更沒禮貌的人。他隨時不客氣的打斷人家的話,提高聲音反對人家的意見,他隨時準備要進行一場無止盡、沒完沒了的辯論。跟他談話,也的確常常都會變成激烈的辯論,然而,我很快就發現一件奇怪的事,和許信良辯論一、兩個小時後,怎麼原本從我口中說出的話,變到許信良的嘴裡,而且成了他熱情護衛的意見?沒禮貌的許信良,其實隨時隨地都在聽,在辯論中接受想法,甚至改變自己的想法、立場。
你永遠沒辦法找陳水扁辯論。後來我明白了,不是因為他客氣,而是因為他自己從來沒有深刻相信,非主張不可的東西。他永遠在那裡算計著,這種狀況下,到底抱持什麼樣的態度立場,最為有利?陳水扁跟毛澤東一樣,是個徹頭徹尾的策略家,一切都是策略,沒有信仰,沒有終極關懷終極目標。
陳水扁執政才半年,我寫過一篇文章,引用了三島由紀夫在日本「安保鬥爭」中,對當時日本首相岸信介的評論。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超過三十萬示威群眾包圍岸信介官邸,三島由紀夫站在國會大樓屋頂,俯瞰被重重包圍的首相官邸。回到書房,他寫道:「並不是因為他是個戰爭的禍首,也不因為他是個馬基維利式的權謀政客,甚至也不是因為他是個專門巴結美國人的馬屁精;人們恨他,因為他是個很小、很小的虛無主義者……他什麼都不相信,而且雖然他或許自認有信仰,但是社會大眾卻很本能地覺得他不能信服自己的政治信條。」
「虛無主義者在政治上最大的殺傷力,是他會破壞一切的信任機制,使得讓政策能夠從思考到實踐的時間完全無法存在,讓必須協調完成政策的各方力量無從集結。大家弄不清楚虛無主義者相信什麼,也就沒有把握他什麼時候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來。換句話說,虛無主義者讓每個人都害怕自己不知什麼時候會被背叛……捉摸不清虛無主義者相信什麼,也就不敢依賴任何需要互信為前提的機制,於是彼此的互動對待就越來越粗暴、赤裸裸,越來越追求一翻兩瞪眼的立即效果。」
【一】
民主政治有許多內在的緊張,其中之一,就是領導人要靠討好大多數人來取得權力。既然要討好大多數人,這種人能有多高的原則?然而,沒有原則的行事方式,卻又必然破壞行使權力的基本條件│信任感。陳水扁是個沒有原則的人,靠著沒有原則的圓滑,靠著許多彼此矛盾的承諾,他才得到足夠的票數,當上了總統。然而,當上總統後,他沒有能聽取美國總統杜魯門最重要的忠告:「一旦當選了,你就得停止競選。」陳水扁沒有辦法讓自己轉型成有原則、可預期的總統,他繼續說著做著矛盾的話矛盾的事,讓所有對他有過期待的人,都在某個時刻,感到深受背叛。彼此矛盾的承諾,沒有原則底線的行為作風,終究還是會在時間的考驗中露出馬腳來。沒有原則的人,也就找不出原則真正原諒自己,於是,只能在精神上架構各種防禦機制。這是陳水扁讓自己走進的另一個沒有出路的黑暗地窖。
「……一連串攻擊別人的指責、令人懷疑到一串類似的自我譴責的存在。我們所要做的,祇需將每一項指責反過來指向自己。在這種以指責別人來轉移自責的自我防禦方法中,有一種不可否認的自動因素。這種方法的一個典型例子,可以在小孩子『你也是』的爭論中發現,如果有一個小孩子被指責為說謊者,他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你也是。』成年人如果要以牙還牙的話,會找尋對手真正暴露的弱點,而不會重複別人咬過的,在妄想病(paranoid)中,自責之對別人外射,其內容沒有任何改變,而一點也不考慮真實,這在妄想的形成過程中變得很明顯。」
讓我們先仔細瞭解一下,佛洛伊德這段話(引自《少女杜拉的故事》)所含的重要洞見。
短短一段話裡,佛洛伊德觸及了幾個人類行為背後的精神因素。第一個是指出一種常見的自我防禦心理行為。不管自覺或不自覺,如果一個人做了帶給自己道德意識壓力的「錯事」,他會轉而以攻擊指責他的人,來替自己脫責脫罪。儘管「錯事」是他做的,然而他卻將錯事的壓力,轉嫁發洩在指出他犯錯的人身上,視其為讎敵。
這就是我們一般語言裡說的「惱羞成怒」,惱羞成怒時,怒氣指向的,一定是暴露其錯誤行為,使其蒙「羞」的人。不過,佛洛伊德在此之上,進一步分辨出「惱羞成怒」之「怒」發洩表達的方式。
一種特別的方式,被佛洛伊德視為不成熟經常都出現在兒童身上的,是要攻擊憤怒對象時,不顧那對象的個別性,不管這個指摘他的錯誤的,是爸爸、媽媽、老師、男同學或女同學,也不管指摘他的人實際有什麼缺點弱點,一股腦兒將自己被指責的錯誤行為,轉套到對方身上。
小孩爭執時,的確常發生這種狀況。A說B「作弊!」B的自然反應,一是:「我沒有!」另一種是:「你亂講!」還有一種卻是:「說別人說自己,你才作弊!」佛洛伊德談的,就是最後面的一種反應。不過佛洛伊德的理論中,進一步劃分出小孩與成人使用這種心理防禦機制的差異,小孩通常是因為對於他人行為累積的理解不足,無能快速尋找到對手的缺點弱點,於是方便習慣地將對方拋來的指責丟回去,做為最方便的防衛。小孩甚至還會用一種籠統、普遍的方式來給自己「防護罩」,例如將「說別人說自己」隨時掛在口頭上。
成人卻不然。成人理應對人的行為有了一定認識理解,不可能天真以為:我做錯什麼事,講我的人也會做同樣的事。於是,會如此倒過來講別人的,心理中勢必要有一定程度脫離現實的「妄想」,他必須在相當程度上製造假象,說服自己讓自己相信:「罵我的人都跟我一樣壞!」他才有可能採取如此的防衛方法。
所以進一步有趣且重要的問題:理應沒有那麼天真,理應有能力去找出別人弱點予以還擊的成人,為什麼還要訴諸於這種幼稚的心理反應?他偏離妄想的來源是什麼?
【二】
佛洛伊德最大貢獻,就是透視了妄想的源頭,那就是深度焦慮刺激出的逃避機制。一個會說:「你也是!」的成人,放棄了替自己舉證辯護的方法,也放棄了真正去攻擊對手的方法,卻寧可在心理創造幻覺,相信罵他的人跟他犯了相同的錯誤,因為:第一、他喪失了足夠強悍的意志辯護自己;第二、他要逃避自己心中對錯誤行為的焦慮折磨。 陷在這種情境下的人,當不能再假裝自己的錯誤不存在時,祇好反過來刻意拿自己的錯誤到處張揚,到處看到別人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如此得到雙重安慰。一重是說服自己相信:「我犯的錯不嚴重,因為有那麼多人都犯同樣錯誤。」另一重則是說服自己:「沒有人會再看到我的錯誤,他們祇會看到其他那麼多人都一樣。」
這樣不成熟的心理防衛,正是陳水扁當總統執政時,最凸出的精神狀態。二○○六年,紅衫軍起,以「反貪腐」為訴求發動包圍總統府,同一年的十月十日,陳水扁在國慶典禮中,竟然公開大談「反貪腐」讓許多人覺得不可思議。自己身陷嚴重貪腐指控的人,照理講不是該迴避「貪腐」話題惟恐不及,怎麼反而自己去提醒別人注意「貪腐」呢?
借用佛洛伊德的洞見,我們就明白:這正是陳水扁僅有的心理防禦了。他們不願也無法在自己的貪腐行為上進行辯護,貪腐錯誤的焦慮,又使得他們的精神能量(psyche energy)被大量吸納在黑洞中,不夠能力另闢戰場去攻擊藍營或紅營真正的弱點,他們就自然地彷彿返老還童,變成一個小孩,指著周遭說他貪腐的人,反覆大叫:「你才是!你們才是!」 一個被控貪腐的人,為了看不到自己的貪腐,他會在其他人身上,到處看到貪腐。這又是佛洛伊德給我們的重要提示。他要拿來攻擊別人的題材,正是他要逃避別人觸及的自身痛處。
「貪腐」是陳水扁第二任期後半才爆發的大炸彈,不過應對「貪腐」的心理機制,卻早就有所鋪陳準備了。從二○○○年政黨輪替開始,陳水扁就逐漸愈來愈依賴「國民黨也是這樣做的」、「國民黨可以,我為什麼不可以」、「至少我沒有國民黨壞 」的論理邏輯,來自我辯護。等到「海角七億」被掀出來,貪腐弊案進入司法程序,陳水扁一貫最明確的自我辯護方式,也依然是試圖證明他所做的,和之前國民黨執政時事一樣的,要不然就是和馬英九的「特別費」是同一回事。
「以前可以,現在為什麼不可以」,是「你也是」的變形,目的都在將罪名推回指責者身上,來堵其指責之聲。然而,放在政黨輪替的特殊歷史背景下,這樣的說法格外缺乏說服力。國民黨之所以失去了中央執政權,之所以會有政黨輪替,正是因為國民黨的做法是錯誤的,在道理上和現實權力合法性上都是錯誤的。道理上的錯誤,過去民進黨講得最多、講得最清楚;權力運作上的錯誤,選票的走向就是最好的證明。
藉著國民黨如此錯誤而得到選票當選總統的人,明白肩負的,是揚棄國民黨的錯誤,走一條和國民黨不一樣的改革道路的責任,怎麼會用「以前可以,現在為什麼不可以」做為自我立場呢?
這麼明顯邏輯上不通的地方,這麼多內部外部意見的批評反應,卻都不能讓陳水扁放棄這樣的說法,我們只能將之解讀為:這應該有精神結構上的理由,換句話說,這是他精神結構中根深蒂固的問題,不只是一時的刺激反應。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心理學家閱讀陳水扁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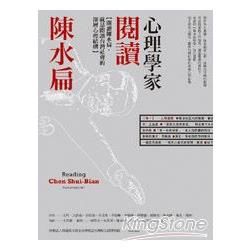 |
心理學家閱讀陳水扁 作者:王丹、王浩威 出版社: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1-29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二手書 |
$ 230 |
Others |
$ 339 |
社會人文 |
$ 351 |
中文書 |
$ 351 |
政治 |
$ 359 |
政治人物 |
$ 359 |
台灣政治 |
$ 359 |
社會人文 |
$ 359 |
政治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心理學家閱讀陳水扁
對許多人來說,陳水扁是心中一抹難以言喻的創傷
究竟他是孤立的偶然,還是集體的責任?
本書以「陳水扁現象」為出發點
用十種多元視角,鑽探台灣社會的深層心理結構
陳水扁,這個在每位台灣人心中都烙下不可抹滅印象的前任總統,2000年以三級貧戶之子躍上權力頂峰,2008年下野後旋即因貪瀆被起訴,從一個政治超級巨星淪落至階下囚,傷了許多支持者的心。細究台灣自解嚴後二十餘年的民主化歷程,我們不禁疑惑:究竟陳水扁僅是歷史長流中一則孤立的案例,還是反映出了一個更幽微的集體社會現象?
本書從所謂的「陳水扁現象」出發,以十篇論文探討政治人物的崛起和殞落,以及這個現象背後相關的心理、社會、歷史、哲學等人文議題,不論是研究人員立場超然的學術探究、支持者的失落批判,或是堅持相挺到底的無悔,還是知識分子對台灣社會深層結構的精準剖析,皆盡收其中,並附有研討會的與談紀錄,是國內第一本以多元學術視角探討「陳水扁現象」的重要論著。
作者簡介:
王丹、王浩威、余伯泉、宋文里、李筱峰、李維倫、林耀盛、孫隆基、陳永興、陳真、楊照
(與談人:平路、宋文里、杭之、張達人、張德聰、梁裕康、陳永興、黃榮村、葉啟政、蔡詩萍
編輯顧問群:王浩威、何榮信、吳英璋、陳永興、黃榮村、葉啟政)
章節試閱
第一名症候群:個人與群體的面向楊照 新新聞副社長兼總主筆前言 十多年前,差不多同一個時間,我有機會接觸到台灣政界三位重要人士──當時的李登輝總統、許信良、以及陳水扁。這三個人,構成清楚的對比。 李登輝對什麼話題都充滿興趣,鮮明對照陳水扁對什麼話題,除了現實政治以外,都沒有興趣。跟李登輝聊天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你提起任何題目,不管是歷史、文學、音樂還是水利工程,李登輝都會興致勃勃地開始炫燿他的知識,熱情地擺出指導者的姿態來。不過相比之下,跟陳水扁聊天是一件更困難的事,因為你講的任何東西,他...
»看全部
作者序
留下歷史記錄,促進族群融合
林清富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董事長
我是整理歷史的人,對於台灣首度政黨輪替的八年歷史,我有使命感與責任感要留下記錄。
二○○○年政黨輪替時,我對陳水扁總統有很高的期待。當時我不但是「扁迷」,還會帶阿扁公仔回家,原因是阿扁完成了台灣民主運動數十年來的願望,讓台灣人民與本土政權真正當家作主。
但是,我逐漸發現有些事情不太對勁。例如「總統府水餃宴」等不正常政商互動,剛開始我還認為只是傳聞、不足為信,但隨著愈來愈多傳聞獲得證實,像我一樣的「扁迷」逐漸失望心碎,心...
林清富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董事長
我是整理歷史的人,對於台灣首度政黨輪替的八年歷史,我有使命感與責任感要留下記錄。
二○○○年政黨輪替時,我對陳水扁總統有很高的期待。當時我不但是「扁迷」,還會帶阿扁公仔回家,原因是阿扁完成了台灣民主運動數十年來的願望,讓台灣人民與本土政權真正當家作主。
但是,我逐漸發現有些事情不太對勁。例如「總統府水餃宴」等不正常政商互動,剛開始我還認為只是傳聞、不足為信,但隨著愈來愈多傳聞獲得證實,像我一樣的「扁迷」逐漸失望心碎,心...
»看全部
目錄
目次
【序】留下歷史紀錄,促進族群融合/林清富
卷一 人物速寫
戰後新生代的覺醒、奮起與失落 陳永興+李筱峰/與談 杭之
陳水扁的婚姻選擇與成就追求 王浩威/與談 蔡詩萍
「國家元首的使命」(虛擬演講稿) 宋文里/與談 黃榮村+陳永興
論形式與家己:從鄭大為到陳水扁 余伯泉/與談 張德聰
「第一名症候群」:個人與群體的面向 楊照/與談 平路
卷二 現象剖析
閱讀陳水扁:一種詮釋現象學的讀法 李維倫/與談 宋文里
異化:領袖與群眾的關係 王丹/與談 黃榮村+陳永興
詮釋陳...
【序】留下歷史紀錄,促進族群融合/林清富
卷一 人物速寫
戰後新生代的覺醒、奮起與失落 陳永興+李筱峰/與談 杭之
陳水扁的婚姻選擇與成就追求 王浩威/與談 蔡詩萍
「國家元首的使命」(虛擬演講稿) 宋文里/與談 黃榮村+陳永興
論形式與家己:從鄭大為到陳水扁 余伯泉/與談 張德聰
「第一名症候群」:個人與群體的面向 楊照/與談 平路
卷二 現象剖析
閱讀陳水扁:一種詮釋現象學的讀法 李維倫/與談 宋文里
異化:領袖與群眾的關係 王丹/與談 黃榮村+陳永興
詮釋陳...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王丹、王浩威
- 出版社: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1-29 ISBN/ISSN:978986611201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00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政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