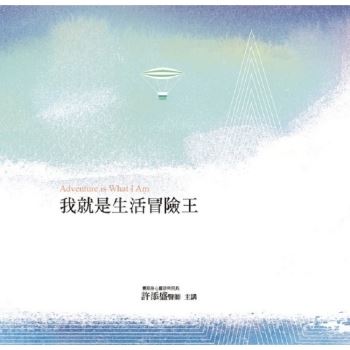推薦序
為什麼是我?
美娟說話直白,「妳知道嗎?我恨透了政大廣告系。」十年前重逢,這是她開口對我說的第一句話。
而我個性怯懦,當她邀我寫序,我不敢多問,立刻在密密麻麻的記事本裡用紅筆以星號標註了這件工作的必要與急迫,但心裡始終納悶著,如同美娟在「靈性書寫」部分劈頭就問的那個問題:「當書寫者開始反思嵌卡在種種複雜處境中的故事時,他們最常浮現的疑問往往是:『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是我?
因為我寫了《多桑與紅玫瑰》這本疑似自我書寫的媽媽故事書嗎?
說「疑似」,是因為二○○○年出書前,我從未聽聞書寫療癒、女性敘事、生命故事書寫這類字眼,但我清楚記得一九九六年媽媽過世後,從小跟著爸爸長大的我,每每因為思念她卻想不起有什麼事情可以思念而流淚,張娟芬對我說:「那妳就從眼淚開始寫吧!」因此,我展開了一段長達四年,用文字找媽媽的旅程。
這樣就是自我書寫療癒嗎?我其實不確定。但書寫的最初,我經常邊寫邊哭,隔一段時間再把稿子拿出來看,總又發現未竟之處,於是修修補補,幾個回合下來,我發現邊寫邊哭的時候少了,取而代之的,竟然是邊寫邊笑。這個歷程,完全符合小說家羅柏森.戴維思(Robertson Davis)的描述:「如果你思量生命究竟是什麼,則悲觀論是很簡便的出路。……只寫悲劇小說相當容易,但是如果論事稍微平衡一點,你就會為其中出現的喜劇、歧義與嘲諷感到驚奇。」
讀完這本書稿,我更確定當年做了一件對自己而言重要的事,就像美娟在書裡說的,「創傷是我一部分的印記,但並不是生命的一切。」但唯有透過書寫,我才得以穿越生命前期的烙印,接納自己是一個擁有獨特成長經驗所以擺盪在出門與回家之間的個體,從此安心地往中年去。
為什麼是我?
小心眼如我,也想過美娟邀序,會不會是為了平反她曾在政大廣告系所受的苦?
我的老師馬賴.撒普(Marye Tharp)曾到智利某所大學廣告系客座半年,回來後告訴我,那些四、五十歲,擔任廣告公司老闆和創意總監的人,當年幾乎個個都是共產黨,難怪南美洲的廣告經常有種憂國憂民的氣味,那樣敏銳和批判的身世,似乎更容易孕育與社會現實緊密牽連的創意養分,「不做共產黨,就做廣告人!」馬賴笑著如是說。
「不做廣告人,就做共產黨!」──反過來,好像也說得通。以美娟為例,讀大學的經驗固然不愉快,但我也看見在她生命最困頓時,那些洞察的本能、收集情報的技術可都派上了用場,而這本書寫得這麼深刻又易懂,結構、解構與文字的能力也功不可沒。
在美娟讀大學的那個年代,廣告系教的、學的以及想成為的,確實是主流菁英,但隨著經濟蕭條、產業黯淡,就業導向的學科也開始反省與左傾。我們認為,去掉為資本主義服務的立意,洞察、策略、創意與書寫這些元素仍具學習價值,而學習的源頭與盡頭,則是多樣、去中心化和具備主體性的青年文化,已過世的廣告人孫大偉曾經這麼鼓勵我:「學校應該有一個理想在裡面,應該製造革命份子,製造出來要去放火的人!」
若非奮力對抗二十八歲之前的人生,美娟也無法成為一位用書寫來放火的革命份子,所以我想呼籲所有因為某校某系而受傷的學生與老師,「不做○○○,就做X X X」吧,而尋找「X X X」的方式,就是美娟書裡說的:「如實地書寫自己的生命故事,重新擁有完整的自己。」與「當我們回首看見生命當年的轉折,便可以重新決定自己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數學方程式裡,「X」代表未知。
英國政府旗艦級創新學習計畫「創意伙伴」的負責人普爾.寇樂(Paul Collard)幾乎在每場演講中都會提到:「在未來,有百分之六十的工作,現在都尚未發明。」然而,學校裡教的,卻都還是已知,這就是政大為什麼要成立「X書院」的理由。
X書院是一個讓大學生跟「不確定」(Tsahaylu,出自電影「阿凡達」,納美語,英文為bond,係指兩個生命體培養感情並建立互信關係的過程)的實驗平台。對政大學生而言,寫字這件事相對熟悉且安全,所以X書院選擇以書寫做為和不確定互動的第一個工具,而光是書寫,就開出三個系列的工作坊:我自己帶自由書寫,資深出版人陳郁馨帶創意書寫,而美娟則負責自我書寫、家庭書寫和夢的書寫。幾年下來,不只致力於鬆動教育,也順便解放了書寫──在X書院,文字不是寫給別人看的,不是用來比賽、較勁和滿足某種特定功能的,而是用來探索、冒險、想像與穿越自我生命經驗,就像美娟書裡所說:「回顧生命,並不只是一種浪漫的情懷,它同時還是一種投石問路的行動,深刻了解自己的生命歷程,讓我們得以更清楚選擇適合自己的路。」我們深信,這樣的書寫,就是自由、有感與充滿動能朝向未來的書寫。
寫到這裡,我還是不確定為什麼是我?
但對於翻開本書讀到此處的你,多少應該明白,為什麼是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