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名稱:輕舟已過萬重山
旅居海外近三十年,李明亮說自己是「一路走來,始終不如一」:一開始他深受基礎醫學的吸引,接著轉入臨床醫療,深深領悟到培養治療人才的重要,1992年回國擔任慈濟大學創校校長,從教育再出發。2000年,他受邀入閣,擔任主導醫療政策的衛生署署長,推動了極為重要的健保IC卡、合理門診量等重大措施。2002年卸任後,他持續投入衛生外交工作,奠立台灣在歐盟國家衛生平台一席之位。後因有感台灣醫療援助廣泛卻欠缺整合,成立了台灣健康服務團,隨醫療團赴喜馬拉雅山區義診……發表的學術論文超過一、兩百篇。
李明亮不諱言用了五十年尋找自己,努力在專業領域之外,探索命運的小框框,盡情發揮生命的創造力。他如此形容自己:「我是一個平凡的知識份子,熱愛古典音樂,是一流的甜食家,二流教育家,三流的醫學家,四流的研究家,五流的行政家,六流的郵學家,其他都是九流或九流以上的。」
作者簡介
李明亮
1936年生,台南縣歸仁鄉。台南一中初中、高中部畢業後,保送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接受小兒科住院醫師訓練,1965年取得邁阿密大學生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哲學博士學位。
1969年,他以Helen Hay Whitney基金會獎學金,赴英國劍橋大學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任博士後研究員,之後再回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接受遺傳醫學次專科訓練。
1972年成為邁阿密大學內科助理教授。
1977年轉任新澤西州立醫科大學Robert Wood Johnson Medical School擔任小兒科副教授、遺傳醫學科主任,後晉升為教授。
1992年回台,擔任慈濟大學創校校長。
2000年,擔任行政院衛生署署長。
2003年,在SARS侵襲台灣期間,他擔任抗煞團隊總指揮,在短短兩個月內,帶領台灣脫離疫區威脅,教國人留下深刻印象。之後,他陸續擔任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衛生政策研發中心特聘研究員主任、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董事長、國光生技董事長等職位。
現任社團法人台灣健康服務協會理事長、台灣工業銀行顧問兼銀行波士頓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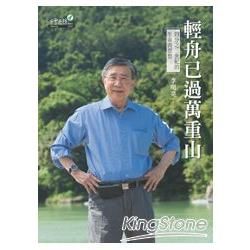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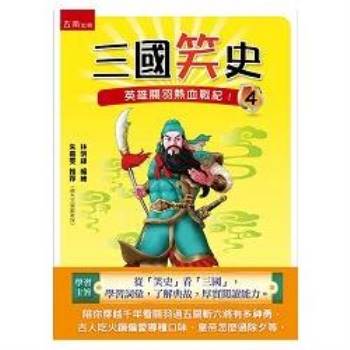







![114年台電新進雇員配電線路類超強4合1[國民營事業] 114年台電新進雇員配電線路類超強4合1[國民營事業]](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1137)

周三下午看完門診進辦公室,桌上擺著一件助理為我領回的郵件包裹,拆開一看竟是李明亮教授寄來送給我的新書,是他剛發行出版的自傳「輕舟已過萬重山:四分之三世紀的生命與思想」,當晚住在醫院值班,翻開書頁閲讀立即被精彩的內容深深吸引,急診病房產房和ICU也超配合,沒有呼叫我出任務,讓我沒被打斷地整晚在值班室裏讀完這本傳記。 我在台大當學生和住院醫師時,李教授人在美國,以致未能親炙他的教導。慈濟醫院啟用的1986那年正是我七年醫學生涯最後的實習intern,八月輪派到花蓮正值開幕義診,大量病患湧入,逼得我們這些小蘿蔔頭也上陣看診,躲開台大醫院門診阿姨的嘮叨絮念,花蓮以美景和剛畢業的護士相迎,讓我留下畢業入伍前最美好的回憶。頭一回聽到李教授的名字,是1994年成立的慈濟醫學院,院長竟是位小兒科醫師,在李教授銳意經營下,很快升格為完全大學,以蒼生為念的李教授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卓越的他頭銜眾多,日後我有幸與他結識,選擇尊稱他為校長,他也始終欣然接受。 喜歡閱讀歷史的我也讀了不少名人傳記,這些或由作家撰寫,或口述由人代筆,但校長這本自傳讀來真誠自然,筆觸常帶感情,一讀就感覺是自己親筆寫成,後來向校長求證果真其然,因此通篇讀來特別真切動人。全書共分六章,若以第三章的慈濟八年為分水嶺,前面談的是成長求學及在美奮鬥三十年的過程,李校長是個庄腳囝仔,忠厚率真卻又能據理立爭,在台大讀五年級時以先天性異常為題的報告獲主任賞識,竟從而代敎兒科遺傳學實習,從而啟動李校長畢生的基因分子生物研究,到美國及英國劍橋與諾貝爾得主同實驗室的經歷都令習醫的我讀來心生無比嚮往......。 其實我讀這本傳記,是由後半部我所認識的李校長往前讀的,相信大家會認識李明亮敎授,有可能同我一般始自他為慈濟醫學院暨大學的創校校長,或是他出任扁政府的首任衞生署署長,更多的該是他帶領台灣走過百年大疫SARS;對比於現今官員之口無遮攔荒腔走板信口雌黃,更令我感念的是2003年全台陷入SARS風暴期間,李校長每天在電視上向大家說明疫情的現況和因應方式,權威堅定而又溫馨真誠的談話安定了多少徬徨的人心,這還是他辭官後為了台灣復出義無反顧的全心投入,光這件事,李校長就足以名留史冊。 我得以有幸與校長結識,其實是拜古典音樂之賜:1998年偶然參與劉岠渭敎授的一場古典音樂導聆演講深受撼動,幾經努力終於邀請劉老師自2002年起在羅東博愛醫院舉辦定期講座,為了將這麼精闢的講解錄製傳世,更於2004年成立「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居中奔走的我成了首任的執行長,同為劉老師講座粉絲的李校長出任董事,這讓我得以近距離接觸這位孺慕已久的長者,李校長對我這個晚輩一點架子也沒有,幽默的他很喜歡開玩笑:有回我到花蓮去拜訪他,知道他久居花蓮卻從沒逛過夜市,於是帶他去吃我最愛的一心泡泡冰和美琪烤玉米,路邊攤老板像看動物般好奇地盯著李校長看,後來終於忍不住過來問說你怎麼跟電視上那個李明亮這麼像?李校長抬頭笑答:嘿,伊是阮乀阿兄啦! 李校長在自傳多次地提到古典音樂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熱情的他偏愛中年以後的貝多芬乃至於舒伯特和布拉姆斯等浪漫樂派作曲家,我有幸出現在這本自傳中,書中提到那個搜集了數十個布拉姆斯交響曲版本的瘋狂醫師就是我。熱愛台灣的他在書中寫道:「我有一個夢想:將來台灣理想國家成立,全民慶祝,我會雇一部大卡車,放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命運交響曲,大聲遊行於大街小巷,我會站在車上,車上放一個超大的大鼓,當樂曲由第三樂章進入第四樂章貝多芬那一段穿透黑暗奔向光明的鼓聲,我會用棒球棒猛擊大鼓,直到倒下為止。」這是多麼動人心弦的畫面,直令我熱血沸騰不能自己! 閲畢全書掩卷憶往,回顧自己二分之一個世紀的生命和思想,年少求學也如校長一般順遂地考進第一志願的台大醫學系,只是畢業退伍後沒出國深造,在台大小兒科受完五年住院醫師訓練後,因緣際會奉派到羅東,從此愛上宜蘭的風土人情,沒有轉換工作地當了近二十年的小鎮醫師,當然遠不如李校長的絢爛多彩。然而我真要感謝父母的基因和師長的栽培,讓我可以當上小兒科醫師每天得與天真的孩童為伍;另方面也要感謝豐富了我生命的古典音樂,讓我可與布拉姆斯等偉大作曲家心靈相通,還因此得以結識李明亮校長,這樣一位足為台灣人典範的人道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