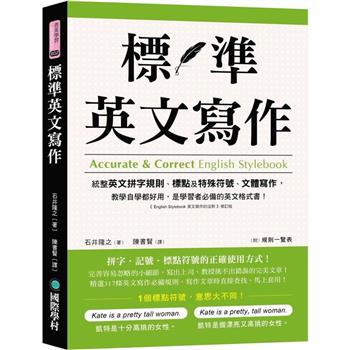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讓人讀來有笑有淚,卻又溫暖得動人心弦的絕妙佳作!
◎知名作家「是今」不但再次演繹了「江山與美人」的氣勢,更精心編織出一個令人心動神往的愛情美夢!
◎晉江原創網上,好評積分高達40,000,000分!
◎高踞三民網路書店「簡體書暢銷排行榜」前十名!
◎當當網上,讀者給予4.5顆星高評價!
初次相見,她還未及笄,羞澀的臉龐卻讓他微微心動;
朝夕相處間,她已然出落得亭亭玉立、含苞待放,
只是,她的笑顏卻不再為他綻放……
「入了七勢門,會有千兩白銀買妳的三年時光,
在這三年裡,妳要對七勢門唯命是從,妳願意嗎?」
司恬原是衣食無憂的大戶人家千金,但一個決定,卻改變了她的未來!
父、弟相繼去世,娘親又染上重病,為了尋得能治病的大夫,
司恬迫不得已,只能拜於七勢門下,以三年光陰換取千兩白銀。
本以為日子再單純不過,就是跟著師父學醫、習毒,
只是她才剛入門,大師兄商雨沒給過她好臉色不說,甚至格外刁難!
司恬默默地承受著,只當他就是看自己不順眼,
可直到娘親病重的那一日,她急得六神無主,
冷靜下來後才發現,一直靜靜陪在自己身邊照拂的,竟然還是他!
她有些感動,卻又想不明白,他對她究竟是存了什麼樣的心?
漸漸的,她越發感覺到他對她的態度丕變,
他對她不再嚴厲、難以親近,甚至於……溫柔得超出了「師兄」的身分!
然而,還未來得及釐清自己複雜的心緒,另一個「他」也闖進了她的世界──
師父竟在此刻安排她前往京城,隨侍在安慶王爺裴雲曠的身邊!
一個是和煦溫文的大師兄,一個是權勢傾天的偉岸男子,
連司恬自己也不知道,她的生命將因他們而發生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作者簡介
是今
女,雙魚座,喜歡寫小說,樂此不疲。
希望能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但基本都宅在家裡,看書喝茶加胡思亂想。
字裡行間,都是心裡的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