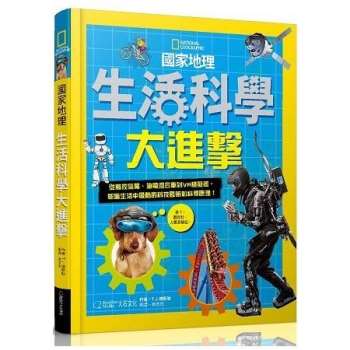老子、孔子、莊子、商鞅、司馬遷……
他們實則活潑、奸詐、或者是憤世嫉俗,
但原來他們跟我們以為的大不相同!
老子是個憤青,《道德經》可看成是變態心理學的典型材料?!
孔子始終參與著後來的歷史,只是他本人沒有到場罷了。
莊子既激情又超脫,江湖上關於他的消息籠罩在雲霧之中。
屈原獨自一人站在全世界對面,他的孤獨正是他可愛之處。
賈誼與漢文帝,賢臣與名君,卻無法相合相得,理由何在?
司馬遷是有自覺的人類學家,他以異乎尋常的方式處理筆下人物……
老子、孔子、墨子、屈原、賈誼、商鞅、董仲舒、司馬相如、司馬遷……
我們自以為很瞭解他們,但其實這些被教科書壓扁的歷史人物,跟我們原先想的大不相同!
看似嚴肅的孔子其實很可愛,偏激的老子可敬,而風流文人的司馬相如卻只是個痞子。
鮑鵬山在本書中選了19位人物,還原並活化,
以人性的角度,呈現他們真實的面貌,
重新賦予他們生命:
他們是誰?他們身處什麼樣的時代?
他們如何面對自己和時代的問題?
作者簡介
鮑鵬山
安徽六安人,現任上海電視大學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古代文化的教學與研究。
2009年登上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節目,創下收視新高。
主要著作有:《寂寞聖哲》、《論語導讀》、《論語新讀》、《說孔子》、《先秦諸子十二講》、《後生小子——諸子百家新九章》、《附庸風雅——第三隻眼看詩經》(合著)、《中國文學史品讀》、《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中國古代文學通論》(主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