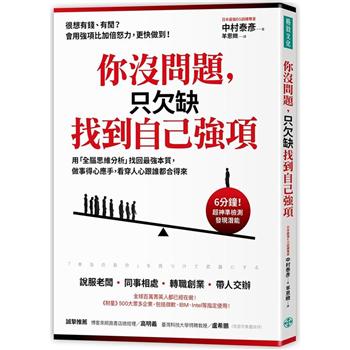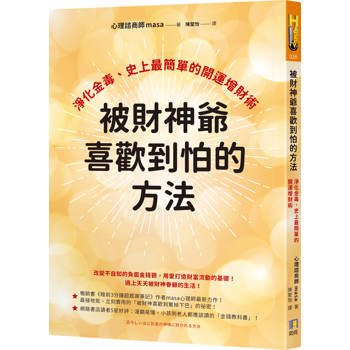序
我在思考《去殖民化的上帝》(Decolonizing God)一書中文譯本的新讀者的時候,首先,我想談論幾點關於本書廣闊的文化處境,這也許會有所幫助。
歷史學家們公正地避免將過去的世紀中興起和衰落的古代以及現代帝國普遍化,但是,也許區分從一個城市中心所施加的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週邊所施加的那種社會生活,是有益處的。聖經文學的形成受到幾個不同帝國浪潮所推動,雖然在短暫的時期內,以色列能夠表述自己的政治主權,但是,其最為基本的神學宣稱是抵擋異邦霸權,或者受到異邦霸權所影響。但是,也許因為這一抵擋的模式,通常借用帝國主義的語言和思想(無論是亞述的,巴比倫的,波斯的,希臘的或是羅馬的)。當基督教最終成為歐洲的合法宗教時,歷史帶來了一個令人好奇的諷刺:大部分是因為抵擋外邦霸權而形成了一個神聖文學,在西方文化中被轉化為允許中世紀殖民政治霸權的一個源頭。雖然在現代革命之後,中世紀基督教的權力極度衰落,但是殖民主義繼續完好存活到二十世紀。本書正是關注於基督教殖民主義的複雜遺產。
在十五世紀晚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在教皇失察的情況下,通過從北極跨越經過南美到南極的子午線的方式,建立了他們自己獨立的司法權區。背後的神學假定是這樣的,基督教教會代表創造主對整個地球的神聖主權,因此天主教的君王們可以 被看作是神的代理,無論新世界是否被「發現」。這一邏輯被很多人看作是在南美進行帝國主義統治的充足理由,雖然著名的天主教法學家如法蘭西斯科.維多利亞(Francisco de Vitoria, 1483–1546) ,反對主流意見,為印度人的原住民權利辯護。類似的例子是,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 1474–1564),即使他最初接受從中世紀的時候就流傳下來的把非洲黑人歸為奴隸的種族等級制度,他反對把正義戰爭的理論應用在南美,作為血腥屠殺和商業利益的一種面具。
在帝國主義統治集團統治下受苦的原住民,一般都會調適融入到廣泛流傳的信念,那就是基督徒,更具體地說是白人基督徒,註定要統治他們。天主教中充斥著種族等級的觀念,新教殖民主義最初稍微抵擋這些種族主義的假定。來自幾個不同國家的歐洲殖民者,認為他們自己是在一個新世界中的新以色列,設想新教國家的新版本,在繼承神對以色列的應許的同時,會超越歷史上的以色列。同樣地,在這樣的想像中,基督教殖民地可以移除原住民經驗所承載的當地的知識形態。原住民知識要不是被認為在神學上是無關的,或者就是如同九世紀早期亞洲的個案,成為「東方」(Oriental)研究的焦點,用來表明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優越性。
與西方商業、神學和哲學的自私浪潮相左,最終湧現出一些重要的自我批判的聲音。例如,一位荷蘭的國家法理論家,胡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試圖在一個自然法的世俗體系中,為原住民權利提供有限的保護。在他的基礎性著作《戰爭與和平的權利》(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1645)一書中,他指出雖然殖民擴張的藉口是更加有效地利用閒置的土地,但是聖經的先例與其他的資料,也肯定佔領的傳統權利。與此類似,艾默里奇.瓦特爾(Emmerich de Vattel)的「萬國公法」(The Law of Nations, 1758),讚揚威廉.佩恩(William Penn)於1682年在美國德拉瓦州(Delaware)的印第安人簽訂協約,作為尊重原住民權利的一個典範。佩恩的文化尊重模式,源自他的 貴格會的和平主義傳統,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詮釋聖經的方法。貴格會也在大英帝國長期反對奴隸制度的運動中廣為人知。
當奴隸制度最終在1833年於英國統治下被廢除,改革的領袖把他們批判的目光轉向英國殖民地的合法剝削原住民的一些最為明顯的例子。基督徒君王所享受的「發現的權利」(right of discovery)受到質疑。但是歷史的潮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不堪這些新道德衝動的重負。早在1823年,美國大法官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已經把傳統基督教的「發現的教義」(doctrine of discovery)世俗化,重新肯定一個基本的觀念,那就是一個開拓殖民地的國家擁有相關的土地所有權,即便佔領地的原住民權利以各樣的方式繼續存在。
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是1836-47年倫敦殖民辦公室一位有影響力的副部長,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表達了對原住民境況的愧疚,但是當後來反思這一時期,他維護殖民化的正義,反對他的批評者,理由是好的政府反駁了湯瑪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人口論》(Essay on Population, 1798)沉悶的科學(dismal science)。在他基礎性的經濟學著作中,馬爾薩斯牧師沒有指出英國帝國邊緣的「商業釋放」(commercial enfranchisement)所帶來的改變和機會。一些英國政客以不假思索的用語,單純樂觀地「剷除乞丐」(shoveling out the paupers)。十九世紀美國的基督徒經濟學家,青睞移民資本主義(settler capitalism)和自然神學,除了其他事項之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新定居的土地上,租金的負擔被從拓荒者的肩膀上卸下了。貿易的文明影響力,通常與基督教影響力交織在一起,提供在殖民過程中神聖眷佑(divine providence)的證據。「最大多數的最大的善」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可能被看作是比殖民地原住民令人愧疚的苦難更加重要。功利主義經濟學相應地強壓原住民不可剝奪的權利的人文主義的宣告。
然而,進入二十世紀初期,殖民主義的倫理和政治問題太明顯,再也不能視而不見了。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確影響重新繪製地圖和殖民司法管轄區,但是這一政治上的重構,也為本色化版本的國族主義打開了可能性。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 )對登山寶訓的詮釋,成為非暴力抵抗的一種激勵,表明聖經如何在教會內和教會外的白話神學(vernacular theology)中發揮作用。開始於1950年代和60年代的非洲與印度的反殖民抗爭,也帶來了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進行比較分析的學術興趣。反殖民史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及文學批評的新表述,一起支持國族主義事業。
在1980年代,「移民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研究在西方開始成為處在帝國強迫與本土抵抗之間中間地帶的社會現象受到調查。「後殖民主義」文學批評也嘗試勾勒在之前殖民地的模擬和文化混雜的諷刺的複雜性。愛德華.薩依德移植了這些方法論議題中的某些部分,加入聖經研究中,他指出對希伯來聖經的「迦南人的閱讀」(Canaanite reading),那麼出埃及的故事就不能被簡單解讀作為支持自由政治或者神學,因為出埃及敘事的展開,表明了一種道德盲點,因為它涉及到了佔有迦南人土地。沿著薩依德的路徑,許多學者開始挖掘聖經詮釋中可能被稱作一個「迦南人的」視角,打開了詮釋的議題,不僅是與特定的聖經經文相關,而且揭露了主導西方的注釋傳統中的偏見。
對於某些人來說,後殖民主義再現的挑戰,代表了一種不受歡迎的聖經研究的政治化,甚至愛德華.薩依德自己對學術生涯中政治身份的擴散表達了愧疚,有時候更多聚焦於特定學術議程中的代表性的聲音,而不是聚焦於因著殖民主義遺產而受苦的成千上萬的人。但是至少在原則上,可以肯定的是,後殖民研究的道德關注,與聖經倫理中的突出軌跡相吻合。如果我們可以設想以色列的律法、先知和智慧書,是倫理文學的三大重要文體,那麼,需要著重認可的是,它們都涉及到了保護邊緣者的利益的原則。邊緣者包括:寡婦、孤兒、外邦人和窮人。一個更加全面的釋經學包括邊緣者在內的「迦南人」,可能超出了一些聖經作者的原意,但是這只是期待學術興趣不應只是局限於歷史描述或者解釋。批判意識形態,從這個角度而言,有明確的聖經先例。
在古代和現代時期,政治張力和衝突的純粹複雜性,難以被輕易簡化為精英階層與弱勢群體,或者帝國主義者與本土主義者之間的簡單對比。例如,如果約翰福音的神學,包括在意識形態上排擠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這種排擠幾乎不可能是跟從耶穌的權力精英群體的行為。但是,具有諷刺性的是,當約翰福音4章描述耶穌把真正的敬拜與錫安山或者基利心山剝離的時候,這類的靈修(spirituality)很容易在大部分後來的殖民時期被移植。約翰的神學有潛力向全球發出,而不只是本土的宣告。批判約翰福音是全球化意識形態的溫床,是有爭議的。這樣的批判假定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依附於文本的,不管它們被詮釋的社會處境是如何。更有說服力的對後殖民理論的應用,關注聖經文本的複雜性,這包括了聖經文本的多種層次、諷刺和對它們的接受。這就是我在《去殖民化的上帝》一書中所嘗試採用的進路。
我特別感謝王東負責翻譯這本書的艱巨任務,很高興看到這本書可以供使用漢語的讀者閱讀。希望這一聖經詮釋的進路,可以促進讀者對聖經一個全新的理解,特別是在華人社群中,那些散居為生活而奔波的,無論是因為政治、宗教還是文化原因感覺自己像二等公民的人。毫無疑問,這一拓展的讀者也會幫助擴大後殖民聖經學術可能會處理的議題範圍 。我感謝幾位同事,在最近幾年他們嘗試教導我中華文化,特別是謝品然、曾慶豹、陳益慧、溫司卡和張纓。他們成功地教授了我很多所要學習的。
馬克.布雷特
墨爾本惠特利神學院
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