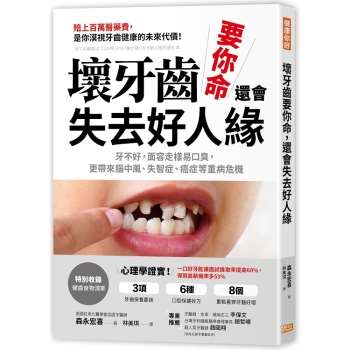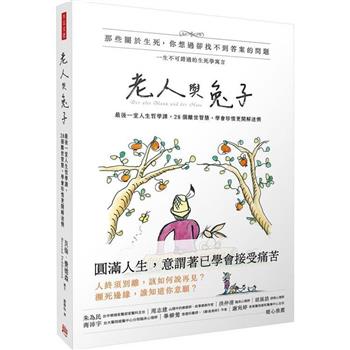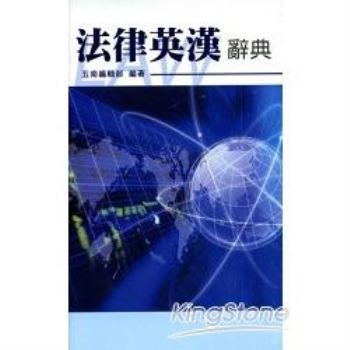本書以晚明耶穌會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c. 1566–1640)譯寫的格言集《譬學》(1633),與英國國教牧師亨利.皮坎(Henry Peacham, Sr., 1547–1634)纂輯的文藝復興修辭格手冊《說苑》(The Garden of Eloquence, 1593)為平行研究標的文本,而以列日學派(Groupe µ)的《普通修辭學》(Rhétorique générale, 1971)及佩雷爾曼(Chaïm Perelman, 1912–1984)的《新修辭學》(Traité de l’argumentation: La nouvelle rhétorique, 1958)兩本歐陸新修辭學專著為分析的準據。
高一志在《譬學.自引》中嘗論譬法十種,其論述的主軸是一則譬喻中的兩端現象──即譬喻中「已明的所取之端」與「未明的所求之端」間,「如何」能達到合胡越而成肝膽的修辭勸說效果,進一步實踐說教與證道的宗教功能。而列日學派提出普通修辭理論的本意,是欲藉現代結構語言學的分析模式,提供更為科學而具系統性的辭格分類方法。因此本書之論旨有二:其一,以皮坎《說苑》中的文藝復興修辭格分類系統,比對高氏《譬學》中各式設譬手法;其二,以列日學派提出的修辭操作模式──抑損、增添、增損、更序──分別重新檢視《譬學》與《說苑》中的語形(metaplasms)、語義(metasememes)、語法(metataxes)、邏輯(metalogisms)四種修辭格,並以佩雷爾曼所謂「論辯」(argumentation),解讀無法歸類於列日學派修辭理論中的其餘辭格。於此架構之下,本書分為五章進行析論:
第一章 本章首先爬梳兩部標的文本與文藝復興修辭學傳統間的關連,並藉由對西方修辭學史的討論,建立本書並時性研究的歷史實證性。其次,高一志在《譬學.自引》中的論述主軸是一則譬喻中的兩端現象,而一則譬喻中的「所取之端」與「所求之端」間,「如何」能達到合胡越而成肝膽的修辭勸說效果,則成為本書申論的起點。本章最後將引導修辭問題至更為深入的結構語言及符號層面,即「為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
第二章 本章以語義辭格的分析為出發點,討論上述「為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的修辭設譬問題。語義辭格討論的是字詞(或小於字詞的單位)與內容意義間的關聯,四種主要轉義俱屬此類。若按《譬學.自引》中所謂「由顯推隱,以所已曉,測所未曉」的設譬原則著眼,則本書欲解答的「為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問題,應由兩個語彙單位(lexeme)間如何形成表達形式的轉換著手;易言之,這也是語言符號中符表(signifiant)與符旨(signifié)的形式與內容問題。
第三章 《譬學.自引》所析「明、隱、直、曲、單、重」六種譬法,都屬於語義辭格的探討範圍,而以重譬為界,之後的「有解、無解、對而相反、無對而疊合為一」四種譬法,除了仍依高氏所謂「兩端相類相稱」的基本法則施譬之外,已經由單純的「轉義」(trope)進入「句式」(schemate)的解析而成為另一個譬法討論範疇,本書也由此進入語法辭格的分析。本章由《普通修辭學》中零度及偏離的理論為始,分別析論《譬學》與《說苑》中語法辭格的四種修辭操作。
第四章 前文已析的語形、語義、語法三種辭格,乃基於語規(code)而成,建立在「文法↔修辭」的關係之上,而本章討論的邏輯辭格則基於符物(object)與符解(interpretant)間的聯結,建立在「修辭↔邏輯」的關係之上。《說苑》中仍有相當數量的辭格無法納入列日學派的辭格總表,而這類辭格在譬法與句式的背後,往往還涉及價值判斷──比方格言背後欲傳達的宗教意蘊。本章藉由佩氏《新修辭學》中的論辯及非形式邏輯理論,補充《普通修辭學》無法解讀的其餘辭格。
第五章 引發佩雷爾曼《新修辭學》理論的關鍵問題是「價值判斷能否通過推理加以證明」,佩氏的這則提問亦為本書關懷所繫,即宗教上的價值判斷能否藉修辭的操作而致正面的效果?譬法與句式的運用不僅只是表面的修辭現象,其背後牽涉的是在四個修辭場之外以勸服為目標的論辯。本書最後提出對列日學派普通修辭理論的檢討,也在修辭、論辯與證道三者間覓得關聯,而重新看待本書發軔的可見與不可見兩端。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修辭.符號.宗教格言:耶穌會士高一志《譬學》研究的圖書 |
 |
修辭.符號.宗教格言:耶穌會士高一志《譬學》研究 作者:林熙強 出版社:橄欖 出版日期:2015-11-13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528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74 |
文學作品 |
$ 540 |
其他 |
$ 540 |
神學/教義 |
$ 540 |
小說/文學 |
$ 540 |
宗教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修辭.符號.宗教格言:耶穌會士高一志《譬學》研究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林熙強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曾任中國文化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於該校英國語文學系及語文教學中心講授英美文學及語言課程(2005–2015)。碩士時期主修英美文學,以戲劇與詩作為主,對西方文學理論興趣尤深。博士時期從事比較文學研究,接觸明清之際的耶穌會士中文譯著,進而對宗教與文學的關係產生興趣。博士論文運用二十世紀歐陸新修辭學理論以及符號學,解析晚明耶穌會士的宗教格言譯作。博士後時期則特別專注於十六世紀末耶穌會士東邁來華之後,譯介的西方古典迄文藝復興時期的各類哲思,其間並擔任四卷《晚明天主教翻譯文學箋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4)主編之一。
林熙強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曾任中國文化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於該校英國語文學系及語文教學中心講授英美文學及語言課程(2005–2015)。碩士時期主修英美文學,以戲劇與詩作為主,對西方文學理論興趣尤深。博士時期從事比較文學研究,接觸明清之際的耶穌會士中文譯著,進而對宗教與文學的關係產生興趣。博士論文運用二十世紀歐陸新修辭學理論以及符號學,解析晚明耶穌會士的宗教格言譯作。博士後時期則特別專注於十六世紀末耶穌會士東邁來華之後,譯介的西方古典迄文藝復興時期的各類哲思,其間並擔任四卷《晚明天主教翻譯文學箋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4)主編之一。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從可見到不可見
第一節 東來會士高一志與《譬學》
第二節 文法、修辭、邏輯:西方修辭學史的回顧
第三節 英國國教牧師亨利‧皮坎與《說苑》
第四節 問題緣起 可見與不可見的兩端
第二章 《譬學》語義辭格分析
第一節 《普通修辭學》的基礎理論
第二節 表達形式的轉換
第三節 分解
第四節 兩個語彙單位的關係:提喻
第五節 隱喻:三個語彙單位的關係
第六節 四個語彙單位的關係:《譬學》
第七節 小結:從譬法到句式
第三章 《譬學》與《說苑》語法辭格分析
第一節 從語言學到修辭學
第二節 零度
第三節 偏離
第四節 《譬學》與《說苑》的語法抑損操作
第五節 《譬學》與《說苑》的語法增添操作
第六節 《譬學》與《說苑》的語法增損操作
第七節 《譬學》與《說苑》的語法更序操作
第八節 小結:句式的背後
第四章 《譬學》與《說苑》邏輯辭格分析
第一節 從語義辭格到邏輯辭格
第二節 語義辭格與邏輯辭格關係再探
第三節 邏輯辭格的修辭操作之一:抑損、增添、更序
第四節 邏輯辭格的修辭操作之二:增損
第五節 辭格之外
第六節 情感現象
第七節 《譬學》與《說苑》中的論辯
第八節 小結:辭格與價值判斷
第五章 結論—修辭的藝術與證道的藝術
第一節 對《普通修辭學》理論的檢討
第二節 修辭、論辯與證道
第三節 再看可見與不可見的兩端
徵引書目
附錄
附錄一 大秦塔考察照片
附錄一 《譬學‧上卷》
(含《譬學‧序》與《譬學‧自引》)
附錄二 《譬學‧下卷》
附錄三 《說苑》1577年初版辭格分類列表
附錄四 《說苑》1593年再版辭格分類列表
附錄五 《說苑》1577年初版獻辭
附錄六 《說苑》1593年再版獻辭
第一章 緒論 從可見到不可見
第一節 東來會士高一志與《譬學》
第二節 文法、修辭、邏輯:西方修辭學史的回顧
第三節 英國國教牧師亨利‧皮坎與《說苑》
第四節 問題緣起 可見與不可見的兩端
第二章 《譬學》語義辭格分析
第一節 《普通修辭學》的基礎理論
第二節 表達形式的轉換
第三節 分解
第四節 兩個語彙單位的關係:提喻
第五節 隱喻:三個語彙單位的關係
第六節 四個語彙單位的關係:《譬學》
第七節 小結:從譬法到句式
第三章 《譬學》與《說苑》語法辭格分析
第一節 從語言學到修辭學
第二節 零度
第三節 偏離
第四節 《譬學》與《說苑》的語法抑損操作
第五節 《譬學》與《說苑》的語法增添操作
第六節 《譬學》與《說苑》的語法增損操作
第七節 《譬學》與《說苑》的語法更序操作
第八節 小結:句式的背後
第四章 《譬學》與《說苑》邏輯辭格分析
第一節 從語義辭格到邏輯辭格
第二節 語義辭格與邏輯辭格關係再探
第三節 邏輯辭格的修辭操作之一:抑損、增添、更序
第四節 邏輯辭格的修辭操作之二:增損
第五節 辭格之外
第六節 情感現象
第七節 《譬學》與《說苑》中的論辯
第八節 小結:辭格與價值判斷
第五章 結論—修辭的藝術與證道的藝術
第一節 對《普通修辭學》理論的檢討
第二節 修辭、論辯與證道
第三節 再看可見與不可見的兩端
徵引書目
附錄
附錄一 大秦塔考察照片
附錄一 《譬學‧上卷》
(含《譬學‧序》與《譬學‧自引》)
附錄二 《譬學‧下卷》
附錄三 《說苑》1577年初版辭格分類列表
附錄四 《說苑》1593年再版辭格分類列表
附錄五 《說苑》1577年初版獻辭
附錄六 《說苑》1593年再版獻辭
序
自序
十五世紀中葉,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c. 1398–1468)發明活字印刷術,於今日德國美因茲(Mainz) 刊印了武加大本四十二行聖經,史稱《古騰堡聖經》(c. 1453–1455),隨後活字印刷技術開始在歐洲廣為流傳。當時人文主義思潮風行的義大利,也因此興起一股將古典文本以印刷方式出版的風潮,不少希臘羅馬典籍的第一個印刷版本(editiones principes),都在此際面世。1469 年,《金驢記》(Metamorphoses) 作者阿普列尤斯(Lucius Apuleius Madaurensis, c. 124–c. 170) 著作集的活字印刷版本發行,時任法國阿萊里亞(Aléria) 主教的義大利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學者卜希(Giovanni Andrea Bussi, 1417–1475) 為之作序。卜希除榮膺聖職之外,在當時方興未艾的出版業裡亦頗負編名,宗教上的文獻集成如聖熱落尼莫(St. Jerome [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 c. 347–420)的《書簡集》等,古典文學作品如老蒲林尼(Pliny the Elder [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所著《博物誌》(Naturalis Historia) 等的第一個活字印刷版本,俱出自他的編訂。在阿普列尤斯著作集的編序中,卜希創造了“media tempestas/middle season” 一詞—即今人所稱的「中世紀」或「中古」,以之區分西方古典與他所處的現代—即今人所定義的「文藝復興」時期。
稍晚於卜希的編序,人文主義史學家布魯尼(LeonardoBruni of Arezzo, 1370–1444) 所著拉丁文《佛羅倫斯人民史》(Historiae Florentini populi, 1442),在威尼斯以義文刊行了第一個印刷版本(Historia Florentina, 1476)。撇開布魯尼歷史書寫的視角不談,這十二卷史冊之所以常被冠以第一部現代史書的頭銜,因布氏之作乃西方首部以「古典‧中世紀‧現代」的三分法為主軸的史牒。而幾乎在布氏寫就《佛羅倫斯人民史》的同時,另一位義大利史學家比翁多(Flavio Biondo of Rome, 1392–1463)寫成三十二卷本《羅馬帝國衰亡史》(Historiarum abinclinatione Romanorum imperii decades, 1439–1453),也使用了「古典‧中世紀‧現代」的三段架構,於《佛羅倫斯人民史》之後亦刊布了印刷版本(1483),其中則以media aetas/middleage—亦即今人所稱的「中世紀」—區分西方上古與其所處的時代,並將西羅馬帝國的覆亡(476) 定義為中世紀的開始。雖然史稱人文主義之父的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早已使用tenebrae/darkness 一詞—即黑暗時代—指稱四世紀基督信仰在羅馬帝國合法化後直至佩氏所處文藝復興萌芽間漫長的近千年,但當史家追溯「古典‧中世紀‧現代」的三段架構,莫不將源頭指向上述幾部古騰堡印刷術開始普及之後的拉丁文著作。及至德國史學家凱勒(Christoph Cellarius, 1638–1707) 完成三部《世界史》(Historia tripartia, 1683–1702),並將東羅馬帝國的覆亡(1453) 定義為中世紀的結束,當時西方歷史分期的三段式架構,便於焉底定。這種三段式歷史架構的影響深遠,幾乎遍及各類人文領域學科史書的分期,宗教史的書寫如此,文學史亦然,而這樣的分段方式當然也延伸到修辭學史的分期。
二十世紀初期,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的符號理論與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的《普通語言學》(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6) 理論,為修辭學研究開啟了結構語言分析的路線。前者的符號理論影響了美國新修辭學派學者如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1979) 的語義研究(見本書第二章第一節),後者對於語言符號的論述則又影響布拉格學派巨擘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 的語言學研究以及其對喻況語言(figurative language)的擘肌分理(見本書第三章第一節、第四章第六節),也引發解構主義學者如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 在〈符號學與修辭學〉(“Semiology and Rhetoric,” 1979) 一文中提出的「語法的修辭化」(rhetorization of grammar) 與「修辭的語法化」(grammatization of rhetoric)等討論。然在此之前,對於西方修辭學史的爬梳亦大多以前述的三段分期,聚焦在古典修辭學(詳參本書第一章第二節第一部分)、中世紀修辭學、文藝復興修辭學(詳參本書第一章第二節第二部分)這三個主要時期,以及其各自強調的修辭功能。而這類研究西方修辭學史的專著,又多將聖奧斯定(St.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論天主教義》(De doctrina Christiana, libri I–III, c. 397; liber IV, c. 426),視為幾乎唯一可以定義「中世紀修辭學」的標誌—原因在於聖奧斯定為古典修辭學中的「題材」(inventio/invention) 開啟了全新的方向(或可稱之為轉向),即對《聖經》的詮釋—雖然奧斯定本不希望這本書成為討論修辭學的專著(IV.i.1–2)。這樣的轉向不僅承接古典修辭學的宗旨,開啟修辭為傳教服務的路線,更隱然具備文藝復興修辭學說著重使用「喻況語言」的特徵。
在《論天主教義》裡不難發現古典修辭學之遺緒,特別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 BC) 發揚自古希臘修辭學的幾種論述(詳參本書第一章第二節第一部分),如傅為西氏所著《致賀仁寧論修辭書》(Rhetorica ad Herennium) 中繼承自竇法德(Theophrastus, c. 371–c. 287 BC) 佚篇《論文體》(OnStyle) 中的三體之說,以及繼承自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BC)《修辭術》(Art of Rhetoric) 所析「說服」中的演說者性格(ἔθος/ethos)、聽眾情緒(πάθος/pathos)、邏輯論證(λόγος/logos),也包含西氏於《布魯圖》(Brutus, xlix.185) 中引申的演說者三種職責,即教人(docere/to teach)、悅人(delectare/toplease)、感人(movere/to move)。這些主題乃奧斯定《論天主教義》關懷所繫,即「說教者如何勸服那些知道該怎麼做,卻不付諸行動的人」(IV.xii.28)。然而其中還與本書主題有所相關者,乃奧斯定所討論(語言)符號的本義與多樣性(I.i.2;II.i.1–2)、辯證法(dialectic) 的運用(II.xxxi & xxxvii),以及《聖經》中的比喻(II.xvi.23–24; III.v.9) 和《聖經》段落因為喻況語言而衍生的可能詮釋(II.vi.7–8)。後者誠大哉問,直到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c. 1225–74) 所著《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 c. 1265–74) 中仍見搉論(見本書第二章第四節及注13)。
奧斯定以古典修辭學的原則戙維,但他也另闢疇人之蹊徑。按奧斯定之見,《聖經》裡較淺顯的段落,可以滿足信眾的飢渴,而晦澀難懂的章句卻能刺激食慾,使人遺倦。而奧斯定所謂的「晦澀」,即是無法從字面得知本義而必須推敲其背後隱含意義的章句,易言之,即使用「喻況語言」的段落。那麼為何這樣的「晦澀」能使人遺倦?按奧斯定的解釋,經由探求而來的事物,往往帶給人更多喜悅,運用「辭格」(figure) 傳達的知識,更能達到「娛人」的效果(II.vi.8)。更精確地說,此處奧斯定所謂「辭格」,其原文乃“similitudo”,即修辭上的「類比」。而這也正是本書標的文本《譬學》(1633) 中,耶穌會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c. 1566–1640) 設譬心法所宗。對於辭格在《聖經》裡的運用,《論天主教義》其他章節仍見端倪。奧斯定援《新約‧羅馬書》為例:「我們連在磨難中也歡躍,因為我們知道:磨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望德,望德不叫人蒙羞,因為天主的愛,藉著所賜與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 羅5: 3–5) 這段經文裡,奧斯定以為由磨難(tribulatio) 而至望德(spes) 的推展,實遵循了修辭的規則,乃「字詞間及概念間相互依賴的關係」,這種關係如同階梯遞進,而這種「遞進」(見本書第三章所析語法辭格的增添操作)辭格在修辭上便以希臘文“κλῖμαξ/climax” 或拉丁文“gradatio” 稱之(IV.vii.11)。奧斯定當然還列舉了《聖經》中的其他例子,說明比喻的運用及句段的優美組合,而這兩種技巧,實際上正分屬日後文藝復興修辭學家強調的辭格兩大領域:「轉義∕譬法」(trope)與「句式」(schemate),也是本書修辭格分析的兩大主軸:語義詞格及語法辭格。奧斯定取《聖經》段落為例說明修辭手段,這樣的論述模式也繼續在中世紀的歐洲發展。如本篤會士聖畢德(Saint Bede, c. 672–735) 所著《句式與譬法全書》(Liber de schematibus et tropis, c. 691–703),乃盎格魯撒克遜英格蘭的第一本修辭學專著,其中便以一百二十二條《聖經》段落,說明二十八種轉義法與十七種句式。文藝復興時期的修辭學專著,泰半仍以拉丁文書寫,直到文藝復興晚期,歐洲的中古王權逐漸從封建發展為現代國家的雛型,因此開始出現以各地本土語言書寫的修辭學專書(見本書表1.1),尤以英格蘭為最。漫長的中世紀過去,然而如奧斯定與畢德這樣自《聖經》取材討論辭格的傳統,並未隨著英格蘭教會脫離天主教廷而流逝,反而可見之於如英國國教伍斯特主教(Bishop of Worcester) 普里鐸(John Prideaux, 1578–1650)《神聖雄辯術》(Sacred Eloquence: Or, the Art of Rhetorick, As It Is Layd Down in Scripture, 1659) 這樣的專書。這也正是本書第二部標的文本,即英國國教牧師皮坎(Henry Peacham, Sr., 1547–1634) 所著《說苑》(The Garden of Eloquence, 1577, 1593) 的時空背景。
十年前此時,我進入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班。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先後有兩門學科,除最令我著迷外,也奠定我未來的研究方向,對我的影響至為深遠:其一是符號學,其二是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研究。帶領我進入西學東漸研究(這裡指的是明清耶穌會士的譯著)的啟蒙關鍵,是2007 年修習了李奭學教授講授的「中國早期基督教文學:唐迄清末」課程;這門課程從唐朝景教文獻《志玄安樂經》與《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開始講述,一路延續到晚清幾部基督教翻譯小說。但課程的中心還是著重於幾位明末「第一代」來華耶穌會士的譯著,如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交友論》(1595)、《西琴曲意》(1601)、《二十五言》(1604),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1565–1654)《聖若撒法始末》(1602),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況義》(1625),高一志《聖母行實》(1631)、《譬學》、《達道紀言》(1636),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天主降生言行記略》(1635)、《聖夢歌》(1637),衛匡國(MartinoMartini, 1614–1661)《逑友篇》(1647) 等。而其中我最感興趣,也持續研究至今未歇的譯著,是高一志有關文藝復興修辭學的專著《譬學》。
早先於2006 年博士班修業期間,我在臺灣大學從恩師張漢良教授研讀符號學,受益匪淺之外,也開啟我在研究方法上全新的視野。因此在「中國早期基督教文學:唐迄清末」課程期末,我便運用所學的符號學理論,完成〈可見與不可見:淺析高一志《譬學》中的符號學方法〉研究論文,並於2008 年在「杭州海外漢學與中外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宣讀。這是我首次結合現代符號學理論與耶穌會傳教士譯介的文藝復興修辭學理論,論文內容的初步嘗試,乃以「符徵∕符表」(signifiant)與「符旨∕符意」(signifié) 間的「指號過程」(semiosis) 為出發點,探討高一志在《譬學‧自引》中析論的譬喻兩端現象。因此這也可說是我就「文法←→ 修辭」的關係,在天主教文學(特別是智言文學)的初探。
隨後我受到李奭學教授〈「著書多格言」──論高一志《譬學》及其中西修辭學傳統的關係〉與許理和(Erik Zürcher, 1928–2008)〈文藝復興修辭學在晚明中國:高一志的《譬學‧自引》〉二文啟發,在2008–2009 年間申請了兩次以《譬學》為主題的獨立研究,並敦請張漢良教授擔任指導人。其間除釐清其與西方由古典而至文藝復興修辭學間的關係外,張漢良教授亦誘掖誨導我就譬喻的結構本質與其在論辯上的功能深入探討。2009 年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之後,我便以高一志《譬學》與亨利‧皮坎的文藝復興修辭格專著《說苑》為平行研究標的文本,輔以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歐陸新修辭學學說──日學派(Groupe μ) 所著《普通修辭學》(Rhétorique générale, 1971)及佩雷爾曼(Chaïm Perelman, 1912–84)所著《新修辭學》(Traitede l’argumentation: La nouvelle rhétorique, 1958)──做為理論分析依據,撰寫我的博士論文:《高一志〈譬學〉與亨利‧皮坎〈說苑〉平行研究──修辭與符號》。
這本論文是我在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研究、修辭學與符號學等領域研究的總和,或許也是相關研究領域中,首先以符號學方法對晚明耶穌會士修辭學譯著進行結構分析的專著,也是拙著《修辭‧符號‧宗教格言──耶穌會士高一志〈譬學〉研究》(2015) 的原型。而論文口試最後獲得的成績,至今仍為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由於這本論文的研究橫跨文藝復興修辭學的「譬法」與「句式」兩個辭格範疇,若就新修辭學的眼光觀之,則又以現代結構語言學的分析方法探討語義場(semic field)、句法場(syntactic field) 與邏輯場(logical field) 的修辭功能。職是之故,這部論文將我對耶穌會譯介的西方修辭理論研究,從「文法←→ 修辭」關係的討論,進入更深層次的「修辭←→ 邏輯」關係爬梳。修辭勸服(rhetorical persuasion) 中的「論辯」一直是我感興趣的主題,當然這也正是「修辭←→ 邏輯」的問題;而從這裡,我的研究興趣延伸到宗教上的論辯與天主教教義,比方阿奎那推論天主存在時所用的「五路論證」(Quinque viae) 類比,以及在宗教修辭中呈現的非形式邏輯(non-formal logic)。這也引導我在宗教與文學關係領域的研究,進入下一個階段。
回顧博士學位口試宣布成績的那一刻,擔任主席的楊承淑所長,代表六位口試委員向我說明這個創紀錄高分的意義。委員們以兩項任務深相期許:其一是希望我不可弭忘對於《譬學》翻譯祖本的探尋,因為唯有找出這個源頭,才能真正理解《譬學》譯入中文的過程,據此方能檢視高一志的翻譯策略與修辭操作,使個人的研究更臻完善。其二是希望我假以時日能夠將這本論文出版,做為個人求學與研究的里程碑。恩師與諸位委員的孜孜策勵,至今言猶在耳,我未敢或忘,而這兩項期許我也逐一完成。
2011 年我進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學者,李奭學教授擔任我的指導人,帶領我主編《晚明天主教翻譯文學箋注》。而我對《譬學》的研究也一路延續,因為學界雖知《譬學》乃是翻譯,但歷來對其歐語祖本與其中譬式原型並無定論,故當時我的博士後研究計畫主題是〈明末耶穌會格言傳統溯源—高一志《譬學》格言翻譯的可能取材初探〉,希望能追本溯源,推敲高一志在《譬學‧自引》中所謂「吾土古賢譬語」的真實身分,也藉此完成博士學位口試時委員們對我的期許。其間我首先修潤博士論文中對於宗教譬喻的語義場研究章節,完成了〈格言‧修辭‧證道──高一志《譬學》語義辭格分析〉一文,並在2012 年於南京師範大學舉行的「IASS第十一屆世界符號學大會」上宣讀,這篇論文最後也在《漢學研究》發表(2013)。而《譬學》譯源的追溯工作上,我也有進展︰我首先歸納了十三條《譬學》中格言例句與老蒲林尼《博物誌》間的關係,在《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的「中國翻譯史專輯」(2012) 發表了〈高一志《譬學》中例句之譯源初溯:從老蒲林尼《博物誌》探起〉一文。2012 年末,我的研究又見斬獲,從新近的研究資料裡,我得知《譬學》與北方文藝復興時期重要人文主義神學家伊拉斯瑪士(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 編撰的格言集子《譬喻集》(Parabolae sive similia, 1514) 與《格言集》(Adagia, or Adagiorum chiliades, 1508) 間頗有關聯後,便著手改寫〈高一志《譬學》譯源初溯〉,重新就《譬學》與《譬喻集》間的因緣探討,在中國文哲研究所宣讀了〈高一志《譬學》譯源再溯:從翻譯到論辯的形成〉。
過去四年,由於擔任《晚明天主教翻譯文學箋注》(2014)主編之一,我有機會在西方古典文叢中參互考尋,因此對於希臘羅馬的古典作家與作品,更有脈絡及內容上的認識。而這些西方古典文本,也正是耶穌會士翻譯的取材來源之一。回顧天主教中國傳教史,萬曆三十八年利瑪竇榮歸主懷,龍華民繼任中國教區會長,並於萬曆四十年(1612) 命金尼閣返歐向教宗及耶穌會總會長報告教務。金尼閣在歐洲廣事募書,萬曆四十八年(1620) 金尼閣再返中國,運抵的這批書籍共有七千餘部。這七千餘部書籍中,很可能也包含了這些西方古典文學與哲學作品,比方亞里士多德與普魯塔克(Plutarch, c. 46–120) 等人,當然也很可能囊括文藝復興時期的天主教人文主義(Christian Humanism) 作品,例如前及伊拉斯瑪士的《譬喻集》和《格言集》。尤為重要者,乃這些西方由古典而至文藝復興的思想背後所形成的龐大知識庫(repertoire),實乃會士布道或論著中修辭勸服的主要取材來源。基於上述工作與《譬學》的研究積累,我從伊拉斯瑪士的《譬喻集》中,考出《譬學》六百條格言近三分之一的翻譯原型,並將之悉數箋釋於《晚明天主教翻譯文學箋注》中。而其餘仍未考得原型的格言,我現另繼續往伊氏《格言集》中賾探隱索。至此,我算是完成了2010 年口試委員們對我的第一項期許。而將博士論文補充改寫,以《修辭‧符號‧宗教格言—耶穌會士高一志〈譬學〉研究》之名忝錄於「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歷史文化叢書」,則讓我得以進稟第二項期許告成。
從取得博士學位到拙著得以梓行,我何其有幸,一路上獲得諸多支持與鼓勵。回首春風,恩師張漢良與李奭學二位教授,對我在智識上的啟牖最深,攻讀博士時期對符號學、修辭學、宗教與文學關係的興趣,以及拙著的研究內容,俱出自我在二位教授的課堂所學。李奭學教授在我博士後階段的栽培與支持,毫無保留提供我研究環境與資源,我銘感在心外,也期勉自己朝著研究目標繼續前行。承蒙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主持人吳昶興教授的賞識,促使拙著得以出版,利瑪竇《交友論》裡那句「德志相似,其友始固」,吳教授契誼篤厚,正是利譯最佳寫照。歷史與文化叢書的編輯陳慧娜女士,常忍受我延誤稿期,在生產期間仍盡心替我處理編務,我特於此致謝也致歉。
我用全部的心意謝謝父親母親,在我工作冗忙之際,從不因我未能克盡人子應盡之孝苛責,反而鼓勵我在研究的冒險旅程中恣意探索各種可能。在這篇長序的最後,我要將這本書獻給我的父親母親。朝乾夕惕,我期許自己能有所為,並非希望成就什麼,只是希望不辜負他們以我為榮的心。
長樂林熙強
乙未蒲月謹誌於南港
十五世紀中葉,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c. 1398–1468)發明活字印刷術,於今日德國美因茲(Mainz) 刊印了武加大本四十二行聖經,史稱《古騰堡聖經》(c. 1453–1455),隨後活字印刷技術開始在歐洲廣為流傳。當時人文主義思潮風行的義大利,也因此興起一股將古典文本以印刷方式出版的風潮,不少希臘羅馬典籍的第一個印刷版本(editiones principes),都在此際面世。1469 年,《金驢記》(Metamorphoses) 作者阿普列尤斯(Lucius Apuleius Madaurensis, c. 124–c. 170) 著作集的活字印刷版本發行,時任法國阿萊里亞(Aléria) 主教的義大利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學者卜希(Giovanni Andrea Bussi, 1417–1475) 為之作序。卜希除榮膺聖職之外,在當時方興未艾的出版業裡亦頗負編名,宗教上的文獻集成如聖熱落尼莫(St. Jerome [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 c. 347–420)的《書簡集》等,古典文學作品如老蒲林尼(Pliny the Elder [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所著《博物誌》(Naturalis Historia) 等的第一個活字印刷版本,俱出自他的編訂。在阿普列尤斯著作集的編序中,卜希創造了“media tempestas/middle season” 一詞—即今人所稱的「中世紀」或「中古」,以之區分西方古典與他所處的現代—即今人所定義的「文藝復興」時期。
稍晚於卜希的編序,人文主義史學家布魯尼(LeonardoBruni of Arezzo, 1370–1444) 所著拉丁文《佛羅倫斯人民史》(Historiae Florentini populi, 1442),在威尼斯以義文刊行了第一個印刷版本(Historia Florentina, 1476)。撇開布魯尼歷史書寫的視角不談,這十二卷史冊之所以常被冠以第一部現代史書的頭銜,因布氏之作乃西方首部以「古典‧中世紀‧現代」的三分法為主軸的史牒。而幾乎在布氏寫就《佛羅倫斯人民史》的同時,另一位義大利史學家比翁多(Flavio Biondo of Rome, 1392–1463)寫成三十二卷本《羅馬帝國衰亡史》(Historiarum abinclinatione Romanorum imperii decades, 1439–1453),也使用了「古典‧中世紀‧現代」的三段架構,於《佛羅倫斯人民史》之後亦刊布了印刷版本(1483),其中則以media aetas/middleage—亦即今人所稱的「中世紀」—區分西方上古與其所處的時代,並將西羅馬帝國的覆亡(476) 定義為中世紀的開始。雖然史稱人文主義之父的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早已使用tenebrae/darkness 一詞—即黑暗時代—指稱四世紀基督信仰在羅馬帝國合法化後直至佩氏所處文藝復興萌芽間漫長的近千年,但當史家追溯「古典‧中世紀‧現代」的三段架構,莫不將源頭指向上述幾部古騰堡印刷術開始普及之後的拉丁文著作。及至德國史學家凱勒(Christoph Cellarius, 1638–1707) 完成三部《世界史》(Historia tripartia, 1683–1702),並將東羅馬帝國的覆亡(1453) 定義為中世紀的結束,當時西方歷史分期的三段式架構,便於焉底定。這種三段式歷史架構的影響深遠,幾乎遍及各類人文領域學科史書的分期,宗教史的書寫如此,文學史亦然,而這樣的分段方式當然也延伸到修辭學史的分期。
二十世紀初期,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的符號理論與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的《普通語言學》(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6) 理論,為修辭學研究開啟了結構語言分析的路線。前者的符號理論影響了美國新修辭學派學者如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1979) 的語義研究(見本書第二章第一節),後者對於語言符號的論述則又影響布拉格學派巨擘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 的語言學研究以及其對喻況語言(figurative language)的擘肌分理(見本書第三章第一節、第四章第六節),也引發解構主義學者如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 在〈符號學與修辭學〉(“Semiology and Rhetoric,” 1979) 一文中提出的「語法的修辭化」(rhetorization of grammar) 與「修辭的語法化」(grammatization of rhetoric)等討論。然在此之前,對於西方修辭學史的爬梳亦大多以前述的三段分期,聚焦在古典修辭學(詳參本書第一章第二節第一部分)、中世紀修辭學、文藝復興修辭學(詳參本書第一章第二節第二部分)這三個主要時期,以及其各自強調的修辭功能。而這類研究西方修辭學史的專著,又多將聖奧斯定(St.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論天主教義》(De doctrina Christiana, libri I–III, c. 397; liber IV, c. 426),視為幾乎唯一可以定義「中世紀修辭學」的標誌—原因在於聖奧斯定為古典修辭學中的「題材」(inventio/invention) 開啟了全新的方向(或可稱之為轉向),即對《聖經》的詮釋—雖然奧斯定本不希望這本書成為討論修辭學的專著(IV.i.1–2)。這樣的轉向不僅承接古典修辭學的宗旨,開啟修辭為傳教服務的路線,更隱然具備文藝復興修辭學說著重使用「喻況語言」的特徵。
在《論天主教義》裡不難發現古典修辭學之遺緒,特別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 BC) 發揚自古希臘修辭學的幾種論述(詳參本書第一章第二節第一部分),如傅為西氏所著《致賀仁寧論修辭書》(Rhetorica ad Herennium) 中繼承自竇法德(Theophrastus, c. 371–c. 287 BC) 佚篇《論文體》(OnStyle) 中的三體之說,以及繼承自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BC)《修辭術》(Art of Rhetoric) 所析「說服」中的演說者性格(ἔθος/ethos)、聽眾情緒(πάθος/pathos)、邏輯論證(λόγος/logos),也包含西氏於《布魯圖》(Brutus, xlix.185) 中引申的演說者三種職責,即教人(docere/to teach)、悅人(delectare/toplease)、感人(movere/to move)。這些主題乃奧斯定《論天主教義》關懷所繫,即「說教者如何勸服那些知道該怎麼做,卻不付諸行動的人」(IV.xii.28)。然而其中還與本書主題有所相關者,乃奧斯定所討論(語言)符號的本義與多樣性(I.i.2;II.i.1–2)、辯證法(dialectic) 的運用(II.xxxi & xxxvii),以及《聖經》中的比喻(II.xvi.23–24; III.v.9) 和《聖經》段落因為喻況語言而衍生的可能詮釋(II.vi.7–8)。後者誠大哉問,直到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c. 1225–74) 所著《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 c. 1265–74) 中仍見搉論(見本書第二章第四節及注13)。
奧斯定以古典修辭學的原則戙維,但他也另闢疇人之蹊徑。按奧斯定之見,《聖經》裡較淺顯的段落,可以滿足信眾的飢渴,而晦澀難懂的章句卻能刺激食慾,使人遺倦。而奧斯定所謂的「晦澀」,即是無法從字面得知本義而必須推敲其背後隱含意義的章句,易言之,即使用「喻況語言」的段落。那麼為何這樣的「晦澀」能使人遺倦?按奧斯定的解釋,經由探求而來的事物,往往帶給人更多喜悅,運用「辭格」(figure) 傳達的知識,更能達到「娛人」的效果(II.vi.8)。更精確地說,此處奧斯定所謂「辭格」,其原文乃“similitudo”,即修辭上的「類比」。而這也正是本書標的文本《譬學》(1633) 中,耶穌會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c. 1566–1640) 設譬心法所宗。對於辭格在《聖經》裡的運用,《論天主教義》其他章節仍見端倪。奧斯定援《新約‧羅馬書》為例:「我們連在磨難中也歡躍,因為我們知道:磨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望德,望德不叫人蒙羞,因為天主的愛,藉著所賜與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 羅5: 3–5) 這段經文裡,奧斯定以為由磨難(tribulatio) 而至望德(spes) 的推展,實遵循了修辭的規則,乃「字詞間及概念間相互依賴的關係」,這種關係如同階梯遞進,而這種「遞進」(見本書第三章所析語法辭格的增添操作)辭格在修辭上便以希臘文“κλῖμαξ/climax” 或拉丁文“gradatio” 稱之(IV.vii.11)。奧斯定當然還列舉了《聖經》中的其他例子,說明比喻的運用及句段的優美組合,而這兩種技巧,實際上正分屬日後文藝復興修辭學家強調的辭格兩大領域:「轉義∕譬法」(trope)與「句式」(schemate),也是本書修辭格分析的兩大主軸:語義詞格及語法辭格。奧斯定取《聖經》段落為例說明修辭手段,這樣的論述模式也繼續在中世紀的歐洲發展。如本篤會士聖畢德(Saint Bede, c. 672–735) 所著《句式與譬法全書》(Liber de schematibus et tropis, c. 691–703),乃盎格魯撒克遜英格蘭的第一本修辭學專著,其中便以一百二十二條《聖經》段落,說明二十八種轉義法與十七種句式。文藝復興時期的修辭學專著,泰半仍以拉丁文書寫,直到文藝復興晚期,歐洲的中古王權逐漸從封建發展為現代國家的雛型,因此開始出現以各地本土語言書寫的修辭學專書(見本書表1.1),尤以英格蘭為最。漫長的中世紀過去,然而如奧斯定與畢德這樣自《聖經》取材討論辭格的傳統,並未隨著英格蘭教會脫離天主教廷而流逝,反而可見之於如英國國教伍斯特主教(Bishop of Worcester) 普里鐸(John Prideaux, 1578–1650)《神聖雄辯術》(Sacred Eloquence: Or, the Art of Rhetorick, As It Is Layd Down in Scripture, 1659) 這樣的專書。這也正是本書第二部標的文本,即英國國教牧師皮坎(Henry Peacham, Sr., 1547–1634) 所著《說苑》(The Garden of Eloquence, 1577, 1593) 的時空背景。
十年前此時,我進入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班。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先後有兩門學科,除最令我著迷外,也奠定我未來的研究方向,對我的影響至為深遠:其一是符號學,其二是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研究。帶領我進入西學東漸研究(這裡指的是明清耶穌會士的譯著)的啟蒙關鍵,是2007 年修習了李奭學教授講授的「中國早期基督教文學:唐迄清末」課程;這門課程從唐朝景教文獻《志玄安樂經》與《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開始講述,一路延續到晚清幾部基督教翻譯小說。但課程的中心還是著重於幾位明末「第一代」來華耶穌會士的譯著,如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交友論》(1595)、《西琴曲意》(1601)、《二十五言》(1604),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1565–1654)《聖若撒法始末》(1602),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況義》(1625),高一志《聖母行實》(1631)、《譬學》、《達道紀言》(1636),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天主降生言行記略》(1635)、《聖夢歌》(1637),衛匡國(MartinoMartini, 1614–1661)《逑友篇》(1647) 等。而其中我最感興趣,也持續研究至今未歇的譯著,是高一志有關文藝復興修辭學的專著《譬學》。
早先於2006 年博士班修業期間,我在臺灣大學從恩師張漢良教授研讀符號學,受益匪淺之外,也開啟我在研究方法上全新的視野。因此在「中國早期基督教文學:唐迄清末」課程期末,我便運用所學的符號學理論,完成〈可見與不可見:淺析高一志《譬學》中的符號學方法〉研究論文,並於2008 年在「杭州海外漢學與中外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宣讀。這是我首次結合現代符號學理論與耶穌會傳教士譯介的文藝復興修辭學理論,論文內容的初步嘗試,乃以「符徵∕符表」(signifiant)與「符旨∕符意」(signifié) 間的「指號過程」(semiosis) 為出發點,探討高一志在《譬學‧自引》中析論的譬喻兩端現象。因此這也可說是我就「文法←→ 修辭」的關係,在天主教文學(特別是智言文學)的初探。
隨後我受到李奭學教授〈「著書多格言」──論高一志《譬學》及其中西修辭學傳統的關係〉與許理和(Erik Zürcher, 1928–2008)〈文藝復興修辭學在晚明中國:高一志的《譬學‧自引》〉二文啟發,在2008–2009 年間申請了兩次以《譬學》為主題的獨立研究,並敦請張漢良教授擔任指導人。其間除釐清其與西方由古典而至文藝復興修辭學間的關係外,張漢良教授亦誘掖誨導我就譬喻的結構本質與其在論辯上的功能深入探討。2009 年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之後,我便以高一志《譬學》與亨利‧皮坎的文藝復興修辭格專著《說苑》為平行研究標的文本,輔以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歐陸新修辭學學說──日學派(Groupe μ) 所著《普通修辭學》(Rhétorique générale, 1971)及佩雷爾曼(Chaïm Perelman, 1912–84)所著《新修辭學》(Traitede l’argumentation: La nouvelle rhétorique, 1958)──做為理論分析依據,撰寫我的博士論文:《高一志〈譬學〉與亨利‧皮坎〈說苑〉平行研究──修辭與符號》。
這本論文是我在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研究、修辭學與符號學等領域研究的總和,或許也是相關研究領域中,首先以符號學方法對晚明耶穌會士修辭學譯著進行結構分析的專著,也是拙著《修辭‧符號‧宗教格言──耶穌會士高一志〈譬學〉研究》(2015) 的原型。而論文口試最後獲得的成績,至今仍為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由於這本論文的研究橫跨文藝復興修辭學的「譬法」與「句式」兩個辭格範疇,若就新修辭學的眼光觀之,則又以現代結構語言學的分析方法探討語義場(semic field)、句法場(syntactic field) 與邏輯場(logical field) 的修辭功能。職是之故,這部論文將我對耶穌會譯介的西方修辭理論研究,從「文法←→ 修辭」關係的討論,進入更深層次的「修辭←→ 邏輯」關係爬梳。修辭勸服(rhetorical persuasion) 中的「論辯」一直是我感興趣的主題,當然這也正是「修辭←→ 邏輯」的問題;而從這裡,我的研究興趣延伸到宗教上的論辯與天主教教義,比方阿奎那推論天主存在時所用的「五路論證」(Quinque viae) 類比,以及在宗教修辭中呈現的非形式邏輯(non-formal logic)。這也引導我在宗教與文學關係領域的研究,進入下一個階段。
回顧博士學位口試宣布成績的那一刻,擔任主席的楊承淑所長,代表六位口試委員向我說明這個創紀錄高分的意義。委員們以兩項任務深相期許:其一是希望我不可弭忘對於《譬學》翻譯祖本的探尋,因為唯有找出這個源頭,才能真正理解《譬學》譯入中文的過程,據此方能檢視高一志的翻譯策略與修辭操作,使個人的研究更臻完善。其二是希望我假以時日能夠將這本論文出版,做為個人求學與研究的里程碑。恩師與諸位委員的孜孜策勵,至今言猶在耳,我未敢或忘,而這兩項期許我也逐一完成。
2011 年我進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學者,李奭學教授擔任我的指導人,帶領我主編《晚明天主教翻譯文學箋注》。而我對《譬學》的研究也一路延續,因為學界雖知《譬學》乃是翻譯,但歷來對其歐語祖本與其中譬式原型並無定論,故當時我的博士後研究計畫主題是〈明末耶穌會格言傳統溯源—高一志《譬學》格言翻譯的可能取材初探〉,希望能追本溯源,推敲高一志在《譬學‧自引》中所謂「吾土古賢譬語」的真實身分,也藉此完成博士學位口試時委員們對我的期許。其間我首先修潤博士論文中對於宗教譬喻的語義場研究章節,完成了〈格言‧修辭‧證道──高一志《譬學》語義辭格分析〉一文,並在2012 年於南京師範大學舉行的「IASS第十一屆世界符號學大會」上宣讀,這篇論文最後也在《漢學研究》發表(2013)。而《譬學》譯源的追溯工作上,我也有進展︰我首先歸納了十三條《譬學》中格言例句與老蒲林尼《博物誌》間的關係,在《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的「中國翻譯史專輯」(2012) 發表了〈高一志《譬學》中例句之譯源初溯:從老蒲林尼《博物誌》探起〉一文。2012 年末,我的研究又見斬獲,從新近的研究資料裡,我得知《譬學》與北方文藝復興時期重要人文主義神學家伊拉斯瑪士(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 編撰的格言集子《譬喻集》(Parabolae sive similia, 1514) 與《格言集》(Adagia, or Adagiorum chiliades, 1508) 間頗有關聯後,便著手改寫〈高一志《譬學》譯源初溯〉,重新就《譬學》與《譬喻集》間的因緣探討,在中國文哲研究所宣讀了〈高一志《譬學》譯源再溯:從翻譯到論辯的形成〉。
過去四年,由於擔任《晚明天主教翻譯文學箋注》(2014)主編之一,我有機會在西方古典文叢中參互考尋,因此對於希臘羅馬的古典作家與作品,更有脈絡及內容上的認識。而這些西方古典文本,也正是耶穌會士翻譯的取材來源之一。回顧天主教中國傳教史,萬曆三十八年利瑪竇榮歸主懷,龍華民繼任中國教區會長,並於萬曆四十年(1612) 命金尼閣返歐向教宗及耶穌會總會長報告教務。金尼閣在歐洲廣事募書,萬曆四十八年(1620) 金尼閣再返中國,運抵的這批書籍共有七千餘部。這七千餘部書籍中,很可能也包含了這些西方古典文學與哲學作品,比方亞里士多德與普魯塔克(Plutarch, c. 46–120) 等人,當然也很可能囊括文藝復興時期的天主教人文主義(Christian Humanism) 作品,例如前及伊拉斯瑪士的《譬喻集》和《格言集》。尤為重要者,乃這些西方由古典而至文藝復興的思想背後所形成的龐大知識庫(repertoire),實乃會士布道或論著中修辭勸服的主要取材來源。基於上述工作與《譬學》的研究積累,我從伊拉斯瑪士的《譬喻集》中,考出《譬學》六百條格言近三分之一的翻譯原型,並將之悉數箋釋於《晚明天主教翻譯文學箋注》中。而其餘仍未考得原型的格言,我現另繼續往伊氏《格言集》中賾探隱索。至此,我算是完成了2010 年口試委員們對我的第一項期許。而將博士論文補充改寫,以《修辭‧符號‧宗教格言—耶穌會士高一志〈譬學〉研究》之名忝錄於「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歷史文化叢書」,則讓我得以進稟第二項期許告成。
從取得博士學位到拙著得以梓行,我何其有幸,一路上獲得諸多支持與鼓勵。回首春風,恩師張漢良與李奭學二位教授,對我在智識上的啟牖最深,攻讀博士時期對符號學、修辭學、宗教與文學關係的興趣,以及拙著的研究內容,俱出自我在二位教授的課堂所學。李奭學教授在我博士後階段的栽培與支持,毫無保留提供我研究環境與資源,我銘感在心外,也期勉自己朝著研究目標繼續前行。承蒙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主持人吳昶興教授的賞識,促使拙著得以出版,利瑪竇《交友論》裡那句「德志相似,其友始固」,吳教授契誼篤厚,正是利譯最佳寫照。歷史與文化叢書的編輯陳慧娜女士,常忍受我延誤稿期,在生產期間仍盡心替我處理編務,我特於此致謝也致歉。
我用全部的心意謝謝父親母親,在我工作冗忙之際,從不因我未能克盡人子應盡之孝苛責,反而鼓勵我在研究的冒險旅程中恣意探索各種可能。在這篇長序的最後,我要將這本書獻給我的父親母親。朝乾夕惕,我期許自己能有所為,並非希望成就什麼,只是希望不辜負他們以我為榮的心。
長樂林熙強
乙未蒲月謹誌於南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