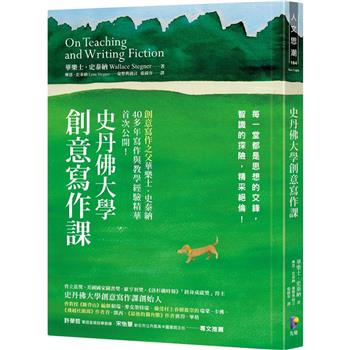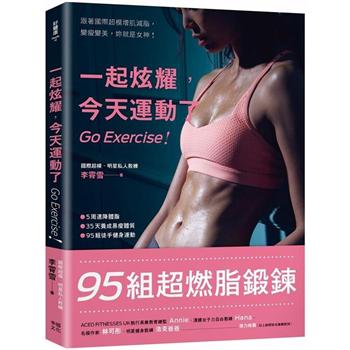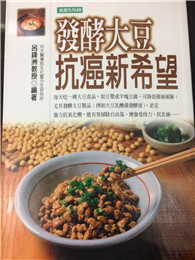美國監理會在近代來華差會中並不是一個大差會,但是該會卻在近代中國留下深刻的影響。思想開放的林樂知教士創辦了晚清最具影響的中文報刊《萬國公報》,成為許多近代中國思想家的啟蒙讀本;他們又創辦了第一流大學(東吳大學)、中學(中西女塾),培養了一批又一批一流的人才(謝洪賚、宋耀如、宋慶齡、吳經熊、費孝通、趙紫宸等)。為什麼監理會能在中國建立起包括佈道、文教、醫療衛生、婦女成長等在內的龐大教會事業?它的經費來自何處?它的人力支撐是什麼?顯然本土社會在其中發揮了相當關鍵的作用,但本土社會究竟是怎樣與教會關聯互動的?通過什麼機制實現互動?所有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討論,本書即對這些關鍵議題做了深入的觀察和分析。
從監理會與地方社會的互動看,地方社會並非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客體,在等待基督教與之相遇,而是一個不斷建構的過程,基督教在此既是外來的,又是本土的,所有外來性元素都參與了本土社會的建構,而中西兩種元素塑造的基督教社區具有不同於傳統地方社會的鮮明的複合文化特徵。監理會憑藉佈道、醫療衛生、教育、文字出版、社會服務等活動,與當地信徒和民眾在宗教認同或不排斥的基礎上在不同的地域建立了涵蓋不同內容的若干基督教社區,嵌入到當地社會之中,不自覺地與當地社會一起參與到近代化發展的歷史潮流中;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有別於當地社會,西學元素較多的基督教社區,其所開展的教育、醫療等現代化活動,為當地社會的教育及醫療等事業提供了學習的範式。
作者也發現,監理會將傳教總站設在傳統江南最核心的城市蘇州,同時又在近代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謀求發展空間,其傳教觸角分佈環太湖流域,監理會的傳教圈與中國最具活力且傳統積澱極為深厚的江南經濟文化圈的重合,可能正是該會能在近代中國發揮重大影響的關鍵所在,馬光霞博士對此的立論和分析實是一項重要的發現,值得學術界予以關注。
作者簡介:
馬光霞
1971年生,山東臨朐人,歷史學博士。先後就讀於內蒙古民族大學歷史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現為上海應用技術大学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中國基督教史研究。
章節試閱
林樂知是美國監理會傳教士,1860 年被派來華傳教,但隨後爆發的美國內戰切斷了他與母會的聯繫,使其在經濟上陷於嚴重困境。為擺脫危機,他開始從事世俗活動,其特殊的世俗工作,不僅解了燃眉之急,還為其結交中國的士和官提供了便利,更使其傳教思路也因之發生變化,由「直接佈道」向「自由佈道」方式轉化,同時注重自上而下的方式,走上層路線。
王立新曾對基督教傳教方法有這樣的總結,縱觀整個19 世紀,基督教來華傳教士主要有基要派和自由派兩種不同的傳教政策,絕大多數傳教士採取傳統的「直接佈道」方法,即宣講教義、巡迴佈道和散發宗教印刷品。 這種「直接佈道」的方法正是基要派宣導的傳教方法,它注重「個人得救」,即不分貴賤、尊卑和階級,每一個人的靈魂都在上帝面前平等,都應得到「救恩」;它還特別強調一切教義的絕對性,對本土文化表現出一種全不妥協的態度。 然而這種通過用純粹的基督教教義來拯救個人靈魂的側重卻使得傳教士在傳道之時不自覺地疏離了傳統文化的代表—士大夫階層,而將佈道對象主要集中於普通大眾,尤其是一些貧苦百姓。因而這種方法又被稱為「自下而上」的傳教方法。早期監理會來華傳教士也是採取這種傳教政策,堅持基督教教義的純粹性,主要通過在教堂佈道、露天佈道,沿街散發傳單和小冊子,創辦義務學校收留貧窮子弟,培養當地傳道等手段開展傳教活動。
林樂知在來華之初,也是沿用前輩傳教士的傳教經驗,採用「直接傳道」的政策,遵循「面」和「量」的原則,擴大傳教範圍,建立更多的教堂,爭取更多的信徒。因此,林樂知在學習漢語之外,就到四鄉佈道,如1861 年就曾到南翔傳教。 然而,林樂知在從事中國現代化的文化活動中,其思想逐漸被「現代化」,其傳教政策也逐漸從傳統方式走向自由多元的轉化。
林樂知及其上海「文化圈」
以藍柏為代表的監理會傳教士在以蘇州為中心的內地城鎮逐步建立起了以當地助手為聯繫紐帶的傳教網路,而上海的林樂知在為擺脫經濟危機而從事世俗活動的過程中,以教習、翻譯和編輯等職業為紐帶構建了不同於以往的以文化為突出特點的交遊網路,形成了以士紳為主體包括高級官員和一些有上進心的青年學者、西方自由派傳教士及部分中國信徒在內的文化圈。這種交遊網路如同無形的神助之手,使林樂知日後的教會事業順利展開,也使林樂知在中國近代化的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林樂知憑藉著一些上海的友人如丁韙良(W. A. P. Martin, 1827–1916)、傅蘭雅及偉烈亞力等介紹結識了一些上海的官紳,這其中就有上海道台應寶時及廣方言館館長馮桂芬等。1864 年2 月24 日,林樂知收到上海廣方言館的邀請函,這可以看作是林樂知與中國政府正式打交道的開始;1871 年後進入江南製造局翻譯館,進一步擴大了其交遊圈;自1868 年他創辦《教會新報》到1874 年改為《萬國公報》後,其輻射圈更為擴大。那麼他究竟是怎樣與他們交往的呢,下面對此做一考察。
1. 官員,如馮桂芬和郭嵩燾。據貝奈特考證,林樂知和馮桂芬的友誼一直持續到馮桂芬去世。馮桂芬(1809–1874)是晚清著名思想家,1864 年後任李鴻章的幕僚,尤其是關於蘇州及其周邊行政事務的顧問,曾任上海廣方言館館長。太平天國運動期間馮桂芬駐上海,林樂知每週與其會談一次,而馮遷往蘇州96 後,林樂知與其每月討論一次。林樂知認為馮桂芬是許多較開明學者中的一個,他向林樂知解釋中國的事情是怎樣和為何這樣,而由於其角色,林樂知也與他討論各種各樣的西方政策, 發展及其態度。另如郭嵩燾,他是19 世紀第一位中國駐外公使,1876 年離華前與林樂知相遇,當時林樂知贈予他一本《中西關係略論》, 這本書分析了中國目前的國際地位,它曾刊行在1875–1876 年的《萬國公報》期刊上。1878 年,林樂知在倫敦與郭再次相逢時,郭告訴林樂知:「當我剛接受中國駐英大使這份工作時一無所知,但幸運的是我有你的書作指導。」馮桂芬和郭嵩燾是晚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視西學及西政等方面的內容,從上面林樂知與兩人的交往看,他主要以「西政」為載體搭起了與晚清改革派官員的聯繫橋樑。
2. 廣方言館學生,如嚴良勳、席淦、汪鳳藻、王遠焜、王文秀等, 與學生的交往,除了課堂上的交流,他還帶領學生參觀法租界的煤氣燈廠,現代化的麵粉廠,參觀江南製造局的機器車間, 這種方式一方面讓學生在學外語的同時學到了一些科學知識,另一方面也密切了與學生的交流。與學生的這種交往,是潛移默化的,後來學生的工作經歷也驗證了林樂知的預測,他們有不少擔任了政府的官職,有的在國內任職,還有的在國外任過公使和領事。1903 年一位19 世紀70 年代上海廣方言館的學生還給林樂知寫信說他在福建的汀州任高官。 後來出使過德國的H. E. Yang也曾是林樂知的學生。
林樂知與學生的交往可看作是他以「西學導師」的身份切入,同時這種身份的建構對其傳教士身份的彰顯無疑是一道美麗的光環。
3. 翻譯館同事,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譯員,可考的有59人,其中外國學者9 人,中國學者50人, 比如徐壽、華蘅芳及徐建寅等。從下表可看出與林樂知直接打交道的學者有嚴良勳、李鳳苞、鄭昌棪、瞿昂來、蔡錫齡、趙元益等,他們在一起合作譯書。林樂知及其中國助手翻譯了大批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其軍事科學等方面的大批西學作品,其中內容較多的還是社會科學方面的內容。顯然在此林樂知與中國學者的交往是以「西學」、「西藝」為媒介的。
林樂知不僅通過上述管道建立了與官員及文人學者的聯繫,而且還因其特殊的貢獻,獲得了名義上的「官銜」。1876 年被清政府賞封五品銜。
報刊社交圈
以藍柏等為代表的早期監理會傳教士在文字方面主要著力於出版一些宗教宣傳品及其用上海方言編成的福音小冊子, 而且其面向的對象是下層民眾;以林樂知為代表的傳教士則由於特殊的編輯和翻譯經歷,在文字方面主要從事翻譯和報刊工作,其面向的對象已逐漸向上層社會擴展。下面主要探討林樂知自己創辦的報刊《教會新報》或《萬國公報》及其聯繫網。
《教會新報》的宗旨為「傳教」與「聯絡信徒」,主要是為基督徒設計的, 刊載的也主要是基督教的內容。隨著林樂與中國士紳交往的深入,林樂知逐步意識到知識份子的力量, 因此1874 年從301 期開始,《教會新報》改名為《萬國公報》(Globe Magazine),「林樂知想使它成為教會性質不明顯,中國知識份子也不很反感的一份報紙」,且「本刊是為推廣與泰西各國有關的地理、歷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學、藝術、工業及一般進步知識的期刊」,這樣「既可邀王公巨卿之賞識,並可以入名門閨秀之精鑒,且可以助大商富賈之利益, 更可以佐各匠農工之取資,益人實非淺鮮,豈徒《新報》雲爾哉!」因此,《萬國公報》不僅以教徒為對象,而且跳出教會圈子,以中國上流階層和知識份子等為對象,淡化宗教色彩和添加世俗內容,使得讀者群及其影響進一步擴大。
該報刊不僅依賴於讀者,也依賴於撰稿人,有的還是讀者兼撰稿人。林樂知開始聘用兩名助手:一位負責宗教內容, 另一位則負責新聞內容由以上資料可以看出,當時報刊的擴散面之廣,不僅地域跨越中西,而且作者也涵蓋中西,形成了兩大作者圈:一是以中國基督徒為中心。二是以傳教士為主的外國人交遊圈,主要是當時在華的西方傳教士。據貝奈特統計:向該報撰稿的西方人大多是傳教士:如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丁韙良、艾約瑟、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慕維廉、花之安(Ernst Faber)、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藍柏、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倪維斯(John L. Nevius)、楊格非(Griffith John)、理一視(Jonathan Lees)、湛約翰(John Chalmers)、潘慎文等。另外,傅蘭雅博士和德貞醫生(Dr. John Dudgeon) 也為雜誌撰過文。西方作者既撰寫世俗文稿也有宗教主題的文章。
在江南製造局的廣方言館和翻譯館中,林樂知就結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外國人朋友,只不過在公報這兒,這個圈子的範圍進一步擴大了。其實,中國學者早就注意到了晚清時期中國傳教士內部形成的這個圈子,比如梁元生就認為這是以廣學會為中心、《萬國公報》為喉舌的自由派傳教士圈,這群人翻譯過不少西學書籍,並發表過有關維新變法的言論。這群志同道合的傳教士們擁有一個共同的交流平臺和社交圈,而且他們交往的目標很明確,那就是中國的「士」。也正是由於他們的聯合行動,中國近代化的舞臺上才留下了他們忙碌的身影和中國學者對傳教士不同評價的聲音,他們甚至被稱為「西儒」。
買辦商人與中西書院
1881 年林樂知擔任監理會中國教區長,並創建中西書院。他批評當時差會所經營的學校,認為「學生來自中國較為低下並毫無希望的階層」,而林樂知的工作經歷,使他看到了結交「士」和「官」的好處,從而使他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辦學思路。他將中西書院的招生對象指向「上層社會」,當時學校初招學生200 餘人,據林樂知稱,「除一人外,所有學生皆來自上海最優秀的家庭,並且代表了中國社會幾乎所有的階層。」
中西書院先後建成的有三處校址:第一分院、第二分院和大書院。按其規制,學生先在分院修讀二年,始進大書院就讀。後來,二分院歸併大書院,1884 年後,中西書院實際上就只有上海昆山路中西大書院一處院址了。對於建設費用,當時「按林樂知與監理會所定之條款,差會承擔購置校舍地皮, 支付外籍教師薪水的費用,餘者皆從當地籌措,自1881 年夏起,林樂知向滬上中外人士籌集資金,迄1882 年底,中西書院已獲足夠『支付兩年的開辦費用』」,這其中「美國本公會撥洋四萬餘元,中朝李傅相、王總戎、邵唐諸觀察暨中西官紳商富慨分鶴俸、惠賜洋蚨。」1883年,「又蒙粵東徐君雨之觀察慨讓虹口空地三十六畝,業也備價購就」,由是觀之,林樂知與徐潤的交情已非同一般。中西書院的舉辦也離不開上海一些文人的支持。如王韜、沈毓桂等,他們都曾作過該校的監院,而沈毓桂和林樂知的合作可以看作是中西融合的典範。
中外人士對中西書院創辦的讚譽也可旁證他們的支持態度。如李鴻章曾致函林樂知,稱其為「影響久遠之偉大創舉, 比任何事都重要」,丁韙良、傅蘭雅等對此也極表讚揚。可以說,中西書院的成功創辦,得益於林樂知在上海的世俗經歷, 更離不開他與當地社會上流人士所建立的人脈網絡,這裏面集結著他曾交往過,或者支持他的官員、文人、傳教士,還鏈結了當地的買辦階層,他們所提供的人力和物力支持為其日後的教會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小結
1848–1885 年是監理會在華各項事業的奠基階段,1886 年中華年議會成立,監理會在華各項工作有綱例可循,逐步趨向正規發展。在此階段由於藍柏、潘慎文等主要以直接傳道為主,在蘇州、南翔等內地城市開展佈道工作,並通過開辦學校培養當地助手,為教會儲備了大批領袖人才;此階段也是林樂知「改直接佈道為間接佈道,走上層路線」傳教思路的形成, 上海中西書院的成功舉辦及其《教會新報》到《萬國公報》的轉變也正好踐行了林樂知的這些思想。
正是由於藍柏和林樂知不同的傳教思路,才使得監理會在以蘇州為代表的內陸城市及以上海為代表的口岸城市所開展的教會事業兼具傳統和現代的特徵,其傳教對象也覆蓋邊緣與主流。如林樂知初來華時,沿循傳統的佈道方法,傳教對象多以來自於社會底層的社會邊緣人物為主,到1875 年,信徒的情況還是「當地每年的捐款數從10–15 美元不等,許多信徒太窮以致捐不出什麼東西」。而在林樂知從事世俗工作,尤其是從事政府工作之後,他的交往圈逐漸滲入到主流社會中的上層人物之中,隨之構建了包括官員、文人、紳商、買辦階層等中上層人士在內的交遊網路。其傳教思路一改傳統風格,由「直接佈道」改為「間接佈道」,並且「兼合中西」、「走上層路線」。中西書院學生的積極報名及社會各階層的踴躍捐款即可看作是林樂知及其事業楔入主流社會的成功嘗試。
同時,通過林樂知的世俗實踐及傳教思路的變化,可以看出林樂知是被中國「啟蒙」後才開始「啟蒙」活動的,也可以說他在從事中國近代化的活動中「被近代化」,才開始擴大教會事業進而加入「使中國近代化」的活動行列。而林樂知的交往圈從邊緣階層到主流階層,由教內人士擴至教外人士的過程,也是其「被啟蒙」到「再啟蒙」過程的反應,它包括從最初的「傳播基督教」到「傳播西學加基督教」的轉變。而「被啟蒙」與「再啟蒙」內容的矛盾,也註定了林樂知「基督教救中國」的願望不會實現。 (節錄自本書第三章「以傳教士為主體的早期宣教」)
林樂知是美國監理會傳教士,1860 年被派來華傳教,但隨後爆發的美國內戰切斷了他與母會的聯繫,使其在經濟上陷於嚴重困境。為擺脫危機,他開始從事世俗活動,其特殊的世俗工作,不僅解了燃眉之急,還為其結交中國的士和官提供了便利,更使其傳教思路也因之發生變化,由「直接佈道」向「自由佈道」方式轉化,同時注重自上而下的方式,走上層路線。
王立新曾對基督教傳教方法有這樣的總結,縱觀整個19 世紀,基督教來華傳教士主要有基要派和自由派兩種不同的傳教政策,絕大多數傳教士採取傳統的「直接佈道」方法,即宣講教義、巡迴佈...
作者序
馬光霞博士告知,她的博士學位論文經修訂後,將收入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的「歷史文化叢書」,並由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我獲知此消息很高興,也很欣慰,她多年的學術追求終於結成果實。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我到蘇州大學進修學習,當時校園裡一些風格獨特的建築曾讓我感到震撼。蘇大的老師告訴我這些老房子是以前東吳大學留下的,而東吳大學是一所基督教大學,我開始對基督教有了一點印象,不過還談不上興趣。後來因緣巧合,我在上海讀研究生時受先師劉學照教授的影響,開始對近代上海文化產生濃厚興趣,同時蒙易惠莉、田文載等校內外老師的指點,遂以上海中西書院為碩士論文選題,對監理會在上海和蘇州的早期教育事業作了一點粗淺的探索。不過,當時受資料的限制,並沒能深入做下去。此後,關於監理會在華的歷史問題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總希望有人能繼續完成這項研究。
馬光霞在跟隨我一起研習基督教史後,她個人因私人原因常在魯滬兩地往返奔波,這使得她逐漸對江南、對上海發生了興趣,並開始關注監理會在華的歷史。確定學位論文選題後,她不辭辛勞,反復到上海、北京等地的檔案館、圖書館搜集資料,歷經數載,終於完成博士論文,順利畢業。
近些年基督教在華歷史的研究在研究取向上已經發生明顯的轉移,即關注的重點逐漸從外國差會轉向本土教會,從來華傳教士轉向本土基督徒,這種轉向與學界「在中國發現歷史」的主流旨趣是一致的。不過,如果稍微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儘管海外漢學界和國內學者都在實踐這一理念,但其實有很大的不同。就前者來說,其研究是希望儘量減少乃至消除西方中心論對研究的影響,盡可能多的關注中國本地因素,盡可能多的使用本地資料,以一種人類學的同情來理解和審視中國人與中國社會。就後者來說,一些研究則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帶有「中國中心論」色彩,民族主義成為其潛在的價值尺度,從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立場出發看待近代的世界交往,將一切外來的因素視為「異己」因素,而一切本土的因素都具有天然的正當性,只有用本土因素改造外來的因素,使其本土化、中國化,外來者才有存在的合理性。這種完全以本土為是、以外來為非的取向實際上是傳統夷夏之防觀念的現代變異,即便是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也是相當偏狹的觀念,更何況身處 21 世紀的世界!這種觀念將本土視為一種固定不變的物件,實際上沒有「外來」,何來「本土」,在歷史上,所謂的本土社會一直就是開放和多元的,是演進和變化的。各種外來和本土因素的交流融合不斷生成新的本土因素,本土社會才能真正具有活力。從兩千多年的中外交往歷史可以看出,正是在與所謂周邊和內部的「夷狄」的交往過程中,華夏文明才得以延續,「中國」才得以不斷成長。在此過程中,無論是邊疆民族的漢化,還是內地漢人的胡化,都是交往過程中的正常現象,並無是非對錯之分。正是通過各種形式的的密切交往,正是彼此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才使得「中國」的元素空前豐富起來,並處於不斷變動的過程之中。
在具體的歷史場景中,無論是「中」還是「外」都只是一種暫時性的空間區隔和身份標識。一旦「外」進入「中」,很快就會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關係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將在華基督教一直視為「洋教」,作為攻擊的物件,只是民族主義的一種話語策略,並非歷史的真實。從馬禮遜進入廣州開始,基督教的本土化、中國化進程就已經開始,這是一種自然發生的過程。在差會和本地社會的互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新的教會模式,美國學者裴士丹(Daniel H. Bays)稱之為「中外新教聯合建制」(Sino-Foreign ProtestantEstablishment)。就來華傳教士設定的最終目標來看,這種模式當然不是理想模式,它只是一種過渡形態。不過,這卻是包括監理會在內的各主流宗派教會的共同模式。在這種模式形成的早期階段,來華傳教士無疑處於核心地位,即使到後來本地教會陸續建立起來後,傳教士仍然佔有很重要的位置。對待這種模式不能簡單地給予肯定或否定,而應仔細分析其在具體歷史處境中的作用和影響。
對於傳教士而言,他們其中一些人已經意識到自身在教會中所處的優越地位,認識到近代西方文明進入中國的強勢姿態,所有這些都有可能構成基督教在華傳播的障礙,所以他們一方面在機制上重視本地教會領袖的培養,希望本地教會人士儘快成長起來,另一方面,在文化取向上,他們強調中西並重,防止教會出現洋化取向。對於本土基督徒而言,一方面重視自立自養,立足本土,努力成長起來,以便獨立擔任自身應負的責任,另一方面,在最具根本性的神學建設上力圖保持足夠寬廣的視野,既不畫地為牢,與教會的神學傳統相割裂,也不願完全因襲特定宗派的歷史包袱。無論在思想層面還是在教會的體制層面,中西並重都是近代中國教會所必走的一段重要歷程。馬光霞博士能注意於此,在研究重心的選擇上保持平衡,在中西之間,差會與教會之間無偏無倚,對監理會的中外教會人士及其所開辦的事業均能持平討論,這種研究方法實是對當前過於偏重所謂本土要素,而將差傳完全忽視,或只視為一種背景性因素的做法的有力糾正,具有明顯的學術意義。
實際上,基督教是一普世性的宗教,其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會面臨與當地社會和文化的調適問題,但所有這些調適都將進一步加強基督教的普適性。當來自美國南方的監理會傳教士進入中國的江南時,這種特定歷史情景下的「南南合作」,不僅使這個較為保守的教派出現了像林樂知這樣的思想極開放的教士,而且為監理會在華事業的落地生根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誠如作者所言,在近代來華的基督教宗派中,監理會無論就派出的人力和物力都難以排入實力雄厚的幾個大宗派之列,但是該會將傳教總站設在傳統江南最核心的城市蘇州,同時又在近代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謀求發展空間,其傳教觸角分佈環太湖流域,監理會的傳教圈與中國最具活力且傳統積澱極為深厚的江南經濟文化圈的重合,可能正是該會能在近代中國發揮重大影響的關鍵所在,馬光霞博士對此的立論和分析實是一項重要的發現,值得學術界予以關注。當然,理解上海和江南社會需要時間,對於來自一個中國北方省份的學者來說更需要時間,空曠乾燥的華北平原與煙雨朦朦的江南畢竟是迥然不同的風景,不過這種差距再大,總比不過納什維爾(Nashville)和上海的差距大,來自萬里之遙的監理會傳教士尚且在江南找到了傳教事業的基點,馬博士現已落籍滬上,假以時日,我相信其在江南基督教史的研究領域當有更豐沛的成果。最後應當特別指出的是,基督教的中國化雖為一自然進程,但絕非基督教單方面適應中國社會,而是基督教與本土社會相互適應、相互調適的雙向互動過程。尤為重要的是,中國化的前提必須是基督化,在保有基督教的核心元素和基本價值的前提下,自主地而非被動地汲取本土的一些文化因素和符號,構建具有帶有本土色彩的信仰表達,成為基督教普適性的證明,而不是以本土性來對抗和消解基督教的普適性。從基督教在中國最近兩個多世紀的歷史經驗和民間基督教強烈本土色彩所衍生的各種實際問題來看,本土化只是問題的開始,而非問題的解決。
數年前,一位對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有開創性貢獻的資深前輩學者對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狀況作出總結性評估,認為這項研究已經由「險學」變成「顯學」。我們這些跟隨先進的後輩學子聞言之後,自然非常振奮。就目前兩岸三地的總體情況來看,這位前輩的判斷仍然是正確的。不過,歷史的長河中不可能總是波平如鏡,總會有不少迂迴和漩渦,在乍暖還寒的時節,幾滴冷雨的確會喚醒人們對冬天的記憶,但我仍然深信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應當不會再經歷風刀霜劍,因為春天確實已經來臨。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胡衛清
馬光霞博士告知,她的博士學位論文經修訂後,將收入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的「歷史文化叢書」,並由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我獲知此消息很高興,也很欣慰,她多年的學術追求終於結成果實。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我到蘇州大學進修學習,當時校園裡一些風格獨特的建築曾讓我感到震撼。蘇大的老師告訴我這些老房子是以前東吳大學留下的,而東吳大學是一所基督教大學,我開始對基督教有了一點印象,不過還談不上興趣。後來因緣巧合,我在上海讀研究生時受先師劉學照教授的影響,開始對近代上海文化產生濃厚興趣,...
目錄
序/胡衛清
第一章 研究緒論
第二章 背景
第三章 以傳教士為主體的早期宣教(1848–1885)
第四章 本土教會的建立和發展(1886–1939)
第五章 監理會在華文教事業
第六章 監理會在華醫療衛生事業
第七章 監理會在華婦女事業
結語
致謝
參考文獻
序/胡衛清
第一章 研究緒論
第二章 背景
第三章 以傳教士為主體的早期宣教(1848–1885)
第四章 本土教會的建立和發展(1886–1939)
第五章 監理會在華文教事業
第六章 監理會在華醫療衛生事業
第七章 監理會在華婦女事業
結語
致謝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