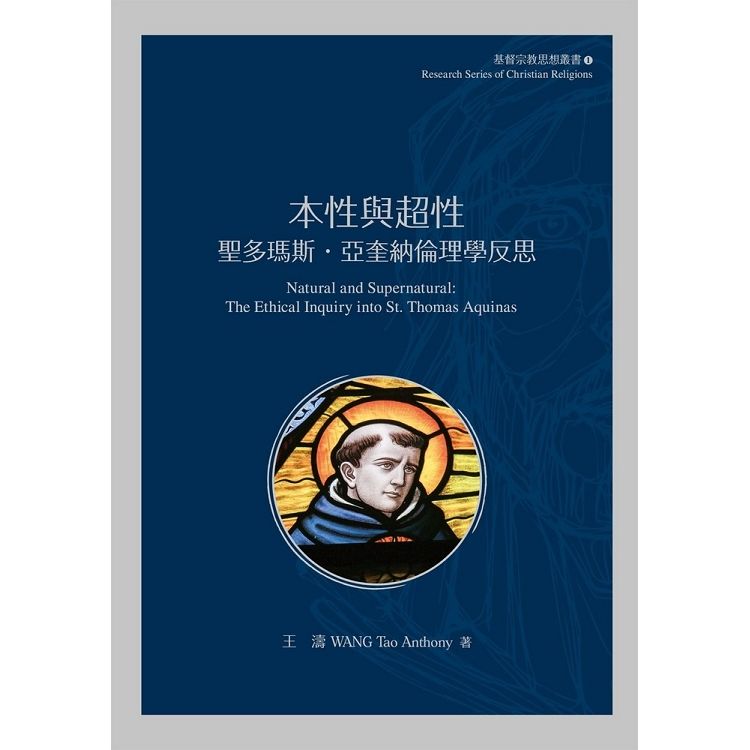本書為作者近十年來所撰寫及發表的八篇圍繞聖多瑪斯‧亞奎納倫理學的學術論文合集,分別在「原理」層面探究意志、慾、德性、良知、愛等元倫理學範疇,並於「應用」層面討論生態倫理、婚姻─性倫理以及倫理學多邊對談等應用倫理學議題,嘗試深掘聖多瑪斯倫理學精髓及適切性,並藉此突出多瑪斯哲學中(自然)本性與超性(恩寵)之間的張力及會通關係。
本書主要面向廣大具基督教神哲學背景的學人及志趣者,尤其是有志於倫理學、士林哲學、基督宗教學術研究事業的人士。書中所涉主題均為聖多瑪斯倫理學的核心内容,作者不但將此中世思想菁華與西方古典思想傳統乃至當代思潮進行比較與互參,更大量藉鑒西方學界前沿成果,在當代具體倫理議題上展開處境化運用,亦嘗試與中國思想傳統資源展開互動關聯,具有原創性價值,已獲學界普遍認可與欣賞。
本書可望有助豐富與推動大中華區聖多瑪斯‧亞奎納思想研究暨基督宗教學術事業。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本性與超性:聖多瑪斯‧亞奎納的倫理學反思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本性與超性:聖多瑪斯‧亞奎納的倫理學反思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王濤
祖籍陝西西安,現任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哲學教授、香港原道交流學會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學哲學博士,並獲義大利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哲學執教學位。
著有《聖愛與慾愛:保羅‧蒂利希的愛觀》(北京,2009年)、《聖愛與慾愛:靈修傳統中的天主教愛觀》(香港,2009年),並譯有《世界的終結:從科學與神學看終末》(香港,2010年)、《二十世紀天主教神學家:從新經院主義到聖婚神秘主義》(香港,2011年)等著作,曾在《哲學與文化》、《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世界宗教研究》等深具影響力的神哲學、宗教學學術期刊以及海外英文學刊、論文集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王濤
祖籍陝西西安,現任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哲學教授、香港原道交流學會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學哲學博士,並獲義大利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哲學執教學位。
著有《聖愛與慾愛:保羅‧蒂利希的愛觀》(北京,2009年)、《聖愛與慾愛:靈修傳統中的天主教愛觀》(香港,2009年),並譯有《世界的終結:從科學與神學看終末》(香港,2010年)、《二十世紀天主教神學家:從新經院主義到聖婚神秘主義》(香港,2011年)等著作,曾在《哲學與文化》、《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世界宗教研究》等深具影響力的神哲學、宗教學學術期刊以及海外英文學刊、論文集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目錄
陳序
自序
上編 原理
第一章 本性(上)
意志哲學中的「意志薄弱/不自制」
第一節 「意志薄弱」問題的經典界說
第二節 聖多瑪斯論「不自制」
第三節 意志與意志哲學
第二章 本性(下)
慾:聖多瑪斯與拉内慾觀念的比較
第一節 「慾」之三端
第二節 聖多瑪斯對慾的界説
第三節 拉内論慾的神學涵義
第四節 慾觀念的比較與反思
第三章 從本性走向超性
異教的羅馬有無德性:「異教德性」理論
第一節 德性與德性倫理學
第二節 聖多瑪斯對德性的分類
第三節 無恩寵灌輸的異教德性
第四節 異教德性相對灌輸性德性:「真正但不完善的德性」
第五節 走向灌輸性德性的異教德性
第六節 反思異教德性
第四章 本性與超性的相通
自然性向與良知
第一節 自然性向與自然本性:習性
第二節 自然性向與超性:共同本性
第三節 自然性向與情感性
第四節 自然性向與良知
第五節 自然性向對多元宗教對談與人類和平的啓示
第五章 本性與超性的聯合
愛的哲學:慾愛、友愛與聖愛
第一節 聖愛─慾愛與友愛之愛─慾望之愛
第二節 聖多瑪斯:友愛之愛與慾望之愛
第三節 田立克:聖愛─慾愛的統一體
第四節 聖多瑪斯與田立克愛觀念的比較
下編 應用
第六章 生態倫理
現代語境下再思中世紀思想遺產
第一節 生態倫理與生態中心論
第二節 人的靈魂與生態倫理:對聖多瑪斯的批評
第三節 善之等階與生態倫理:對聖多瑪斯思想的正面發掘
第四節 天主創造的人與生態:從聖多瑪斯反思生態倫理
第五節 分析對聖多瑪斯的不同評價
第六節 中國文化語境下的生態倫理
第七章 婚姻與性倫理
婚姻中的兩性關係:傳統與挑戰
第一節 婚姻‧聖事
第二節 房事‧夫妻關係
第三節 婚姻倫理:傳統與挑戰
第四節 中國的處境
第八章 倫理學多邊對談
從基督宗教、儒家及演化論看利他主義
第一節 演化論與利他主義
第二節 演化論對利他主義的解釋
第三節 儒家與演化生物學
第四節 基督教倫理中的血親關切
第五節 愛的秩序:聖多瑪斯與演化論
第六節 愛的秩序作為耶儒會通的切入點
第七節 耶、儒、演化論三邊對談
參考文獻
自序
上編 原理
第一章 本性(上)
意志哲學中的「意志薄弱/不自制」
第一節 「意志薄弱」問題的經典界說
第二節 聖多瑪斯論「不自制」
第三節 意志與意志哲學
第二章 本性(下)
慾:聖多瑪斯與拉内慾觀念的比較
第一節 「慾」之三端
第二節 聖多瑪斯對慾的界説
第三節 拉内論慾的神學涵義
第四節 慾觀念的比較與反思
第三章 從本性走向超性
異教的羅馬有無德性:「異教德性」理論
第一節 德性與德性倫理學
第二節 聖多瑪斯對德性的分類
第三節 無恩寵灌輸的異教德性
第四節 異教德性相對灌輸性德性:「真正但不完善的德性」
第五節 走向灌輸性德性的異教德性
第六節 反思異教德性
第四章 本性與超性的相通
自然性向與良知
第一節 自然性向與自然本性:習性
第二節 自然性向與超性:共同本性
第三節 自然性向與情感性
第四節 自然性向與良知
第五節 自然性向對多元宗教對談與人類和平的啓示
第五章 本性與超性的聯合
愛的哲學:慾愛、友愛與聖愛
第一節 聖愛─慾愛與友愛之愛─慾望之愛
第二節 聖多瑪斯:友愛之愛與慾望之愛
第三節 田立克:聖愛─慾愛的統一體
第四節 聖多瑪斯與田立克愛觀念的比較
下編 應用
第六章 生態倫理
現代語境下再思中世紀思想遺產
第一節 生態倫理與生態中心論
第二節 人的靈魂與生態倫理:對聖多瑪斯的批評
第三節 善之等階與生態倫理:對聖多瑪斯思想的正面發掘
第四節 天主創造的人與生態:從聖多瑪斯反思生態倫理
第五節 分析對聖多瑪斯的不同評價
第六節 中國文化語境下的生態倫理
第七章 婚姻與性倫理
婚姻中的兩性關係:傳統與挑戰
第一節 婚姻‧聖事
第二節 房事‧夫妻關係
第三節 婚姻倫理:傳統與挑戰
第四節 中國的處境
第八章 倫理學多邊對談
從基督宗教、儒家及演化論看利他主義
第一節 演化論與利他主義
第二節 演化論對利他主義的解釋
第三節 儒家與演化生物學
第四節 基督教倫理中的血親關切
第五節 愛的秩序:聖多瑪斯與演化論
第六節 愛的秩序作為耶儒會通的切入點
第七節 耶、儒、演化論三邊對談
參考文獻
序
推薦序
陳序
亞洲被譽為偉大宗教的搖籃。然而,除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之外,包括佛教、儒教、道教、印度教、神道教在内的世界各大主要宗教,以及多不勝數的民間宗教都未被認可為擁有「神學體系」(theologies)。有關這些宗教的科目在神學課程安排上普遍缺席的現象令人側目。即便存在,類似的科目也只是以選修的形式出現,旨在對世界諸大宗教加以簡要介紹而已。以西方神學家最嚴格意義上的「神學」(Theology)標準來看,這些科目都不能算是「神學的」。這種帶有些許歧視意味的觀點,基於「神學」之作為基督宗教研究以及服務於基督教會之需的悠久歷史。神學這門關於基督信仰的科學,更多披戴著希臘與拉丁兩種語文,並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由這兩種文化的思維邏輯所引領,而於神學院系當中──例如神職人員的培育中心等──加以傳授。在該傳統當中,曾被視為「鄉儺異教」、「百無一用」、甚或對基督宗教貽害萬方的亞洲宗教,在神學世界的版圖上並無立錐之地。
面對我們在實際遭遇和學術交流過程中所獲得的嶄新理解,這樣的世界宗教觀則有失於偏頗。因此,傳統的保守神學觀念便難免坐井觀天之隘見,且對於我們當下這個「平面的」、「動態的」、「開放的」世界中的宗教間對談、福傳事業、甚至基督徒生活均荼毒匪淺。將神學視為獨一無二的基督教科學,正如「教會之外無救恩」(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的教條一樣,遭到來自於廣大神學界自身的挑戰,這也引致羅馬天主教會的開放政策(梵二會議)和當前神學的全球化,最終成就了世界神學的崛興。作為世界神學的一部分,文化神學、宗教神學也進而贏得了一定的尊重。它們對於神學作為信仰科學的成長所做出的貢獻,甚至獲得了傳統神學最為忠實的捍衛者──基要主義者們的極力贊賞。
正是在這一脈絡當中,亞洲神學(Asian theology)浮出水面,最初羞羞答答、身居邊緣,宛如「猶抱琵琶半遮面」,但近來則勇猛精進,鋒芒畢露。亞洲神學的興起正在經歷著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亞洲」嶄露頭角,第二階段則是作為「亞洲的」關鍵部分而進行自我構建。著名神學家、喬治城大學的潘庭卓(Peter C. Phan)教授在評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九九年頒佈的教宗通諭《教會在亞洲》(Ecclesia in Asia)時,曾對「在亞洲」(in Asia)和「亞洲的」(of Asia)兩個概念進行了區分。在第一階段中,除南韓和香港外,幾乎所有的神學機構都未曾被亞洲各國所承認。故此,對於亞洲而言,倍感陌生乃至於難以接受的「亞洲神學」不得不奮起圖存。在這一階段,為獲得接受,亞洲神學採用了利瑪竇的策略,先以朋友的身段示予亞洲(可參看利瑪竇《交友論》),隨後,它必須展現自身積極參與亞洲主流生活的意願。因此,亞洲神學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帶有「亞洲面容、亞洲聲音、為亞洲服務」的基督教神學。中國、印度、韓國、斯里蘭卡、台灣、泰國、越南的神學家們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神學著作,便運用了這一策略。他們的著作多數是對聖經、基督信仰、教會訓導等的介紹與展示,著者們使用各自的母語寫作,並在各自的文化(哲學、宗教)脈絡中完成他們的闡釋,例如輔仁學派(包括于斌樞機、羅光總主教、成世光主教,以及耶穌會士陳綸緒神父、房志榮神父、谷寒松神父等)的著作。自不待言,暫且抛開為打造最嚴格意義上的亞洲神學所付出的孜孜不倦的辛勞不談,第一階段的構建工作可以被帶有批判性地淡化為一場面部整形手術──這是一種貌似不幸的措辭,但對於「在亞洲的基督教神學」而言卻是千真萬確的描述。亞洲神學的第一階段成功地「在亞洲」亮相,但問題在於,它還不是「亞洲的」,它仍處於實驗當中。
我們必須再進一步來到成就亞洲神學的第二階段,也就是把自身構建為「亞洲的」的天主道成肉身之途。亞洲神學的確不僅展示著亞洲的面容、亞洲的聲音,而且更多地是以亞洲的邏輯進行思考,並分擔著亞洲的命運。一言以蔽之,亞洲神學必須「道成肉身」而成為「亞洲的」。
亞洲神學的第二階段便開始帶著如此的省覺舉步前行。神學在亞洲的興盛──包括韓國的民衆神學(Minjung Theology)、台灣的第三眼神學(Third Eyes Theology,宋泉盛)和後殖民主義神學(長榮大學黃伯和)、日本的處境神學(Situational Theology)和神痛神學(Pain of God Theology,北森和雄)、泰國的水牛神學(Water-Buffalo-Theology)、人間神學(Planetary Theology)或亞洲版的解放神學(巴拉蘇里亞,Tissa Balasuriya)、宗教多元論神學(迪皮伊,Jacques Dupuis)等等──都確證了亞洲神學方興未艾的態勢,以及宣稱自身發展路向、承當自身命運的勃勃雄心。亞洲神學深刻地浸淫於亞洲生活的深層,把握著亞洲的命脈,懷抱著亞洲的生活方式。總而言之,亞洲神學在反映亞洲精神、以亞洲的邏輯進行反思、把捉亞洲命脈、活出亞洲生命的意義上,必須是亞洲式的,這也是基督降生成人、度人之生活、承擔人之命運、以人的方式思維的路向。
王濤博士的專著《本性與超性:聖多瑪斯‧亞奎納倫理學反思》應當被理解為是在上述第二階段的框架内構建一種中國神學(Chinese Theology)的努力。他在神學上反思了聖多瑪斯兩個最基本的概念:本性(實在)與超性(超越),但這一反思並非單純在士林哲學傳統中進行,而更多是在中國文化如儒教的脈絡中展開,後者具有亞洲思維模式的印跡:即依據實踐生活來思考。「實在」的形上學根基不僅是抽象的存有,更是具體堅實的人生;「超越」所表達的不再是從人類世界一飛衝天,進入至高的神聖世界,而毋寧是達致君子─聖賢層次的持續性自我修為,一如修身養性的階段,王博士專著的副標題「聖多瑪斯‧亞奎納倫理學反思」清晰地指明了這一意義。在此,我們發現,王博士在對超越性的人文主義(transcendent Humanism)進行追問的過程當中,是如此深刻和精到地運用了卡爾‧拉内(Karl Rahner)「在世天主」(Gott in Welt)的形上學洞見,而這恰恰是亞洲神學的核心所在。
我鄭重向那些對亞洲神學的發展、拉内的「新多瑪斯主義」、亞洲神學脈絡中的基督教倫理學,特別是聖多瑪斯神哲學思想及中世士林思想研究方面充滿興趣的諸位,推薦王濤博士這部充滿哲思智慧的著作。
陳文團(Tran Van Doan)
長榮大學神學院
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
陳序
亞洲被譽為偉大宗教的搖籃。然而,除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之外,包括佛教、儒教、道教、印度教、神道教在内的世界各大主要宗教,以及多不勝數的民間宗教都未被認可為擁有「神學體系」(theologies)。有關這些宗教的科目在神學課程安排上普遍缺席的現象令人側目。即便存在,類似的科目也只是以選修的形式出現,旨在對世界諸大宗教加以簡要介紹而已。以西方神學家最嚴格意義上的「神學」(Theology)標準來看,這些科目都不能算是「神學的」。這種帶有些許歧視意味的觀點,基於「神學」之作為基督宗教研究以及服務於基督教會之需的悠久歷史。神學這門關於基督信仰的科學,更多披戴著希臘與拉丁兩種語文,並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由這兩種文化的思維邏輯所引領,而於神學院系當中──例如神職人員的培育中心等──加以傳授。在該傳統當中,曾被視為「鄉儺異教」、「百無一用」、甚或對基督宗教貽害萬方的亞洲宗教,在神學世界的版圖上並無立錐之地。
面對我們在實際遭遇和學術交流過程中所獲得的嶄新理解,這樣的世界宗教觀則有失於偏頗。因此,傳統的保守神學觀念便難免坐井觀天之隘見,且對於我們當下這個「平面的」、「動態的」、「開放的」世界中的宗教間對談、福傳事業、甚至基督徒生活均荼毒匪淺。將神學視為獨一無二的基督教科學,正如「教會之外無救恩」(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的教條一樣,遭到來自於廣大神學界自身的挑戰,這也引致羅馬天主教會的開放政策(梵二會議)和當前神學的全球化,最終成就了世界神學的崛興。作為世界神學的一部分,文化神學、宗教神學也進而贏得了一定的尊重。它們對於神學作為信仰科學的成長所做出的貢獻,甚至獲得了傳統神學最為忠實的捍衛者──基要主義者們的極力贊賞。
正是在這一脈絡當中,亞洲神學(Asian theology)浮出水面,最初羞羞答答、身居邊緣,宛如「猶抱琵琶半遮面」,但近來則勇猛精進,鋒芒畢露。亞洲神學的興起正在經歷著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亞洲」嶄露頭角,第二階段則是作為「亞洲的」關鍵部分而進行自我構建。著名神學家、喬治城大學的潘庭卓(Peter C. Phan)教授在評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九九年頒佈的教宗通諭《教會在亞洲》(Ecclesia in Asia)時,曾對「在亞洲」(in Asia)和「亞洲的」(of Asia)兩個概念進行了區分。在第一階段中,除南韓和香港外,幾乎所有的神學機構都未曾被亞洲各國所承認。故此,對於亞洲而言,倍感陌生乃至於難以接受的「亞洲神學」不得不奮起圖存。在這一階段,為獲得接受,亞洲神學採用了利瑪竇的策略,先以朋友的身段示予亞洲(可參看利瑪竇《交友論》),隨後,它必須展現自身積極參與亞洲主流生活的意願。因此,亞洲神學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帶有「亞洲面容、亞洲聲音、為亞洲服務」的基督教神學。中國、印度、韓國、斯里蘭卡、台灣、泰國、越南的神學家們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神學著作,便運用了這一策略。他們的著作多數是對聖經、基督信仰、教會訓導等的介紹與展示,著者們使用各自的母語寫作,並在各自的文化(哲學、宗教)脈絡中完成他們的闡釋,例如輔仁學派(包括于斌樞機、羅光總主教、成世光主教,以及耶穌會士陳綸緒神父、房志榮神父、谷寒松神父等)的著作。自不待言,暫且抛開為打造最嚴格意義上的亞洲神學所付出的孜孜不倦的辛勞不談,第一階段的構建工作可以被帶有批判性地淡化為一場面部整形手術──這是一種貌似不幸的措辭,但對於「在亞洲的基督教神學」而言卻是千真萬確的描述。亞洲神學的第一階段成功地「在亞洲」亮相,但問題在於,它還不是「亞洲的」,它仍處於實驗當中。
我們必須再進一步來到成就亞洲神學的第二階段,也就是把自身構建為「亞洲的」的天主道成肉身之途。亞洲神學的確不僅展示著亞洲的面容、亞洲的聲音,而且更多地是以亞洲的邏輯進行思考,並分擔著亞洲的命運。一言以蔽之,亞洲神學必須「道成肉身」而成為「亞洲的」。
亞洲神學的第二階段便開始帶著如此的省覺舉步前行。神學在亞洲的興盛──包括韓國的民衆神學(Minjung Theology)、台灣的第三眼神學(Third Eyes Theology,宋泉盛)和後殖民主義神學(長榮大學黃伯和)、日本的處境神學(Situational Theology)和神痛神學(Pain of God Theology,北森和雄)、泰國的水牛神學(Water-Buffalo-Theology)、人間神學(Planetary Theology)或亞洲版的解放神學(巴拉蘇里亞,Tissa Balasuriya)、宗教多元論神學(迪皮伊,Jacques Dupuis)等等──都確證了亞洲神學方興未艾的態勢,以及宣稱自身發展路向、承當自身命運的勃勃雄心。亞洲神學深刻地浸淫於亞洲生活的深層,把握著亞洲的命脈,懷抱著亞洲的生活方式。總而言之,亞洲神學在反映亞洲精神、以亞洲的邏輯進行反思、把捉亞洲命脈、活出亞洲生命的意義上,必須是亞洲式的,這也是基督降生成人、度人之生活、承擔人之命運、以人的方式思維的路向。
王濤博士的專著《本性與超性:聖多瑪斯‧亞奎納倫理學反思》應當被理解為是在上述第二階段的框架内構建一種中國神學(Chinese Theology)的努力。他在神學上反思了聖多瑪斯兩個最基本的概念:本性(實在)與超性(超越),但這一反思並非單純在士林哲學傳統中進行,而更多是在中國文化如儒教的脈絡中展開,後者具有亞洲思維模式的印跡:即依據實踐生活來思考。「實在」的形上學根基不僅是抽象的存有,更是具體堅實的人生;「超越」所表達的不再是從人類世界一飛衝天,進入至高的神聖世界,而毋寧是達致君子─聖賢層次的持續性自我修為,一如修身養性的階段,王博士專著的副標題「聖多瑪斯‧亞奎納倫理學反思」清晰地指明了這一意義。在此,我們發現,王博士在對超越性的人文主義(transcendent Humanism)進行追問的過程當中,是如此深刻和精到地運用了卡爾‧拉内(Karl Rahner)「在世天主」(Gott in Welt)的形上學洞見,而這恰恰是亞洲神學的核心所在。
我鄭重向那些對亞洲神學的發展、拉内的「新多瑪斯主義」、亞洲神學脈絡中的基督教倫理學,特別是聖多瑪斯神哲學思想及中世士林思想研究方面充滿興趣的諸位,推薦王濤博士這部充滿哲思智慧的著作。
陳文團(Tran Van Doan)
長榮大學神學院
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