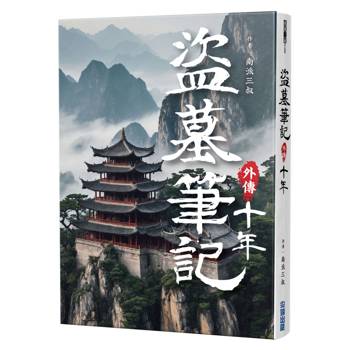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新編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32 |
📌宗教79折起 |
$ 357 |
基督教總論 |
$ 369 |
中文書 |
$ 370 |
基督宗教 |
$ 378 |
基督教總論 |
$ 378 |
宗教命理 |
電子書 |
$ 420 |
基督教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新編基督教在華傳教史
內容簡介
《新編中國基督教史綱》是裴士丹教授醞釀和撰寫了近三十年的學術成果,刷新了自1929年賴德烈出版《基督教在華傳教史》以來的長段空白。該書以簡潔而精準的表述梳理了自西元7世紀景教來華至21世紀頭十年基督宗教在華傳教活動的通史(包括俄羅斯東正教在華傳教史),並深刻地分析和揭示了基督教在華傳播的各個階段中所面臨的文化與政治等方面的本土化困境;同時該書還全面介紹了文革之後基督教在中國的迅速發展以及對隨之出現的複雜局面的深刻反思。Paul Cohen對此的評價是:「沒有人對基督教在華事業的複雜性比裴士丹教授瞭解得更為透徹」、「這是一本真正的突破性的著作」;Mark Noll稱該書為中國基督教史領域的聖經,讀者通過該書(無需閱讀其它著作)即可全面而準確地瞭解基督教在華傳播的整個動態歷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裴士丹(Daniel H. Bay)
美國加爾文大學前歷史系教授和亞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基督教史和美國傳教史資深專家。畢業於斯坦福大學(學士)、密西根大學(碩士、博士)。代表作有《基督教在中國:從18世紀至今》(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新編基督教在華傳教史》(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Wiley-Blackwell, 2012)等。
譯者簡介
尹文涓(Yin Wenjuan)
2003年獲北京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清華大學哲學系博士後(2006年),法國巴黎11大古典法研究中心博士後(2009年)。現任教於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系,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外文學關係、中國基督教史、海外漢學。相關譯著有《歷史遺蹤—正福寺天主教墓地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傳教士裨治文傳》(廣西師大出版社,2008年)。
裴士丹(Daniel H. Bay)
美國加爾文大學前歷史系教授和亞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基督教史和美國傳教史資深專家。畢業於斯坦福大學(學士)、密西根大學(碩士、博士)。代表作有《基督教在中國:從18世紀至今》(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新編基督教在華傳教史》(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Wiley-Blackwell, 2012)等。
譯者簡介
尹文涓(Yin Wenjuan)
2003年獲北京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清華大學哲學系博士後(2006年),法國巴黎11大古典法研究中心博士後(2009年)。現任教於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系,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外文學關係、中國基督教史、海外漢學。相關譯著有《歷史遺蹤—正福寺天主教墓地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傳教士裨治文傳》(廣西師大出版社,2008年)。
目錄
總序 vi
致謝 xv
前言 1
第一章 唐代景教與蒙元時期基督教在華的傳播:635–1368 5
第二章 近代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及其命運 23
第三章 基督新教來華、天主教回歸以及中國本土教會的萌芽:1800–1860 53
第四章 清末基督教在華的擴張和機構建設:1860–1902 85
第五章 傳教活動的「黃金時代」和「中西新教合作機制」:1902–1927 119
第六章 中國基督教的多重危機:1927–1950 157
第七章 基督教與新中國:1950–1966 205
第八章 從文革結束到21 世紀初的中國教會 239
附錄 俄羅斯東正教會與在華傳教使團 271
參考書目 281
索引 301
致謝 xv
前言 1
第一章 唐代景教與蒙元時期基督教在華的傳播:635–1368 5
第二章 近代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及其命運 23
第三章 基督新教來華、天主教回歸以及中國本土教會的萌芽:1800–1860 53
第四章 清末基督教在華的擴張和機構建設:1860–1902 85
第五章 傳教活動的「黃金時代」和「中西新教合作機制」:1902–1927 119
第六章 中國基督教的多重危機:1927–1950 157
第七章 基督教與新中國:1950–1966 205
第八章 從文革結束到21 世紀初的中國教會 239
附錄 俄羅斯東正教會與在華傳教使團 271
參考書目 281
索引 301
序
致謝
在本書的醞釀和撰寫過程中,我曾受惠於多人。本研究始自1985 年,那時我尚在堪薩斯大學任教,那一年我的「基督教在華傳教史」課題獲得了亨利‧盧斯(Henry Luce) 基金會的資助。自那時起,亨利‧盧斯基金會的亞洲項目主管勞泰瑞(Terry Lautz) 先生不僅給本課題提供了諸多的、持之以恆的支持,在這過去的25 年中,我們還建立起珍貴的友誼。
諸多從事中國教會和中國基督教研究的學者如:狄德滿(Gary Tiedemann)、陳劍光(Chan Kim-kwong)、洛德威克(Kathleen Lodwick)、張格物(Murray Rubenstein)、鄢華陽(Bob Entenmann)、戴日安(Ryan Dunch)、連曦(Lian Xi)、魯珍晞(Jessie Lutz)、李可柔(Carol Hamrin)、馬德森(Dick Madsen)、孟德衛(David Mungello)、魏思特(Phil West)、吳秀良(Silas Wu) 等同仁,為本課題的研究提供了無私的幫助和鼓勵。
除了基督教研究領域的同道學者給予我的支援,本課題還得到了中國學研究領域諸多資深學者的勉勵和關懷。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 和楊格(Ernie Young) 兩位教授是我1960 年代在密西根州立大學安娜堡分校求學時的導師,這兩位出色的導師對我從不吝於指教,並一再熱心為我撰寫推薦信。我還要感謝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和劉廣京(K. C. Liu) 這兩位已故的前輩學者、以及柯文(Paul Cohen) 和史景遷(Jonathan Spence) 兩位教授為我提供的各種幫助。同時,我還從瓦克(Grant Wacker) 教授、諾爾(Mark Noll) 教授、卡彭特(Joel Carpenter) 教授、哈奇(Nathan Hatch)、布魯姆何費(Edith Blumhofer) 等從事美國宗教研究的學者那裡,學習到了如何拓寬研究視野、將基督教史的關注納入到更寬闊的宗教研究的大背景中去。此外,我還要感謝安德森(Jerry Anderson) 博士,他邀請我參加了他的課題小組,該課題小組在1990 年代的大部分時間是設在紐黑文的海外傳教研究中心(Overseas Ministers Studies Center, New Haven);在那裡,我深受沃茲(Andrew Walls)、桑奈(LaminSanneh)、弗里肯貝格(Frykenberg) 以及達納‧羅伯特(Dana Robert) 等學者的新觀念和分析模式的啟發。本書從醞釀到完成是一場歷經數十載的「奧德賽」之旅。
1984–1985 年,我在臺灣剛著手本課題研究之時,國立臺灣大學和中華福音神學院的查時傑(James Cha/Cha Shih-chieh) 教授給予了我最大的支援,他向我全面開放了他收藏在神學院裡關於基督教研究的豐富的文獻。與此同時,已故的趙天恩(Jonathan Tien-en Chao) 先生也同樣毫無保留地為我提供了他收藏在香港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的珍貴史料。香港的陳劍光(Kim Chan) 教授在過去的20 多年裡不僅是我的同事、合作者,還是我可貴的朋友。在香港,我還多次承蒙吳梓明(Peter Ng) 教授、梁元生(Philip Leung) 教授、黃文江(Timothy Wong) 教授和李金強(K. K. Lee) 教授的接待。
在中國大陸,我到處都欠下了人情。1986 年秋天,在李世瑜先生的陪伴下,我們一起走遍了山東全省:我們一起參觀各地的教堂,我們曾經在淩晨3 點才找到旅館歇腳,也曾一起在水泥地面上打地鋪過夜,曾一起搭乘農機車趕路,還曾一起走訪仍在開展活動的「耶穌家庭」原址......還有許多其它的冒險經歷。李世瑜先生當時已經65 歲,卻能在爬泰山登頂時遙遙領先於我,喝「老白乾」時,酒量也遠勝於我。我對他有無盡的感謝之情,不僅僅是因為我們之間深厚的友誼,還因為他讓我對民間宗教信仰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體認。
在中國大陸,我還有很多的同仁和朋友,如上海大學的陶飛亞教授和山東大學的劉天路教授,兩位教授當時均任教於山東大學,陶飛亞教授如今在上海大學工作。復旦大學的徐以驊教授、以及華中師範大學(現任教於山東大學)的劉家峰教授。在老一輩的學者中,山東大學的路遙教授和華中師範大學的校長章開沅教授一向好客且樂於助人。我還要感謝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先生,以及前社科院副院長趙復三先生。他們以及所有在此未能一一述及的朋友,讓我多年來在中國的研究既感到心情愉快、也充滿了智識上的碰撞與交匯。
我要特別感謝諾爾(Mark Noll) 和卡彭特(Joel Carpenter),他們不辭辛苦通讀了本書初稿所有章節並提出修改意見。還要感謝布萊克威爾出版社(現在的威利-布萊克威爾)的編輯安德魯‧胡弗利(Andrew Humphries) 和伊索貝爾‧拜恩頓(Isobel Bainton),感謝他們對我書稿的拖延和錯漏所表現出的極大耐心。感謝加爾文大學在2007 年為我提供了休假,並在數年間慷慨地資助了我的學術訪問旅行;我還要感謝加爾文基督教研究中心在我需要的時刻所提供的一切幫助。十年前,加爾文大學歷史系和亞洲研究項目的同事們熱情地歡迎我加入到這個大家庭,並為我的研究和創作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對此我充滿感激之情。
從某些方面而言,本書中的觀點和思想肇始於30 多年前。儘管我從他人那裡已獲益良多,但囿於本人才學,本書仍難免存在缺陷和不足。
我將本書獻給安德魯‧沃茲(Andrew Walls),他待人總是親和而彬彬有禮,同時也大膽地拓展了我們關於西方國家之外基督教史研究的視域;我還將本書獻給李世瑜,他像安德魯一樣,賦予我學術生涯和人生方面諸多啟迪。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妻子珍妮,這些年來,她不僅和我分享了對中國的熱愛,並一直督促我完成這項任務。沒有她,我無法完成本書。親愛的,謝謝你!
裴士丹
密西根州,急流城
2010年10月
前言
這本書在我心中已經醞釀多年,從某些方面而言,本書是我過去三十年學術生涯所有努力之結晶。二十世紀80 年代初期,當基督教和其它宗教一起在文革後的中國大陸開始復興、並展現出強大活力的時候,眾多中國和包括我在內的歐美新一代學者,都意識到了中國基督教史是一個重要而且尚待開拓的研究領域。實際上,這一領域的某些方面在當時已經有了很好的研究,這些研究主要集中於外國傳教士生平及其在華事工。然而,在中國基督教史這幅宏大的畫卷中,在中外教會共同努力將基督教信仰培植於中國文化土壤的這一過程中,更重要的畫面是中國本土基督徒的成長和參與。這一過程具有一個持續的、鮮明的發展規律:中國基督教徒首先是參與者,然後是附隸於外國傳教士的合作夥伴,最後成為中國教會的繼承者、或是獨掌教會的「主人」。這也是一個「跨文化交流」的過程,其結果是在我們的時代締造了一個異常複雜的中國基督教世界1 。這些年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試圖追尋過去數個世紀中這一文化交流活動的主要特徵。我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中國大陸;關於中國少數民族以及海外華人群體的基督教信仰,則還有待於其他學者的深入探討。
有很多人都和我談到了出版這樣一本中國基督教通史的必要性。而我自己也感到了強烈的願望去撰寫一本這樣的書—即使僅僅是為了進一步加深我自己對於中國基督教的理解。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的目標是將自己過去25 年的所有研究納入到一個連貫的敘事中去。此前做出類似努力的著作有賴德烈(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的《基督教在華傳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1929),這部鴻篇巨著文獻詳備,遺憾的是該書出版距今已有80 多年。鮑勃‧懷特(Bob Whyte) 所著、1988 年出版的《未結束的相遇:中國與基督教》(Unfinished Encounter: China and Christianity) 同樣是一部卓越的通史性著作。這是懷特本人主持的一項中國研究專案的成果,該項目歷時多年,得到了英國多個新教和天主教團體的聯合資助,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國基督教會聯合會(British Council of Churches) 下屬的愛丁堡世界宣教大會(Conference for World Mission)。但是該書早已絕版,而且該書未能收錄過去20 多年來本領域的優秀研究成果,而這些成果絕大多數是中國學者的貢獻。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外方傳教會中國專案負責人沙百里神父所著的《基督教在中國:從西元600 年到2000 年》(Christians in China A.D. 600 to 2000,法語版,Paris,2002;英譯版,San Francisco, CA: Ignatius Press, 2007),該書重點對天主教在華的事工進行了詳實而全面的論述。從某個角度而言,沙百里神父在該書中對天主教的偏重,恰好平衡了包括拙著在內的諸多作品對基督新教的偏重。
本書在總體結構上,試圖儘量在現代早期部分(1800 年之前共兩章)、現代部分1800 年-1950 年共四章)、當代部分(1950 年至今共兩章)的時期之間保持平衡。本書的核心部分是第3 章至第6 章的這四章,這幾章討論了在華外國傳教差會和中國教會之間橫亙了150 多年的衝突與張力;以及另外一個反覆出現的重大話題,那就是中國政府或統治集團長期以來對宗教活動一貫的監控和壓制,其結果是,基督教在中國通常不僅不先被視為一種宗教或信仰體系,而是被看作可能會導致無窮麻煩的隱患因素。
本書附錄部分,簡要敘述了俄國東正教會在華傳教使團自17 世紀末入華、至20 世紀中期在華活動終結的這一段歷史。俄國東正教在華使團的歷史是中國基督教史中不可忽略的一節,但鑒於其諸多獨特之處,本書為避免將其事蹟零散分佈於各章,單闢附錄對此進行了概述。
我決定在本書結尾不做一個獨立的「結論」。正如目前中國的許多事務一樣,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仍處於不確定的狀態。因此,除了第八章最後幾頁的小結之外,我不想再對基督教在中國從當下到未來的發展做更多的推斷—尤其是在評論家們對「當下」的情形還很難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但我仍希望本書能啟發讀者對某些重大問題的認識,其一就是,基督教在脫掉我們稱之為「基督教世界」的這一西方文化外衣之後,是完全能夠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長的—當然,這一適應過程通常會經歷一段可能是破壞性的跨文化交流。由此,我們獲得的教訓是:在「非基督教世界」,人們同樣可以蒙主恩典。本書希望表達的另一個觀點是:中國人在接受基督教(或說基督教的多個宗派)的過程中,體現出了非凡的靈活性與創造力。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景教使用道教和佛教的術語譯經、19 世紀太平天國領袖富有感召力的聖經幻象、中國天主教徒重新命名祭祖儀式以變通教皇禁令的手段、以及今天中國農村地區頻繁出現的白蓮教式的新教千禧年宗派。這一切,都會引導觀察者得出一個結論:萬變不離其宗(plus a change, plus c’est la mme chose)。
註:
1 沃茲,《從基督教世界到世界基督教》(Andrew Walls, From Christendom to World Christianity),收入沃茲編纂,《基督教歷史中的跨文化過程》(The Cross-Cultural Process in Christian History, MaryknoII, NY: Orbis, 2001)。
在本書的醞釀和撰寫過程中,我曾受惠於多人。本研究始自1985 年,那時我尚在堪薩斯大學任教,那一年我的「基督教在華傳教史」課題獲得了亨利‧盧斯(Henry Luce) 基金會的資助。自那時起,亨利‧盧斯基金會的亞洲項目主管勞泰瑞(Terry Lautz) 先生不僅給本課題提供了諸多的、持之以恆的支持,在這過去的25 年中,我們還建立起珍貴的友誼。
諸多從事中國教會和中國基督教研究的學者如:狄德滿(Gary Tiedemann)、陳劍光(Chan Kim-kwong)、洛德威克(Kathleen Lodwick)、張格物(Murray Rubenstein)、鄢華陽(Bob Entenmann)、戴日安(Ryan Dunch)、連曦(Lian Xi)、魯珍晞(Jessie Lutz)、李可柔(Carol Hamrin)、馬德森(Dick Madsen)、孟德衛(David Mungello)、魏思特(Phil West)、吳秀良(Silas Wu) 等同仁,為本課題的研究提供了無私的幫助和鼓勵。
除了基督教研究領域的同道學者給予我的支援,本課題還得到了中國學研究領域諸多資深學者的勉勵和關懷。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 和楊格(Ernie Young) 兩位教授是我1960 年代在密西根州立大學安娜堡分校求學時的導師,這兩位出色的導師對我從不吝於指教,並一再熱心為我撰寫推薦信。我還要感謝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和劉廣京(K. C. Liu) 這兩位已故的前輩學者、以及柯文(Paul Cohen) 和史景遷(Jonathan Spence) 兩位教授為我提供的各種幫助。同時,我還從瓦克(Grant Wacker) 教授、諾爾(Mark Noll) 教授、卡彭特(Joel Carpenter) 教授、哈奇(Nathan Hatch)、布魯姆何費(Edith Blumhofer) 等從事美國宗教研究的學者那裡,學習到了如何拓寬研究視野、將基督教史的關注納入到更寬闊的宗教研究的大背景中去。此外,我還要感謝安德森(Jerry Anderson) 博士,他邀請我參加了他的課題小組,該課題小組在1990 年代的大部分時間是設在紐黑文的海外傳教研究中心(Overseas Ministers Studies Center, New Haven);在那裡,我深受沃茲(Andrew Walls)、桑奈(LaminSanneh)、弗里肯貝格(Frykenberg) 以及達納‧羅伯特(Dana Robert) 等學者的新觀念和分析模式的啟發。本書從醞釀到完成是一場歷經數十載的「奧德賽」之旅。
1984–1985 年,我在臺灣剛著手本課題研究之時,國立臺灣大學和中華福音神學院的查時傑(James Cha/Cha Shih-chieh) 教授給予了我最大的支援,他向我全面開放了他收藏在神學院裡關於基督教研究的豐富的文獻。與此同時,已故的趙天恩(Jonathan Tien-en Chao) 先生也同樣毫無保留地為我提供了他收藏在香港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的珍貴史料。香港的陳劍光(Kim Chan) 教授在過去的20 多年裡不僅是我的同事、合作者,還是我可貴的朋友。在香港,我還多次承蒙吳梓明(Peter Ng) 教授、梁元生(Philip Leung) 教授、黃文江(Timothy Wong) 教授和李金強(K. K. Lee) 教授的接待。
在中國大陸,我到處都欠下了人情。1986 年秋天,在李世瑜先生的陪伴下,我們一起走遍了山東全省:我們一起參觀各地的教堂,我們曾經在淩晨3 點才找到旅館歇腳,也曾一起在水泥地面上打地鋪過夜,曾一起搭乘農機車趕路,還曾一起走訪仍在開展活動的「耶穌家庭」原址......還有許多其它的冒險經歷。李世瑜先生當時已經65 歲,卻能在爬泰山登頂時遙遙領先於我,喝「老白乾」時,酒量也遠勝於我。我對他有無盡的感謝之情,不僅僅是因為我們之間深厚的友誼,還因為他讓我對民間宗教信仰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體認。
在中國大陸,我還有很多的同仁和朋友,如上海大學的陶飛亞教授和山東大學的劉天路教授,兩位教授當時均任教於山東大學,陶飛亞教授如今在上海大學工作。復旦大學的徐以驊教授、以及華中師範大學(現任教於山東大學)的劉家峰教授。在老一輩的學者中,山東大學的路遙教授和華中師範大學的校長章開沅教授一向好客且樂於助人。我還要感謝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先生,以及前社科院副院長趙復三先生。他們以及所有在此未能一一述及的朋友,讓我多年來在中國的研究既感到心情愉快、也充滿了智識上的碰撞與交匯。
我要特別感謝諾爾(Mark Noll) 和卡彭特(Joel Carpenter),他們不辭辛苦通讀了本書初稿所有章節並提出修改意見。還要感謝布萊克威爾出版社(現在的威利-布萊克威爾)的編輯安德魯‧胡弗利(Andrew Humphries) 和伊索貝爾‧拜恩頓(Isobel Bainton),感謝他們對我書稿的拖延和錯漏所表現出的極大耐心。感謝加爾文大學在2007 年為我提供了休假,並在數年間慷慨地資助了我的學術訪問旅行;我還要感謝加爾文基督教研究中心在我需要的時刻所提供的一切幫助。十年前,加爾文大學歷史系和亞洲研究項目的同事們熱情地歡迎我加入到這個大家庭,並為我的研究和創作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對此我充滿感激之情。
從某些方面而言,本書中的觀點和思想肇始於30 多年前。儘管我從他人那裡已獲益良多,但囿於本人才學,本書仍難免存在缺陷和不足。
我將本書獻給安德魯‧沃茲(Andrew Walls),他待人總是親和而彬彬有禮,同時也大膽地拓展了我們關於西方國家之外基督教史研究的視域;我還將本書獻給李世瑜,他像安德魯一樣,賦予我學術生涯和人生方面諸多啟迪。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妻子珍妮,這些年來,她不僅和我分享了對中國的熱愛,並一直督促我完成這項任務。沒有她,我無法完成本書。親愛的,謝謝你!
裴士丹
密西根州,急流城
2010年10月
前言
這本書在我心中已經醞釀多年,從某些方面而言,本書是我過去三十年學術生涯所有努力之結晶。二十世紀80 年代初期,當基督教和其它宗教一起在文革後的中國大陸開始復興、並展現出強大活力的時候,眾多中國和包括我在內的歐美新一代學者,都意識到了中國基督教史是一個重要而且尚待開拓的研究領域。實際上,這一領域的某些方面在當時已經有了很好的研究,這些研究主要集中於外國傳教士生平及其在華事工。然而,在中國基督教史這幅宏大的畫卷中,在中外教會共同努力將基督教信仰培植於中國文化土壤的這一過程中,更重要的畫面是中國本土基督徒的成長和參與。這一過程具有一個持續的、鮮明的發展規律:中國基督教徒首先是參與者,然後是附隸於外國傳教士的合作夥伴,最後成為中國教會的繼承者、或是獨掌教會的「主人」。這也是一個「跨文化交流」的過程,其結果是在我們的時代締造了一個異常複雜的中國基督教世界1 。這些年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試圖追尋過去數個世紀中這一文化交流活動的主要特徵。我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中國大陸;關於中國少數民族以及海外華人群體的基督教信仰,則還有待於其他學者的深入探討。
有很多人都和我談到了出版這樣一本中國基督教通史的必要性。而我自己也感到了強烈的願望去撰寫一本這樣的書—即使僅僅是為了進一步加深我自己對於中國基督教的理解。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的目標是將自己過去25 年的所有研究納入到一個連貫的敘事中去。此前做出類似努力的著作有賴德烈(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的《基督教在華傳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1929),這部鴻篇巨著文獻詳備,遺憾的是該書出版距今已有80 多年。鮑勃‧懷特(Bob Whyte) 所著、1988 年出版的《未結束的相遇:中國與基督教》(Unfinished Encounter: China and Christianity) 同樣是一部卓越的通史性著作。這是懷特本人主持的一項中國研究專案的成果,該項目歷時多年,得到了英國多個新教和天主教團體的聯合資助,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國基督教會聯合會(British Council of Churches) 下屬的愛丁堡世界宣教大會(Conference for World Mission)。但是該書早已絕版,而且該書未能收錄過去20 多年來本領域的優秀研究成果,而這些成果絕大多數是中國學者的貢獻。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外方傳教會中國專案負責人沙百里神父所著的《基督教在中國:從西元600 年到2000 年》(Christians in China A.D. 600 to 2000,法語版,Paris,2002;英譯版,San Francisco, CA: Ignatius Press, 2007),該書重點對天主教在華的事工進行了詳實而全面的論述。從某個角度而言,沙百里神父在該書中對天主教的偏重,恰好平衡了包括拙著在內的諸多作品對基督新教的偏重。
本書在總體結構上,試圖儘量在現代早期部分(1800 年之前共兩章)、現代部分1800 年-1950 年共四章)、當代部分(1950 年至今共兩章)的時期之間保持平衡。本書的核心部分是第3 章至第6 章的這四章,這幾章討論了在華外國傳教差會和中國教會之間橫亙了150 多年的衝突與張力;以及另外一個反覆出現的重大話題,那就是中國政府或統治集團長期以來對宗教活動一貫的監控和壓制,其結果是,基督教在中國通常不僅不先被視為一種宗教或信仰體系,而是被看作可能會導致無窮麻煩的隱患因素。
本書附錄部分,簡要敘述了俄國東正教會在華傳教使團自17 世紀末入華、至20 世紀中期在華活動終結的這一段歷史。俄國東正教在華使團的歷史是中國基督教史中不可忽略的一節,但鑒於其諸多獨特之處,本書為避免將其事蹟零散分佈於各章,單闢附錄對此進行了概述。
我決定在本書結尾不做一個獨立的「結論」。正如目前中國的許多事務一樣,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仍處於不確定的狀態。因此,除了第八章最後幾頁的小結之外,我不想再對基督教在中國從當下到未來的發展做更多的推斷—尤其是在評論家們對「當下」的情形還很難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但我仍希望本書能啟發讀者對某些重大問題的認識,其一就是,基督教在脫掉我們稱之為「基督教世界」的這一西方文化外衣之後,是完全能夠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長的—當然,這一適應過程通常會經歷一段可能是破壞性的跨文化交流。由此,我們獲得的教訓是:在「非基督教世界」,人們同樣可以蒙主恩典。本書希望表達的另一個觀點是:中國人在接受基督教(或說基督教的多個宗派)的過程中,體現出了非凡的靈活性與創造力。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景教使用道教和佛教的術語譯經、19 世紀太平天國領袖富有感召力的聖經幻象、中國天主教徒重新命名祭祖儀式以變通教皇禁令的手段、以及今天中國農村地區頻繁出現的白蓮教式的新教千禧年宗派。這一切,都會引導觀察者得出一個結論:萬變不離其宗(plus a change, plus c’est la mme chose)。
註:
1 沃茲,《從基督教世界到世界基督教》(Andrew Walls, From Christendom to World Christianity),收入沃茲編纂,《基督教歷史中的跨文化過程》(The Cross-Cultural Process in Christian History, MaryknoII, NY: Orbis,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