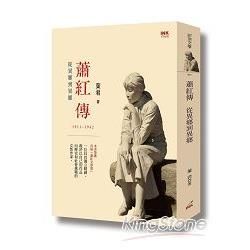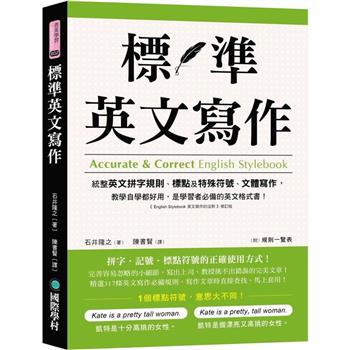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日] 平石淑子 序
二十世紀七○年代末期,即從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基於眾多研究學者的不斷努力,發掘出了各種有關蕭紅的史料,其中也包括了她本人的一些作品。但是在今天,由於熟知蕭紅生前生活的前輩們都相繼不在人世了,不太可能再發現什麼新的史料。在這個意義上,整理總結迄今的史料,力求於客觀研究蕭紅的這本著作,就當之無愧地成了蕭紅傳記的集大成了。正是它極力站在客觀的角度上,才避免了男性讀者們陷於對蕭紅的過度同情,同時還沒有失去對蕭紅的熱切目光。我想這些都是本書作者嚴謹的研究態度和其誠實寬厚的人品所致。
這裡再重複一遍,在我看來,這是一本非常受人喜歡的好書。但是,同時又感到還欠缺點什麼。這是一種與上述觀點極其矛盾的感覺,也許這正是起因於此書的客觀性。
眾所周知,蕭紅三十一歲就英年早逝了。在抗日戰爭這個全中國的受難時代,蕭紅還背負著作為女性的苦難,她沒有時間回顧自己的一生,是因為她還在人生的中途就離開了這個世界。所以,要瞭解她的短暫生涯的旅途,就只能憑藉她周圍的人,例如蕭軍、端木蕻良等人的回憶,《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這本書也不例外。也正是因為如此,特別是關於逃離上海為止的蕭紅的前半生,就是說基本上依賴於蕭軍的追述的這段時間裡的蕭紅,也許是蕭軍的過於饒舌,她給人的印象就猶如是蕭軍思想和行為的附屬品一樣。換句話說,前半生的蕭紅的形象是非常模糊的。與此相比,轉到武漢避難以後的蕭紅,就以鮮明的主體性展現在讀者面前。此時的蕭紅已經作為有名的作家受到很多人的注目,並且有關她的言論也多了起來。這些言論的產生可能與人們對端木蕻良的反感多少有些關聯。從武漢到臨汾再到重慶以至香港的這段時期,關於蕭紅有著非常詳實的記述和史料,這些史料裡有很多是我未見到過的很值得參考的東西。
我感到書中的不足主要集中在以蕭軍的回憶所寫的前半部分。作者將兩人的同居以及分居,作為蕭軍的「愛之哲學」的主題,然而就產生了兩人生活的主導權在蕭軍的印象,使蕭紅成了一個沒有主見、附屬於男性的在精神上不成熟的女性。而另一方面,在蕭紅與端木蕻良的這段生活裡,作者又只強調了蕭紅的自主性。這樣一來,讀者就看不到蕭紅從前半生到後半生精神上的成長過程。如果再深讀一下,還會得出蕭紅的精神獨立是來自於蕭軍的背叛(女性問題)。當然,蕭紅在《生死場》出名後,生活上還是不得不由蕭軍掌握主導權。但是正如駱賓基所指出的那樣,蕭紅固有的「矜持」才是將她引向精神自立的源泉。我並不完全認為蕭紅所寫的作品就記錄了她所走的人生之路(這一點與本書作者略有分歧),但是她的作品仍反映了她精神世界的成長,也是最值得依據的資料。
筆者之所以認為蕭紅是一位精神獨立的、具有主見的作家,也是對迄今賦予蕭紅的「被男性所擺布,從而無法實現自己夢想,充滿悲哀的可憐女性」形象的一種抗議吧。如果不是站在與蕭軍同居,後來又分離,然後和端木蕻良生活在一起,都是蕭紅自己做出的選擇這一角度看的話,就無法真正將蕭紅作為一個作家來評價。我充分認識到《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是一本以廣大讀者為對象的作品,而不是一部研究專著;但作為一個熱愛蕭紅的讀者,仍因為書裡沒有把《跋涉》、《生死場》及《商市街》裡所反映出來的蕭紅的思想介紹給讀者,而略感不滿。
作為一名國外的讀者和研究人員,在史料的發現和發掘上無法與中國同行們相比。只能依據這些成果來閱讀蕭紅的作品,並且,在她的作品裡哪些是帶有超越時空的普遍性,進一步講,文學對人類社會產生著什麼樣的普遍性力量,我們通過文學能夠做什麼等話題上,坦率地發表一些看法。當然,這也是我們的使命。喜愛蕭紅的讀者往往會被作品所打動,而失去自我。這也正說明了文學作品所特有的力量。在承認這一點的基礎上,作為一名研究人員,更要盡可能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來看待作家和其作品,從中找出真相,把它放在歷史和社會變遷的洪流中,通過向人們的展示,進而加深人們對歷史、對社會的認識;繼承其優良的,改正其錯誤的,並為歷史不再重演而不斷警示自己,努力不懈。我想這才是文學所擔負的責任。在這本書的基礎上,我期待著能看到作者有關蕭紅的作品論,並衷心祝願由蕭紅結成的緣分更加發展,使它連接起日中兩國以及全世界。
後記
蕭紅是我的情結。
我想,她或許也是大多數研習中國現當代文學者或深或淺的心理情結。
蕭紅棄世近七十年,而這本書面世於她百年誕辰前夕。死時年僅三十一歲的她,在我的想像中,始終是個命途多舛的姐姐。這一想像如此真切,每次接觸到關於其生平的資料,心底便瀰漫淡淡傷感,湧動著強烈的表達衝動。
香港中文大學資深蕭紅研究者盧瑋鑾教授,基於女性立場,出於對蕭紅的細膩感知,寫下了一段很能引我共鳴的話:「愈看得多寫蕭紅的文章,特別是與她有過親密關係的人寫的東西,就愈感到蕭紅可憐─她在那個時代,烽火漫天,居無定處,愛國、愛人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而她又是愛得極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傷也愈深。命中注定,她愛上的男人,都最懂傷她。我常常想,論文寫不出蕭紅,還是寫個愛情小說來得貼切。」
多年來,我一直想在進入關於蕭紅及其作品的論述之前,寫一部她的傳記,以此傳達對她的理解和對其生命歷程進行細緻觸摸之後的感受。閱讀已有蕭紅傳記,老實說常常令人失望。我每每感到敘述者那份貌似追求客觀的冷漠。同時,由於時代的局限,敘述中那種政治意識形態動機的彰顯,亦讓人十分生厭。我想在自己的敘述裡,最大限度地將她還原成大時代裡的一個普通女性,一個命運坎坷的天才女作家,一個任性的姐姐;而與革命、進步、左翼沒有太多關涉。另有蕭紅傳記雖出自女性作者之手,但敘述中卻莫名帶有極其怵目的男性中心主義立場。表面上在敘述蕭紅的經歷,實則成了幾個男人的故事。更不用說那些瀰漫著濃郁小農意識的偏見文字,出發點大都急於為蕭紅生前身邊的男人們正名而喋喋不休,觀念淺陋、文字拙劣。
我想,我的敘述全不如此。我要寫一部全然關於蕭紅自己的傳記,在想像中,隔了漫長的時空與她做一次精神的對話,對其精神苦難感同身受。
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莊嚴的舉意。
二○○五年隆冬,我從武漢第一次來到哈爾濱。那天夜裡,一下火車便覺得自己已然進入這個留有太多蕭紅印記的城市,心理上是如此親切,以至於在計程車上便迫不及待地向中年司機打聽東興順旅館、歐羅巴旅館、商市街。不想對方一臉茫然,「蕭紅」這個名字在他全然陌生。我無比失望,覺得這座城市在漸漸將她遺忘。那些建築還在,但那些哈爾濱往事卻漸成淡漠的傳說。
我的生命中或許注定與蕭紅存有一個約會。二○○六年定居哈爾濱之後,便借來大量關於她的資料,力圖實現心中那個莊嚴的寫作計畫,那個富有激情的舉意。經過一年多的準備,二○○七年八月二十日,正式動筆前,在一個學生的帶領下,我來到呼蘭蕭紅故居,想親眼看看她的「家」。不巧,故居因裝修已於頭一天關門了,向工作人員說了許多好話,才讓我們進去看看。所有展品都已經收起來了,只剩下幾間空蕩蕩的屋子和空蕩蕩的後花園。能夠親眼看看,我就已經非常滿足,在我內心,老實說,蕭紅的「家」是我並不願意去的地方。看看這空蕩蕩的屋子倒是恰到好處。
「從異鄉又奔向異鄉,這願望多麼渺茫,而況送著我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著我的是鄉村的風霜。」蕭紅在詩句裡對自己大半生經歷有過極為精粹的概括。「從異鄉到異鄉」成了我的題目。兩天後,關於她的敘述正式開始。一年多完全沒有休息和娛樂的日子,卻給了我十分愉快的體驗。我覺得自己的敘述平穩而從容,二○○八年九月二日終於告竣。文字無論好壞,我都非常滿足。「蕭紅百年」在即,在心底,我終於完成了對於她的「一個人的紀念」。
二○○九年三月,《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後,《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讀書》等大陸十多家主流媒體給予了介紹,黑龍江省作家協會於九月二十四日專就此書舉行作品研討會。會上宣讀了日本大正大學平石淑子教授、美國索思摩大學孔海立教授等海外資深蕭紅、端木蕻良研究專家對此書的高度評價。學界前輩獎掖後進的熱情鼓勵,令我非常感動。爾後,在《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基礎上,精簡文字、增益圖片,編成《蕭紅圖傳》,於二○一○年四月由廣東教育出版社推出。
今年夏天,中國作家協會組織了台灣作家代表團來大陸采風的「蕭紅文學之旅」活動。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我有幸對台灣作家們發表關於蕭紅生平的講演,並結識著名詩人、出版家初安民先生。出版一部繁體字的著作是我的夢想。為此,我冒昧向初先生表達了在台灣出版《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的訴求。沒想到,初先生回到台灣不久,我的願望便得以實現。
九、十月間,我對《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進行了全面修訂,訂正不實資料、修改不恰當的表述,同時增加了後續發現的史料,增益、改動近千處。即便如此,由於淺陋,我自知,修訂版的《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仍有諸多訛誤,乞求大方之家的指正。收入修訂版的圖片一百多幅,有些珍貴圖片仍是第一次面世。這些圖片參與蕭紅的生平敘述,我想將會為讀者重新認識蕭紅提供可能。
《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修訂版)在台灣即將面世,此刻處於北國冰城一隅的我,內心平靜而喜悅,充滿無盡感恩。因為蕭紅,我與大陸、台灣的多位出版人結緣,一次次愉快的合作,讓我覺得自己是何其幸運。再次感謝印刻出版公司社長初安民先生。同時,我也要向為編輯、設計、宣傳此書付出辛勤勞動的江一鯉、鄭嫦娥等素未謀面的印刻同仁表達敬意與感謝。
非常感謝蕭紅嫡親侄子黑龍江省蕭紅研究會副會長張抗先生、前呼蘭蕭紅故居副館長王連喜先生、黑龍江《生活報》記者蕭紅研究會副會長章海寧先生,為本書提供了大量珍貴圖片。
最後,感謝我的妻子和女兒。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作者於哈爾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