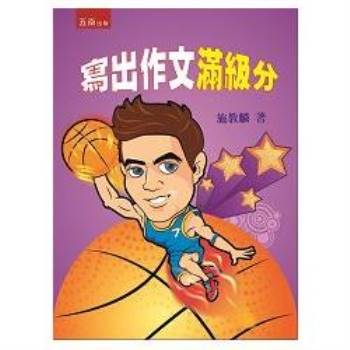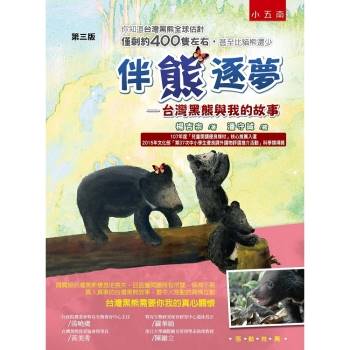化俗為雅的文人,馮傑 張輝誠
我和馮傑相識,主要還是因為文字。
去年受邀擔任時報文學獎複審委員,看到入圍文章中有一篇〈器皿記〉,驚為天人。──文學獎比賽文章雖看過不少,但印象深刻者卻寥寥無幾,比賽結束後,我對馮傑產生興趣,又在網路上搜尋其他作品,所見皆水準極高,令人嘆伏。不知怎地我竟興起了應該要設法結識這樣高手好砥礪自己的念頭,便向副刊編輯問得馮傑郵件信箱,冒昧去函,有點兒近乎攀交、或者粉絲要朝拜偶像一般。後來通了音訊,幾回書信往返,每每都要驚訝於他調配文字的火侯,不炎不冷,字字昂然,句句珠璣。再後來因緣際會得以和馮傑在河南開封見面,同時和兩位當地小說家,一桌四人,吃飯、喝酒、聊天,飯後再一起乘車夜遊開封,真是不亦快哉。
馮傑出版這本新書,我有幸沾上一點邊,因為我把他的文章推薦給印刻出版社,初安民和江一鯉小姐欣然接受,同意出版。我這樣做完全只是像粉絲想幫偶像作一丁點兒小事而已。照理說,馮傑的文章不用我推薦,也合該好多人要搶著幫他出書。值此之故,馮傑希望我能寫篇短文當序,記錄一下這段文字因緣。
至於馮傑的散文,我可以說出一大堆好處,並且我是真的要這麼做,一點一點不厭其煩寫在下面。
頭一個好處是:素樸真心
馮傑常說自己是鄉下人、邊緣作家,他讀完高中就出社會掙錢養家,沒上過大學,也鮮少在大都市長時間住過,因此他的散文題材幾乎都是以鄉村生活為主,寫鄉村人、事、物,寫草木、寫生活、寫動植物,可說是一往情深,難以自拔。以現在的標準來看,馮傑是不折不扣的鄉土作家,他的鄉土是古稱中原的鄉土,從我們這裡看反成異鄉文學,但是能夠掙脫掉「地域」的界線,使異鄉的讀者引發共鳴的,正是隱藏在不同風俗習慣之下的人情世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馮傑用他的素樸真心,去看故土的親人、鄉鄰、草木鳥獸的身世、特性和意義,而讀者從他所描繪的事物感受到他熱愛鄉土、熱愛親人的素樸真心。
這種素樸真心,是長期居處鄉下孕育出來的自然性格,因此他的文字沒有城市文學的疏離、冷漠和焦慮感,有的全是鄉野之人的豪爽、舒緩和溫厚。
其次:化俗為雅,雅俗並陳
以前讀黃庭堅,都說他能「以(化)俗為雅」,當時不是很懂,看了馮傑的散文之後,終於恍然大悟,原來馮傑這就是了。先不說他的房子有個很美的齋號叫「聽荷草堂」,每回通信,寫上的地址彷彿都成了配角,最後填上的「聽荷草堂」往往喧賓奪主。他的散文最擅長於把生活中習以為常或毫不起眼的人事物,寫出它的精緻、美好和意味深長,如他經常把植物派給古代的大畫家們去商量、去斟酌、去品味、去表現美,再讓它們從古今畫家的畫裡頭高貴地走出來,走進鄉間的日常生活去,與他並肩著。如他寫鄉下星星、月亮、燈之類的事物,又讓它們先在古今中外的詩句裡遊走一番,才映照到他站在鄉村曠野中、庭院裡或窗戶下的臉上。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些其實都關涉到文化的涵養與文學想像,一草一木、兩豬三牛,都因為浸潤在豐厚文化的湖海,出現在鄉間忽然就不顯得寒傖、不顯得單調、不顯得一般。
這是馮傑的大手筆所在,他把一切看似俗瑣之事物,寫出常人難以言說的深度和雅致,即使他的寫作題材大多來於鄉村,好像跟整個進步工商業時代格格不入,但其實沒有,因為他精緻地排列出鄉村種種,沒有一個是低俗的,草木自具品格,鳥獸自備風骨,連豬和驢都有可親可愛之處,昂然地去對照新時代的怪異風貌。
其三,詩化語言
馮傑是個詩人,出過好幾本詩集,雖然也寫散文、寫小說、也畫畫,但他骨子裡外完完全全是個詩人,他善於想像,巧於譬喻,嚴於用字,精於節奏和聲音。沒有一個人讀馮傑的文章,不會發現他的文字充滿詩意。馮傑雖擅長多樣文藝,但他所有文體表現出來的本質,全都是詩,散文、小說可說是詩的擴充與延伸,就連畫畫裡頭也全是詩。
而他的詩,一言以蔽之,就是雅。
在台灣,能把文字像詩一般拿捏著恰到好處寫散文的,大約就屬余光中和楊牧兩位先生,前者陽剛,後者舒柔,馮傑恰好就在兩者之間,不濃不淡,他可以用這種詩化文字析理論事,也可以敘事抒情,而且風格獨具,面目特殊,既不模仿誰,也不比較誰,自然而然,合該如此,因為他原本就是一位獨特真性情的詩人。
其四,古書即生活
馮傑喜歡在文章中徵引古籍,這些古籍上自《詩經》、《韓詩外傳》、《說文解字》、《世說新語》,下自《三國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經史子集,農牧畜產,樣樣都有,他不是中文系出身,可見都是自修得來,他讀這些書、舉這些書當例子沒有半點炫學意思,而是他真實生活裡頭的東西,如語言、如掌故、如隨處可見的草木鳥獸,好比說《詩經》裡頭的「鄭」風,就在他們河南境內;《水滸傳》裡頭的宋代官話就是他們現在還在用的河南話;更不用說開封、新鄭這些古都就是他們腳踩的地方。拿古書舉例只是便於印證生活,讓今人的生活和古人生活通貫在一起,有了時間的聯繫,彼此呼應。
然而作為讀者,不免心生羨慕,馮傑和他的鄉人們居然都可以生活在古典之中。
其五,人世滄桑
馮傑的文章,經常回憶他外祖父母及父母的往事,因為他們是他的文學和藝術的啟蒙,也是他鄉村智慧的起源。他寫這些親人往事,極為有趣,亦極有意思,但往往最後處筆鋒一轉,物是人非,難免愁惘,由樂說起,以悲作結(其他談草木鳥獸之文,亦常用此法)。只是馮傑在寫這些愁惘時,筆調卻極為斂抑,點到為止,絕不讓悲傷毫無遮攔地泛流,像是大自然本就如此,生衰興滅,草木如此,人亦不可免。
故有悲傷,亦有通透之處。
其六,諧趣
馮傑的文章充滿諧趣,這種諧趣來自於對人的觀察和對草木的想像和體會,一小節一小節的趣味,分布在不同文章之中,像含羞草一樣,一碰到了,就骨碌碌地收枝斂葉,不由得你不注意,不由得你不會心一笑。
馮傑文章的諧趣,總歸還是雅,是一種精緻的趣味,俯拾即是。
其七,小嘲諷
馮傑偶爾在文章流露嘲諷,大多是對文革時期的荒謬事件或現代政治人物的難看嘴臉與乖張行事,他有時就老大不客氣神來上一筆加以嘲諷,這些地方讀來很是過癮,但我經常都替他捏把冷汗,這種寫法在大陸能否出版不得而知,我只怕他會因此惹上麻煩,當然這是我做為一位朋友的關心。
這些小嘲諷,都像一根細針,給人一痛,也給一快。
其八,以物喻人
馮傑經常喜歡拿物來比喻人,草木鳥獸、器皿農物皆可喻人。這樣寫,一方面,草木鳥獸、器皿農物便各自有了人的面貌、脾氣、性情和質地,栩栩如生,個性十足;另一方面,人和草木鳥獸、器皿農物,有了融通,成為共同體,多少就有點「人與萬物一體」的道家意思了,雖然馮傑並不道家。
其九,詩意畫境
馮傑在這本書的插畫,都是他自己畫的,他的畫受齊白石和八大山人影響頗大,畫面單純,經常是鄉村一物,特寫,滿佔畫面,空白處再加以相映成趣的題款。如他畫一隻鳥閉眼,題曰「沉思集」;四條黃瓜,叫「四條漢子」;洗過的蘿蔔,喚「濯纓圖」;諸如此類,而且大部分題款頗長,搭配圖看,極有趣味。
只是馮傑的圖,題款文字往往超過圖象本身給人的感受,圖象只有在文字的說明中才得到更多豐富的意義。這對馮傑來說,恐怕是難以避免的,因為前面說過,馮傑本質是詩人,這些尋常事物要賦予更多意義,就必須靠詩意的文字來補足。
其十,鄉村辭典,多識草木鳥獸之名
辭典體,很多作家拿來用,最著名應屬韓少功《馬橋辭典》,該書敘寫韓氏年輕時被安排到馬橋村(位處湖南省汨羅縣,即屈原流放地)下鄉插隊,體驗當地方言文化,寫出以馬橋詞彙、帶點筆記體味道的小說集。如果說《馬橋詞典》是南方的,那麼馮傑這本同是辭典體的書則屬於北方,一南一北,像《離騷》和《詩經》,一個浪漫綺想,一個樸素敦厚。
《馬橋辭典》關心的是口語和人情世故,重視說故事;馮傑的《泥花散帖》,固然也關心,但他更在乎草木鳥獸、器皿農物,更重視感受。
以上是我對馮傑《泥花散帖》的十全看法,當然還有其他的,但我決定留著讀者去細細品嘗、去慢慢發掘。
二○一○年九月十九日,凡那比颱風侵台之際。
泥花散帖 編輯語
剛拿到《泥花散帖》稿子時,我就在猜馮傑肯定曾披著蓑衣陪蘇東坡一起去定風波,要不就是哪天夜裡同李白月下喝酒,兼種荷花?他還到《詩經》裡去拔蘿蔔,然後不小心被楊凝氏的韭花逼出眼淚,連三國裡的英雄、孤傲的明末遺老都親切起來,因為馮傑說他們的味道像荊芥,也就是芫荽一類香菜,這下子我下回吃蚵仔麵線時,說不定得先跟張岱打聲招呼。讀著,嘴角不自覺上揚,有陣風拂過,帶著鄉間田埂的氣息,多好,喝一碗麵湯都有畫,兩隻茄子、四條黃瓜、五根紅辣椒,他說「辣椒是窮人的饞」,我想起外公的獨門醬菜——高粱酒醃辣椒,可惜,就像書裡寫的「絕麵」一般,吃不到了。
那一刻,我終於理解馮傑的思念,願那或許早已消逝的美好時光,留在紙上,你想念時,永遠可以回憶。
文/陳健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