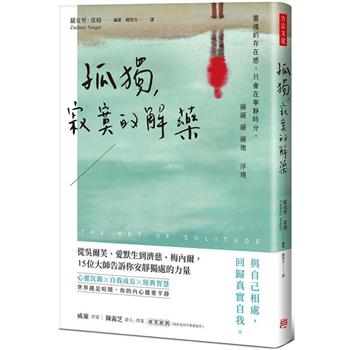用一顆蘋果喚醒魯迅與馬奎思
所有文字爬行者的果實之書
閱讀與寫作,均能在哲思層面深刻豐收赫然發現
以此為地,小說開始發芽了
世界上所有的故事(小說),既在時間與空間中展開,又在因為和所以中進行。
留下那巨大的因為之因為的空白,正是令讀者和研究者著迷的黑洞……
本書以引文對照的舉證方式,反映不同層次的小說書寫,顯現隱藏於故事背後小說家的創作初衷與情非得已。以如此推理般同步書寫與閱讀的方式,作為一種寫作技巧的高度展演,也提供了一種哲理式的閱讀脈絡。這是走進現實的一種新徑,也是認識世界的方法。
作者簡介
閻連科
一九五八年生,河南省嵩縣田湖鎮人。一九七八年入伍,一九八五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系,一九九一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一九七九年開始寫作,作品有長篇小說《我與父輩》、《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四書》等九部,小說集《年月日》、《耙耬天歌》等十餘部,另有《閻連科文集》十二卷。曾獲第一、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並先後獲其他全國性文學獎二十多項,其作品被譯為日、韓、越、法、英、德、義大利、荷蘭、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爾維亞等近二十種語言,在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二○○四年退出軍界,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駐校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