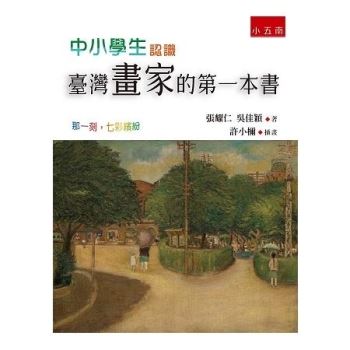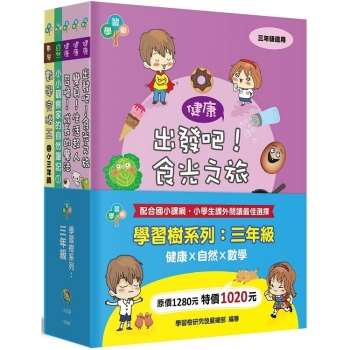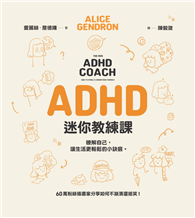書前的話
二OO七年初安民先生和季季小姐約我為《印刻文學生活誌》寫一專欄,並為之取名為《回首我們的時代》。這當然是指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事,因為在那之前,我還只是個十三歲的少年,對世事即使有所認識,也一定是跡近模糊。十三歲那年,我飄泊到了台灣,沒想到一轉眼之間,時間已經超過了六十年。原來的世界,完全變了樣子。
記得不久之前,朋友間有一場聚會,其中有些人當年曾是左派,也有人曾是右派;有人曾是統派,也有些人曾是獨派,現在雖然好幾位已經滿頭白髮,頭開天窗,老友相會總不免「偷閒學少年」那樣唱起年輕時唱過的歌來,不過多少憑添了嘲諷的意味而已;不知是嘲諷自己,還是嘲諷已經過去的那個時代。那天,有人三杯酒下肚,就扯開嗓子大唱「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接著就有人唱「總統蔣公,您是民族的救星……」。唱來唱去,毫無當年的嚴正氣象,於是其中有人就說了:「管他們那類人物是甚麼,如果我要蓋個人民紀念碑,第一件要做的事,一定要塑一群只爭個人名位、不顧人民死活的政黨人物的群像,要他們一個一個硊在碑前懺悔。……」更有一位舉起酒杯說:「你們這批人真是不知好歹,──今天我們能夠這樣放肆,不被抓去坐牢,真是莫大的幸福……」。他連喝三杯,興猶未盡。這顯示一個時代已經進入了歷史。
事實也是如此。但這幾十年的日子雖然已經不再像我們童年時代那樣,幾乎每天都流徙在戰火動亂之間,然而隨著年歲的增長卻經常也會不時地向已經走過的歲月提出質問。質問甚麼,卻也不甚了了,這証明成長於我們這一環境的一代不是長於深思的人;在過往的日子裡經常被一些動人的、屬於意識形態的語言鼓動著;有時激昂慷慨,有時一片沮喪。我自己和一些朋友就是一些經過這樣遭遇的人。那一個時代過去了,但是由於自己的大半生都是過著教書匠的生活,每當碰到一些歷史的問題苦思不得其解的時候,便也往往會在前人的智慧中尋求答案,卻也經常感到惘然。其所以如此,大部份是由於面對那些前賢對近一個多世紀所作的判斷時,經常會感到他們所作的論斷過於嚴肅,而其所作的動人的揭示也距離我們太遠。像美國籍的西班牙哲人桑塔亞納(G. Santayana),一生中寫了那麼多有關生命和真理的大書,臨死的時候,只對二十世紀說了一句評定的話:「絕望」。又如德國哲人洛維特(K. Loith)身歷兩次世界大戰,卻認為自己所經歷的世紀是一個「一無所成的時代」。他們的悲憤和焦慮是那樣悲壯和崇高,絕不是我們這般活在平凡之中、苟安於世俗中的人所敢或所能望其項背的。尤其在我們這樣長時期處於殺伐、鬥爭和相互迫害的國家,一個人或一家人能夠在最低條件下不虞匱乏、能夠活在無恐懼的日子裡做點自己可以做的事,就已經是心滿意足了,哪裡還會有著像他們那樣莊嚴的憂心和思考呢?
既然如此,現在輪到自己要回首我們的時代,一時之間便不知道應該從哪裡說起。猶疑之際,忽然想到:從小以來雖然教育給予我們的大都是一些「救國救民」或「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官冕堂皇的「大話」,但一落到實際的生活,最後讓我們為之心動的卻仍然是些平常而又平凡的小事。這些小事,看來沒有甚麼大不得了,其中所孕涵的意義卻往往會成為我們思辨的基礎,幫助我們成長。譬如小學的時候老師要大家背誦〈木蘭辭〉,同學們「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地唸著,並各自編構著一幅女英雄的形象,但是在後來的流亡途中,經常見到抓兵的殘暴,有時連個子長得高的兒童和婦女都不放過。看多了,〈木蘭辭〉早先給人的感受便隨之變了樣子。又如,少年時看戲,看到岳母在兒子背上刺上「精忠報國」,心中覺得非常氣節凜然,但在自己有了兒子以後,才感到那種母愛真是人世間最大的荒唐。至於〈趙氏孤兒〉中的那種拿自己嬰兒為主子的兒子替死效忠的作為,再怎樣解說,都無法令人看得下去。而相反的,歷經了大半個人生,倒覺得苦難中一聲從千里外傳來的安慰、口袋中保有很多年的一封舊的家書、臨終病房中親人的一聲叮嚀,卻往往成為生命中最有力的支持。這樣一想,便覺得:在整個人世、整個歷史、整個從古到今的爭爭奪奪、殺殺砍砍、富貴貧賤的幻滅生死中,到頭來最讓人念念不忘的可能並不是那些名大位高人物的訓誡,而是一些看來微不足道的人與人間相互關懷的瑣事。它們是那那樣平凡地存在於我們的現實生活之中,卻又與我們的一言一行緊密地纏在一起,讓人無法擺脫得掉,而且,日子久了,便不知不覺地融入自己的血肉中,成為生命的養份和力量。
由於有了這樣的涉想,我便決定在這個專欄中,與其去思考、探索那些自己無能為力的世紀大事,不如藉著自己經歷過的點點滴滴對那個即將逝去或逝去不久的時代,作一平實的重溫。這樣想著,第一個出現在我心中的人物便是臺靜農先生,他雖然生活在一個如莊子所說的「無可奈何」(甚或過之)的時代,卻依然保持著他的自在和誠懇,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都是一代的典範。特別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經由生活的陶鎔,他的思想和寫作都提昇到他的同輩作家所未達到的高度。古人所說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在他的書藝的純淨境界中也讓人見得出來。就此而言,他所顯示的風格便有了時代的意義。因之,他在中國文學史、特別是魏晉、晚明等大變動之際的認識,也就有了前人未及的深刻。這些即使在他平日的點點滴滴的言談中,也會讓人有所領會。
在這個專欄中,我就是循著這樣的道路寫下來的。我希望,經由我的追憶,讓人不再把它們當作是出土文物,而是在那些歷史的重現中認出:不管那些過往的日子是多麼令人感到沮喪,而我們自己當年又如何衝動、幼稚、甚至盲從過;想起來讓人不勝唏噓。但追根究柢,卻可從另外某些人的有形或無形的所作所為中體認出:那並不是一段只是空白的歲月。不管這世界上的事多麼令人失望,令人難堪,在艱困之中,總依然有著無數向上的力量在運作著;「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這些文章在當初書寫時,有的稍嫌簡略,現在一一校定,予以增刪,除了這些篇外,也把這些年在別處發表的同類作品一併收了進去,使得原來的專欄成了目前這樣的樣子。
在寫作和整理這些作品時,我已經年過七十;回想舊事,便不時出現事件散亂、引証重複一類錯誤,在這方面,我的兒子任之(可可)替我幫了大忙。他擔心老爸年紀大了,語言瑣碎、敘事顛倒,經常在我初稿後,提出意見。有時我也執著自己的筆法,依老賣老,兩個人有時就會爭吵起來。當時也許會心有不豫,到了後來卻使我在再次檢訂中學會謹慎小心,而不至於早點走上老人痴呆的道路,因此不對他說聲謝謝,也就真的不夠意思。
二O一一年三月五日於台北木柵
寂寞的時光與靈光
陳芳明
記憶總是靈光一閃,迸發出來的色澤與情調,漫漶在無法確定的泛黃時間裡。那絕對是無與倫比的真切,也絕對是難以捕捉的光影;但可以感知它黏附在流動的血液,緊密與心臟一起跳動。
發生過於久遠的台灣文壇舊事,即使出現在一九六○與七○年代,只要化成文字留存下來,必然較諸肉體還要生動,還要持久。跨過七十歲以後,尉天驄老師完成的這部《回首我們的時代》,重新描繪消失已久的風景,容許年輕世代窺見曾經浮現的盛況與蕭瑟。落寞的學者,孤寂的作家,又從蒼茫的歷史迷霧中走出。不為人知的感情,不易察覺的思考,再次湧動。那種力道,在回首時,產生一種重量。來回行走在他的文字之間,簡直是穿越一部戰後台灣的人文精神史。
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浪潮席捲之際,人文精神似乎是過時的一個名詞。在舉世滔滔的資本主義化過程中,或許更需要注意到人的價值與氣質。所謂人文,絕對不可能屬於魅惑的神學,更不能屬於精確的科學,而應歸諸於與生俱來的情感與思想。它永遠充滿彈性,也是一種難以定義的心靈狀態。生而為人,自然會帶有貪念,而且也充滿私慾。人文精神在於講求人格的鍛鍊與改造,為的是更勇敢強悍地面對不斷變動的世界。它不可能是僵化頑固的態度,而是在不同社會條件,不同歷史階段,表達深切而溫暖的關懷。尉老師的這冊人物誌,對台灣文壇的重要學者與作家投以深情回眸,也是戰後人文精神的一個雄辯。在生命中浮現的前輩與朋輩,所表現出來的藝術追求與社會關懷,都歷歷在目,完整保留在這本很精采的散文作品。
在他溫潤的文字裡,釋放出一種慈悲,截然不同於他年少時期的脾性。曾經批判過現代主義文學的尉老師,經過長期思考的辯證轉化,慢慢培養更為從容的審美觀念。當他轉身回看歷史的成長與成熟,似乎也變得慈眉善目。如果時光回流到一九七○年代,當他還在主編《文季》的時期,可以發現他抱持著對峙與對抗的態度,毫不留情,嚴厲剖析現代主義作家的小說。那時他還未到達四十歲,曾經發表過一篇〈幔幕掩飾不了汙垢──對現代主義的考察兼評歐陽子的「秋葉」〉,充分流露他強烈的批判態度。曾經站在現代詩與現代小說的對立面,他不能接受文學揭開人性的黑暗與墮落,即使到今天為止,他的評價還是有所保留。但是當他訴諸文字時,許多憤懣之氣逐漸收束起來。
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爆發,他是重要的旗手。但是比起朋友陳映真與王拓,他出手的力道,還是相當節制。三十餘年過去了,曾經飄揚的論戰硝煙,完全歸於平靜。尉老師從未表示有任何意見的改變,不過他與現代小說家、現代詩人又重修舊好。那種情誼,無需任何文字來解釋。在平日言談中,他仍然尊重五四以降的文學傳統,對自由主義與民主精神,從未偏離他的理想。二○○六年出版的《棗與石榴》,恰如其分可以解釋那種開放、平等、寬容的思維方式。他的文字,經過時間的淘洗,讓許多雜質沉澱下來,浮現一種前所未有的澄明清澈。沒有遭遇思想上的風暴,沒有經過情感上的過濾,就不可能使狂飆的語法與句式獲得昇華。
對於後現代的新世代而言,他或許被視為一個保守主義的據點,或是一個懷舊思想的剩餘。凡是親近他的人,當可理解他的心靈向整個社會、整個家國敞開。若是要定位他的思想光譜,七十歲的他,應該還是相當激進。當資本主義的生活成為一種風尚,他對於權力在握者,有頗多微詞。對於台灣這小小海島,他懷有無比的信心,永遠堅持民主改革的立場,不會因為早年閱讀過社會主義書籍,而幻想著烏托邦式的革命。台灣漸進式的民主過程,使他看見潛藏在社會底層的文化能量不斷釋放出來。自私的政客耽溺於權力爭奪,卻無法善用民氣,使台灣走向更為理想的境界。痛心於意識形態的對決,扼腕於藍綠鬥爭的內耗,他總是擔心台灣社會可能失去翻轉的可貴機會。歷史改造的契機一旦錯失,極有可能使這小小海島萬劫不復。常懷憂心的他,總是感嘆最好的時代遲遲不能降臨。
他比任何一位知識份子,還更具有深沉的台灣感情。對岸中國的不斷崛起,並不會使他感到恐懼。他非常清楚社會主義並不等於中國,而真正背叛理想的反而是中國共產黨。他總是密切觀察,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與天安門事件何時能夠獲得平反。對他來說,念茲在茲,無非是從基本人權的觀念出發。一個有力的當權者,竟然沒有勇氣面對歷史的錯誤。在拒絕面對歷史真相之餘,還繼續干涉知識份子的思想,檢查作家的文字,阻擋資訊的開放。強悍的黨,表現出來的竟是一個弱者。表面上看起來是巨人,實際上的行動是侏儒。他總是相信,知識份子不能因為意識型態而捨棄真理。所有的理想都是必須經過真正的實踐,也經過落實的追求,如果只是蹈空地迷信政治信仰或立場,最後都無可避免走向悲劇。像他這樣與時俱進,不僅不是保守主義者,而是在這時代瀕臨絕種的進步份子。
必須理解他的思想狀態,才能夠清楚看見這本作品的用心良苦。生命中的每一個時期,他從未虛擲。台灣戰後史上的重要時刻,他也沒有輕易放過。從五○年代末期創辦《筆匯》開始,就比任何一位朋輩還更早熟地涉入現代主義運動。在那段時期,他並不只是參與,而是率先領導。他未嘗虛矯地燃燒熱情,做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絕對不容許自己沉溺於幻想或夢境,而是訴諸實踐與行動,真正勇敢去追求。台灣現代主義運動的先驅者,如紀弦、何欣、姚一葦、劉國松、陳映真,都是與他一起出發的重要作家。他們橫跨現代詩、現代畫、現代小說、現代批評,預告了一個更為成熟的時代就要到來。沒有經過實踐,他不可能當做信仰。必須看見,而且介入,他才有可能建立信心。一場文學運動的展開,形成於思想條件與歷史環境未能配合的階段,但他還是堅持走出來,甚至還造成無可抵禦的風潮。
如果從輩分來看,他應該是與創辦《現代文學》的白先勇、王文興屬於同一世代。從起步的時間來看,他竟是提早三年出發。發展出來的路數,也與外文系出身的現代主義者截然不同。《現代文學》因為有夏濟安的引導,很早就有系統地汲取西方文學的養分,《筆匯》則是以中國文學傳統為基礎,慢慢建立起與西洋文學的對話。他們的老師是王夢鷗,頗具古典文學的修養,同時暗藏強烈的民族主義立場。書中他所懷念的前輩,如臺靜農、高陽、子于、俞大綱、楊逵、程兆熊、何欣、王夢鷗、姚一葦、無名氏,幾乎是一個時代的重要人格。這是尉老師平生最幸運,也最幸福的時期。他們的地位與學養,代表那蒼涼年代的精神象徵。整個社會還未脫離蕭條而殘酷的階段,卻已經釀造後代無盡追索的思想指標。 從年少歲月開始,他就已經與如此珍貴的人文風景相遇。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能夠與一代的最佳心靈對話,交談,請益。那種文化洗禮,可遇而不可求。
尉老師表現出來的風範若是值得學習,應該是一個世代學術與藝術的價值,直接間接灌注到他的生命。他以如此龐大的文字,去描摩前人的智慧結晶與行事風格,似乎是在定位前輩文人的歷史座標,同時也是在定義他所接受的歷史意識。回到前面所說的人文精神,那不僅僅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可以觸摸、可以感覺的生動魂魄。它並不會因為社會變遷或政治改造,就永遠一去不復返。尉老師企圖要證明的是,人的學術,人的文學,從來就是可以傳承,甚至可以用精緻的文字去追索。當他寫到俞大綱的喪禮,那是由俞大維主持,拒收任何輓聯。尉老師的這篇散文做了相當漂亮的結尾:「期間有人報告:『經國先生送來了喪幛!』大維先生坐在那裡,嚴肅地揮揮手,說:『收起,不掛!』於是在寧靜中,大綱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這是非常乾淨俐落的回憶,也是不拖泥帶水的行文。不這樣寫,就不足以彰顯俞氏家族的情操風格。
對於朋輩,他精確掌握彼此過從的情誼。幾乎傳說中的作家,都在他的文字裡又重新回到青春歲月。他所寫的唐文標、王禎和、黃春明、陳映真、葉笛、紀弦、梅新、大荒、商禽、楚戈、逯耀東、奚淞、聶華苓,幾乎構成一個世代的感覺;而這樣的感覺,又構成尉老師人格的重要部分。沒有這些作家,六○、七○年代的批判精神,恐怕會出現缺口。他們被記錄下來,是因為在曲折的命運中,倒影著蒼白時期的飛揚與挫折。當他寫到葉笛,簡直就是寫到骨髓深處。其中的哭與笑,只有真性情的男人才會表露無遺。他容許我們看到一個沉默日文翻譯者的內心世界,也看到一位芥川龍之介崇拜者的藝術奧秘。挺著一支靈動的筆,他寫活了台灣文壇感到陌生的燃燒靈魂。這種處理友誼的方式,顯然也是尉老師人格的一種延伸。有幸與他相遇,有幸與他交往,也有幸受到他這樣的追念,使那些遠逝的人,從此不再遠逝。
其中最令人感傷的一篇文章,莫過於〈理想主義者的蘋果樹──瑣記陳映真〉。他不憚其煩,細膩地追憶一位左翼知識分子是如何誕生。在他筆下,陳映真可能不是一位社會主義者,而是有血有肉的浪漫主義者。他們之間如今已是音信全無,但是長年建立起來的感情,無論如何是不能切斷。寫到最後一次見面,他委婉暗示,兩人之間的思想取向已經背道而馳。當陳映真說:「這些年來,大家都把文化大革命批評得體無完膚,這是不公平的。──文革是有它莊嚴的意義的。」他刻意插入這一段話,等於是表明一條路已經走向兩頭。他與黃春明面面相覷,簡直不知如何回應。這是思想的分歧點,也是情感的斷裂點。在時間的無情沖刷之下,這篇文字還是勾起了無盡的懷念。這當然是一場令人無法忘懷的離別,也是一個永遠回不去的記憶。在字裡行間,沒有絲毫的譴責,更沒有細微的感嘆,然而一字一句,彰顯了他們之間的友情是何等親密,何等相知,又何等疏離。讀完之後,不免使人欲淚。
七十歲後的尉老師,仍然還是性情中人。他的回首,其實是不堪回首。當他轉身回望,恐怕不是驚鴻一瞥,而是投以深情的凝視。二十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經歷過那麼多的生生死死,那麼複雜的分分合合,他還是勇敢寫下靈魂深處無可磨滅的身影。寂寞的時光,竟是充滿奇異的靈光。一個時代的人文精神,是這樣那樣分散在各種不同的人格特質身上,他耗費心神,重新拼圖思想的斷片,藝術的碎片,使一個時代的風貌又再度降臨。浩浩蕩蕩二十萬字,為台灣歷史築起一塊豐碑。舊時代欲逝未逝,新時代欲至未至,其中的微言大義,帶來無窮的意志,以及無盡的悲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