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詹集__王淮論文及其他作者一生清楚的切割為兩個全然不同的時期。無論待人處事或學問理想,都有很大的轉變。正如蔡仁厚在悼念王淮教授一文中所不解的:「中年以前.常相聚首,論東論西,中年以後,行跡漸疏,難得面敘」(見本書233頁)。作者生前反省自己的改變,說;之前因為過繼給儒家,要為孔孟盡孝,之後認祖歸宗、回歸道家、還其本來面目,清靜無為,神隱谷中數十年。
《詹詹集——王淮論文及其他》中七篇論文正是之前他追隨牟宗三先生,熱衷於儒學,為中國文化辯護的文章。牟先生曾肯定他說:「來台後,為諸生講授中國哲學,王淮君所得獨多,乃將所譯資料授之,王君潛心玩索、心領神會、乃撰為此文。於神善、神意、神智、神愛、神力、一一予以疏導補充,而以究竟了義為歸」。(見本書15頁)
作者簡介
王淮
王淮,字百谷,安徽合肥人(一九三四~二○○九),畢業於師大,執教於中興,早年著有《老子探義》一書,終生服膺老子之道,清靜無為、淡泊自然,尤其對老子所謂:「治人事天莫若嗇」,一義體會深刻,嗇者、收斂精神,拒絕釋放能量,不得已,為了謀生及升等需要,勉力著述,曾獲第五屆菲華中華文化優等著作獎及三次國科會獎助。但皆束諸高閣、未予發表。
因其行事踟躕,顧慮太多,如今匆匆離去,並無交代,而學生故舊,殷切期盼,今特將其早年著作加以搜集分類,整理出四冊定名為「王淮作品集」交由印刻公司出版。以免留下遺憾。
武陵唐亦男 謹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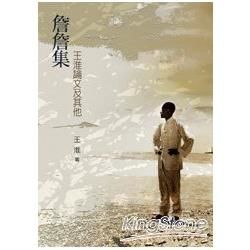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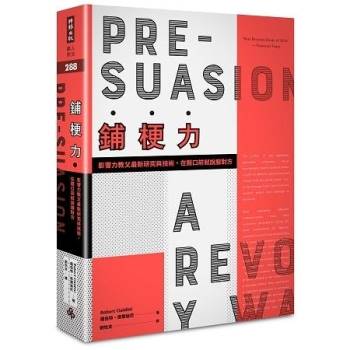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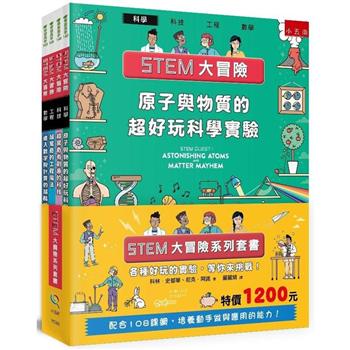





 2025【精選作文範例】國文(作文)[速成+歷年試題](不動產經紀人)](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5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