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民國一百年,
我們終於等到曾源流於同一片黃土地,
因改朝換代而離家離鄉離國的人,
之後的故事。
〈百年好合〉百歲金蘭熹從家中總管到鋼筆小姐,以貴族身世自我推銷給企業家二代的平生緣。
人人羨慕她命好,不知道訣竅就是心淡;「心淡」說起來容易,可是人生要不經過些事先把心練狠,哪兒就能淡得了?
〈女兒心〉初老的陸貞霓因丈夫黃智成過世犯了抑鬱,在香港重遇發仔後引動少女情思而漸釋懷……
無憂無慮的日子是從離開門前植滿梧桐的上海老家後就不見了嗎?那麼是從離開擺滿了蠟梅和水仙慶賀新年的香港父母家以後嗎?
〈北國有佳人〉上海灘名舞女淑英分別在上海、台灣、美國侍候過男人,每個都是她逃離從前的依託。
車行漸去,淑英感覺自己像故事裡遇鬼的書生,次日清晨醒來看見昨夜的庭台樓閣變成了土丘荒塚;她疑惑了……
〈鳳求凰〉穆斯林古麗與學生兵國清因戰爭無依因愛情犯死罪,逃到天涯海角無歸期的私奔情事。
兩朵紅雲湧上她的臉頰;她結過婚有過男人的,都不知道兩個人只說著話,手都沒碰著,也能讓人口裡生津,心裡發毛。
〈珍珠衫〉溫柔婉約的愛芬在分居的丈夫大偉與老情人朔平間長期維持著恐怖平衡,兩老的初戀最終……
女人記得一切細節。朔平一生……卻作夢也沒想到能靠三腳貓的閨房術被愛芬當成「大情人」來愛戀了半生。
〈昨宵綺帳〉舜美與雪燕年紀輕時都愛上飛官也都遭遇女人最悲苦的命運;只是舜美付出了最慘痛的代價。
恨呀!沒見沒聯絡都能藏一條手絹偷著想,舜美的嫉妒讓她心痛到連至儀落在她身上的拳頭都成了解脫。
童年時在眼前閃過的身影,窩在蔣曉雲的心頭,記憶反芻了大半生,等到民國一百年才開始訴說……
故事雖屬拼湊和虛構,我創作時,人物的一生歷歷在目,他們的英靈也與我同遊天地。我清楚地知道他們從哪裡來,會到哪裡去,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了什麼樣的痕跡。
和眷村裡「效忠領袖」與「官大一級」的鮮明階級意識不同,我成長過程中遇見的從大陸流亡到台灣的難民好像對政府都是牢騷滿腹,談到兩岸當時的「民族救星」更是意見比敬意多。既是難民,應該可能也有生計之憂,可是他們碰在一起卻很少聊油錢米價,反而喜歡讀他們不大相信的報紙,交換小道消息,和分析時勢;彷彿身在鄉野,卻覺得廟堂之事也是生活的一部份,自己可以置喙。等我長大後反芻才想通,原來這群人是民國的「士大夫」,經濟社會中叫「中產階級」。同是難民,雖然不是富貴的「上流社會」,他們卻或有文憑,或有技能,即使在難中,基本的飽暖問題還是可以得到解決,就有餘力繼續「生活」。
他們在自己的小世界裡,追求事業、愛情、婚姻,喜歡和朋友分享對人生的期望和想法;他們也關心大世界裡的經濟,政治,和時局,很長的時間他們都在擔憂「老美」隨時會放棄彈丸之地的台灣;好像他們相信第七艦隊還勝於保衛復興基地的國軍。他們講起領袖並不比今天在電視上罵馬英九像罵兒子一樣的名嘴更仁慈,對軍人和他們的眷屬也都沒有什麼崇敬之意,反而會指名道姓地怨怪哪位將軍不會帶兵要為打敗仗負責任。生活中娛樂顯然對這些「難民」很重要,他們上館子,聽戲,和看電影;友誼也很重要,他們老是聚在一起怨天尤人或者八卦配對;除了時空不一樣,他們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都和如今的中產階級沒什麼不同。這些人遭逢亂世,其中有些際遇比我寫的小說還離奇……
作者簡介:
蔣曉雲
出生於台北,祖籍湖南岳陽。現旅居美國。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畢業,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育系博士班。
曾任《民生報》兒童版、《王子》雜誌主編。
學生時期即開始寫作;一九七五年發表處女作〈隨緣〉,一九七六年起連續以短篇〈掉傘天〉、〈樂山行〉,中篇〈姻緣路〉,三度榮獲聯合報小說獎,以媲美張愛玲的驚人才華飲譽文壇。作品後來結集成《隨緣》、《姻緣路》出版。
一九八○年後結婚去國,匿跡文壇三十年。
二○一一年春天以長篇小說《桃花井》驚喜復出,短篇小說集《掉傘天》於夏季出版。民國素人誌第一卷《百年好合》在民國百年年末推出,餘將陸續出版。
章節試閱
百年好合
許多客人都找不到酒店的入口,幾隊人馬從大廈這個門口轉進去,從那個門口轉出來,電梯換乘了幾部就是到不了請柬上標明座落於酒店大堂的自助餐廳。幾張生面孔都反覆遇見看熟了眼,大家卻只當對方是空氣,一次次冷漠地從身邊穿過去。等到終於找對了電梯又發現同撳38 樓,心裡知道彼此之間就算不沾親可能也帶故;最起碼確定了擠在這一部超大電梯裡的哪怕不講本地話也不會是沒有來歷的「外地人」以後,眾人這才卸下了本地稱冠全中國的嚴重心防。一位自覺的客人怕讓其他賓客誤解自己這幾個是「阿鄉」,就搶先對同伴自嘲地調笑道: 「陸家裡今朝吃老酒派頭大來兮! 欸,儂天天軋南京路,否曉得一只電梯藏在個搭啊?」
電梯帶上來一批批客人也帶來嘈雜,就有坐在正對電梯咖啡座上的三個洋人商務客要求換到遠離電梯的僻靜位子。來客中也有幾個態度從容的,好整以暇地打量一下富麗的大堂,以及座落在城市天際線上大窗戶望出去的繁華夜景;繞場參觀的時候走過剛換到遠座的洋客身旁還歉意地微微一笑,預告自己這幾個人懂文明不會發出噪音,果然就低聲讚嘆那窗外如黑絲絨的天空襯托著七彩寶石般的閃爍霓虹。一個青少年模樣的來客用英語跟身旁像妹妹的女孩子說「看起來就像香港」,父母模樣的中年人聞言,就相互用廣東話表贊成,道:「嗨呀,詹姆士講的安,真跟那間同名酒店沒莫不同嗟。」
幾位客人觀察入微,雖然半空中的景觀窗看出去美景如畫,卻全仰仗這城市本身的麗質,這個全球連鎖的大酒店其實有點「偷吃步」,它只是跟隨著做房東的香港建商就近把本家建築物搬了過來的機會在市中心佔了個好位置,連裝潢的風格都因為和香港的酒店類似而有偷懶的嫌疑呢。幸而大堂夠大,天際線的夜景也確實美得奪人心神,分散了所有來客的注意力。其他吵吵嚷嚷的客人讓酒店知客帶領前往電梯後方數十步之遙的自助餐廳時,行經半途走到大三角鋼琴旁已經主動的降低了音量,樓層這半邊琤琤的琴聲便漸漸取代了入口處的一味喧嘩。
「哪能還賴個搭白相啊? 快點進去叫人!」兩位年長如祖父母模樣的客人走近為城市光影美景流連未去的雙語家庭,催兒孫們先進去和主人打招呼,卻說的是寧波腔滬語。
五湖四海各種口音都先到主桌去「叫人」。操寧波腔的都是金家這邊的客人,年紀大的叫金蘭熹「篤孃孃」,叫陸永棠「篤爹爹」或「篤姑爺」。長得高高壯壯講葡文或英語的幾堆人有白有黃有棕更有膚色含糊的都是陸家這邊的,老少都叫壽星和壽星公洋名,過來親吻面頰行禮。
「蘭熹,你今天真漂亮! 那張照片完全像個電影明星!」一個說英語的老太太親熱地摟著蘭熹,指向餐廳門口的大照片。女主人蘭熹隨著客人的指尖瞄了一眼,優雅地微笑著用英語稱謝: 「你是太仁慈了。」怎麼說也一百歲的人了,哪怕戴著高倍數雙光眼鏡,也是遠的近的都看不真切了。不過她拿放大鏡在強光下自己挑的照片,看不清楚也知道拍得好。影中人最多上看70,穿著淺粉紅色的香奈兒套裝,被金黃色的百合簇擁著,大照片上方橫幅寫著「金蘭熹女士95歲華誕生日會」。
客人急道: 「真的,我就是講真話!」
蘭熹的微笑加深了一點,懶洋洋彷彿不太在意地說: 「謝謝了。」活到她這個年紀,世界上還有什麼需要較真的呢? 人人羨慕她命好,不知道訣竅就是心淡;「心淡」說起來容易,可是人生要不經過些事先把心練狠,哪兒就能淡得了?
「什麼像?」坐在一旁的男主人陸永棠忽然對算自己姪女的老太怒喝一聲。又瞬間換了張嘻皮笑臉,大聲而誇張地說: 「她就是明星嘛! 」一桌人都為高齡96的老牌花花公子的做作和幽默而哄笑了。只有蘭熹不為丈夫的老把戲所動,依舊只懶懶地微笑著。
遠點一桌的客人沒聽見主桌這邊的洋笑話,可是一樣笑聲連連。
「什麼? 不會吧!」一個客人詫笑道,「100歲還瞞年齡?」
「噓!噓!」講的人噘嘴蹙眉又帶笑地要大家噤聲,「這是大秘密! 」又忍不住要多說兩句: 「她本來比她老公大四歲,結婚的時候少報五歲,變成比男方小一歲。哈哈!」
有人衷心讚嘆道:「那真看不出來一百歲! 老是老,漂亮還是邪氣漂亮!」
「做過,做過的呀! 」知情的客人兩隻手把眉眼吊上去比劃著。旁邊一淘的豎起一根食指在嘴上示警: 「噓! 噓! 秘密! 都是秘密!」可是聽見有人笑罵胡說八道,就鄭重地透露消息來源: 「否瞎講! 這種事體哪能瞎講? 金家篤孃孃自家妹妹講出來的。」
蘭熹的妹妹多,認真計較也找不出是哪家走漏的消息,反正陸家是老華僑,三、四代真假洋鬼子,知道了也沒人在乎女大男小拉不拉皮這種瑣碎。蘭熹在家中居長,她父親金八爺前後裡外三個老婆,統共養活了七女二男,蘭熹是早逝元配的獨女,原來起的學名叫舜華,在寧波老家跟著祖母長大,到了十五歲祖母去世才被父親領到上海,托給「城裡太太」。城裡二媽媽是讀過書的,懂得憂饞畏譏,怕人說後母虧待前房沒娘的孤女,替蘭熹放大了腳跟幾個妹妹一起送去上學。學校填寫報名表,蘭熹在生年一欄寫上宣統三年,管報名的先生微微一笑,塗改成民國一年。過了幾年她考初中的時候,自己又拿墨水筆把原先的學籍資料點了幾點,「一」就成了「六」,蘭熹也就從原來全班年齡最大的變成適齡就讀。舜華那個名字也是從那個時候起就不用了。後來她自己想起來也相信是命,那時候可沒料到將來會釣著個金龜婿硬比她的真實年齡小幾歲。反正蘭熹的生年就此成為懸案,不過金家很多親戚都確實聽說過八房鄉下上來的大阿姐是「跑反」那年生的。
馬路邊上兩排梧桐樹春天抽嫩芽,夏天成綠蔭,秋天黃葉落滿地,冬天就剩下一排灰黑的枯樹樁頂起幾隻朝天的烏雞爪伸向當時本市還不罕見的藍天。留聲機上平劇、越劇、時代歌曲輪流轉著,哼哼唧唧地唱不停,伴隨著小洋樓裡晝伏夜出嘩啦啦的洗牌聲。在租界裡「避難」的大清臣民們日復一日家長里短,盡著生物沿續物種的天職,並不理會外面的世界沒有為他們的消極而佇足;歐美帝國經歷了經濟大蕭條又漸漸復甦,中國的天災人禍就像他們唱衰的那樣因為趕跑了皇帝遭到報應而從沒消停。蘭熹沒再回過老家,她徹底成了個城裡小姐了。
蘭熹初一的時候得了感冒轉肺炎,等病好了自覺功課落下多了,就不想回去學校,再說20歲的大姑娘實在也受不了學校裡同儕的幼稚了。二媽榮升八奶奶的繼母那時候已經有了三個女兒,心思完全在下回怎麼生個男孩,才能和八爺有兒子的外室打成平手,別說前娘的女兒,親生女兒也都丟給老媽子教養。就任蘭熹休學在家,跟一個南洋土生不太白的洋人女家庭教師學禮儀和英語,八奶奶自己也前前後後多個幫手。蘭熹閒的時候,還讀八爺訂的幾份中外報紙,也算是進修外文、白話文。何況只要搭子對,人在牌桌上一樣長知識,並不會落伍;蘭熹即時掌握金子行情和米麵糧油的價格,有時覺得消息來源可信,她也拿出私房跟幾個常打牌的女太太一起搭夥「炒一炒」。
受祖母影響,蘭熹一直有記帳的習慣,她每天睡前都要把當日銀錢進出理一理,一面記一面口中像祖母那樣唸唸有詞: 吃不窮,穿不窮,勿會算計一世窮。八奶奶一天看見她那本帳簿,借來一翻,全是幾分幾釐麻將輸贏的賭帳,就笑道: 「這也好記? 那你來替我們家裡記記吧! 」就這樣八奶奶架空了原來被認為是八爺親信的帳房先生。有蘭熹替她看家,八奶奶可以專心金家的百年大計,就果然在生了四女之後索得一男。
蘭熹對金府總管這份「工作」很勝任,她對數字的精明和對人的統御才能更得到八爺夫婦的賞識與授權,不多久就把家裡的財務、庶務和人事權一起拿下,還沒許人家的大小姐正式成了宅子裡的大當家,也就等同今天一個小企業的總經理了。蘭熹的能力受到肯定,自己也做得開心。
夾在新舊土洋之間的金公館裡邊亂七八糟的人事傾軋只比現代的辦公室政治有過之無不及,更別提八爺還有大小兩個公館。「那邊」哪怕規模小點,一樣有主人、僕人等著領每月規費、三餐吃飯、四季裁衣、隔幾年養小孩。蘭熹記帳、管家、三節、過年、請客、社交、打麻將、看戲、恩威下人、應酬富親戚應付窮親戚,金八爺家裡她一呼百諾,過得忙碌充實。和同時輩流行的「女結婚員」不同,蘭熹的心態更接近現在叫「敗犬女王」的事業型女性。可是金公館大小姐卻畢竟不是前朝的內務府,不算是個出身,蘭熹卻一直為這個家忙到有人來向小她五歲的大妹提親時才終於警覺自己可能上了八奶奶的當,耽誤了婚姻的大事。
「多少年阿拉就講有後娘就有後爹呀!」跟著她從老家來的周媽一面侍候蘭熹晨起梳妝,一面為主子憤憤不平。表示自己有先見之明以外,更重要的是傳播小道消息:「她們講得勿要太高興,講張家那個兒子多少好! 捧舞女怕人不知道? 什麼『小北京』還是『小南京』!」
蘭熹不悅道: 「你包打聽啊?」蘭熹當家以後越見有威嚴,周媽不敢多說,咕噥著端洗臉水出去。蘭熹對鏡修眉,心想那兩個是什麼時候好上的? 蘭熹彎彎的柳葉眉全靠天天拿小鑷子除雜草一樣的拔,才把遺傳自父親家族的天生濃眉維持在她要的眉型。眉毛一根根鉗掉哪有不痛的呢? 可是蘭熹扯得狠心又仔細,簡直是除惡務盡的架式。她並看不上那個張家二兒子,可是想到男方跳過姐姐去跟妹妹提親,蘭熹把臉貼近鏡面用力地拔下一根幾次從鑷子下逃了開去的頑固份子,口中罵道: 「濁氣!」
蘭熹挺直身子,對鏡端詳;半長不短的一頭鬈髮輕攏在腦後方便梳妝,清水鵝蛋臉上是修眉杏目,瑤鼻櫻唇;櫻唇在蘭熹臉上主要是取顏色的比喻,絕對不會讓人聯想到櫻桃。照中國審美標準,蘭熹的嘴是大了點,不過唇型端正,算是歐風美唇,塗上豔紅的唇膏嫣然一笑,並不輸給那時幾個走紅的好萊塢明星。何況人都知道她頗有私房充妝奩,怎麼會滿二十四歲了連上門提親的都沒有呢? 蘭熹側過臉,伸長脖子搭拉著眼皮繼續顧影自憐;她想張家老二一定知道自己看不上他才連提都不敢來提。蘭熹倒真沒想過做幾年金府「當家人」能在親友之間把名聲搞得有多臭;張家太太恐怕寧願讓「小北京」先進門也不敢去招惹蘭熹這樣一個待嫁王熙鳳。
蘭熹摘下髮網把頭髮搖蓬鬆,正要拿梳子刷順卻瞥見下面壓著她幾天前留下的那張「字林西報」。她拿著髮刷的手停在半空,對鏡高高挑起一邊眉毛,做了個怪相;哼! 父母、媒妁都不可靠,她決定自走一步險棋。
金八爺府上大阿姐受聘成了美國名牌「鋼筆小姐」,巧笑倩兮的照片登上了西文報紙,再又被中文報紙轉載。這樣的大新聞比陽曆正月國民黨開大會決議國共合作還要讓在祖宗割給外國殖民地上避難的前朝臣民議論。
「嘖嘖嘖¬──」那個時候被小報稱為「名媛」差不多就是「交際花」的意思了。「金老八塌招式!」有一向眼紅她們家的親友幸災樂禍,認為女兒拋頭露面削了父親的面子。
間中也有持平之論,卻還是不無憂心: 「女兒大了留在家裡要出事情的! 」
「都說大了留在家裡要出事情的──」八奶奶轉述給八爺聽。形勢逼得她不能不正視大齡繼女的終身大事了,而且這幾年讓蘭熹替她當著家,現在自己兒子有了,奶媽又接上了手,是時候收回那一大串鑰匙了。「幾個女太太鞋底都跑穿了──」八奶奶確實託了好幾個人,可是願意談老姑娘的無非鰥夫或者破落戶,還真拿不出手。「──就這個南京曾家的看來可以點,也出來十幾年了,」她沒說也大了女方十來歲,老家可能有髮妻,做媒的都說不清楚不敢保。八奶奶自己是城裡太太出身,覺得城鄉「兩頭大」的情況並不是問題,沒聽說過哪個上海太太要回鄉下磕頭的。「讓他們見見面?」
金八爺伸出兩根指頭夾起放在他面前毛筆小楷寫得漂漂亮亮的拜帖,橫瞄一眼,哼了一聲;手指配合鼻孔噴氣向旁一鬆,紙片飛過桌面,紙飛機一樣地降落到地上。
「嘿!」八奶奶不高興了,「算我多事! 以後不要說我沒管你的女兒──」她拾起唯一候選人古色古香的簡易履歷表嘟嚷著走了。聽見八爺在她身後嘰嘰咕咕甩洋文,她聽不懂也猜得到,就嘀咕地回嗆道: 「哪能嘛,嫌鄉下人,嫁個外國人那麼英文靈了‧‧‧」
還真有外國人寫求愛信到西報館和鋼筆公司給蘭熹。蘭熹這份工作相當於現代的品牌形象大使,一星期中有幾天還要去門市駐店坐堂,幫人簽簽名什麼的,不怪別人看金家笑話,那確實是像那些刻薄太太叫的「生招牌」工作,真名媛不宜。可是這牌子的產品金貴,夠身家穿越店堂走到跟前的倒都是本埠正牌華洋富豪。在那個年代待嫁老小姐能夠這樣豁開來拓展社交圈,增進自己的機會,蘭熹也是膽識不一般了。
這天蘭熹來到公司時拉長了一張臉顯得特別不高興;原來拖了一陣子,八奶奶等不及了,竟以蘭熹要專心工作發展事業為藉口,把象徵當家人權威的鑰匙給收了回去。蘭熹沒想到繼母能做得這麼不漂亮,被殺了個措手不及,周媽卻不懂體恤主人心情,不安慰人,反而節骨眼上講些廢話刺激她,搞得主僕內訌,周媽鬧著要告老還鄉,過幾天兒子就來接娘了。雖然只是個老佣人,畢竟周媽是從小帶她大的,又還是家中唯一的心腹,蘭熹一時只覺得眾叛親離,心中感傷。她想: 周媽總說繼母偏心是隔層肚皮,自己還不是什麼都只想到在鄉下的兒子。可嘆她金蘭熹人才再出眾還是一個沒有親娘替她打算的孤女。
洋行有著裝規定,坐堂要穿西服,蘭熹藉機裁製各式新衣,把原本就和她洋氣長相不搭架的旗袍全部束之高閣。這天蘭熹穿了一件歐美最時興的白底黑點圓領低腰洋裝,上面套了銀灰真絲鬆身長背心,長頭髮盤進一頂鐵灰色淑女呢帽裡,露出的長而潔白脖頸上戴一條渾圓珍珠項鍊,襯上她五官鮮明的輪廓,坐在敞亮豪華店堂深處胡桃木造景的書房裡,手拿一隻貴氣金筆,眼睛卻悠悠遠望,不知道她正在為媒自傷的人,只看見一位西化的知性美人坐在大書桌前彷彿思考未來世界和平。
「你從不回信!」一個男人用英語在她桌前低聲說,「我賭你連我的信都沒打開過!」
蘭熹回神一望,只見是一個黃黑皮膚,長相平凡,幸而身板還算挺拔,一身西裝也剪裁合度的華人青年;口中說著彷彿賭氣的話,卻又瞇著一雙眼睛笑看著她。蘭熹客氣而冷淡地道: 「先生,回信不是我的工作! 。」一面望向店外,納悶紅頭阿三怎麼就這樣把人放進來了,卻意外見到屁顛顛從外面趕回來的洋人經理一壁用手帕擦著汗,一壁老遠打起招呼道: 「陸先生! 陸先生,你到早了!」。
「我的祖先是漁民、冒險家和苦力。」陸永棠從初相識就喜歡拿兩人的血統說事,「骨子裡就階級不同,不像蘭熹,天生的貴族。」最後還要挑挑眉毛,誇張地壓低聲音,用「我賺到了」的語氣說,「She married the wrong class!」
幾句老話從民國25年講到了兩人兒孫滿堂,永棠都沒講膩。在兩人漫長的緣份之中,哪怕永棠早對老婆和婚姻都膩煩過了好幾遍了,「祖先」的成份顯然一定程度地庇佑了這段姻緣;起碼未負當年在異邦發家的陸老先生送獨子返回祖國娶個名門淑女的初衷。
「看到報上的照片和文章介紹我就愛上了她,送信、送花她都不理會,只好說要投資她工作的公司 ──」喜歡開玩笑的永棠常常半真半假地告訴親友,卻沒說這是他一向「花差差」使慣了的招數。「最後? 最後不知道是誰上了誰的當? ──哈哈!我後來比較懷疑是蘭熹著急要嫁給我!」
其實兩個人都著急,除了郎有情妹有意,中外局勢都不好,世界亂成一鍋粥,租界裡人越來越多,外面的消息越來越壞,舞廳裡流行跳起快狐步,跑馬場的馬都老傳跑破記錄,人心不安定,好像連地球也越轉越快。蘭熹鐵了心要趕快離開娘家,一定要比有了人家的妹妹先出嫁;永棠在外面混了幾年,社交圈裡盡是些花花草草,也只有蘭熹一個年紀相當的真淑女「派司」他的老太爺,可以為傳承香火兼提高出身階級的家族大任交差。兩人初識於夏末,才到中秋就決定了婚禮在同年的12月12日。
「嗐,以為選了個好日子,」在慶祝結婚70週年「白金婚」紀念酒會上,永棠比畫著兩根指頭調侃自己: 「1212,一變成兩,單變成雙,好不好? ── 哈哈哈,我也以為蠻好,結果現在上海滿馬路紀念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不久,中日正式開打,然後抗戰未已內戰又起,老百姓也就跟著家國的動亂遭劫。隨著千萬中國家族被時代無情地打碎飄零,成了陸太太的蘭熹與永棠也迅速結束了王子公主婚後的日子,加入「20世紀猶太人」中國難民的大軍走向世界。
那個時候的青年夫婦半世紀後再回到本市,竟然不覺得改變太大不習慣。10年前他們在原來住的街上買了外銷樓,道旁梧桐青青鬱鬱,不是從前還勝似從前。那棟比照紐約豪華公寓蓋的大廈沒掛什麼「一品」「帝苑」的招牌,黃銅門牌上就「某某路某號」。全樓住的不是他們這樣衣錦返鄉的老華僑就是洋人高層租客,前台沿習百年租界作風用外語跟住戶打招呼。街市上倒是鄉音依舊,只多出幾個他們耳朵聽起來粗糙的「外來」形容詞。除非國外兒孫來訪,老年夫婦一般很少出門,平日跟鄰居打打麻將,再就是幾個在地親戚偶爾走動,司機佣人簇擁著去下館子。雖然高樓單位沒有當年的獨立庭院,坐在客廳裡卻可以看到近處的幾個外國領事館圍牆內花團錦簇,草木扶疏,一恍神會以為裡面還住著從前那些人。那天警察為世博加強治安來查戶口,他們拿出市政府鼓勵僑民買房時發的藍印戶口本,兩人生年分別是1916和1917,警察大驚小怪地讚嘆二老高壽健朗,蘭熹淡淡地微笑著,心裡想: 小駒頭,否曉得吾快要一百歲了!
百年好合
許多客人都找不到酒店的入口,幾隊人馬從大廈這個門口轉進去,從那個門口轉出來,電梯換乘了幾部就是到不了請柬上標明座落於酒店大堂的自助餐廳。幾張生面孔都反覆遇見看熟了眼,大家卻只當對方是空氣,一次次冷漠地從身邊穿過去。等到終於找對了電梯又發現同撳38 樓,心裡知道彼此之間就算不沾親可能也帶故;最起碼確定了擠在這一部超大電梯裡的哪怕不講本地話也不會是沒有來歷的「外地人」以後,眾人這才卸下了本地稱冠全中國的嚴重心防。一位自覺的客人怕讓其他賓客誤解自己這幾個是「阿鄉」,就搶先對同伴自嘲地調笑道: 「...
作者序
等到民國一百年
少年時對感覺不可能發生的事,會跟朋友賭氣一樣地說: 「那你就等到民國一百年吧!」
我的父親是民國二年的春天出生的,比中華民國只小一歲。可是他的身份證年齡卻在由香港到臺灣時被代填入境資料的友人誤填成民前一年,那又比中華民國大了一歲。因為需要填寫表格時記的父親生日跟他實際在家慶生時的生年月日不符,所以很大了我都搞不清楚他的年紀。我三十歲以後,他常常跟我說一句俗諺:「人人有個36, 喜的喜來憂的憂。」我一直以為他是勉勵我在而立之後要時時戒慎恐懼,努力不懈。一直到他過世之後,我常常因為思念,把記得的父女互動在心中一遍遍回憶分析,才覺悟到一九四九年中國動亂的時候,他的實際年齡正好是36歲;那一年發生的事情讓他,和許多像他一樣的中國人,人生產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
父親在湖南老家是一個地方型的政治人物,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是他「在臺上的時候」。國共內戰,他被迫離開家鄉,失去了政治舞臺。因為不能忘情,在我出生後,他還曾逼迫對政治完全沒有興趣的我母親去競選臺灣省議員;因為他評估當時有婦女保障名額,要求票數有限,在當時算高學歷又風度極佳的母親會有機會當選。沒有想到為此加入國民黨,卻因為拉不下臉到處求人賜票的母親,差一票飲恨,那也斷了父親想在臺灣繼續家族「政治生命」的夢想。
可是這個挫敗卻沒有影響父親對「管理眾人之事」熱衷的脾性,我小時候家裡一直人來人往地很熱鬧,事後回想,簡直是常常有人在我家「全民開講」。我喜歡自己看書,對大人講話從不旁聽,這個良好的品行總是被客人盛讚,這就更讓我遠離客廳裡的清談。現在想起來,我大概錯過了旁聽一整部民國的稗官野史。然而即使這樣自外於客廳裡的「座談會」,不小心飄進耳朵的一些事情和人名卻在我此後的一生於完全想不到的時空和書頁之中與之重逢或證實。事後追憶,這個奇妙的童年環境是讓我變成一個在臺灣戒嚴氛圍中長大,卻對威權或權威一無所覺的主因。
一九七九年我以文藝界青年代表的身份應邀去總統府,十個樣板人物輪流跟蔣經國握手,個個沉默不語,行禮如儀,我身旁的大明星林鳳嬌(成龍的妻子,房祖名的媽媽)還緊握我的手,微微發抖,我想一個女明星什麼場面沒有見過,跟兩個老頭(另一位是副總統謝東閩)握握手,何以激動至此?輪到我的時候,我特意示好,說:總統你好,我也姓蔣。蔣經國聽說不過一愣,旁邊的侍衛大概覺得於體制不符,就有點粗魯地用手臂把我隔開了。回家後我不大高興,父母就安慰我說:你願意跟他握手還搭講,真是看得起他,小蔣怎麼這麼不懂禮貌!
和眷村裡「效忠領袖」與「官大一級」的鮮明階級意識不同,我成長過程中遇見的從大陸流亡到臺灣的難民好像對政府都是牢騷滿腹,談到兩岸當時的「民族救星」更是意見比敬意多。既是難民,應該可能也有生計之憂,可是他們碰在一起卻很少聊油錢米價,反而喜歡讀他們不大相信的報紙,交換小道消息,和分析時勢;彷彿身在鄉野,卻覺得廟堂之事也是生活的一部份,自己可以置喙。等我長大後反芻才想通,原來這群人是民國的「士大夫」,經濟社會中叫「中產階級」。同是難民,雖然不是富貴的「上流社會」,他們卻或有文憑,或有技能,即使在難中,基本的飽暖問題還是可以得到解決,就有餘力繼續「生活」。
他們在自己的小世界裡,追求事業、愛情、婚姻,喜歡和朋友分享對人生的期望和想法;他們也關心大世界裡的經濟,政治,和時局,很長的時間他們都在擔憂「老美」隨時會放棄彈丸之地的臺灣;好像他們相信第七艦隊還勝於保衛復興基地的國軍。他們講起領袖並不比今天在電視上罵馬英九像罵兒子一樣的名嘴更仁慈,對軍人和他們的眷屬也都沒有什麼崇敬之意,反而會指名道姓地怨怪哪位將軍不會帶兵要為打敗仗負責任。生活中娛樂顯然對這些「難民」很重要,他們上館子,聽戲,和看電影;友誼也很重要,他們老是聚在一起怨天尤人或者八卦配對;除了時空不一樣,他們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都和如今的中產階級沒什麼不同。這些人遭逢亂世,其中有些際遇比我寫的小說還離奇,真事隱,假語存,我就謅出了這第一卷裡的「北國有佳人」和「昨宵綺帳」。
從中產階級社交圈衍生出去的:有依附他們為生的服務業,和他們為之提供知識和技術的達官貴人階層。
服務業階層的難民可能受教育程度比較低,求職的通路受限;聰明或有技能的就賣手藝或做小生意,老實或沒有文憑卻有力氣的可能當僕役或賣苦力。他們的時間更多花在為衣食謀,沒有時間和書本知識搞些風花雪月,人和人之間的感情就也更火辣直接。在《百年好合── 民國素人志(一)》裡的代表人物就是《鳳求凰》裡的主人翁。我還記得我到了快30歲才發現文盲跟非文盲的世界有多麼不同。我開始回想生命中曾經擦身而過的幾位不識字的長輩,遐想他們跟著一九四九年的難民潮來到臺灣的無奈和際遇。他們也曾在我童年的某時某處短暫出現,他們不是我父母親侈談天下事的座上客,我應該對他們的瞭解很有限,可是我的記憶和想像卻忍不住要去捕捉他們的身影。
等我到了海外求學並且定居,發現原來很多和我父母一樣的「民國素人」在天下大亂時沒有去臺灣,他們直接去到了世界各地,他們在民國的社會階級更往上層,很多昔日王謝流落異鄉,後代也就成了你我身邊的尋常百姓。我的思想也跟隨他們的足跡四處流浪與尋訪。然而我直接認識的其實有限;《民國素人志(一)》裡的《百年好合》、《女兒心》、《珍珠衫》就是我瞎編胡寫的這類人的故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很難說清《民國素人志》裡的人物究竟有多真實?講的是「素人」的事,寫的時候實非「素描」。故事雖屬拼湊和虛構,我創作時,人物的一生卻歷歷在目,他們的英靈也與我同遊天地。我清楚地知道他們從哪裡來,會到哪裡去,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了什麼樣的痕跡。
我不能具體的指出我的父母,和他們的朋友,或者在我童年時曾經閃過的身影,都出現在哪一個故事裡?可是那一雙無邪小女孩的眼睛卻跟著我的上一輩走了一遍他們的民國。然後,我花了大半生反芻,追尋,和思考,等到了民國一百年才開始訴說。
等到民國一百年
少年時對感覺不可能發生的事,會跟朋友賭氣一樣地說: 「那你就等到民國一百年吧!」
我的父親是民國二年的春天出生的,比中華民國只小一歲。可是他的身份證年齡卻在由香港到臺灣時被代填入境資料的友人誤填成民前一年,那又比中華民國大了一歲。因為需要填寫表格時記的父親生日跟他實際在家慶生時的生年月日不符,所以很大了我都搞不清楚他的年紀。我三十歲以後,他常常跟我說一句俗諺:「人人有個36, 喜的喜來憂的憂。」我一直以為他是勉勵我在而立之後要時時戒慎恐懼,努力不懈。一直到他過世之後,我常常因為思念,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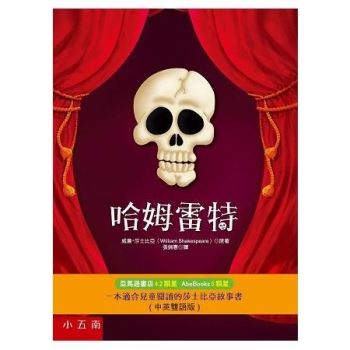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