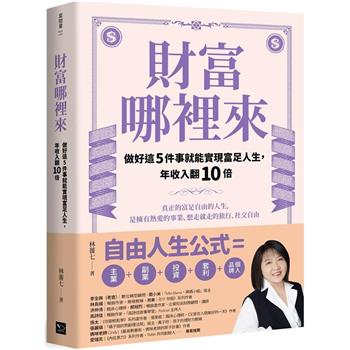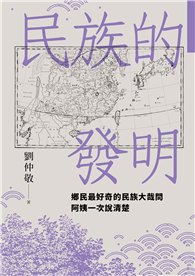他雖不斷面臨精神與身體的傷痕,但這些考驗也讓他走向一個更加靜謐與大器的世界。郭松棻的文學實踐所走向的遠方,不是一個聲名,不是一種定義,而是應許更多解消與自由的可能。──簡義明
特別收錄/簡義明教授至郭松棻紐約住所六天專訪內容
簡義明教授至紐約郭松棻住所六天專訪,郭松棻談到在台灣的成長記憶、保釣時期經歷的人與事、寫作與閱讀的思索等。讓願意閱讀和理解郭松棻的讀者,找到更多靠近作家精神世界的方法與路徑。
收錄郭松棻《驚婚》手稿與攝於書房照片
是驚婚,也是驚於命途,驚於人的難以理解無法捕捉。
關於一對男女倚虹與亞樹,與各自父親的故事,漫漫生涯、曲折心境在短短一段婚禮紅毯上鋪展開來。
憤世嫉俗的哲學青年,對父親有著無法消解的怨恨,卻與只顧好友遺族不管家庭的女友父親成為忘年交,兩代不被社會接受的男子,兩個隱藏激動與充滿祕密的反抗靈魂,在漫長的沉默中溝通,彷彿他們此生的壓抑在對方身上終於獲得解脫……
非以曲折的生命為代價,否則必不為人間所擁有。
而父親難道在母親的身上實驗著愛情的能耐?殘酷啊,難道父親以為凡是相互愛過的就不再破碎,或甚至不惜於破碎。
「現在不這麼想了﹐現在只感到亞樹這樣的人實在是稀種﹐實在是難得﹐然而實在是太痛苦了。」
「如果還能夠和他在一起呢﹖」
「那一定也惹得自己痛苦不堪﹐不過……」
「不過﹖」
「不過﹐還是值得的﹐有時候痛苦又怎麼呢﹐總比不知痛苦要好得多。」
「你這樣以為嗎﹖」詠月瞇笑起來。
你忘了你以前的痛苦﹐我給整得夠苦的。也唯有那段時間覺得自己活過﹐活得很充實。現在這種清靜反而落空了﹐反而不算生活了﹐反而是像一個廢人一般。
朝陽的房間﹐窗玻璃上都垂著花布簾﹐印花都被陽光曬淡了﹐日間這間睡房被父親
弄得很幽暗。這個世界的日光﹐他懼怕。簾布的灰塵沉沉積累﹐ 成為不斷膨脹的嘈雜的低語。
不能想像一個現代青年揹著父親的墓石一步一步穿過白天的鬧街。
也就在那後車站的台階上﹐在九月初的刺眼的陽光下﹐看見了他的臉永遠掛上了那記號。仔細看去﹐一條比膚色稍白的鋸齒形的裂痕從臉膛的中央劃下來﹐彷彿是雲端的一道閃電﹐從額庭乍現﹐直劈下來﹐在鼻樑開始的地方收煞了。那是一條憂鬱之疤﹐他在那疤記的後面﹐人更沉默了。
她失戀了﹐而他從來就不知道自己有過戀愛。他是一個被過去吞食了的人﹐他不知
道戀愛是什麼﹐他是最合算的。當她這麼想﹐他是無辜的﹐現在她仍然懷著懷疑﹐甸甸地注視著他。十幾年的見識和年紀沒有替她贏得一點智慧﹐如今她對他還是一無所知。最不合算的是她﹐遇到這樣的一個人﹐而這又已成為過去﹐當她的腳步踏著音樂的此時﹐她又能說些什麼呢﹖現在的現在的現在﹐如重複的旋律。
未來或許是不斷回憶著現在的一種生活。
作者簡介:
郭松棻
一九三八年生於台北市。父親為畫家郭雪湖。一九五八年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王懷和他的女人〉於台灣大學的《大學時代》。一九六一年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一九六三年,在台大外文系教授「英詩選讀」,一九六五年參加黃華成導演電影《原》的演出。一九六六年赴美進加州柏克萊大學念比較文學,一九六九年獲比較文學碩士。一九七一年放棄博士學位,投入保釣運動。其後於聯合國任職。一九八三年再度開始創作小說,以羅安達為筆名發表作品於《文季》,接著〈機場即景〉、〈奔跑的母親〉、〈月印〉、〈月嗥〉陸續發表於港台報章。出版有《郭松棻集》、《雙月記》、《奔跑的母親》三本小說集。二○○五年七月因中風病逝於紐約,享年六十七歲。
簡義明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現為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曾為Fulbright 哈佛大學東亞系訪問學者。研究領域為:自然書寫與生態論述、保釣世代文學與思潮、台港文藝互動、現代散文。著有《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博士論文)、〈當代台灣自然寫作(1981-2000)的危機論述與論述危機〉、〈愛與冒險——論一九九○年代之後劉克襄的「都市轉向」〉等論文。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郭松棻舉重若輕,真的像編蛛網般,一線一線細細靜靜的吐。他擅於形構,編織複雜交錯的各個線索,有時你橫走直走,亂了譜,但他清明安靜,慢慢網住整體時空引導著你。也是因為這種織蛛網般必須反覆必須專注的力量,才能鎮定沉穩地形塑如〈驚婚〉第一段這樣的小說開局,幾乎每一句都翻轉著時間空間,一句一轉,時間轉,空間轉,人物轉,敘述轉。小說所展現的企圖與實驗可能是空前絕後的,轉得不動聲色,轉得目不暇給。就像他稱讚他喜愛的小說家福克納長篇傑作《聲音與憤怒》,「一部帶有濃厚實驗精神的作品,跳接很快……才開場第十段文句,就跳接往事了」,而他的跳,更加驚人,或許是所有現代小說從未出現過的一個開端。
──印刻文學生活誌編者前言
在姊妹親密傾訴中,過去種種不曾消失,且重新滋潤了逐漸乾枯的身體。再由家族故事思考,女人(妻母女)的生命深受男人影響,家族故事的女性敘述中,女人話題多半是男人;或繞著男人轉,但是本來無聲無息的女性此際擁有話語權,由她們眼中心中看男性,往往把男性自己也看不清楚像「騷擾而顯得不安的檻裡的獸」的顢頇頹廢蠻力剖析得淋漓盡致。郭松棻還讓二女寬大;女性困於家逃之既不得,往往同理包容男性對生命性情的耗擲揮霍,縱容欣賞「夢想家瞬息間的喜悅」,只為了分享見證她們自己作不來的部分,而預備陪他們同生死。──吳達芸
〈驚婚〉寫的不只是兩人之間的愛情故事。照顧朋友遺孀的父親,以及反抗日本學監的父親,是兩種典型。一種是未完的溫婉之情,一種是未了的抵抗意志;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變成灰燼,而是像餘燼那樣不停煨燒。作為這樣父親的後裔,先天上都傾向把真實感覺埋在心底。在生活中找不到答案時,他們從來都是回到記憶裡,尋求與父親對話。在威權時代,度過幽暗歲月的青年,往往找不到精神出口。對於政治,就像面對愛情那樣,神經變得纖細而敏感。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不免是產生高度警覺。兩人明明已經相愛,卻總是不快樂,那是歷史經驗遺留下來的憂鬱,既唯美,又不切實際。──陳芳明
當郭松棻說「不為誰為何而寫」的時候,並不是狹隘的個人主義、菁英主義的思維,相反的,那是一則最徹底的反叛和抵抗各種「主義」的宣言。他雖不斷面臨精神與身體的傷痕,但這些考驗也讓他走向一個更加靜謐與大器的世界。郭松棻的寫作雖然安靜與緩慢,但那是為了更深沉的溝通與理解所做的努力與準備。在客觀條件上,他不是很容易被現有的台灣文學研究給標定位置,劃入流派與社群;在主觀意志上,他的文學與思想,亦有著一種對「無法定義」、「拒絕位置」的認知與精神向度。郭松棻的文學實踐所走向的遠方,不是一個聲名,不是一種定義,而是應許更多解消與自由的可能。──簡義明
郭松棻的小說往往長到不像短篇,卻也不是長篇,彷彿每開一個頭,就像走在沒有盡頭的公路,終點卻又是你意想不到的所在。雖然一如〈論寫作〉所寫:「剔除白膩的脂肪,讓文章的筋骨峋立起來」,小說的質地卻是飽滿豐饒、綿密細緻的。即使你專心凝神,在敘述人稱變換不定的行與行、段與段之間,隨著文字的走向,梳理出時空交錯、不斷來回過去與現在的意識流動之時間順序,讀到最後一行,終於了然小說人物曲折的內心世界,文本背後,作家幽微的內在,仍是你無法到達的孤島。──許素蘭
名人推薦:郭松棻舉重若輕,真的像編蛛網般,一線一線細細靜靜的吐。他擅於形構,編織複雜交錯的各個線索,有時你橫走直走,亂了譜,但他清明安靜,慢慢網住整體時空引導著你。也是因為這種織蛛網般必須反覆必須專注的力量,才能鎮定沉穩地形塑如〈驚婚〉第一段這樣的小說開局,幾乎每一句都翻轉著時間空間,一句一轉,時間轉,空間轉,人物轉,敘述轉。小說所展現的企圖與實驗可能是空前絕後的,轉得不動聲色,轉得目不暇給。就像他稱讚他喜愛的小說家福克納長篇傑作《聲音與憤怒》,「一部帶有濃厚實驗精神的作品,跳接很快……才開場第...
章節試閱
驚婚
牧師站在台上,用手拂了一下前襟,他抬起頭來,很難揣摩他歲數。他毫無生色,在教堂廂房的辦公室低頭盤算。秋日的午後,稀微的落日從鑲邊的玻璃窗照到他灰色的鬢角。如果不笑,臉上是沒有皺紋的。為了預祝這一天,兩星期前的那笑容擠出了他滿滿的紋溝。音樂已經在風管裡響起來。透過晃搖的紗影,看到牧師今天格外年輕的顏靨,那是他因站到了壇上,突然喚回了生命的緣故。二姊站在走道上,已經在打準焦距了。她從自己的腳尖才微抬起頭,閃光燈嚓的一聲,照痛了她一夜未眠的眼睛。坐在兩邊排椅上的一、二十付眼睛轉過來,釘在她的身上。那都是無辜,也是無知的眼睛。今天她無心應付這些眼睛啦。
「那是個好日子。」牧師坐在廂房裡說。對於她終於不再堅持選擇聖誕節那天舉行,牧師舒了一口氣,然後瞪著她笑起來。牧師說聖誕節忙不過來,日子雖好,怕是照顧不周的,一有疏忽,那就不好了。「這是一輩子的大事啊。」
擇在一月份是好的,節日過去了,但是節慶的餘緒猶存,大地的皚雪也是充滿了搖鈴般的喜悅。這時牧師站在窗口,雙手剪在身背後,突然墜入了沉思般,就這樣解釋說。已經到了牧師吃午點的時候了。每次他突然從辦公桌後站起來,他們就知道應該告辭了。幾乎總是在這個時候才注意到窗外的日光已經薄了,房間裡不知不覺已襲入教堂將有的一般冷冰,即使再輕步,總是覺得自己像是走穿過陰濕的地窟似的。
她把自己關在樓上,拔出電話的接頭。窗外的雪光越來越亮,照進屋裡。她要好好想一想,其實她什麼也不想。其實她就是不去想。他突然臉色暗下來,把一根剛剛夾起的菸扔掉,用腳重重去踩息它。他說他真不懂,訂婚已經這麼幾年,在這種地方,人家連手續都省了。她一句話沒說,只站在超級市場的門口,無端望著一輛一輛的汽車,車輛頂上都蓋著上個星期的雪。他抓起了地上幾包紙袋,放進車廂裡。車上他們沒有一句話,直把她送到她的公寓。
樓梯有詠月的聲音。她在門上敲了兩下,只輕聲說了一句晚飯放在爐裡,然後自己就走了。詠月這一去就得在實驗室裡留到天亮。有時她出門了,詠月都還沒回來呢,沒想到來到這裡還可以交到這麼好的朋友。她輕聲輕氣又下樓了。
今天詠月也是輕步繞著她忙。這個婚禮,詠月比自己都還高興。或許也因為這門親事畢竟是她期待的。
屋裡沒有燈,詠月也知道她沒有睡。她凝視著牆,視線落在白茫茫的一片上,每次的敲門都讓她驚動起來。門雖是關著,也感到詠月是看到她了。
那是我的錯了,詠月這麼說,我不該催妳……。詠月,她說。
於是她們之間就沉默了下來。兩人共賃的公寓曾經有過快樂的時光。她們輪流做晚飯,直到詠月開始忙起她的實驗。
樓下是一片空寂,剛剛詠月才把門鎖上。接著她窗下的車房裡,汽車發動了。
汽油味滲進來,汽車的輪子在雪地上滑出去,安靜和平,這就是詠月。
「他打工時,傷了胸部。」十年前離開時,竟不會要他一張照片。詠月形容不出他的樣子,每天難得開口講話的一個人,寧願仰望著天花板。
她則有亞樹的照片。人影已經模糊,站在小學背後的一段短牆前面。細瞇著兩眼。一定是太陽正射在他的臉上。照片的曝光過強,那時他已經是大學生了,很鬱鬱不樂的樣子,照片是她照的。另外一張是她和他站在同一個地方,請過路的人幫他們照的,他們對著夕陽的兩張臉都很寂寞。那時她要出國了,他剛要留下來當兵。妳走吧,妳走吧,祝妳生活美滿。不會的,不會的,我是不會結婚的,我不會的。
她微微抬著頭,但不想對著鏡頭,人是在前進,但走得很慢。她對自己說,她的確是一步一步在沿著甬道走,大致是隨著音樂的緩慢節奏。她在前進,因為面對著她的二姊一步一步在往後退,測著鏡頭的焦距,閃光燈已經使她本就未眠的頭更加昏眩了。
她低下頭看著自己的腳一步一步慢慢的踏著,沿著小學的後牆,看麥娘長滿一大片,穗花摩著她的膝蓋。小學已經放長假了。牆的裡頭空曠無人,他指著從牆外只看到鱗鱗的瓦片向他們傾倒過來的禮堂說,那一年禮堂失火,讓他以後的小學生活空虛而慌張。他的童年就在和小學毗連的這一片小公園裡度過的。她順著他舉起手來指出的方向望去,那無非是一塊在市裡可以稍稍看出去的空地,檳榔樹遠遠印在晚霞的西天上,再過去就是他的家。他就在那裡出生的,現在還住在那裡,他說。
她們各自談著一段往事,那是詠月還沒有去實驗室以前,晚飯的桌上,詠月開始喜歡喝點紅酒。你不能想像沙漠是那麼的寂寞,你也不能想像一個人會為了一本書整個沉迷下去。我是不應該離開他的,可是那時誰懂得這些。一心只想早點離開那片沙漠。他嗎?後來就斷了音信了,我想他或許還留在亞利桑那州的沙漠上。那是什麼時候?那是……我想……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
要不是突然接到亞樹的電話,這件事恐怕要再拖延下去的。她在電話裡突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是亞樹,還記得吧?只是淡淡的一句話,然後就是突然暗淡的沉默……。多久了?也該是十幾年了吧?噢,記得,記得。怎麼不記得。其實這幾年才把照片收到抽屜底下,以前還是動不動就拿出來看的。這個牆角槍斃過人,那是我小學三年級,他的口氣竟會這樣平淡。我早上上學走到這裡,看到黑壓壓一群人擠在那兒等著看槍斃。
於是你就擠在人群裡?
於是我也就擠在人群裡。就在這裡,他的腳在牆腳跺了跺,像一團草包似的,應著槍聲癱下去,就在這裡,你給我照一張。每一次看著照片,人影慢慢退色了,而照在身後牆上的黑影則越來越浮上來,好似亞樹離不開那鬼影。
他是怎麼樣的人呢?他是一個可憐的人。聽說是搶了兩條街外的華南銀行。
你為什麼要看呢?這種可怕的事。
那天下課了,我又走到這裡來,人們已經洗去了血跡,牆腳還是濕的。我只對自己說,那麼我的小叔們也是這樣死的。來,我們一齊照一張,於是她踏進了齊膝長滿一片草的牆腳。
詠月敲著門說,晚飯放在爐裡,她從失神裡驚坐了起來,照片落到床底下。
亞樹的臉在她的腳邊,依然細瞇著眼,望得很遙遠,她方彎下身,想把照片撿起來,詠月說晚飯放在爐裡,這聲音也遙遠得好像從世界的那一頭傳來。站在黑暗的房間裡,她的腳步有點踉蹌。於是又躺回床上去。現在只有屋角老舊的熱氣管在滋滋作響的聲音。
我可以不可以過來看妳?還是若無其事的口吻。你一個人嗎,不,他是一群人,開著一輛舊車,橫跨美國而來的。她從二樓的窗口望出去,胸口一下子怦怦跳了起來,跳下車的那個人不就是亞樹嗎?一部濃密不馴的長髮在風中翻蕩,像牆腳的一片看麥娘。
他向她揮手,沒有說什麼。她好像聽到了轟隆的聲音。令人惶惑的北風吹著她的髮。她看著照片,看著影子,現在看著人了。
後來留宿的問題是由他提出來的。能不能過來看妳,能不能在妳的地方宿一夜,大家都帶著睡袋,吃睡都不用妳操心。在電話裡他說。當然。當然。方便嗎?當然。當然。但是她沒這麼說,只說可以安排,反正她的室友都在實驗室。
樓下的客廳充滿了汗臭,他們幾天沒洗澡了。其實天天都洗的,他說。不過他們在趕路,吃宿很隨便。聽說他們為了一些地圖上找不到的小島嶼在奔走運動,怕又被日本人佔去了。那麼你呢?你的學業呢?還是哲學嗎?沖了一個澡以後,讓人都記起了從前。
他們面對面,站在廚房裡,為大家燒一壺熱茶。無形的距離橫梗在中間,問一句,縮小一點。再問一句,又縮小一點。窗外三點鐘的太陽已經混渾了,慢慢像煎熟了的一只雞蛋,蛋黃躲進蛋白裡。地上的積雪亮了起來。廚房暗了,啪,打開了燈,看到他的笑臉。已經很遙遠,畢竟十幾年了。
她一步一步走上前去,牧師的笑臉在前邊等著。
你使我痛苦,你故意使我痛苦,第一次驅車去看牧師,他的車子橫衝直闖,一邊開一邊這麼說,負氣要撞出車禍來似的。站在教堂的草地上,她感覺到牧師聰明的眼光在他們面前溜轉著。她沒有轉頭看他,他的話是向牧師說的,但是她聽得出來是向她責備過來。
他們三人靜悄悄在教堂旁邊的一條甬道上走著,現在牧師一言不發,走在他們兩人之間,只感到一個身子硬擋在他們中間而不便,不時在思索著一兩句話,然而卻在窒息的空氣裡走完了那條漫長的甬道。或許你們好好再想想,最後牧師只想起了這樣一句凡俗的話。
那一年他們走過華陰街。
鐵路倉庫的那條狗,站在滿是簷漏的遮棚底下。他說他再也不原諒他的父親。在一條雨街的盡頭,他還要不停的往前走。
那種事情不會再發生了。
他的祖母生了四個男孩,現在只剩下老大,也就是他的父親,還留在世間。
三個叔叔死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是這一點,他和父親疏遠了。
那一夜,他沒多說,一路把她送回家,他準備上山守齋。
再下山的時候,那一定是秋天,因為他們踩著乾黃的樹葉。
他們走過一條後街,走進鐵路倉庫的馬路,一股開始成熟的水果香飄在欲雨的空中。倉庫的閘門都拉下來,最後的一批搬運工人跳上一部卡車都走了,突然被遺棄的馬路一時很荒涼。稍遠的地方,火車頭忙著在調轉,一聲尖幽幽的汽笛,接著就聽到蒸氣的排洩,這一切忙碌都被一場快來的西北雨的等待所掩蓋而顯得瑣碎和無意義。現在倉庫的遮簷下,浸著冷露的角落裡,充滿著被遺棄而有了安適的恍然。
現在由於沒有一點陽光,他的臉驟然有了光亮的銅色,然而兵營裡的陽光曬不到埋在他眼窩裡那逼人的憂鬱的寒氣。他的全部的生命集中在這上面。愛著她的彷彿就是一股憂鬱,她經常是為此而好奇,要抬頭去直望著他那雙沉默的眼睛。
一種幽幽醒來的恍然,彷彿頭上被遺忘的一片雲,影子落在他們的身上。現在這個人突然站在她的面前,在波士頓的蓋滿皓皓一片雪的夜裡。時光令她激動,開口竟得鼓足勇氣,而在這一無聲籟的夜裡,她感到震耳欲聾的是什麼呢?
轟轟的聲響一輪一輪包裹著她。他的嘴在動,噢,但是她聽不見,她只看到他依然蒼白的那種激烈,十多年了,她不應該去揣測他的念頭。她從他的身邊移開了。他身上的熱氣緊緊又攏過來。還是憤憤的不樂嗎?生命的活力一如火車蒸氣的排洩。她那樣站著,對著一向自以為熟悉的後院,被一陣慌亂所佔據。她不應該背著他,她不應該悄悄移開,她應該站在那兒,不來人的地方,面對面好好談談,談談這些離開以後的年月。然而她現在已經提不起勇氣再轉過頭來,他的腳隨著她踏入雪裡,在一種恍然有了記憶的同時,他的雙手,仿如無形的過去,落在她的肩上。
這時,火車的聲音在雨中消失。搬運工人離去以後,馬路留下的空白現在被雨的滴答代替。青年時代的那雙唇抿得緊緊的。當她一再勸慰以後,他停止了憤怒的顫抖。她從他的臂裡脫開,靠在閘門的鐵皮上,她不想阻止他。她正愛著他。她想著他那種稚氣地喊著她的名字,一身淋在雨裡,她已經在自家的門口了,只得再奔出巷口,為的是深怕他的叫喊吵醒了鄰居。然而她不知道他心裡的鬱結竟會那麼緊。第二天他不告而別,入山守齋去了。
還是哲學嗎?她的爐火燃起來了。
她避開了他的注視,走向停車場。低垂的電線懸在廣闊的空中,頭上的鉛雲層層疊積,西天掀開了一塊薄暮,幾天大風雪後,難得一見的殘陽,微弱的光芒照射在寂寞的山巒上,顯示了這邊谷地一片雜亂的來往。每次雪封之後,超市就有搶購的現象,你走進市場,總覺得肉都不新鮮了,都是剩餘的東西,也不怕沒人來搶走它。站在超市的簷下,他呵出一口熱氣。一種她不曾期待的生活出現在她眼前,曾經夢見過自己一個人站在山崖上,瞭望著無際的海面,事後想起還感到心悸。那是因為海的遲鈍。聽到海濤,好像走進一個無盡的世界,那起伏是永遠可以預期的。汽車駛入公路,天色已經暗下來,雖然還只是下午三點鐘。在公寓的門口,他曾經耐心的等待過她,也是攝氏零下的天氣,一如此刻,他開車替她買菜,一個星期一次,她坐在身邊,車子在兩邊堆成雪牆般的路上緩慢的駛著。她有點溫馨的恍惚,把全部的心思貫注在未來那種無望的生活裡,直到那一天在電話裡突然又聽到了他的聲音。你好像嚇了一跳,其實那已經死了好幾天都有了。那是一隻被輾死的野兔,血跡已經是一團黑色,車子快從身上駛過時,她在車座上突然怔了一下,驚回到現實。
最後來到了自己的家門,她還是沒有一句話。他把一紙袋一紙袋的食物替她拿進去,放在廚房。然後,在她還來不及想要如何反應時,他只說了聲再見,搶著向門口走了出去。
窗外的天光很耀眼,那是紛落的雪花隨風在飄蕩。有時風強一些,雪片像瘋婦一般現出教堂裡音樂的柔弱。耶穌受刑的木像懸在牧師的頭頂上。
牧師是時下到處可見的樂觀的人。冬天被室內熱氣熏得透紅的雙頰總是緊緊地抽動著,露出了他的笑容,好似那是他的職責的一部分。緩慢而猶豫的話語,總在他嘴裡,不輕易說出來,那是思維的表示,隨時在與遙遠的冥暗處溝通著什麼。當他截然地說出話時,那必然是終於從遠方接到了訊息的緣故,然而那是不可思議的軍事。當她在無法接受結婚這念頭而陷於紊亂時,她突然一個人拜訪這位牧師,而他站在走廊上,頸子在一環賽璐珞的頸圈裡扭動了起來,支吾著。三月的雪滴子已經從雪地裡綻開了花瓣,遙遠的地方沒有給他任何訊息。
或許年底再說吧,情況可能會改變的。七月的陽光從簷下照到他稀疏的頭髮,他紅潤潤的臉色依然是人類精神從哀樂中提昇出去的業績。人類是個個應該避進教堂裡的,然而他從來沒有明白的主張過,只有他的笑臉遠遠在那裡招著。
春天以來不斷的失眠,使她的面頰漸漸蒼白,她知道自己在七月的廊下是咬緊著牙根才把頭撐起來的。
今天也是一樣,她整個人撐著昨日一夜未眠的遲鈍和重量,一層薄紗掩飾不了她的惶惑。無法睜開的眼睛緊緊被蛛網罩著,視線是遲鈍的,耳朵卻靈敏。
為了結婚這件事,她那樣不敢苟且,隨時熱衷在攻修的藝術史課程也零亂了,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一點透視的鑒賞力也突然停頓了下來。這將是一種莫大的犧牲,驟然的恍然倒令她驚嚇了,而想起了自己的年紀。
那一年,颱風的那一學期,唯一不同的是老工友歐吉桑細弱的手指戴上了相形之下極其碩然的金印戒,說是媳婦給他打的,六十歲的壽禮。
一天下雨,在黃檀樹下他遞給她一把傘,自己淋著雨,走過那一條小徑,她奔過去,他也開始跑,跑離了她。
父親本以為學監是救了自己一命,其實或許那是父親從少年時代開始就一連串災厄的一個轉機。父親成為有機會而又為機會所制的人,現在回想起來,總覺得是他一生悲劇性的總結。沒有這個學監,父親可以和其他人一樣過著他平穩的一生,當然這也是難講的。這就是如若沒有什麼什麼歷史就不會這樣那樣發生的後見之明。不過「如果沒有這個學監……」的想法經常在我的腦裡閃過。即使父親打了那日本人,而那日本人在法庭上不推翻一切事實的話,父親會怎麼樣呢?事後想起來,坐幾年牢,在人的一生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唯其父親僥倖避過了牢獄的生活,才開始了他一連串的災難。
父親凹陷的眼窩充滿死亡的幻影。使人沉潭溺水而死的也是另一種生活所安排的錯誤嗎?涌著岸邊水浪而成的那長髮的節奏,被過路人猜測著,沒有人相信仰背浮在水上的會是一個有了高中兒子的婦人。那豐美的頭髮,皙白的肌膚,終於證明了非以曲折的生命為代價,否則必不為人間所擁有。站在岸邊圍睹的閒人在經常發生的溺亡的圍觀中多了一層驚艷的眼神,那是再自然不過的,那是神明的一次豐收。接著父親在黑暗的厭倦中聽著夜夜的雨聲,自己生起一盆炭爐,烤著突然血再也不流的那雙過於奔波的冷腳,連他的手心也溫熱不起來了。每夜自己搖著頭,不肯相信這一生發生的一切。
(未完)
驚婚
牧師站在台上,用手拂了一下前襟,他抬起頭來,很難揣摩他歲數。他毫無生色,在教堂廂房的辦公室低頭盤算。秋日的午後,稀微的落日從鑲邊的玻璃窗照到他灰色的鬢角。如果不笑,臉上是沒有皺紋的。為了預祝這一天,兩星期前的那笑容擠出了他滿滿的紋溝。音樂已經在風管裡響起來。透過晃搖的紗影,看到牧師今天格外年輕的顏靨,那是他因站到了壇上,突然喚回了生命的緣故。二姊站在走道上,已經在打準焦距了。她從自己的腳尖才微抬起頭,閃光燈嚓的一聲,照痛了她一夜未眠的眼睛。坐在兩邊排椅上的一、二十付眼睛轉過來,釘在她的身上...
作者序
謄文者後記
李渝
《驚婚》手寫本頗完整﹐頁邊和文內常有紅﹑藍筆批註,是作者留給自己的編輯指南﹐多在調動字句段落﹐添增補延內容﹐勾勒下文走向等。後邊頁數的行段之間偶然出現空白,為補白而留出。在我的謄稿過程中,更正字面手誤不難﹐按照批註修輯也還可以應付﹐不容易的是怎麼處理留白,怎麼根據了筆批的提示,和對作者的文體和思路的瞭解,揣摩出它們若隱若現的原形和原意,而把上下文連貫起來。這部份約佔全文的十之一、二。
《落九花》謄完後,松棻要我幫他把《驚婚》的手稿也打成電腦檔,應是二○○五年冬春交替的時際。○五年五月我去香港教書前,打到了全文三分之一左右的地方,自然是計畫回來後完成它的。七月松棻驟逝,工作戛然中止,以後有很長一段日子無法再看原稿。我將它藏進了一個檔案夾,開始擔心因我的無能它將失落。怎麼也拿不出勇氣,曾允諾的協助也有待落實,這樣又過去了好幾年。精神言行各方面都嚴重失序的時間﹐我不時跟自己說,這件事必須完成,必須由自己完成。二○○九年勉強再啟動,拿起放下停停續續,到底是謄完共五十六頁的全稿。二○一○秋我去台大台文所教書,學期結束回來紐約,正值深冬一月,寧靜的季節。打開電腦文字檔,手抄本置放在肘邊交互參照,開始了編輯的工作。這年雪不多,庭院草地不曾枯黃,窗外始終是綠顏色。
從觸目驚心失魂而畢竟能當作一篇稿件冷靜處理,經過了八年,不能算不長。如果說,和文稿的搏鬥就是與松棻的記憶搏鬥,與自己搏鬥,也不為過。就像小說中的自閉的父親一樣,﹁在那幕帷的那邊,在那關閉的小屋內裡,或許是把世界看得最清楚的時候了。﹂在混亂的日子中, 竟也是我把世界和自己看得最清楚的時候。
雖是虛構小說,虛構建基於私人和眾人記憶,二者松棻和我共有而同享,例如五、六○年代的純情和鄉愁,虛無和失落,例如文學院後門春天最早開的那朵芙蓉,中庭台階旁的老黃檀樹,為院長燒茶水的鋁壺在工友室過道旁的小火爐上冒白煙,上課的時候你可以聽見歐吉桑在庭院裡咳嗽等。這是我們一起成長的環境,庭院外的世界尚未撲來,生命尚未曝露真相的少年時光。好在文學和回憶究竟不同,回憶固然總是傷懷,文學卻能拔昇回憶,而到底是完成了小說的謄輯工作,無非是我更相信後者而已。
謄文者後記
李渝
《驚婚》手寫本頗完整﹐頁邊和文內常有紅﹑藍筆批註,是作者留給自己的編輯指南﹐多在調動字句段落﹐添增補延內容﹐勾勒下文走向等。後邊頁數的行段之間偶然出現空白,為補白而留出。在我的謄稿過程中,更正字面手誤不難﹐按照批註修輯也還可以應付﹐不容易的是怎麼處理留白,怎麼根據了筆批的提示,和對作者的文體和思路的瞭解,揣摩出它們若隱若現的原形和原意,而把上下文連貫起來。這部份約佔全文的十之一、二。
《落九花》謄完後,松棻要我幫他把《驚婚》的手稿也打成電腦檔,應是二○○五年冬春交替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