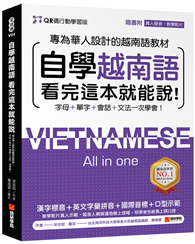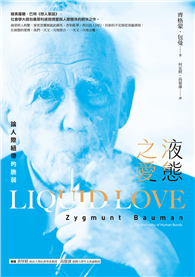二○○九年五月,登山家李小石背負媽祖聖像從珠峰頂著暴跳如雷的風雪回到台灣後就開始盤算,下一次八千公尺以上的登山計畫要如何完成。他花了兩年時間,終於在各方熱情人士的贊助下,籌足經費,於二○一一年三月出發前往世界第八高峰:標高八一六三公尺,喜馬拉雅山脈的馬納斯鹿。
攀登馬納斯鹿有二大難關:首先,機械運輸工具只能抵五百七十公尺高的村落,剩餘路途僅能徒步,且途中幾無山屋可宿,須搭建臨時帳篷,所有登山設備、食物須靠人力及騾隊運送至四千四百公尺高的基地營,約耗時十三到十五天;另一個障礙是大雪崩,因地質關係,馬納斯鹿雪崩情況比聖母峰嚴重許多。
同時入山的伊朗和法國隊伍都有人員傷亡,李小石自己亦一度凍到意識不清,雙頰也被破損的氧氣罩刮得面目全非,不難想像登山過程之艱難。在李小石暢快淋漓、一氣呵成的筆下,攀登過程的奇險與驚喜,讓讀者彷彿親臨其境,時時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氣;而他的攝影鏡頭更讓無法親炙奇景的讀者得以一窺世界頂峰的動人∕駭人面貌。
為何選擇既高且險的馬納斯鹿峰?或許如校注者林燊祿教授所言:
馬納斯鹿在尼泊爾的西北,屹立千萬年,觀盡世情,護蔭尼人:山,其有魂也;客登馬納斯鹿,親炙自然,赤子情懷:山,客魂之所嚮往也;登山者或不幸而罹難,死得其所:山,客魂之所寄也。
李小石自己則說:「登山對我而言,非為超越巔峰或挑戰極限,純粹是喜歡山。第一次登山在高中,內心突有一股莫名的情緒不知何以紓解,便隨意遊走,潛意識地想躲開人群,信步往高處攀爬,走了幾個小時,驚覺身在山林中,又飢又渴,意圖返家卻遍尋不著來時路,就這樣在山裡亂竄了數小時,倒因為集中注意力搜尋歸途,自然忘卻感情受挫的哀傷,不經意發現登山是療治情傷的好方法。日後,只要心緒苦悶就往山裡跑,上了山就能達到身、心、靈舒暢。攀登過程歷經千辛萬苦,甚而不見天日,終究來到山頂,視線豁然開朗,將氣喘噓噓的自己交付美景中,漸漸氣定神閒,達到山人合一,心領神會,不可言喻。」
作者簡介
李小石
1955年10月10日出生在台灣海峽的一個小島——馬祖。從小與山林為伍,喜歡在課本上塗鴉。
1972年擁有第一台Nikon相機。
1973年第一次登山攝影,五指山、月眉山、大屯山、七星山,漸漸走上台灣山林。
2000年11月完成百岳,從此走盡台灣的千山萬水,在山的時間比在家的時間多;完成大、小鬼湖攝影,內本鹿古道縱走;三次帶領布農部落入山尋根。
因藝術創作遇瓶頸而走入山林,結果卻愛上山岳攝影,使藝術創作的素材更為寬廣。
2007年至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健行,攀爬卡拉帕坦(海拔5592公尺)及三山越嶺,並攀上Gokyo Peak(海拔5360公尺)。
2008年再度至尼泊爾攀爬Island Peak(海拔6193公尺)、Ama Dablam(海拔6896公尺)。
2009年三度至尼泊爾經三啞橫斷攀爬Lobuche East(海拔6119公尺),抵聖母峰基地營,5月22日攀上聖母峰(Everest,海拔8848公尺),並於2010年出版登頂紀實《喚山》。
個人網站:石頭剪刀部 amoformosa.idv.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