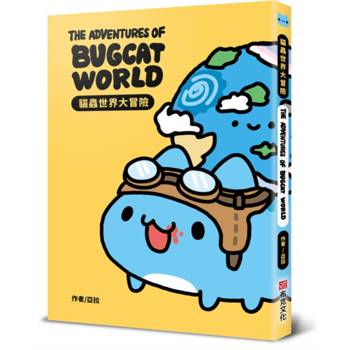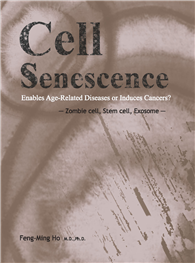尋找塔斯馬尼亞虎 我爸常說,富豪會讓自己的身邊圍繞著會增值的物品,一般人選擇的卻都是些會貶值的東西。這棟房子除了有斯特利的風景畫、走廊上的鐘、表面上了法式拋光漆的古董餐桌等資產,還有梅卡夫。他的價值也是一年高過一年。他不像老爺鐘那麼高,也比桌子方便運送,雖然沒戴眼鏡,但這樣一個小缺點用錢就能解決。
我不認識梅卡夫,但我也沒這個需要。光看就知道他的政治傾向、常去哪些餐廳,還有是誰幫他剪的頭髮。我早知道這棟房子看上去會是這個模樣,而且必定位於富人區圖拉克的眾多豪宅之間。每個地方的人都會扮演自己分配到的角色。生在富豪之家,與隸屬某種過度控制信徒言行的教派無異。
這間房間的燈光寧靜祥和,比外頭的光線優雅,更為溫柔,有種誠惶誠恐投射到古董上的感覺。柯教授在桌子對面,坐在梅卡夫的右方。柯教授在執掌這個信託以前,原為數學領域的研究人員,在北半球一間歷史悠久的大學任教。不過他最近顯然和科學界的人疏於往來,在我選定的大學中既沒有朋友,也沒有同僚。因為健康亮起紅燈而退休之後,現在這份工作是他唯一的職務。他和梅卡夫的父親是朋友,所以接下這個工作算是道義上的相挺,只是有利可圖。
柯教授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完成他的職務。事情向來是他說了算,而且似乎沒有多少規則可言。梅卡夫等於是顆橡橡皮章,在這些最後面談中,他的現身參與徒具形式。對他來說,兩萬五千澳幣不過是可以扣稅的小錢。
我強迫自己的視線回到梅卡夫身上。這間房間的富裕令我飢渴。我眨了好幾下眼睛,才與他四目相接。
※ ※ ※
「我今年二十九歲,」我說:「我從二十一歲開始就是個演化生物學家。自從交出博士後論文以來,我做了該做的研究。我有過很好的工作,在正確的期刊上發表了很不錯的論文。但現在……我以為這是我的機會。我知道這個計畫不是很正統,但它是我從小到大的夢想。」
「妳真的想在威爾森岬國家公園找到一隻塔斯馬尼亞虎?」柯教授的聲音如履薄冰,宛如即將說出什麼壞消息。「康博士,牠們已經絕種了。即便是還沒絕種以前,牠們在維多利亞省棲息也是好幾千年前的事。妳知道有多少觀光客造訪那座國家公園嗎?還有露營和健行的人會在那裡度週末或是更長的時間?那裡到處都是人,妳卻從小懷抱著這個夢想?」
我不看他。他要說什麼都無所謂,那又不是他的錢。我的雙眼始終注視著梅卡夫。他聳了聳肩。
「真不一樣。」他說:「大多數的小女孩想要的是一匹小馬。」
祕書在我面前放了個杯墊,接著是一杯水。我喝了一口,穩住自己。還不到窮途末路。
「這不是你們贊助的第一項非正統研究經費申請案,貴信託在給人機會方面很出名。你們知道,科學界也有小道消息,我們都會談的。」
柯教授輕哼一聲,我說錯話了。「妳錯了,」他說:「我們的,嗯,選擇比較寬廣,可是很謹慎。我們是墨爾本最古老的私人贊助信託之一,不能壞了自己的名聲。」
「我們贊助那個想知道狗會不會用不同口音吠叫的研究那一年呢?」梅卡夫說。
「那是個很傑出的研究,」柯教授說:「是溝通理論的先鋒。」
「還有那個研究雪花的人?安格教授?」
柯教授眨了幾下眼睛。「完全是有憑有據。有個未經證實的假設說,每片雪花都是獨一無二的,而那個計畫是對這個假設第一項適當的統計研究。」
「還有那個博士,叫什麼名字來著?就是那個想要隨機挑選個案,強迫他們離婚的人。」
「如果你還記得,我們最後並沒有贊助那項研究。」
「沒有嗎?」梅卡夫往後靠著椅背坐,雙手交叉。「我倒覺得那是個不錯的點子。我的已婚朋友總是爭論,不離婚但整天吵架,還是離婚並整天吵架,哪個對小孩比較好。」
「她不會得到道德委員會的許可。」
「可惜。」梅卡夫說。他拉開我旁邊的椅子,坐下來,直直望進我的眼裡,好像是第一次看到我。「跟我說說妳的計畫。」他說。
「嗯。」我打起精神。「每個人都認為塔斯馬尼亞虎在三○年代就絕種了。然而,每年還是有目擊塔斯馬尼亞虎的報告,有些是在維多利亞省。」
「一派胡言,不可能有人真的在這裡看到。」柯教授說。
「讓她說完,老柯。」梅卡夫說。
「我知道機會渺茫,」我說,一手放在梅卡夫的膝蓋上,這是個下意識的動作。「就說草原西貒好了,一種像豬的物種,在巴拉圭發現的,但在一九七五年前,大家都以為牠早已絕種。現在我們知道全世界有三千隻草原西貒。」
「三千隻豬。」柯教授說。
「不只是豬。負鼠呢?一九六一年前,世人也以為牠們絕種了。還有澳洲白尾鼠呢?有二十五年的時間不見蹤影,後來卻又冒了出來。紅木袋鼯呢?我們原以為牠們已經絕種一百年,一九八九年時卻出現了幾隻。一百年!牠們失蹤得真是徹底。」
「妳說得對。」梅卡夫聳聳肩。「這可不是不跟任何人說一聲,就衝去店裡買牛奶那樣。」
「各式各樣的動物從公認的絕種狀況重現於世。」我說:「牠們被稱為拉薩路斯物種。都在裡面,」我重拍一下桌子,「我的申請書上寫得很明白。」
「我想我開始了解了。」他說:「很吸引人,絕對勝過那個研究雪花的傢伙。」他站起來,兩手交互揉搓雙臂,一副不習慣久坐的樣子。「唔,康博士……妳的名字是?」他問。
「艾拉。」我說,停頓得剛剛好。不太快,以免顯得我有什麼要他認同。不太慢,以免表現得像是不記得自己叫什麼名字。
「嗯,艾拉,這真是我參加過最有趣的面談。」他對我伸出一手。「我可能還會有些額外的問題要問,需要釐清一些重點。我能打電話給妳嗎?」
「當然可以。」
詐騙家族 我們都在坎柏蘭街的餐廳參加週四晚上例行的家庭會議,每個人輪流討論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和需要其他人配合的事項。我爸坐在主位,餐廳的桌子和梅卡夫豪宅裡的很像,但坎柏蘭街既不冷淡,也沒有自命不凡。這棟房子有個送菜用的小型升降機,地毯的花色各有不同。走廊去不了哪裡,門會自己打開。這裡是數個不同年代衍生而出的迷宮,是數十年來從事暴利工作的結果。主屋至少有十二間臥室,蘋果樹下也有幾間可以住人的小屋,還可以藏東西。這裡有我們才找得到的地窖和避難所,門齊平埋在地裡,藏在落葉之下。
雖然我爸的書房仍然藏在廚房的活板門下,但餐廳是我們吃東西和工作的地方。餐具櫃上堆放了晚餐用過的髒盤子,角落裡有塊我們用來做計畫的老舊黑板。我爸不肯聽我們的話,換一塊新發明的白板。當然,紙就更不用提了。小茶几上放了一組我爸的象牙西洋棋,這是他教我們重要策略的方式。我們全都在很小的時候,學會像個惡魔般下棋。
露比坐在我爸的左邊,她現在五十幾歲了,不過全身上下一直到暗紅色的指甲仍是優雅的代言人。她的坐姿有種退休芭蕾舞者的氛圍,像是我們非正式的祕書。
我的嬸嬸艾娃和叔叔席德坐在我的旁邊。席德叔叔看來像是我爸的年輕翻版,但少了那種衣冠楚楚的魅力。相反的,席德叔叔很樸實,他總是穿著一件背心,在家裡幫手時,他會照料屋子西側溫室內的蘭花,花言巧語地要它們扭曲乾燥的枝芽開出情感洋溢的花朵。嬸嬸艾娃有一張苦瓜臉,身材嬌小,臉上充滿憂慮的皺紋給人她很不幸的假象。許多耗子都被她和藹可親、嬌小老婦女的人格特質所騙。
我哥哥山姆坐在桌子的最尾端,我爸的對面。山姆看起來很放鬆,好像在做白日夢,不過我知道他的心思如刀鋒般銳利,專注在我們的工作上,思考著我們的未來。有一天,我們所有的人,還有這棟房子,都會是他的責任,但現在,他穿得像個流浪漢,像是地下水流一樣抗拒著不肯浮上地表。
桌子的另一邊,坐在露比旁邊的是我的四位堂兄姊。他們是艾娃嬸嬸和席德叔叔的孩子。我的堂哥小波只對小騙局感興趣。這是不對的,我們總是這樣告訴他。要說服一個耗子拿出一小筆錢和一大筆錢的困難度是一樣的,有時候小錢更不容易到手。那些小勾當唯一的好處是比較安全。
坐在他旁邊的是嘉蕾。她正在一本便條簿上塗鴉。我看得出來,她覺得很無聊。我們整晚都沒有談到她。開完會後她要出門,她的裙子比我會穿的短了些,乳溝也露得太多了點。接著是她的雙胞胎兄弟安迪。他穿著T恤,渾身大汗地直接從健身房過來。他很聰明,但在我們的工作中,最好用的常常是他的力氣。
最後一位是朱利,他穿著一身灰色精緻的羊毛西裝,領口敞開的白色襯衫在他的肌膚上異常顯眼,因為他的膚色是黑色的,不像我們是白皮膚。朱利一向是我最親近的同盟,這份工作若是成功,我照常會和他利益均分。當我說到梅卡夫問我的電話號碼時,朱利對我露齒一笑,還眨了一下眼睛。
我爸右邊的椅子上沒有坐人。那是我媽的位置。
※ ※ ※
「梅卡夫逃不了的。」朱利說。
「反正,他對我有沒有興趣都不重要。」我說:「這是很高明的騙局。就算我看起來像個巨人,他也會上當的。」
安迪方正的下巴一緊,不過沒有說話。城裡有好些有錢的年長女人曾投資他的景觀美化事業。山姆有次開玩笑說,如果安迪把他賣出去的每筆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加在一起,答案會是百分之一千。嘉蕾傻笑著,她是家族中的美女,有一頭金色長髮,還有電影明星般的微笑。每隔幾個月,她會很有策略地運用她的微笑,在黃金海岸販賣分時度假房間。
「不要表現得太酷了。」她說。
「我知道黛拉不想迎合梅卡夫,」山姆說:「她已經有男友了。」
「山姆,」我說:「你脖子上那個凸起是什麼?一顆特別大的青春痘嗎?」
「我想她一定有滿腹怨言或什麼的。」他說。
「我希望妳沒有倉皇失措,黛拉,」我爸說,「只因為妳在談戀愛。」
「提姆算不上戀愛。」我說。
「他是條大魚。」嘉蕾說。
「妳不應該隨提姆無理的嫉妒起舞。」我爸說:「賣弄風騷是工作的一部分。擅用自己的天賦沒有什麼好羞恥的,但它們只是誘餌。妳還是需要鉤子、線和鉛錘。」
「老爸,他們可以在這裡辦婚宴,不是嗎?」山姆說。
「山姆!」露比說。
「噢,唔,他還得先求婚才行,你們知道,要很正式的。」
「山姆,」我說:「閉嘴。」
「羅倫,」露比說:「手邊的工作。」
「好啦,好啦。」我爸皺起眉頭,慢慢走向黑板,上面的第一個句子寫著:梅卡夫信託。他修改了我們在這件工作上投入的總工時,把我今天面談所花的時間加上去。黑板的另外半邊是一個圈在圓圈裡的數字,也就是預期的報酬。
「這不是很大一筆錢,不過我們也沒花多少力氣。」他把粉筆丟到空中再接住,一邊計算一邊說話,添加幾行數字,乘以我們每天和每小時的費用,加在開銷上。「朱利,你花了多少時間?」
朱利打開他小小的黑色筆記型電腦。「申請書花了兩天,黛拉的網頁用掉一天半,博士學位花掉半天,總計四天以內。」
「做得好,朱利。」我爸說:「這是一筆小而美的收益。做得好,黛拉。」
我爸負責分配角色。提出想法的人通常會是作手,也就是我在梅卡夫的工作上所扮演的角色。我要負責執行,將計策付諸實現。其他人的角色會視工作而異,但通常會有一個人負責把風,或許也會有一個冷卻者,在事情變得過熱時讓局面冷靜下來,協助作手逃脫。在這件工作上,朱利是後援。沒有他,我可辦不到。
「或許黛拉可以用她分到的錢買個訂婚戒給提姆。」山姆說。
「或許你可以用你分到的錢租一位女友。」我說。
「你們兩個會是天造地設的一雙。」我爸說:「我知道提姆的爸媽很喜歡妳,黛拉。」
「我以為我們有條規則,」露比說:「支票兌現後才能慶祝。」
動物學系大作戰 週一早上九點,當梅卡夫黑色的BMW從他的私人車道上開出來,發出震顫的聲音轉進圖拉克路時,我們都在看他。我們看著他行駛在一輛電車旁,然後在進入高速公路的紅綠燈前排隊等候。我們看著他在城裡穿梭前進。我挑選的大學是墨爾本最古老的一間,建於澳洲剛被白人偷走之際,高雅的學習座位公認為舊世界輝煌的極致,整個學園像座小城市,入口不只一處,通路也很多條。我們看著梅卡夫以令人毛骨悚然的輕鬆找到一個停車位。他停在帕西.葛人傑博物館和音樂學院之間的皇家巡行大道上──完全正確的入口。
為了這個工作,我們需要兩個把風的人,負責一邊盯著耗子,一邊掃視有無潛在的麻煩。小波是第一個,他在梅卡夫家外面等待,並跟著他上路。到了皇家巡行大道,小波在自己的車上對著手機吹口哨。
「我得說他的停車運真好。好久沒看過有人有這麼好的停車運了。」
「好。」我說。我在動物學大樓,拿著手機。「謝謝你的評論,我會抄筆記。」
在梅卡夫開車的最後二十分鐘,安迪必須從前門進入動物學大樓。他穿著大學校地與校園服務部的制服。那個部門的人真該把儲物櫃鎖好才對。安迪腳蹬一雙前頭覆蓋著鋼片的靴子,腰帶圈上掛著一套鑰匙。海軍藍與螢光黃的襯衫在他的胸膛附近有點緊,長褲的褲管是艾娃嬸嬸昨晚很晚的時候放長的,現在還是稍嫌短了些。安迪拿著一條長長細細的鋁帶,走路的時候搖晃著臀部,像是一個沒有多少事情卻可以做上一整天的人。他看來昏昏欲睡,但手腳很快。他要用他收集到的工具,打開大樓大廳兩個玻璃展示櫃的小鎖。學生和學術人員會走來走去,與他擦身而過,看都不會看他兩眼。
安迪不會緊張,也不怕被人發現。他懂得制服的神奇力量,這是他爸教過他的一課。席德叔叔年輕的時候,在衣服還沒有裝上安全標籤以前,曾經有一整年推著一排排昂貴的連身裙,在百貨公司的門口賺了不少錢。穿著制服的人不只從來不會被人質疑,也沒有人會看他們的臉。為了更加確定自己的隱匿性和自由行動的能力,也為了防止制服不夠適當,安迪知道要帶夾紙板和筆。
他打開的第一個櫃子,是動物學系對訪客、學生和職員展示刊物的櫃子,以動物學系的成員上新聞了,標榜學系的成功。這裡展示的是白紙黑字的科學論文,用膠水黏在藍色的硬紙板上。安迪要拿走其中兩份,放進看來一模一樣的論文,只是主要研究員變成了康艾拉博士。不會有人低下頭來看的,而你若非已經看過上百次,也不會發現它們和以前有何不同。
第二個櫃子是大樓的指南,一個寬大的嵌板,裡面有數十條扁平的鋁條,上面用黑色的字體刻著姓名和辦公室號碼。這裡有的空格很多,安迪會把從家裡帶來的鋁條放進其中一個空格,展示我的名字和辦公室號碼。他會一邊做,一邊用鋁條敲擊玻璃,故意發出很大的聲響,引人注目。走出去時,還會重踩著步伐。這也是學來的。旁觀者會對鬼鬼祟祟的人起疑。走出前門後,他會左轉,在大樓後面等待正確的時機,再去把東西恢復原狀。只要時機抓對了,當他左轉時,會看到梅卡夫走上斜坡。
梅卡夫走到門口時,一個女人剛好走出來,他會替她撐住打開的門。這個女人五十出頭,但要扮得年輕點也唬得了人。她穿著量身訂製的花呢套裝,黑色高跟鞋,帶著用一條鏈子串著並懸掛在脖子上的黑色眼鏡。她對梅卡夫微笑,眨眨眼。梅卡夫也會回她一個微笑。兩人就在這時產生了互動。梅卡夫在這裡是個陌生人,不是很確定要往哪裡走,或許會不時低頭檢查手中的大學地圖。女人是大學裡的人,知道方位,所以很自然地開口問道:
「我能幫上忙嗎?」
她可能是系主任的祕書或是行政人員,但其實不是。
「我在找康艾拉。」梅卡夫會說。
「噢。」露比會說。在這件工作上,她是我們的舵手,任務是表現得和我好像沒有關聯,實際上卻引導耗子走向我。
她會輕哼一聲,宛如她很清楚我這個人,但視我在她之下。她也可能對梅卡夫比個手勢,指示他從走廊要怎麼走。「康博士如果不是在實驗室借設備或是在田野裡,你會在她的辦公室找到她。二樓,靠近電梯。」
梅卡夫對這個建議會不疑有他。他不會在標示著詢問臺的窗口詢問我的辦公室,不過經過牆上的指南時,他會看到我的名字。
我的家人是一群專業人士的團隊,像精緻器械中的齒輪一樣通力合作。所有的事情都會在接下來幾分鐘動起來,這是為何詐騙是世上最令人興奮的工作。我幾乎要為梅卡夫感到難過了。
這次的入侵若是發生在幾年前,情況會棘手得多。當時大學還是個人潮熙來攘往的地方,充滿了研究人員和各式各樣的點子。但現在思想已經不再被人看重,這對我們來說倒是很幸運。大學原本是個狹小的地方,有太多的學術人員擠在擁擠的房間裡,現在卻變成各個廳堂的人員不足,許多辦公室不是空蕩蕩的,就是半空狀態,由非正式和短期聘用的講師占用,他們的臉或甚至是名字,都不見得會有人認得。
動物學系的257號房,就是這樣一間無人辦公室,位於二樓電梯的附近。靠近電梯是好事,比起走廊最遠端的房間更不可能被人目擊進出。我已經先在這棟大樓裡探路,檢查過出口,不過更重要的是去廁所看看。上週五在梅卡夫的豪宅裡,在柯教授帶我去見梅卡夫前,我也做了同樣的事。即使是十拿九穩,還是該去檢查廁所窗戶上有沒有鐵條或鎖,看自己能不能在需要的時候擠著身子從窗戶逃出去。工作有可能在瞬間凍結,做好萬全的準備比較聰明。
當我抵達257號辦公室時,那裡已經有一張書桌和一張椅子,油漆正剝除到一半。沒有人注意到一名送貨女子在早上八點時把多餘的箱子送進來。房間的牆面上裝飾著裱框好的報紙剪貼、一張哈佛的玩笑道別卡,還有從身分模糊的機構而來的幾份學術引文。此外,這裡有一只寫著「艾拉」的咖啡馬克杯,兩張年老夫婦的照片和一張三個金髮小孩的照片,扮演我虛構的父母、姪子和姪女,外加一疊疊的紙和期刊,一罐用錫箔紙包裝的比利時巧克力,以及一把雨傘。
送貨女子的工作服現在摺疊好放在桌子下面的箱子裡,我穿著合身訂製的長褲和黑色短袖上衣。我通常不會穿太露的衣服,只展現玲瓏的曲線。在上衣外面,我加穿了一件實驗袍,這對在辦公室辦公的一天,嚴格來說或許不是很正確,但卻符合一般人的期望。脖子上掛著的藍色繩子原本應該要連結到一張通行證,不過通行證放在外套上身的口袋裡,所以沒有人會看到那不過就是一張薄紙板。這算不上是個妥當的解決方式,但我們沒有時間取得真正的通行證。安迪昨晚調整過我的眼鏡。一支鏡腳歪了,造成我上回的麻煩。現在戴在臉上的情況好多了。
還剩下二十秒,我打開新辦公室的門,用雙面膠把三個姓名鋁條貼在前門上,其中一個刻著康艾拉博士,另外兩個列在我的假名之下,草草寫在撕下來的紙片上,分別是「貓王」和「雪人」博士。第一聲敲門聲響起,我立刻去應門。
梅卡夫用手比著門上的招牌。「妳和很有名的人共用一間研究室呢。」他說。
我皺起眉頭,對著走廊左顧右盼,確定走廊上沒有人,然後拿下假名紙條,揉成一團。「隔壁同事做的好事。他們是有袋類的研究員,一直拿我的計畫來說笑,顯然不認為我有什麼勝算。」
梅卡夫站在辦公桌前,我關了門後背靠在門上。「聽我說,梅卡夫,你介不介意我們到別的地方談?如果被隔壁的拉瑞、克里和莫伊發現,我會被他們取笑個沒完沒了。」
「敲他們的門,請他們進來。」他說:「我確定妳可以說服他們,真的有活生生的塔斯馬尼亞虎,而且就在維多利亞省這裡。跟他們說牛的事,還有西瓜。妳很有說服力的。」他走向門口,距離一公尺時才停下腳步。我待在原地不動。
「我試過了,他們聽不進去。」
「給他們看看妳的文件。」
「我什麼都試過了。我有威爾森岬管理委員會從一九○八年開始的紀錄,內容是他們討論在塔斯馬尼亞捕捉塔斯馬尼亞虎,釋放到國家公園供人狩獵的好處,還有十九世紀水土適應協會進口其他動物,然後在不固定地點放生的證據。塔斯馬尼亞虎曾在威爾森岬國家公園裡出現的說法絕對可信,再加上目擊報告,可能性就更高了。我對他們解釋過我的整個論據。」
「聽起來很有說服力。他們怎麼說?」
「他們問我,能不能幫他們申請捕捉牙仙子的研究經費。」
「呀,科學家啊!」他說,搖了搖頭。「我可不想和那個仙子有什麼關係。完全沒有商機可言,現金都流到錯誤的方向,牙齒庫存不斷增加。」
「我會跟他們說的。」
「而且喔,還不只是她而已。到處都有經營不善的企業。看看復活節的兔子吧,把生意經營得像是慈善機構。市占率當然是百分之百啦,但營收在哪裡呢?最後全都得靠政府紓困。世界市場太大了,妳瞧,可經不起失敗。」
他用一種調情的方式說這些話,所以我知道他上勾了。我有一點失望。想到這整個點子的愚蠢,還有像他這樣的人必定吸引到很多女人,我原本期望挑戰會更大些。結果,他和其他人一樣可悲。我用一根手指纏繞一撮鬈髮,嫣然一笑,突然靦腆起來。「所以我該賣掉我的聖誕老人股票嘍?」
「唔,禮品企業的利潤反正形同廢物。我聽說聖誕老人多年來都在付馴鹿聖誕獎金。至於他們的晚餐,讓我們這樣說好了,我不介意在快要退休時當隻小精靈。」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