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奎斯筆下的百年孤寂,已經走到了盡頭!
拉丁美洲不再是問題製造者,而是提供解答的國度!
獨裁者、游擊隊、毒梟、貧民窟……,這些亂源關鍵字,一直是拉丁美洲給世人的印象。
誰能想到,當今歐美面臨次貸、債信危機的紛亂時刻,拉丁美洲這個被世界遺忘的孤寂之境,正悄悄崛起,提供一股正向的力量,解答全世界都面臨的問題!
化種族衝突為「混血主義」:西班牙後裔、原住民、黑人、印第安與歐洲族裔的混血後代、世界各地的移民,經過幾百年的融合之後,在拉丁美洲學會了共存、繁衍、交換傳統……。多種族原本是衝突的亂源,如今反形成「混血主義」,成為血統、文化藝術和經濟上都具備多元基因的創造性樂土。
唯一制定文化憲章的大陸: 拉丁美洲土地上雖林立了數十個國家,卻能彼此結盟,形成單一的「未來之國」,並主動制定了全球唯一的文化憲章,作為這塊大陸的合作指南,將混血主義的力量發揮到最大。
修正「挖掘主義」,回歸印第安式環保:以往在殖民經濟體制下,不斷輸出自然礦藏、咖啡、香蕉等農作物的「挖掘主義」生產模式,如今改採對環境友善、不危害農民健康的種植法。安地斯山與亞馬遜河回歸印第安「精簡是美」的世界觀,訴求以尊重的態度來運用地球資源。
女性與原住民執政,左派民主當道:原住民不再以長矛和吹箭來戰鬥,而是以手提電腦和選舉海報為工具,二○○五年更在玻利維亞贏得總統選舉,將印第安傳統精神寫入憲法中。相較於歐美大國的保守,拉丁美洲已出現四位女性總統,包括世界第六大經濟體巴西。此外,許多在一九八○獨裁年代的政治受害者,不約而同在千禧年之後,經過公平的選舉成為國家領導人。
科技取得領先地位:巴西在農業方面的成功實驗確保未來的糧食供給;拉丁美洲的醫學家對瘧疾的研究居於領先地位;阿根廷出口原子科技;二○一○年,智利在一次礦坑意外後,以傑出的行動能力拯救了三十三位礦工,而收看該次行動的電視觀眾甚至比觀看登陸月球者更多。
哲學療癒力,提供快樂的天賦:以歐洲思想歷史作為遺產,混合新世界原住民的遠見,使得這塊土地不斷孕育出卓越的思想家、音樂家、藝術家,乃至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如聶魯達、馬奎斯和尤薩,人們得以把文化活動當作救贖之道,將過往的悲慘歷史化為自我修正和療癒的動能。
以上的轉變,來自於拉丁美洲內部的力量。拉丁美洲為何擅長將潛在的弱點轉變成優點?這塊大陸上的思想家、文學家已做了適切的分析。從帕斯(Octavio Paz)的評論集《寂寞迷宮》、馬奎斯的小說《百年孤寂》,到博爾比(Jorge Volpi)所說的「世界已經遺忘了拉丁美洲」。「孤寂」這個概念貫穿了拉丁美洲思想家們的文字。但也正因為這樣的孤寂,造就了拉丁美洲獨創性的內在:反思而非反擊,反省而非擴張,最後引領拉丁美洲走上正確的道路。
作者簡介:
賽巴斯提安.修普(Sebastian Schoepp),德國人,自二○○五年起擔任《南德早報》的國際政治新聞編輯,負責西班牙與拉丁美洲的相關報導,並在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擔任新聞學講師。過去他曾任職於尼加拉瓜報紙《新聞社》,及其他西班牙語出版社。
譯者簡介:
麥德文,台北市人,德國語言文學碩士,譯有《閱讀平面設計》一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陳小雀(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拉丁美洲研究博士、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嚴震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余佳璋(公共電視「全球現場」節目製作人、主持人)
◎陳小雀(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拉丁美洲研究博士、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本書作者賽巴斯提安.修普以歷史為背景,實地走訪拉美國家,透過訪談與觀察,以細膩筆觸寫出拉美的「堅韌」,也道出拉美的「堅持」,在荒謬與嚴肅之間,呈現真實的拉丁美洲。走出生命迷宮,走出獨裁與戰亂的陰影,即便仍有毒品問題困擾,拉美國家的民主素養日益成熟,並以快速的經濟成長率再度躍上國際舞台,她給世人寶貴的一課,不可不了解!
◎嚴震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二次大戰後和拉丁美洲相關的議題如卡斯楚的古巴革命和古巴飛彈危機,或是美國介入多明尼加、智利、尼加拉瓜、格瑞那達等,都具有美國的外交或是安全意涵,並且多數是從美國的角度或是國家利益為其觀點。基於此,任何有關拉丁美洲的著作能夠在台灣有中譯本發行,我都認為有擴大我們視野的功能,特別是不出自於美國的觀點更是值得我們重視。《孤寂的盡頭》是《南德日報》負責西班牙及拉丁美洲的國際新聞編輯賽巴斯提安.修普在長期觀察後所完成的專著。它並非拉丁美洲或是美國的新聞記者所寫,因此可能更為客觀。
◎余佳璋(公共電視「全球現場」製作人、主持人)
當北半球忙於從紛擾中找出重建秩序法則,解決問題與沉澱雜念,南半球的拉丁美洲卻悄悄地從孤寂中摸索出自己的道路,那怕是略帶實驗性的冒險,也無損其浪漫情懷,對土地的熱愛,以及好惡分明的是非準則。我們或許將看到拉美世界更大幅度的改變,但趁此扭轉之前,若藉由修普已經搜尋過的階梯,似乎亦不難隨之登入這曾經豐富的古文明區域,未來所可能高亢發聲邁步的方向,並且從中提醒著我們,哪些珍貴的資產與價值,正是當前世界所欠缺的元素。
名人推薦:陳小雀(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拉丁美洲研究博士、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嚴震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余佳璋(公共電視「全球現場」節目製作人、主持人)
◎陳小雀(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拉丁美洲研究博士、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本書作者賽巴斯提安.修普以歷史為背景,實地走訪拉美國家,透過訪談與觀察,以細膩筆觸寫出拉美的「堅韌」,也道出拉美的「堅持」,在荒謬與嚴肅之間,呈現真實的拉丁美洲。走出生命迷宮,走出獨裁與戰亂的陰影,即便仍有毒品問題困擾,拉美國家的民主...
章節試閱
【引言】從拉丁美洲傳來的好消息
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歐斯瓦多.羅沙樂斯(Osvaldo Rosales):「接下來的十年將是屬於拉丁美洲的。」
一八三○年,當解放者西蒙.波利瓦(Simon Bolivar)瀕臨死亡,搭船順著馬格達連納河(Río Magdalena)而下時,他已經身心俱疲。他曾夢想一個統一而進步的、由原來各個殖民地建立起來的偉大帝國。如今這個夢想已經破碎。他被敵人追逐,被高燒打擊,被憂鬱症糾纏,於是發出他著名的喟嘆之聲:「他的革命只是在海裡犁田。」
在經年的戰役下,波利瓦在多場殺戮之中攻擊西班牙的軍隊,逼退並擊潰他們,從加勒比海岸的卡拉卡斯(Caracas)到安地斯山裡的拉巴斯(La Paz),他將一大片區域從異國統治之下解放出來。然而他推進的每一尺,他為統一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在他的背後被自私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密謀者所抵消:大地主、寡頭統治者、大農場主人、軍事領導人、教會諸侯和軍官一起分贓,他們共同策劃陰謀詭計,也彼此坑陷。農場工人、牧人、農夫、栽種者、工匠、礦工、印第安人和黑人仍然被剝奪權利,依舊一貧如洗。這塊次大陸在政治上碎成片片。一八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離死期不遠的波利瓦對殘破的終生志業下了一個苦澀的結語:「主耶穌基督、堂吉訶德和我,我們是歷史上最愚蠢的三個人。」
的確,因為所說的語言是羅馬語,也就是「拉丁語」,從十九世紀後半得以自稱為「拉丁美洲」的這塊次大陸,依然是一片混亂:失序、政變、危機、災難、國家面臨破產沒有支付能力。在二十世紀末,從格藍德河(Rio Grande)到火地島(Feuerland)之間──先不論足球勝利──的區域所製造的幾乎都是壞消息。叛變和大屠殺,陰騭的獨裁者,貧民區和毒販頭子的畫面,都深印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民眾對拉丁美洲的觀感上。
然而就在獨立整整兩百年後,這個畫面開始改變。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在短短幾年當中建立起民主體制,不再像它們的前代那樣容易被動搖,大部分選舉都得以公平而自由地進行。而且還不僅如此:有些政府領導者的得票率是歐洲政治家夢寐以求的。在經濟方面,也就是拉丁美洲幾百年來的主要問題,這時不僅蓬勃發展,甚至展現出比歐洲和北美更強韌的危機耐受力。貧窮雖然仍是最迫切的議題,卻藉著社會救助計畫而顯著地改善,中產階級擴大了。
此外還有其他成就。仇外辯論──在西方舊世界像是無法徹底撲滅的瘟疫一般──對拉丁美洲而言是陌生的。在幾百年滿是衝突的融合過程之後,不同的民族──克里奧人(在拉丁美洲出生的西班牙後裔)、原住民和黑人學會了共同生活。有些人甚至從這種成功的融合,也就是混血主義(Mestizentum),歸納出一種示範作用,例如哥倫比亞作家和評論家威廉.歐斯皮納(William Ospina)在他的著作《美洲混血》(America Mestiza)當中所表示的:「混血曾是我們的一大難題,卻也是目前文化舞台的一大契機,因為混合的趨勢是現代性的主要特徵之一。」
就連大男人主義似乎也在消褪當中。二○一○年時,拉丁美洲有四位女性領導著大國或重要國家。這和美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或是義大利相反,這些國家在同一個時間點還不曾出現過女性領導人。在阿根廷由費南德茲(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執政,面積狹小卻富影響力的哥斯大黎加的國家領導人名為羅拉.琴奇亞(Laura Chinchilla)。在智利,米雪兒.巴切萊(Michelle Bachelet)於二○一○年三月卸任,她所曾贏得的選票是創紀錄的。在大國巴西,迪爾瑪.蘿瑟芙(Dilma Rousseff)於同年十月贏得總統大選。
古老拉丁美洲的自卑情結似乎隨著進步而煙消雲散。巨幅成長的巴西,甚至覺得自己強大到足以要求重新分配全世界的權力關係,其大聲一呼也受到富裕世界的嚴正關注,而這個富裕世界早已對超級強權的獨大,以及超級強權對其他不同宗教及世界觀國家採取的對立態度感到厭煩。
在拉丁美洲內部,幾世紀以來大量減少的原住民後代,從前受到輕視與壓迫,現在開始爭取自己的權利──不再以長矛和吹箭來戰鬥,而是以手提電腦和選舉海報為工具。原住民爭取權利,並且於二○○五年在玻利維亞取得政權。安地斯山和亞馬遜河的世界觀在厭倦文明的歐洲人之間獲得支持,因為這樣的世界觀宣示「精簡是美」,且鑑於氣候變遷而訴求人類應帶著尊重的態度來運用地球資源。
墨西哥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歐塔維歐.帕斯(Octavio Paz)於一九五○年指出,拉丁美洲優點也許在於「重振歐洲思想」。在他的文集《孤寂迷宮》(Das Labyrinth der Einsamkeit)當中,他以墨西哥為例,提問:「我們能發展出一個並非奠基於統御他人的社會嗎?」民族互諒、民主化以及經濟發展的成就都顯示:拉丁美洲辦得到。
那麼,拉丁美洲可能如墨西哥哲學家荷西.法斯孔謝洛斯(Jose Vasconcelos)於一九二○所表示的,甚至提供世界一股動力,造就一段和平時期嗎?這似乎是烏托邦的想法,然而對拉丁美洲而言似乎找到了一條道路。當世界其他區域因為恐怖攻擊而顫抖時,拉丁美洲機場既沒有全身掃描機也沒有液體禁令。就在從前的殖民地大陸上,人們可以毫無窒礙地在大部分國家之間來回移動。
幾個國家的內部看起來當然有些不同──拉丁美洲仍然是暴力以及毒品交易猖狂之地,這是貧窮導致的直接結果。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的財富分配比拉丁美洲更不平均──這是殖民主義的後果之一,一種即使是十九世紀的解放者如西蒙.波利瓦都無法改變的結構。後繼者不想改變這種結構,因為後殖民小菁英,如財閥與軍閥從貿易流通獲利,這種貿易流正是殖民主義造就的,而拉丁美洲出產的金、銀、鉛、銅、硝酸鉀、鈾和原油促進了歐洲和北美的工業化。必須從土地刨出財富的人被送上了沉淪之路,一條無法輕易回頭的路。
然而,革命份子藉由過程血腥卻大半無疾而終的策反嘗試,希望以武裝抗爭來改變上述不公平關係,最後落到殘酷獨裁者的酷刑煉獄裡,這樣的時代似乎已成為過去。拉丁美洲的現代革命是以民主方式來進行的,使許多人下獄的暴力統治者幾乎都被各國獨力推翻,大部分沒有藉助外界的力量,沒有國際法庭、聯合國維和部隊,以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參與。如果民主化過程受到挫折,例如宏都拉斯於二○○九年發生政變時,拉丁美洲國家保持團結的方式足堪爭論不休的歐盟借鏡。
千禧年以來的政治進步推手通常是一九七○及八○年代受到迫害、從酷刑監獄存活下來的人:智利的米雪兒.巴切萊、巴西的迪爾瑪.蘿瑟芙與路魯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阿根廷的基希納(Nestor Kirchner)與費南德茲夫婦,以及烏拉圭的荷西.穆吉卡(Jose Mujica),他們都是曾經受到迫害的當事人,或是其親近人士。有鑑於自身的血腥過往,他們進行政治復興,在總統任內,乃以互諒與法治為治理國家的根本。這一切正有如世界正義的體現。
這些政治家的崛起顯示,導正歷史的另一種政治顯然是可行的。他們的政治傾向是左傾的,這是之前幾十年右傾的直接後果。然而他們及時告別階級鬥爭的終極訴求,而走上艱辛的改革道路。身為民選的總統,將拉丁美洲各國自獨立後走上歧路的畸形發展,以市場經濟為導向,將國家帶往另一個方向。
這樣的任務不會在一屆或兩屆任期內達成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已經開啟了充滿希望的先機。即使權力轉移重回右端,比如二○一○年的智利或是巴拿馬大選,也都和平而有序地進行,新任總統也不將前任的成就一筆抹殺。
這是如何辦到的?也許拉丁美洲的悲慘歷史所擁有的自我修正以及療癒動能,比接連不斷的壞消息所暗示的來得多?拉丁美洲除了陰騭的獨裁者以及粗暴的革命份子以外,不就正是從這塊土地所不斷孕育出的具有真知灼見的思想家,以歐洲思想歷史遺產混合新世界原住民遠見為基礎,適切地分析過往悲慘,並且描繪出美好未來?拉丁美洲的作家、哲學家及評論家一直都是世界翹楚,許多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拉丁美洲作家正足以說明這一點。
帕斯寫道:「哲學觀察成為有益而迫切的任務,(……)以找出確切解決之道,找到能賦予我們存在的意義為目標。」科技世界傾向將文化成就貶低為休閒活動。在拉丁美洲,文學、藝術和音樂的發展比科技化世界更卓越,文化活動一直都是救贖之道,是人們在困頓之中的心理支柱和道德鼓舞。因此,這麼多拉丁美洲作家成為政治家也就不足為奇,從十九世紀阿根廷的多明哥.法斯提諾.薩勉多(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到二十世紀祕魯的尤薩(Mario Vargas Llosa)都是。
拉丁美洲人一直都能將潛在弱點轉變成優點,他們習慣悲哀,而且比其他民族更快從悲哀中復原,可能具備更多讓自己快樂的天賦。二○○八年,BBC拉丁美洲新聞引述一項蓋洛普民調中心和美洲發展銀行對這塊次大陸的各國民眾滿意度研究,該研究指出,民眾對自己生活滿意程度最大的,並非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如烏拉圭或阿根廷這兩個生活形態比較接近北美的工業國家,而是出現在瓜地馬拉或是哥倫比亞,也就是戰爭和危機導致嚴重問題的區域。因此研究總結,國家的經濟成長和人民的幸福感受並非總是相等的。
研究人員並進一步確認,尤其是在比較窮的國家中,家庭、人際關係和宗教對人們更形重要,這些價值判斷的標準明顯有別於北美以追求進步和完美為主的新教—清教徒社會。根據這份研究,雖然北美地區的民眾所得較高、生活也比較安定,但他們對自己的生活基本上比較不滿意。威廉.歐斯皮納表示:「和生產力的純粹福音相反,它並未給生活或是想像力留下空間;也和權力的可怕信息相對(……),拉丁美洲各個民族展現了兩項根本的最高指導原則:其一是生存,正如大自然訂定並且蘊含的深刻法則,要保護我們賴以存續的自然宇宙;第二就是追求幸福、美與和諧。」
近年來,拉丁美洲甚至在科學和科技方面迎頭趕上。巴西在農業方面的成功實驗確保未來的糧食供給無虞;拉丁美洲的醫學家對瘧疾的研究居於領先地位;阿根廷出口原子科技;二○一○年,智利在一次礦坑意外後,以有效的行動拯救了三十三位礦工,收看該次行動的電視觀眾甚至比觀看登陸月球者更多。
此外,不管各個民族彼此間有多少差異,文化和情感的大致相同也讓拉丁美洲可以被視為一個整體。拉丁美洲人早已這樣看待自己,歐斯皮納甚至有些獨斷地稱拉丁美洲為El pais del futuro,未來之國:「這裡存在著一種大陸文化,我們在文化上是一個單一國家,一個巨大的國家,有能力彼此同盟合作,不必加以宣揚,只要藉助心靈深處的啟發。」
拉丁美洲必須由自身來成長,這將有益於這塊次大陸。在獨立之後,帕斯形容人們起初自覺像是「世界歷史的觀望者,沒有受邀而由西方人後門進入的客人」。拉丁美洲精神狀態因此長期以來被比喻成「靜水的孤寂」,帕斯表示:「我們在歷史裡遲到(……),我們的人民起初沉睡了一整個世紀,就在他們沉睡之時被掠奪一空。」因此對自身能力所產生的不信賴感,對進步所抱持的頑抗態度,這一切都反應在「孤寂」這個概念裡,這個貫穿拉丁美洲思想家的文字,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arquez)直到荷爾賀.博爾比(Jorge Volpi)。然而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的孤寂,這種造就獨創性的內在強制,平和的非理性傾向,反思而非攻擊,反省而非擴張的特質,最後使得拉丁美洲走上正確的道路。事實上拉丁美洲之道越來越受到重視,正是在工業化世界的進步模式本身遭遇瓶頸之時。人類學及文化學家康斯坦丁.巴洛文(Constantin von Barloewen)就表示:「令人驚訝的,拉丁美洲成為世界文明的政治工作室。」
二○○一年,這個政治工作室的運作在經過一段特別孤獨的時間之後開始步上正軌。拉丁美洲在將近二十年間,由獨裁者以及他們只稍經民主程序合法化的後繼者唯唯諾諾所貫徹的外來市場自由經濟實驗之後,在經濟和社會方面一敗塗地,是世界經濟體系的賤民。成千上萬人在外移當中尋求解救,導致暴動和街頭巷戰,政治家被驅逐,投資者撤回資金。美國,原本一直是主導南美的霸權國家,在二○○一年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將關注力轉向世界的另一個區域。留著落腮鬍的游擊隊再也不是美國生活方式的威脅,而是頭纏布巾的穆斯林和塔利班人士。北美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受宗教啟發而讓其他人享有同樣生活模式的意志──即使藉助暴力──開始在中東及近東肆虐。二○○八年,墨西哥作家博爾比在他的作品《波利瓦無法成眠》(El Insomnio de Bolivar)中肯定地表示:「世界已經遺忘了拉丁美洲。」
然而就是這樣的遺忘對拉丁美洲有益,在新產生的漠不關心的背風面,拉丁美洲得以用自己的力量開始發展,抓住機會從過往的失敗之中找出癥結,嘗試改變,這些改變多來自它的天性更甚於之前兩百年被強加的模式。正當世界的其他區域選擇偏右的時候,拉丁美洲開始選擇左傾。在二○○一至二○一○年間掌權的政府雖然保持各自的目標,然而這些政府卻有一點是一致的:再也不讓自己被外界操縱。他們開始一點一滴建造以重新分配和團結互助為基礎的共同體模式,拒絕外人的監管。美國總統歐巴馬於二○一一年三月拜訪美國往昔的「後門」時表示:「世界應將拉丁美洲視為充滿活力而成長的區域,拉丁美洲早已如是。」在智利和巴西等國之中的民主化被歐巴馬稱為近東的典範,那裡的人民正起而反抗他們的獨裁者。拉丁美洲所彰顯的價值對所有「正要踏上自己的民主旅程」的人是種示範。
所以拉丁美洲之道是存在的,然而這條道路千瘡百孔,毫無防備,有時還長滿了盛開的荊棘。其實這條道路比較像是繞遠路,然而現在目標似乎比任何時候都更唾手可及:如同英國《經濟學人》雜誌(Economist)所認為的,拉丁美洲有機會變成一個更富裕而公平的大陸。拉丁美洲將會繼續製造好消息以及壞消息,然而許多跡象顯示,好消息暫時會比壞消息來得多。
【引言】從拉丁美洲傳來的好消息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歐斯瓦多.羅沙樂斯(Osvaldo Rosales):「接下來的十年將是屬於拉丁美洲的。」一八三○年,當解放者西蒙.波利瓦(Simon Bolivar)瀕臨死亡,搭船順著馬格達連納河(Río Magdalena)而下時,他已經身心俱疲。他曾夢想一個統一而進步的、由原來各個殖民地建立起來的偉大帝國。如今這個夢想已經破碎。他被敵人追逐,被高燒打擊,被憂鬱症糾纏,於是發出他著名的喟嘆之聲:「他的革命只是在海裡犁田。」在經年的戰役下,波利瓦在多場殺戮之中攻擊西班牙的軍隊,逼退並擊潰他...
推薦序
◎陳小雀(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拉丁美洲研究博士、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本書作者賽巴斯提安.修普以歷史為背景,實地走訪拉美國家,透過訪談與觀察,以細膩筆觸寫出拉美的「堅韌」,也道出拉美的「堅持」,在荒謬與嚴肅之間,呈現真實的拉丁美洲。走出生命迷宮,走出獨裁與戰亂的陰影,即便仍有毒品問題困擾,拉美國家的民主素養日益成熟,並以快速的經濟成長率再度躍上國際舞台,她給世人寶貴的一課,不可不了解!
◎嚴震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二次大戰後和拉丁美洲相關的議題如卡斯楚的古巴革命和古巴飛彈危機,或是美國介入多明尼加、智利、尼加拉瓜、格瑞那達等,都具有美國的外交或是安全意涵,並且多數是從美國的角度或是國家利益為其觀點。基於此,任何有關拉丁美洲的著作能夠在台灣有中譯本發行,我都認為有擴大我們視野的功能,特別是不出自於美國的觀點更是值得我們重視。《孤寂的盡頭》是《南德日報》負責西班牙及拉丁美洲的國際新聞編輯賽巴斯提安.修普在長期觀察後所完成的專著。它並非拉丁美洲或是美國的新聞記者所寫,因此可能更為客觀。
◎余佳璋(公共電視「全球現場」製作人、主持人)
當北半球忙於從紛擾中找出重建秩序法則,解決問題與沉澱雜念,南半球的拉丁美洲卻悄悄地從孤寂中摸索出自己的道路,那怕是略帶實驗性的冒險,也無損其浪漫情懷,對土地的熱愛,以及好惡分明的是非準則。我們或許將看到拉美世界更大幅度的改變,但趁此扭轉之前,若藉由修普已經搜尋過的階梯,似乎亦不難隨之登入這曾經豐富的古文明區域,未來所可能高亢發聲邁步的方向,並且從中提醒著我們,哪些珍貴的資產與價值,正是當前世界所欠缺的元素。
◎陳小雀(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拉丁美洲研究博士、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本書作者賽巴斯提安.修普以歷史為背景,實地走訪拉美國家,透過訪談與觀察,以細膩筆觸寫出拉美的「堅韌」,也道出拉美的「堅持」,在荒謬與嚴肅之間,呈現真實的拉丁美洲。走出生命迷宮,走出獨裁與戰亂的陰影,即便仍有毒品問題困擾,拉美國家的民主素養日益成熟,並以快速的經濟成長率再度躍上國際舞台,她給世人寶貴的一課,不可不了解!
◎嚴震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二次大戰後和拉丁美洲相關的議題如卡斯楚的古巴革命...
作者序
【推薦】走出生命迷宮:拉丁美洲寶貴的一課
◎陳小雀(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拉丁美洲研究博士、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常常聽到國人以「浪漫」形容拉丁美洲這個地區的人事物,但事實上,我所認識的拉丁美洲很難用「浪漫」簡單描寫之。拉丁美洲不是地理名詞,而是文化用語,象徵絢麗、繽紛、精采,同時又代表政變、動盪、貧窮,就如魔幻寫實作家筆下的情節一般,既神奇又悲慘。的確,除了非洲那個被大國丟棄的戰略棋盤之外,還有哪一個地方如拉丁美洲一般充滿矛盾荒謬?
地理上,北起美墨邊界格蘭德河(Rio Grande),南至巴塔哥尼亞高原(Patagonia),並可擴及加勒比海地區。在這廣袤區域內地形多貌:沙漠礫土、崇山峻嶺、荒蕪莽原、沼澤雨林、平原曠野、冰川極地……,各種奇異景觀,莫不具備。時間上,跨越數千年歷史,追溯至前哥倫布文明,歷經西、葡等國三百年的拓殖,再鋪寫兩百年的獨立建國史。如此繁複多樣的時空元素交織出一張迷人的人文地圖,然而,其歷史真相卻是崎嶇坎坷。
自從哥倫布踏上美洲土地起,這塊列強眼中的「次大陸」,每日不斷上演著荒謬劇,一齣接著一齣。首先,監護制(encomienda)和米塔(mita)改變了原住民的生活型態,旖旎風光也跟著走樣,彷彿大型的生產中心。接著,克里奧人編織了獨立美夢,意圖仿傚美國建立聯邦政體,孰料,鬩牆之禍導致「中美洲聯邦」分裂,波利瓦的「大哥倫比亞共和國」同樣難逃解體命運,短短數年間,原來的西班牙殖民地分裂出十八個共和國,巴西也跟著脫離葡萄牙獨立。最後,拉丁美洲竟然成為獨裁者的天堂,同時培養出無以數計的民族英雄。獨裁者與民族英雄看似天壤之別,有時僅一步之遙,拉美知識份子就以「完美笨蛋」(perfecto idiota)嘲諷那曾經揭竿起義的英雄,待大權在握之後,自己也變成獨裁者。
獨立後,各國政局不穩,為了實施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而吵吵鬧鬧,再加上保守派與自由派之間的政爭,不僅內戰不斷,對外又因疆界紛爭和經濟利益,甚至莫名細故而與鄰國大動干戈。三國聯盟(Guerra de la Triple Alianza)、硝石戰爭(Guerra del Guano y Salitre)、夏谷戰爭(Guerra del Chaco)撕裂了拉美國家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愫,更導致戰敗國瀕臨崩潰邊緣。二十世紀初,美國資本家趁虛而入,與拉美獨裁者勾結;於是,巴拿馬地峽被鑿穿成運河,蓊鬱林地改種咖啡、香蕉等經濟作物,蘊藏於地底的銅、錫、鎢、鉛、鋅、銻、鈾、石油等礦產紛紛被挖掘,拉丁美洲宛如進入經濟繁榮期。事實上,龐大經濟利益大多由美國企業所攫取,拉美底層社會依然一貧如洗。更為甚者,美軍隨著水果公司、鐵路公司、採礦公司順理成章進駐,破壞了拉美國家主權,讓原本就已經變形的社會更加扭曲。
獨裁統治、美國干預、經濟剝削、游擊戰爭、農民革命、民粹運動幾乎占據了兩百年的歷史扉頁。打著民主共和國的旗幟,拉丁美洲卻陷入自己所營造的迷宮之中,在錯綜複雜的迴廊通道裡跌跌撞撞,找不到出口,用生命寫下昂貴的一課。這座迷宮匯聚了衝突與磨合、落後與進步、蒼涼與繁華、孤寂與喧鬧、死亡與重生,讓拉丁美洲在挫敗中締造神話,在神話中幻想民主。文學家將這座迷宮化為文字力量,一部部精采的文學作品宛如暗夜裡那久久不散的燦爛煙火,讓國際文壇見識到拉美「爆炸文學」的魔力。
一九○○年,對羅多(Jose Enrique Rodo)而言,迷宮係被束縛的精靈「愛麗兒」,是面對美國的霸權時的自我解放意識。一九五○年,對帕斯而言,迷宮乃「孤寂」的意象,是憂患意識的哲學觀察。一九六七年,對馬奎斯而言,迷宮則為「馬康多」,勾勒出拉美民主烏托邦的輪廓,流洩出充滿矛盾荒誕的黑色幽默。
我不由地將「馬康多」那一場下了四年十一個月零兩天的大雨比喻為大革命。在小說裡,那場彷彿永不止休的大雨象徵洪水神話,將人世間的貪、嗔、癡、愛、恨一掃而空。然而,隨著洪水過後大地得以休養生息,等待新生的來臨,馬奎斯儼然先知,以魔幻寫實的筆觸悄悄埋下希望種子。翻閱歷史,墨西哥大革命(1910~1917)推翻的不只是獨裁體制,也突破了階級藩籬,喚醒蟄伏的民族魂魄,從原住民傳統中找到文化認同。以墨西哥大革命為榜樣,卡斯楚所領導的古巴大革命(1956~1959)在短短兩年內便取得政權,再加上後來的社會改革成效,鼓舞了拉美貧窮國家的左派份子,於是,二十世紀成為拉丁美洲的革命詩篇,是游擊隊的抗暴史詩。只是,戰雲瀰漫數十載,在薩爾瓦多、哥倫比亞等國演變成血腥內戰,宛若受到大雨掃滅的「馬康多」,國家社會殘破不堪。
若要描寫拉丁美洲人,「堅韌」應該是最適切的詞彙。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寫活了古巴老人的傲骨,主人翁聖迪亞哥(Santiago)多日來一直沒捕到魚,仍舊持續出海作業,終於在八十四天後捕到一條比船身還大的馬林魚,卻受到鯊魚攻擊,老人獨自與海博鬥,對抗鯊魚,堅決將馬林魚拖回上岸,最後上岸時,整條魚只剩魚骨,如此執著信念流露出拉美人民的奮鬥精神。另外,從馬奎斯的《沒有人寫信給上校》(El coronel no tiene quien le escriba),也可以窺見堅韌的生命力。書中的上校深信政府的撫卹金承諾,但是十五年過去了,他並沒有等到撫卹金,伴隨著他的,只有飢餓,還有受哮喘病折磨的妻子,以及死去兒子所留下的鬥雞;最後,他把希望寄託在鬥雞上,既然等了十五年的撫卹金,何不再等個四十四天,來證明那是一隻不會輸的公雞。
一絲希望、一點滿足,即可帶給拉丁美洲人無窮的希望,個人如是堅韌,同樣,國家也是如此。毋庸置疑,拉丁美洲不僅肯面對過去的傷痛,也有很強的自我修護機制。
遭禁運長達半世紀,古巴今至仍堅守「意識形態」。經歷蘇慕薩家族四十三年的獨裁統治,再走過了十七年的游擊戰,儘管桑定諾陣線的戰友一個個遠去,尼加拉瓜正努力對抗貧窮,試圖挽回逐漸模糊的昔日革命理念。以豐富的石油礦產為後盾,並以波利瓦主義為圭臬,委內瑞拉全力建設自己的社會福利國家。曾經在獨裁與民主之間徘徊,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讓驕傲的中產階級不得不撿拾回收物維生,阿根廷在左派與右派之間找到平衡的民主秩序。巴西曾經在政局動盪、貧富懸殊、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中載沉載浮,然而,巴西人不以為意,替自己許下美好未來:「巴西是明日之國,始終如此,永不改變。」果真,巴西在二十一世紀初搖身一變,成為南方大國。
本書作者賽巴斯提安.修普以歷史為背景,實地走訪拉美國家,透過訪談與觀察,以細膩筆觸寫出拉美的「堅韌」,也道出拉美的「堅持」,在荒謬與嚴肅之間,呈現真實的拉丁美洲。走出生命迷宮,走出獨裁與戰亂的陰影,即便仍有毒品問題困擾,拉美國家的民主素養日益成熟,並以快速的經濟成長率再度躍上國際舞台,她給世人寶貴的一課,不可不了解!
【推薦】走出生命迷宮:拉丁美洲寶貴的一課
◎陳小雀(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拉丁美洲研究博士、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常常聽到國人以「浪漫」形容拉丁美洲這個地區的人事物,但事實上,我所認識的拉丁美洲很難用「浪漫」簡單描寫之。拉丁美洲不是地理名詞,而是文化用語,象徵絢麗、繽紛、精采,同時又代表政變、動盪、貧窮,就如魔幻寫實作家筆下的情節一般,既神奇又悲慘。的確,除了非洲那個被大國丟棄的戰略棋盤之外,還有哪一個地方如拉丁美洲一般充滿矛盾荒謬?
地理上,北起美墨邊界格蘭德河(Rio Grande),南至巴塔...
目錄
【引言】從拉丁美洲傳來的好消息
第一章 迷失的十年
獨裁與民主之間的阿根廷
一九八九年,梅稔當選阿根廷總統後,他所實施的私有化使國家建設落入財團之手,摧毀阿根廷辛苦建立的工業化,並毫無節制的發行國債以挽救經濟。阿根廷的經濟終於在二○○二年崩盤,是史上最大規模的破產。
回歸陌生之鄉
一九九○年代,拉丁美洲的政治家們所積極實踐的「華盛頓共識」,催毀了原本就相當脆弱的公共服務,私有化導致大幅解雇。變窮的人民選擇經濟情勢正看漲的西班牙——他們的雙親與祖父母的故鄉——作為移民目標。
第二章 格瓦拉之魂
出發前往目的國
基希納在二○○三年當選阿根廷總統之後,在經濟方面,解決國債問題,將私有化的企業再度收歸國有。法治上,落實法治精神,軍政府的將領重新站上法庭。外交上,積極參與拉丁美洲事務,主導區域整合以對抗美國。
「超級巨星魯拉」
魯拉將巴西的國力帶到頂峰,成為經濟大國。他的施政原則是「取之於巴西,用之於巴西」,例如石油工業上的獲利用於增加國內基礎建設或是資助社會方案,使巴西貧窮率下降,人民得以晉身中產階級。
波利資產階級
委內瑞拉的查維茲借用他的革命先祖西蒙.波利瓦之名,發動「波利瓦革命」。在他的政權底下,貪污、裙帶關係當道,他的追隨者被諷刺地稱為「波利資產階級」。
伸手摘取天上星
玻利維亞的印第安人總統莫拉勒斯執政時,公務員必須學說任何一種印第安語言,印第安人的生命觀也寫進憲法裡;石油與天然氣收歸國有,所得提供國家支出;每個國民擁有退休金,每個家庭有錢送孩子去唸書。
革命再見
尼加拉瓜左派政黨桑帝諾陣線的奧帝嘉在一九八○年代,根據馬克斯主義統治國家,但該國的經濟從未自震災與戰爭中復原。二○○六年奧帝嘉再度執政,被媒體評論為停駐在過往之中的政治恐龍,只為掌權,沒有施政規劃。
第三章 兩百年的孤寂
波利瓦的夢想
在一八一○至一八二四年,西蒙.波利瓦將統治拉丁美洲三百年的西班牙人逐出南美的大部分區域,但他所構築的新世界權力夢想,隨著他每推進一里,就在背後崩解一寸,地方獨裁者、大農場主人、礦山大亨瓜分他的成果。
剩餘物資的詛咒
尼加拉瓜的香蕉工人、智利硝礦坑裡的玻利維亞籍礦工、祕魯海岸蔗糖區的非法收成工人……這些人從地底挖出礦藏,在田地上挖掘,維持著「挖掘主義」的經濟運作模式。過去的統治者未試著在拉丁美洲塑造生產社會。
白色粉末之路
種植古柯葉在玻利維亞具有古老的傳統。總統莫拉勒斯甚至在國際場合公開咀嚼,為爭取古柯葉合法化。自古柯葉萃取古柯鹼當作大買賣,從安地斯觀點來看,是工業世界追求極端刺激的典型表現。
強暴而誕生的孩子
墨西哥人長久以來自認是因強暴而誕生的孩子。哲學家法斯孔謝洛斯將印第安與歐洲混血轉而詮釋成優勢:混血民族因為將多種文化元素結合於一身,不斷學習共存、繁衍,交換傳統,所以更能因應挑戰。
不能跳舞的勝利者
和美國對話是困難的。清教徒只和上帝以及自己交談,從不曾和其他人。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勝利,是紀律勝過本能,然而紀律可以征服一切卻征服不了心。美國軍隊在一九六○年代占領多明尼克共和國,非常成功地結束了一場內戰。他們被當地人稱為「宴會守護者」:舉行慶典時只站在場邊觀看的人,他們獲勝,卻不會跳舞。
第四章 拉丁美洲之路
從馬孔多到馬克翁多
拉丁美洲的魔幻寫實主義風格製造了矛盾,批評者認為那是嘗試將醜陋的政治與社會狀況加以美化。到了馬奎斯的孫輩作家,強力鼓吹完全捨棄魔幻寫實主義,尋求能表現出拉丁美洲現實的文學形式。
清算過往
獨裁結束之後二十年,阿根廷、智利及烏拉圭的年輕人對前一個世代提出質疑、傾聽人權組織以及受難者團體的意見;作家與記者則將這個主題以文字置於公眾的評判之下。雖然人們對逐漸被揭露的罪行的憤怒不斷升高,這三個國家並未發生報復式的勝利者司法。
南方新勢力
巴西已經安然度過二○○九年的經濟危機,二○一○年的經濟成長率甚至可達百分之十,即將在二○一四年舉辦世界盃足球賽、二○一六年舉辦奧運。巴西有自信在未來幾年內,成為世界前五大經濟體。
【後記】從外界看拉丁美洲◎羅貝托.黑爾雪
【引言】從拉丁美洲傳來的好消息
第一章 迷失的十年
獨裁與民主之間的阿根廷
一九八九年,梅稔當選阿根廷總統後,他所實施的私有化使國家建設落入財團之手,摧毀阿根廷辛苦建立的工業化,並毫無節制的發行國債以挽救經濟。阿根廷的經濟終於在二○○二年崩盤,是史上最大規模的破產。
回歸陌生之鄉
一九九○年代,拉丁美洲的政治家們所積極實踐的「華盛頓共識」,催毀了原本就相當脆弱的公共服務,私有化導致大幅解雇。變窮的人民選擇經濟情勢正看漲的西班牙——他們的雙親與祖父母的故鄉——作為移民目標。
第二章 格瓦拉之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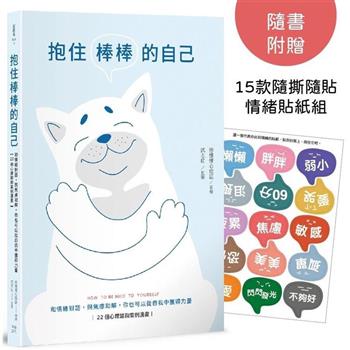







本書的副書名:「全世界能向拉丁美洲學到什麼?」,顧名思義本書是本有關拉丁美洲的論述,拉丁美洲對於台灣而言一向是相當陌生,大家如果曉得操拉丁語的族群是全球第三大語言區,以及操西語的拉丁後裔是美國第二大族群,不論是原物料蘊藏量、經濟成長率還是人口成長率,拉丁美洲很有可能會躍居全球重心。 這塊擁有全世界最年輕的國家,也具有全世界最古老的文名的大陸,從前給人的印象不外乎足球、毒品、雨林、軍事獨裁、政變頻繁、游擊隊、偷渡客、或壁崩盤與經濟蕭條......。 本書的宣傳重點是要論述今日的拉丁美洲的巨大蛻變,然而,令我感到些許\失望的是,本書的內容十分之九在拉丁各國的政權與政客更迭上頭,雖然不可諱言的,閱\讀本書後,的確可以更了解最近幾十年來拉丁美洲的政治變化,以及一些政權的興起衰敗,但是若只從政治面去切入這個號稱幾百年自外於世界的孤寂大陸,是無法窺得全貌。 作者是德國人,自二○○五年起擔任《南德早報》的國際政治新聞編輯,負責西班牙與拉丁美洲的相關報導,也正因為是記者出身背景,論述起來總是感到有其侷限性,我讀不到拉丁美洲的民族意識的論述,也讀不到拉丁美洲社會階級的問題,本書也沒有碰觸拉丁各國的經濟問題,整本書的論述重心放在拉丁各國的近代政治史上,尤其是用相當的篇幅去描繪各個國家的領袖,而且除了少數如委內瑞拉總統以外,作者的論述似乎「很官方」,雖然不能說是歌功\頌德,但多少似乎站在宣傳的立場上,這點是我比較無法認同的。 若對一個完全不認識拉丁美洲的讀者而言,本書確實可以帶給讀者某種程度的入門知識,由於作者具記者背景,所以本書的論述口吻與編輯接近新聞報導,大家都知道新聞報導的特點就是易懂,但其缺點確是狹隘淺碟。讀完本書的讀者一定會感覺到少了什麼東西,對!就是少了中心思想,少了意識型態,少了靈魂,這是記者書寫的通病,論點忽左忽右,忽環保忽經濟,一下子人文關懷一下子又推崇公權力的效率,一下子說親美是務實,一下子又讚揚哪個國家哪個政客能夠擺\脫美國。 但無論如何,這本書讀起來不算枯\燥,讀完之後還是可以建立一些對拉丁美洲的基本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