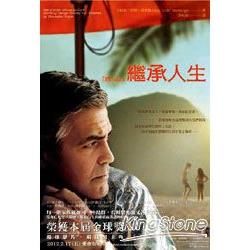我看著我太太,我需要妳,我如此想著。
我需要妳在這裡幫助女兒們和我。
我不知道要怎麼與人交談,
我不知道什麼樣的生活才是正確的……
每一個家族就如同一座島群,看似緊密卻又各自獨立。
從死亡與忠貞開始,進而衍生出細膩而詼諧的情感。
.《舊金山紀事報》《紐約時報書評》《書單雜誌》《出版人週刊》《柯克斯評論》《舊金山雜誌》《倫敦每日郵報》
《奧勒岡日報》《邁阿密先鋒報》《紐約客》《Elle》 — 盛讚推薦
.作 家王盛弘/小說家伊格言/作家李明璁/出版人李 航/影評人但唐謨/影評人膝關節 — 誠摯推薦
.AMAZON書店 ★★★★ 評價/同名改編電影IMDB網站 ★★★★★★★★推薦
.同名改編電影《繼承人生》預定2月17日上映,由亞歷山大派恩Alexander Payne導演(《尋找新方向》、《心
的方向》),喬治庫隆尼George Clooney主演,榮獲金球獎戲劇類最佳電影、最佳男主角,並獲全美各大影評人
協會肯定:美國國家電影評論協會/美國國家影評人協會/美國廣播影評人協會/洛杉磯影評人協會/華盛頓
影評人協會/休士頓影評人協會/聖路易影評人協會等
About The Descendants
「妳愛我,」我說,「我們有我們的相處之道,而且一切都會很好。妳會醒來的,對吧?」
故事從一場賽船意外開始,麥特那即有魅力又愛冒險的妻子喬安妮陷入重度昏迷並已決定放棄治療,導致他必須獨自負起維繫家庭運作之重責。平時忙於工作而與家人疏遠的他,被迫與兩個女兒—正值叛逆期的史嘉蒂以及對人生方向未明且正在戒毒中的雅莉,重新建立起荒疏已久的父女關係。在夏威夷悠然閑靜的時態裡,事情宛如一座被海潮悄悄拆卸的沙堡,時間的秩序一點一滴流逝,生活的線條與輪廓必須再填實與修補……
我看著我的女兒們,對我而言,就像一團迷霧,有那麼一瞬間我有種厭惡感油然而生,在這世上我一點也不想跟這兩個女孩一起過日子,還好她們沒有問我愛她們什麼,讓我頓時鬆了一口氣……
當父女決定聚集親友向妻子做最後道別時,卻發現得難堪地面對另一秘密存在之人—妻的情人……為了讓生者與死者都能得到應有的交代,他們決定上路,展開一段檢視生命意義的旅途。麥特繼承了祖先大片土地與攸關當地人未來的歷史責任,而兩個女兒也繼承著父親的憂傷與痛,兩代之間是相互承繼的血緣體,故事一旦開啟,角色命運便已被決定,所有情感的流動都在解釋彼此存在的理由。
【本書特色】
各界媒體推薦
「如同潘朵拉的盒子一般的悲喜劇…卡娃依‧哈特‧漢明絲的首部小說,精巧地琢磨喜劇氛圍,亦帶來全新的詼諧感受。」─《紐約時報書評》
「隨著優美而直率的筆調,漢明絲探索著悲傷的情感領域,最終讓我們看到比天堂,更具現實意義的價值。」
─《舊金山紀事報》
「這部小說中所累積的渾沌多少要歸功厄普代克學派中的美國創傷……漢明絲是個堅毅不濫情的作家,而她卻有辦法處理這個充滿風險的題材─極富張力的情節,寫來卻輕描淡寫,遊刃有餘。」─《紐約時報書評》
「令人無法抗拒……主題與劇情的鋪陳,在在表現出高超的成熟風格與令人迷醉的情節掌握,漢明絲的演譯手法辛辣中帶溫柔、迷人又詼諧地呈現出一個家庭面對悲劇時的反應。」─《書單雜誌》
「銳利的觀察中充滿了詼諧情節又同時交織著傷心的樣貌,用心良苦卻困惑的父親試圖要讓自己那不傳統的家庭團結起來。」─《出版人週刊》
「漢明絲演繹出絕佳的故事情節。」─《柯克斯評論》
「漢明絲輕巧又風趣的筆法特別發揮在描寫二十一世紀難讓人了解的青少年身上……我們都發現自己在為這一家人打氣與喝采。」─《舊金山雜誌》「漢明絲多變的筆鋒還有她對於抽象的細膩掌握讓這部小說,在心碎與歡喜之間徜徉。」─《倫敦每日郵報》「性愛、死亡、家庭與金錢:這麼多的議題要咀嚼,漢明絲明快的表現出麥特的挫折、不甘願以及責任感。」─《奧勒岡日報》「充滿了對真實的親情與觀察……自信筆法遊刃有餘。」─《邁阿密先鋒報》「放肆的幽默劇情……漢明絲用精湛筆鋒靈活呈現出故事主人翁所面臨的中年困惑。」─《紐約客》「這部小說最美的地方在於你也會關心麥特‧金……是一部成功振奮人心的小說」─《Elle》雜誌
作者簡介:
卡娃依‧哈特‧漢明絲Kaui Hart Hemmings
卡娃依‧哈特‧漢明絲(Kaui Hart Hemmings)在夏威夷出生長大,畢業於美國克羅拉多學院及莎拉勞倫斯學院,並曾獲華萊士‧斯特格納(Wallace Stegner)創意寫作獎學金,現定居夏威夷。《House of Thieves》是她第一部出版的的短篇故事集,《繼承人生》則是她第一部小說作品。
譯者簡介:
李昕彥
荷蘭鹿特丹大學藝術行銷碩士(英語組)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暨外文系雙學士
1997年起開始從事口筆譯及英語教學工作;曾任駐倫敦台北辦事處翻譯員、知名外商與竹科醫療公司行銷經理。現旅居歐洲,從事產業行銷顧問及文字翻譯工作。
章節試閱
1
窗外陽光普照,成群的八哥鳥啁啾個不停,棕櫚樹一棵棵隨風搖曳著,但又怎樣?我人好好的卻待在醫院裡。我的心臟盡責地跳著,腦裡卻不停地竄著各種訊息,既響亮又清楚。我的妻子坐靠在病床上,就好像搭飛機時的睡姿一樣。她的身體僵硬,頭歪歪地側向一旁,雙手擱在大腿上。
「不能讓她躺平嗎?」我問。
「等一下。」我的女兒史嘉蒂說完,便拿起拍立得相機對著她母親拍了張照片。我按下床邊的控制鈕讓妻子的上身緩緩躺下,我的女兒則在一旁搧著那張照片,直到她幾乎躺平後,我鬆開按鈕。
這是喬安妮陷入昏迷的第二十三天,接下的幾天內我得根據醫生所下的最後判決做出一些決定。老實說,我只要知道醫生對於喬安妮病情的看法就夠了,因為喬安妮有生存的意志,我沒有什麼插手的,她一向都是自己做決定的。
今天是星期一,強斯頓醫生說星期二會與我談談。這個約定搞得我很緊張,像是要去赴個浪漫約定一樣,我不知所措、不知所云、更不知道要穿什麼才好,我甚至排練著自己的回答與反應,但我只知道在理想狀況下該說些什麼,而對於不利的情勢卻絲毫沒有準備。
「你看!」史嘉蒂說,她的本名就叫史嘉蒂,因為喬安妮以為援用她父親「史卡特」這名字會很酷,我卻無法茍同。
我看著這張照片,感覺很像那種偷拍別人睡覺表情的惡作劇照片,這到底哪裡有趣了?「人在睡覺時真的不知道可以發生多少事,」我心中默默想著,「看看這些無法察覺的事情,妳就知道自己有多脆弱了。」但這張照片中,誰看了都知道她不是單純地在睡覺而已。喬安妮的手臂上吊著點滴,還有一種叫做「氣管內管」的東西插在她的口中,外面接著一台通氣機來幫助她呼吸。她還需要靠鼻胃管來進食,而醫生開給她的處方也夠維持斐濟島(Fiji)上一整村人口的醫療使用了。
史嘉蒂在一旁紀錄我們的生活以作為她社會課的研究報告。躺在皇后醫院病床上的喬安妮,持續昏迷進入第四周,昏迷程度用格拉斯哥指數(GCS, Glasgow Coma Scale)來說明為十分 ,以瑞裘認知功能層級 (Rancho Los Amigos levels of cognitive functioning)來看則是達到第三級。意外發生時,她正在比賽,她從離岸的快艇上摔出,快艇當時正以時速128公里前進著……我想她應該會沒事的。
「她目前對於外界刺激,呈現無定向的非特定型態反應,雖然偶爾會出現些特殊反應,卻沒有任何一致性。」她的神經科醫生這麼向我解釋著。這神經科醫生是個年輕女人,說話時左眼會輕微地抽動,而她極快的說話速度,總是讓我不知道要怎麼發問。「她的反射動作有限,對任何形式的外界刺激,都會以相同的反射動作回應。」她接下來的敘述,怎麼聽都不覺得是好消息,但我知道喬安妮一定還堅持著。我相信她會沒事的,而且總有一天一定會復原的。我對事情的判斷很少有偏差。
「她為什麼參加比賽?」神經科醫生問我,這問題對我來說有些莫名其妙,「想贏吧,我想。第一個達到終點的就贏了。」
「把那關了吧!」我對史嘉蒂說。她把照片貼在書上後,拿起遙控器將電視關了。
「不,我說的是這個。」我指著窗戶說著─外頭的陽光、綠樹以及那些在草皮上跳來跳去的鳥兒,喙裡啣著遊客與路旁那些瘋女人丟的麵包屑,「關上吧!真是糟透了。」
這些熱帶風情真的讓人很難專注在憂鬱的情緒上。在大城市裡,就算皺著眉頭走在大街上,也不會有任何人向前關心或是鼓勵你面帶笑容,但在這裡每個人的態度都以為能住在夏威夷是件非常幸運的事,就如同置身天堂一般……真去他媽的天堂。
「真夠噁心的!」史嘉蒂說,她將窗簾拉上,直到遮住窗外所有的景色。
我希望她沒有發現我正在打量她,而眼中所見也真讓我渾身不自在。她看起來是個很敏感又讓人感到生疏的人。她今年十歳,而十歳的人都在做些什麼呢?她用手指繞著窗戶玩著,又在那喃喃道「這樣搞不好會得禽流感」,然後拱起雙手放在嘴上發出小喇叭的噪音。她腦袋真的有問題,天曉得她腦袋裡在想些什麼?說到她的腦袋,她好歹也該去剪個頭髮或梳個頭,她頭頂上竟然起了一團一團的小毛球。「她都去哪剪頭髮?」我心裡想著,「她到底有沒有剪過頭髮?」此時她搔搔頭皮,然後盯著自己的指甲看。她穿在身上那件T恤印著「不是你要的女孩,但也不是不行。」感謝老天她長得不是特別漂亮,但我想以後也可能會改變。
我看著自己的手錶,這錶是喬安妮送我的。
「夜光錶針搭上珍珠母貝鏡面。」她送我時這麼說。
「花了多少錢?」我問。
「想不到你看到手錶後的第一個問題竟是這個?」
我當下就知道自己所說的話傷了她的心,因為她花了很多功夫來選這個禮物給我。她是個喜歡送禮的人,而且總會花心思去注意他人,然後藉由送禮來告訴他們,她是個有花時間去了解與聆聽他們的人,至少表面上看起來是這麼回事。我當初不應該問價錢的,因為她不過只是想表現出她是懂我的而已。
「幾點了?」史嘉蒂問我
「十點半。」
「還早。」
「我知道。」我回答,但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好。我們兩個現在會在這裡,不只是因為我們來這看顧喬安妮,期望她每晚能有些進展,像是對光、聲音或是刺痛能有些反應;除此之外,其實我們也無處可去。史嘉蒂平常都要整天上學,然後艾絲特會接她下課,但這星期我覺得她應該跟我一起在這裡多待點時間,所以我讓她向學校請假。
「妳現在想幹嘛?」我問她。
她打開她那本剪貼簿,這作業好像佔去了她所有的時間。
「不知道,吃東西吧。」
「平常這時候妳都在幹嘛?」
「上學。」
「星期六呢?要是星期六妳會幹嘛?」
「去海邊。」
我試著回想上一次由我負責照顧她是什麼時候的事?然後又為了什麼要照顧她?想想好像是她一歳、一歲半左右的時候,那時因為喬安妮得要飛去茂依島(Island of Maui)拍照,但她找不到褓母,而她爸媽也沒空之類的。我那時候正在出庭辯護一場官司,趁休庭之際在家繼續準備資料,所以我把史嘉蒂放在浴缸並在裡頭丟了塊香皂,然後站在一旁看會發生什麼事。她先是用手拍打水花,然後想要喝浴缸裡的水,接著她發現那塊香皂後就伸手想去抓,香皂溜掉了,她又想再抓一次,她小小的臉蛋上滿是驚奇。我悄悄地回到走廊上,在那我架設了自己的工作檯還有一個嬰兒無線監視器,只要聽到她在笑就知道她沒有被淹死。不知道這招現在還有沒有用?—把她丟進浴缸裡,然後給她一塊肥皂。
「那我們可以去海邊,」我說「妳媽有帶妳去俱樂部嗎?」
「當然,不然是要去哪?」
「那就這麼說定了。等妳跟妳媽講完話,我們跟護士打聲招呼,然後回家準備一下就去海邊。」
史嘉蒂從她的相簿裡抽出一張相片,揉一揉後丟掉。我不知道是哪一張相片,但如果是她媽媽躺在病床上的照片,那也不會是最好的傳家相片。「我想要許願,」史嘉蒂說,「我想要許願去哪呢?」
這是我們常玩的遊戲之一,時不時她都可以許願講一個我們曾經去過的地方,只要不是我們當下所處的地方即可。
「我的願望是我們在牙醫診所那裡。」她說。
「我也是,我希望我們是去那照口腔X光。」
「然後媽媽她一定是要去美白牙齒。」她說。
我真希望我們是在布藍奇醫生的診所裡,我們三個因為笑氣 而嘴唇發麻,但是心情卻好得很,來個根管治療,「笑果」可能會更好,或是隨便來個手術之類的,真的。我希望我現在是待在家裡工作,因為我要決定誰能夠得到我們家族從一八四○年代就擁有的那些土地。這筆交易將會售出我們家族所持有的全部土地,六天後我就要跟「六罐堂哥」見面,所以現在我很急著想要研究所有相關資料,然後我們將會一起決定要選哪位買家。我把這件事情一拖再拖實在是不太負責任的行為,但其實我們家族對於這件事情也拖了很久,我們對自己的家族財產漠不關心,包含了各自的財產與債務,非要等到有其他人來承擔這些事情。
看來非得讓艾絲特帶史嘉蒂去海邊了。我想跟她說,但又覺得很丟臉而說不出口。我老婆躺在醫院裡,我女兒需要雙親的陪伴,而我卻必須要工作,這跟我把她放在浴缸裡有什麼兩樣?
史嘉蒂正盯著她媽媽看,她倚身靠在牆上,手不停玩著自己的裙襬。
「史嘉蒂,」我說「如果妳沒有話要講,那我們就可以走了。」
「喔、好,」她說「那走吧。」
「妳不想跟妳媽說一些學校的事情嗎?」
「她從來也不在乎學校發生什麼事……」
「那妳的課外活動呢?妳事情多到比總統還忙。看看妳的剪貼簿,給她看看。還有妳那天口吹玻璃做了什麼?」
「做了個『蹦』 。」她說
我屏氣凝神看著她,一邊想自己該怎麼接這段話。她的表情看起來不像是覺得自己說了什麼不尋常的話,而我也真的搞不懂她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喔?這麼有趣,」我接著說「什麼是『蹦』?」
她聳聳肩地說,「有個高年級的傢伙教我做的,他說蹦可以拿來裝洋芋片、莎莎醬或是任何我想的到的食物,就好像個盤子之類的。」
「妳有留著這個……『蹦』嗎?」
「算有吧,」她說,「但是拉森老師要我改做成一個花瓶,這樣我就可以插點鮮花,然後送給她。」她指著她媽媽。
「這建議太棒了!」
她滿臉狐疑地看著我,「你不需要對我用『女童軍日行一善』的口吻講話。」
「喔,不好意思。」我說。
我坐在椅子上往後仰,眼睛盯著天花板那些洞看著。我不懂我為什麼不擔心,而我真的不擔心。我知道喬安妮一定會沒事,因為她總是沒事的。她一定會醒來,然後史嘉蒂就會有媽媽,然後我們可以坐下來談談我們的婚姻,然後我就可以卸下心中那些懷疑。我要把那些土地賣掉,然後買艘船給喬安妮,這樣的驚喜一定會讓她高興地對我回眸一笑。
「上一次躺在病床上的可是你。」史嘉蒂說。
「沒錯。」
「而且上次你對我說謊。」
「我知道、史嘉蒂,請原諒我。」
她講的是我上次住院的事情,因為我騎機車出了小車禍。我在跑道上打滑,整個人飛過機車手把摔進一堆紅土裡。出事後我自己回家,然後告訴喬安妮與史嘉蒂事情的經過,我堅稱自己沒事而且不需要去醫院。接著史嘉蒂就開始對我進行一連串測驗來證明我講的話一點也不可信,喬安妮也參與其中,她們倆一搭一唱,極其嚴厲,真是壞透了。
「你看到幾根手指頭?」史嘉蒂問我,我以為自己看到的是她的小指頭跟拇指。
「鬼扯!」我說,我才不想要這樣被測試。
「回答她。」喬安妮說。
「兩根?」
「嗯、好」史嘉蒂小心翼翼地說「把眼睛閉上,用手摸你的鼻子,然後站起來。」
「鬼扯、史嘉蒂,我才不幹。而且妳根本把我當酒後駕車一樣……」
「照她的話做!」喬安妮對我大聲了起來。她對我一向是這麼大聲的,但這真的就是我們的溝通方式,她一大聲我就會覺得自己很笨,但又有被愛的感覺。「用手摸你的鼻子,然後站起來!」
我站著不動以示抗議。雖然我覺得自己不太對勁,但是我真的不想去醫院。我想讓這不對勁的感覺留在身體裡,看看最後會怎樣。不過我卻沒有辦法自己把頭抬起來,「我沒事。」
「你很賤。」喬安妮說。
當然,她是對的。「妳說得沒錯。」我說,腦袋同時浮現醫生對我說「你受傷了」,然後要我支付一千美金的醫療費用去做一堆不必要的事,再給我一堆不可靠又充滿警告的建議,就為了怕被我告。此外,我還要自己去應付那些會故意弄丟資料文件的保險公司,為的就是拒絕理賠,因此醫院只好把我的名字列入欠款催繳名單裡,之後我就會開始接到一堆催繳電話,成天跟那些連高中學歷都沒有的人打交道……即使到現在我也不太相信醫生,那個說話很快的神經科醫生都說他們必須維持她腦中的氧氣濃度以及控制腦水腫的程度。這聽起來很簡單啊!要讓一個病人吸到足夠的氧氣,根本不需要外科醫生。我揉一揉自己的右邊腦袋,邊想著醫生們對於喬安妮病況的那些對話。
「看看你自己。」喬安妮說,我正盯著牆上那幅畫,試著回想當初是在哪買這幅畫的?我試著唸出畫家的名字,「布藍迪.裘基爾?邱吉爾?」
「你連看都看不清楚了!」喬安妮說。
「所以我怎麼可能看得出來,我現在到底好不好?」
「閉嘴、麥特。準備上車去醫院。」
我穿好衣服後坐進車裡。
檢查結果發現我的第四對腦神經受損,就是連結大腦與眼睛的神經,這也說明為什麼我看東西時會無法對焦。
「你很有可能會死掉!」史嘉蒂說。
「不可能,」我說「誰需要第四對腦神經呀?」
「你說謊,因為你說你沒事,還說你看得到我的手指。」
「我沒有說謊,我猜對了。而且,那時候我還會看到疊影,有兩個史嘉蒂。」
她瞇著眼睛,仔細地檢視我講的這些藉口。
我記得那時我住院的時候,喬安妮會在我的果凍裡加伏特加;她還會戴上我的眼罩,然後跳上病床跟我一起小睡片刻。真的很棒,那大概是我們在一起做過最後一件美好的事了。
我心中叨叨地懷疑她一件事,就是覺得她好像,現在或是過去,愛上了另一個男人。她當初被送進這間醫院時,我翻了她的皮夾想要找她的保險卡,卻在她的皮夾中找到一張小小硬硬的紙條,這種藍色的紙好像就是設計用來寫秘密一樣,寫著「想妳,我們在靛藍見」。
這紙條可能好幾年有了。她常常會找到很久以前旅行時留下的泛黃收據,或是一些公司早消失的名片,還有《水世界》及《光榮》 的電影票根。這張紙條也有可能是她那些同志模特兒給她的,那些傢伙總有一堆甜蜜的屁話,而這張小紙卡真的就是很女性化的蒂芬妮藍。那時我告訴自己不要亂想並試著去忘記這張紙條,一直到最近我開始想到她喝酒時那種迂迴又帶挑逗的態度,一旦喝多了,身邊又總是那些女性朋友時,如果她不刻意避免的話,婚外情似乎理所當然。我老是忘記喬安妮小我七歲,也總是忘記她需要常常被讚美與取悅,她需要被渴望的感覺,但我卻常因為忙碌而沒空讚美她、取悅她,或是渴望她。不過,我還是很難想像她真的有婚外情。我們已經認識彼此超過二十年了,我們懂得彼此也不會過度期望。我喜歡我們所擁有的,我知道她也這麼以為,而現在我的疑慮真的不怎麼合宜……
史嘉蒂還在凝神盯著我看,「你很可能就這樣掛掉。」她說。
我想不透我在那場意外裡,有沒有改變了什麼。最近史嘉蒂老是在挑我的缺點講,還有我的把戲跟謊話,好像她是面試官一樣,而我是個應徵「父親」這職務的候補人選,她跟艾絲特都像在幫我準備面試一樣。我想告訴她們我沒有問題,雖然現在我只是個替身角色,但我很快就會恢復大明星的身份了。
「你還想許願去哪呢?」我問。
她正坐在地上,用下巴靠在椅子座墊上「去吃午餐,」她說,「我肚子快餓扁了,還有汽水,我要汽水。」
「我希望妳可以跟她說說話,」我說,「妳要在我們離開前完成這件事,我可以去買汽水給妳,給妳一點隱私。」說完我便站起來伸個懶腰,當我眼神掃到喬安妮時,我感覺很糟,因為我竟然活動自如。
「妳要無糖汽水嗎?」
「你覺得我很胖嗎?」史嘉蒂反問我
「不、我不覺得妳胖。但是艾絲特餵妳吃太多甜食,我覺得妳要開始吃一些排毒餐。,如果妳沒有意見的話,我們要開始做些改變了。」
「什麼是排毒餐?」她舉起她瘦長的手臂伸了個懶腰。我注意到她在模仿我的動作與談話。
「就是妳姊姊早該做的事……」我喃喃說著,「我一下就回來,不要亂跑,跟妳媽說話。」
2
我走到走廊上,空蕩蕩地毫無聲響。中間櫃檯有很多護士跟接待人員,還有一些人在那等著,等護士跟接待人員抬頭注意到他們的存在。每當路過其他病房時,我總告訴自己不要轉頭窺看,但偏偏每次都忍不住。我探了探喬安妮的隔壁病房,那是間人氣很旺的病房,常常都有一堆來探視的家人、朋友、汽球、花環、以及鮮花,搞得好像慶祝他成功戰勝病魔一樣。今天他卻落單了,他赤腳從浴室走出來,用手抓牢身上鬆散的醫院病服。其實不難發現他在外面應該是個硬漢,只是醫院病服讓他看起來很脆弱。他拿起桌上的一張卡片來讀,放下後再一把將卡片掃到床上。我很討厭那些祝人早日康復的卡片,那就像是祝人飛行愉快一樣,因為我們能做的真的不多。
我繼續往櫃台走去,看到裘悅跟另一個護士向我走過來。裘悅 是個人如其名的人。
「金先生,」她說「今天好嗎?」
「好極了、裘悅,你呢?」
「不賴,還不賴。」
「那真是好。」我說。
「今天報紙有你的新聞呢!」她說「你做決定了嗎?大家都在等呢!」
另一個護士推了她一下說,「裘悅!」
「幹嘛啦,我跟金先生就是這樣呀……」她把她的中指放到食指上
我繼續往醫院商店走去「管好你自己的事吧,小姐!」我盡量讓自己聽起來輕鬆愉快。有這麼多人自以為他們認識我是一件很尷尬的事,而且還有這麼多人,特別是我的堂兄弟姊妹們,都還在等我的決定。當高等法院裁定該信託管理中的比例架構後,我就成為其中的最大股東,但現在我卻只想躲起來……這責任實在太大了,或許是因為自己有那麼多主導權而充滿罪惡感。為什麼是我?為什麼這麼多事情要靠我決定?我的祖先們是做了什麼才讓我現在擁有這麼多?或許我應該想一想,是不是每一筆財富的背後都什麼偷雞摸狗的勾當,是不是這麼說的?
「再見,金先生,」裘悅說,「要是明天報紙有再寫什麼,我會跟你說的。」
「好極了、裘悅,謝謝妳。」
我可以感覺到我和裘悅這樣的戲謔對話,已經引起其他病人的注意。為什麼大家都認得出我?我想他人的妒火也因為我的姓氏更加強烈,就像這姓氏聽起來一樣;「金」先生,好像我要求他們在「皇后」醫院裡都要這樣尊稱我一樣。沒有病人喜歡我是名人這件事,但他們並不了解我也不想在醫院變成名人這件事,我只想當個普通人,進進出出,沒人記得我。
這間小商店裡充滿各種用來表達關心的東西;糖果、鮮花、填充娃娃,這些東西都可以讓收到的人有備受呵護的感覺。我走向後方的冷藏區去找無糖汽水,我對於自己這條無糖汽水的家規感到相到驕傲,我從沒有用過這麼明確的家規來管教我的孩子,除了「不、我沒有要買給妳」之外。
結帳前,我轉了轉卡片架,想找一張卡片讓史嘉蒂寫給她母親。保重、醒來吧、我愛你,再也不要把我丟給老爸了。
那裡也有賣明信片,我看了看夏威夷的風景明信片;夏威夷大島上岩漿從熔岩流出的照片、大捲浪區的衝浪人群照片、茂伊島海岸拍攝的鯨魚水面照片、波里尼西亞文化中心舞者口中噴火的照片……
我轉了轉架子,然後她出現了:雅莉珊卓,這張照片我以前就看過了。我好像做壞事怕人知道一樣地看看四周,一個男人從我後方經過,我稍微移動一下身體好擋住女兒的照片。雅莉珊卓十五歲的時候,替「島嶼卡片公司」拍了一組明信片,上頭寫著「人生就需要一座他媽的熱情沙灘」;從一件式洋裝變成綁帶比基尼,然後綁帶比基尼又變成更小件的那種帶子比牙線還要細的比基尼。她跟她媽媽一直到這些照片已經發行了,才告訴我這件事,接著我就終結了她的模特兒生涯,但是三不五時我還是會在隆氏藥妝店 看到這些明信片。大多數都是出現在威基基(Waikiki)的商店裡,而我認識的人都不會去那,所以我忘了我女兒的性感照還在市面上販售,還會被蓋上郵戳寄到奧克拉荷馬州或是愛荷華州之類的─一邊寫著「可惜你沒來」,一邊是雅莉在豔陽下用誇張的姿勢放送飛吻。
我轉頭想找店員,但發現身邊都沒有人。我開始找更多有她入鏡的明信片,但只看到五張這組照片的明信片;她身穿白色比基尼跨坐在衝浪板上,有個沒有入鏡的人向她潑水,她正舉起手來擋水,而她笑得很開,頭向後仰,上半身看起來很輕盈,串串水珠在她的肌膚上閃閃發亮。如果非要我選的話,其實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張,因為至少她臉上掛著笑容,作著屬於她這年紀該做的事。其他的照片裡她看起來成熟、性感又傲慢,臉上就是一副她知道全天下男人想要什麼的表情,那種帶著慍怒與放蕩的表情,也就是任何人不想在自己女兒臉上看到的表情。
當我問喬安妮為什麼要讓她去拍這種照片時,她說,「因為這也是我的工作,我要她學習尊重我的工作。」
「妳是替型錄和報紙廣告當模特兒,這有什麼好不尊重的?」我當下就發現自己詞不達意。
一個中國女人走進店裡,然後走向櫃台後面「好沒? 」她問。
她穿著一件穆穆袍 ,下身搭著一條海軍藍人造纖維褲,看起來好像是剛從難民庇護所逃出來一樣。
「你們為什麼要賣這個?」我問,「這種禮品店裡,應該要賣那種希望人早日康復的卡片,這些不是。」
她從我手中拿走那些明信片,一張一張翻過,「都一樣,你買都一樣的卡片?」
「不、」我說,「我在問妳為什麼要在醫院裡的禮品店賣這種東西?」
我知道這個對話不會有什麼結論,終究會變成一場殺氣騰騰又令人困惑的洋涇濱 口角。
「啥?你沒喜歡女人還怎樣?」
「不、」我說,「我喜歡女人,但不能是未成年的女孩子,妳看,」我拿起一張卡片,上面寫「身體健康,爺爺」,「這樣的卡片相當不得體,」我把我女兒握在手裡,「這很不得體,這根本不是卡片,這是張明信片。」
「這是我的店,醫院人也有白人 ,來這,好了就要買紀念品給美國本土。」
「他們來醫院探病,然後想要買紀念品?好了、算了,拿去。」
她把卡片拿去後就往卡片架上走去。
「不,」我說「這些我都要買,全部都買,還有這兩罐汽水。」
她頓了一下,滿臉狐疑,腦袋似乎閃過了我們剛才的對話,但是她一句話也不講,也不想看我,我付錢,她找錢。
「我要個袋子,謝謝。」我說。她拿了個袋子給我,我用來蓋住我的女兒,「謝謝。」
她微微點頭,但不正眼看我,自顧自地在櫃台忙她的,我發現我總是會跟中國老太太起口角。
我走回六一二號房,繼續面對我那有點瘋癲的女兒。手裡拿著雅莉的明信片讓我感覺很不自在,好像是她一直被困在這裡,然後我終於來解救她了。
喬安妮跟雅莉兩個人鬧得不太愉快,每次我問的時候,喬安妮都會說,「等她大了就會懂了。」不過我常常又覺得喬安妮應該也要成熟一點才是。她們之前總是黏在一起做任何事,喬安妮是個很有趣的母親,年輕、又酷、又時尚。一直到雅莉不再做模特兒之後,她們的關係就終止了,雅莉退縮了。喬安妮開始熱衷參加比賽,雅莉開始翹家,接著沾上了毒品,於是喬安妮決定在上個學年度,把雅莉送去住宿學校。本來去年一月雅莉打算轉回以前的學校,但在耶誕假期間似乎發生了什麼事,雅莉跟好像她媽媽有什麼不愉快或爭執之類的,突然間她又說她喜歡住宿學校,自己甘願回去住校。我向雙方詢問原因,為什麼雅莉又要回住宿學校?但是她們沒有人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覆,而且家裡一直都是喬安妮在做這類決定的,包括學校或任何跟女兒有關的事,所以我就不多追究了。「她要自己收拾爛攤子,」喬安妮說,「她就得回去。」
「我受夠了,」雅莉說,「媽她根本就瘋了,我不想跟她有任何牽扯,勸你最好也不要。」
她們倆之間竟有這麼多灑狗血的劇情,真的很悲哀,因為我很懷念以前我跟雅莉之間的關係,我甚至曾經想過要是喬安妮死了,我跟雅莉也是可以好好活下去的,而且會活得更好;我們會彼此信賴、彼此相愛,就像我們以前一樣。她可以回家裡來住,生活也不會一團糟。不過話說回來,我也不相信要是我老婆死掉了,我們真的可以過得更好,剛才那想法真是糟透了……而且我不覺得雅莉的問題僅來自於喬安妮,我想我應該也是其中之一。一直以來,我不是那種隨時守候在小孩身邊的父親,過去的我好像長期失去知覺一樣,不過現在我在嘗試改變了,而且我想我表現得還不錯。
我站在我太太的病房門口,看到史嘉蒂在方型油氈地板上玩跳房子,一邊用木製壓舌片標記她跳過的格子。
「我好餓,」她說,「我們可以走了沒?你有買汽水嗎?」
「妳講了沒?」
「嗯?」她說,我馬上就知道她在說謊,每次她說謊都會用反問的方式回答。
「好吧,」我說,「我們回家。」
史嘉蒂直直向門口走去,看都沒有看她媽媽一眼,一把從我手裡抓走她的汽水。「說不定我們晚點再過來。」我多此一舉地跟她說。我看著我太太,她臉上有一抹淺淺的微笑,好像她知道什麼我不知道的事一樣,於是我又想起那張藍色紙條,要不去想還真難。
「跟妳媽說再見。」
史嘉蒂頓了一下又繼續向前走去。
「史嘉蒂!」
「再見!」她叫了一聲。
我抓住她的手臂,雖然我可以因為她這麼迫不及待想離開而兇她幾聲,但我沒有。她從我手裡掙脫,我抬頭看看四周有沒有人在看我們,畢竟這年頭似乎不太能這樣對待小孩。那些打屁股與威脅利誘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式療法、抗憂鬱藥還有甜蜜素 。我遠遠看到強斯頓醫生從走廊盡頭向我們走來,他暫停了與其他醫生的談話向我招手,要我等他,「停」,他的手勢就是這個意思。他的表情看來熱切卻不帶一絲笑容,我馬上轉頭背向他朝另一邊看;接著他加快了腳步,我斜眼留意他的動作,但又裝作我好像沒看到他一樣。我心裡想,『要是我錯了怎麼辦?要是喬安妮撐不過去怎麼辦?』
「史嘉蒂,」我說,「走這邊。」
我轉了個方向以遠離強斯頓醫生,史嘉蒂也轉身跟著我走。
「走快點。」我對她說。
「幹嘛?」
「玩遊戲,比賽看誰走得快,跑!」她跑了起來,背包叮叮噹噹響個不停,我也跟著她快步走著,最後慢跑了起來。因為強斯頓醫生是我朋友的父親,也是我父親的舊識,我瞬間覺得自己回到了十四歲,那個總想遠離家族長老的年紀。
我還記得有次為了整他的兒子「史基普」而蛋洗強斯頓醫生的家,我們三個人─布萊克.凱利、凱可亞.劉和我,被強斯頓醫生開的卡車追著跑。他是真的在追捕我們,就算我們切進小巷裡,他還下車飛奔追趕我們,最後還是被他逮個正著。他手裡拿著一個福聯 超市購物袋,告訴我們有以下兩個選擇;要嘛就是他打電話叫我們的爸媽來領人,不然就是幫他處理掉他老婆的「驚奇豆腐料理 」。我們選擇後者,於是他手伸進購物袋裡,然後讓我們嚐嚐惡作劇的苦果。我們離開的時候,「驚奇豆腐料理」遍佈在我們的頭髮、耳朵……到處都是。從那天起他只要看到我們就會瘋狂大笑地叫我們「黃豆男孩」,然後大叫一聲「噗!」,好一陣子我都因為這樣被嚇到微微跳起來。當然現在不會了,畢竟他也好久沒有這樣了。
我跟我女兒在走廊上奔跑著,感覺好像身處在一個陌生國家,身邊的人都在講洋涇濱英語,看我們的表情就好像我們是兩個發癲的白種笨蛋一樣,雖然我們明明就是夏威夷人,但我們不像,而且我們的英文講得不夠「不道地」,根本不能算是本土或是正統的夏威夷人。
強斯頓醫生自己說好是星期二的,那就是我們訂的日子,到時候我自然會現身,我現在還不想知道任何事情,而且我現在要照料太多事情了。我放眼看看自己的周遭,已經二十三天了,我就活在這個世界裡;每個人都在猜想其他人來醫院的原因、每本雜誌都用身體健康的人做封面、玻璃櫥窗裡那輛小火車模型正緩緩地沿海岸繞著,而沙灘上坐著直挺挺的居民模型……我逃離醫生的診斷說明,我確信明天會準備好自己的。
1
窗外陽光普照,成群的八哥鳥啁啾個不停,棕櫚樹一棵棵隨風搖曳著,但又怎樣?我人好好的卻待在醫院裡。我的心臟盡責地跳著,腦裡卻不停地竄著各種訊息,既響亮又清楚。我的妻子坐靠在病床上,就好像搭飛機時的睡姿一樣。她的身體僵硬,頭歪歪地側向一旁,雙手擱在大腿上。
「不能讓她躺平嗎?」我問。
「等一下。」我的女兒史嘉蒂說完,便拿起拍立得相機對著她母親拍了張照片。我按下床邊的控制鈕讓妻子的上身緩緩躺下,我的女兒則在一旁搧著那張照片,直到她幾乎躺平後,我鬆開按鈕。
這是喬安妮陷入昏迷的第二十三天,接下的幾天內...
目錄
PART_01_荳蔻之戰THE MINOR WARS
PART_02_國王步道THE KING'S TRAIL
PART_03_獻 品THE OFFERING
PART_04_方 向WAYFINDING
PART_01_荳蔻之戰THE MINOR WARS
PART_02_國王步道THE KING'S TRAIL
PART_03_獻 品THE OFFERING
PART_04_方 向WAYFI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