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亞馬遜編輯年度選書
★亞馬遜讀者四星半高評價
「皮拉哈人讓我了解到,即便沒有天堂的慰藉與地獄的恐懼,也能有尊嚴並心滿意足地面對生命,帶著微笑航向生命的混沌深淵。」
一種語言代表一種世界觀,一種瀕絕語言則代表一種瀕絕的世界觀
而這套瀕絕的世界觀,為何能讓他背棄信仰,從傳教士變成無神論者?
先有語言還是先有思想?人類能在沒有語言的情況下思考嗎?
這是科學家長期以來亟欲探究的問題,而一個孤絕的人類部落,或許可以給我們答案……
但是丹尼爾.艾弗列特偕同妻小住進亞馬遜叢林,還有另一個理由:他要帶著皮拉哈人一起上天堂!然而經歷大半生,他最後卻孑然一身地離開,不但與妻子離異,更成了無神論的語言學家。
他拋棄原本舒適的生活,忍受身體不適、文化差異,與瘧疾、孤獨、語言障礙共處,在原始部落中陸續生活三十年,以肉體最近身的搏鬥,追尋語言和思想起源這個最形而上的探問。
他付出昂貴的代價,為我們換來這一篇篇精采、深情、趣味、令人深思的叢林故事。他揭露一套前所未見的語言系統及宇宙觀,在學術象牙塔中激起一場意義深遠的爭辯,並對自我進行最沉痛的探索與重生。
一段關於知識、叢林、家庭、信仰的冒險之旅。
他以自己留不住的東西,換得不會失去的東西。
關於皮拉哈族……
.皮拉哈語裡只有3個母音與8個子音
但每個皮拉哈語的動詞,卻至少有6萬5千種可能形式
.皮拉哈人會不時更換名字
理由通常是他們在叢林與相遇神靈交換了名字
.皮拉哈人不會將做夢視為幻境
清醒與沉睡時所看見的東西,皆屬真實經驗
.皮拉哈人互道晚安時會說:「別睡,這裡有蛇!」
因為叢林中危險環伺,熟睡會讓他們無從防備。他們很少一連睡上幾小時。
作者簡介
丹尼爾.艾弗列特 Daniel Everett
曾任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語言、文學暨文化系主任,現任本特利大學瓦珊分校文理學院院長。他本是傳教士,為了「帶著皮拉哈人一起上天堂」,攜家帶眷在亞馬遜叢林裡住了三十年。他離開部落的時候放棄了基督教信仰,卻成了語言學家;與妻子離異,卻與許多皮拉哈人成為摯友。
丹尼爾.艾弗列特是唯一一位能夠流利操持皮哈拉語的外來者,而他在這套語言系統上的發現,不但挑戰了語言學界權威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既定主張,更向上追溯了語言和文化上的先後關係。
攝影者簡介
馬汀.薛勒 Martin Schoeller
知名德國人像攝影家,現居紐約,拍攝對象從明星、政治家到部落叢林族人,從歐巴馬、安潔莉娜裘莉到不知名的皮拉哈人都有。
他的拍攝特點在於一視同仁且毫不留情地捕捉臉部所有細部特徵,以同時呈現個人與群體的共相和殊相,引發觀看者留意或意外發現被攝者作為人類所凸顯 / 揭露的本質。
曾與美國世界級人像攝影家Annie Leibovitz共事,從中習得重要拍攝技巧。
譯者簡介
黃珮玲
比利時魯汶大學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碩士。見本書作者從語言最細緻處撼動所屬專業學科與信仰,並透過自身經歷與反省,試圖回答人何以為人的根本問題。翻譯本書因而是個除塵去蔽、明見自身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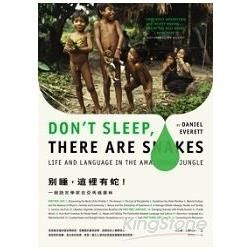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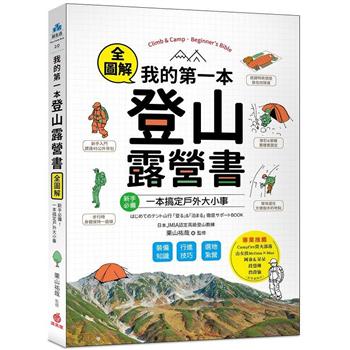








乍看之下,您會以為這是一本搞笑書籍—別睡,這裡有蛇!真的蛇還是假的蛇?大的蛇還是小的蛇?對於顯然極少野外生活經驗的我們而言,很難想像位於亞馬遜河密林中的皮哈拉人的生活,但這種文化上的差異卻打破了習以為常的「普世語法」理論,反應在該族人的語言上,同時也讓一個深入當地研究二十多年的語言學家發覺出了該民族的文化特質及其特異之處,進而進一步研究歸結,甚至為此放棄了自己的信仰…因此,該書取了「一個語言學家在亞馬遜叢林」來讓讀者進一步融入書中情境。 語音、語概是語言學的基本學科,而在往昔,一般都會認為田野調查是研究這門學問的必經之路,但自從杭士基提出「語言文法為天生」的奠基理論後,這些學門都變的優雅而充滿哲理!唯有像作者這種起先打算「馴化」未識上帝的皮哈拉人的傳教士,才會深入密林,企圖傳播唯一的福音。但皮哈拉人活在當下、不識數字、沒有時態等文化特色卻也同時反映在其語言中,挑戰大師的理論,反倒比較傾向較「古早」的的斯皮爾假設。筆者第一個心得是讚嘆作者的使命感與學習的熱忱,他結合了生活與研究,不斷精進自己的理論,同時不畏大師、直指證據,這樣的學者國內少有…而每位研究者都該自問:你會不計時間、學位,認真的發掘現象,深入研究嗎? 也因此,杭士基在2005年曾為此修正其理論,而這本自傳類的研究報告實為一本相當值得推薦的科普書籍,它以深入淺出且生動的文字介紹研究者的付出,不管你用人類學、語言學、或是抱持純欣賞的態度來讀,都定能深有所得。這群葛天氏之民也許終將面臨文化的衝擊,屆時這個語言也將毀棄,但我們總可以反思在這全球化的世界裡,是否也可以有一點不同的色彩,給我們一些反思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