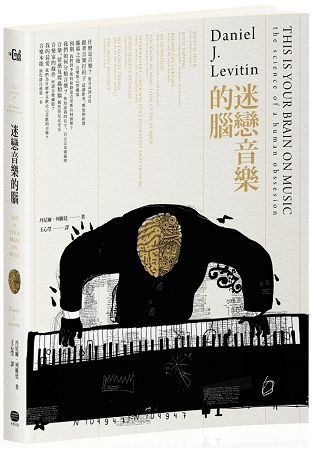結合音樂分析、心理學與神經科學,述說音樂如何令人迷戀,解釋人類最優美的神經衝動。☆ 哈佛大學「新鮮人通識教育核心計畫」指定閱讀
☆ 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史丹佛大學等校課堂教材
有時一段旋律就能喚起許多回憶
有時一首歌就能為我們阻擋世界為何音樂在我們心中占有如此獨特的地位?
我們都能說出自己喜愛的音樂風格與類型,但你真的知道為何自己喜歡的是這種,而不是那種音樂?
資深音樂人〔史提夫.汪達、死之華樂團製作人〕暨心理學教授丹尼爾.列維廷,結合音樂分析、心理學與神經科學,述說音樂如何令人迷戀,解譯人類最優美的神經衝動。
從音樂認識大腦,從大腦認識音樂;
結合兩者使我們更加認識自己。音樂是最能貼近心靈、感染情緒的創作形式,也是我們唯一隨身攜帶、不時重新溫習的藝術作品。
我們都能輕易舉出喜愛的音樂家或音樂類型,卻難以解釋為何自己喜歡的是這些音樂,而非其他作品。彷彿在音符與和弦之間,還有某種我們能夠感知,卻無法言說的神祕。
作曲家荀白克曾說:「總有一天,心理學家將能解譯音樂語言。」如今預言的時代已然來臨。心理學家運用磁振造影與記憶理論,探究人類心智與大腦如何傾聽、感受音樂,以完形理論分析音樂家如何顛覆聽眾心理,創作令人驚豔的樂曲。但科學研究的意義不在於驅除一切神祕,而是重新創造、活絡神祕的面貌。當我們理解人類對音樂的迷戀的本質,也更能深入地認識自己。
作者簡介:
丹尼爾.列維廷 Daniel J. Levitin
專業音樂人,成長於1970年代搖滾狂飆的加州。出身中產階級家庭,母親所彈奏的蕭邦與舒曼是他對音樂最初的記憶,然而丹尼爾卻在大學時代為組搖滾樂團而輟學。在音樂界浮沉數年後,丹尼爾闖出一番成績,擔任史提夫.汪達、死之華樂團、藍牡蠣樂團的唱片製作人、錄音師,更與史汀、大衛.拜恩同台共演。
三十歲後帶著對音樂的熱情重返學界,現為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心理學教授,主持音樂感知與知覺研究實驗室,致力探究音樂如何引發情感,以及人類如何記憶、再現音樂,他的實驗室也是妃絲特、巴比.麥菲林等音樂人的朝聖地。丹尼爾堅持以真實音樂取代傳統實驗所用的機械人工聲響,以取得貼近現實的數據。著有《迷戀音樂的腦》、《傳唱世界的六首歌》、《認知心理學基礎》,其中《迷戀音樂的腦》為麻省理工學院、UCLA的課堂教材,及哈佛大學的新鮮人通識教育核心計畫指定閱讀。
譯者簡介:
王心瑩
夜行性鴟鴞科動物,出沒於黑暗的電影院與山林田野間。日間棲息於出版社,偏食富含科學知識與文化厚度的書本。譯作有《我們叫它粉靈豆─Frindle》、《女孩的In發明》、《小狗巴克萊的金融危機》等,合譯有《你保重,我愛你》、《上場!林書豪的躍起》,並曾參與「魔法校車」、「波西傑克森」等系列書籍及《科學人》雜誌翻譯。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媒體推薦:
史旻玠 配樂家、2012金鐘獎得主
沈鴻元 爵士樂評人、廣播人
陳德政 作家
蘇重 爵士樂評人
Cicada 新銳樂團,一致推薦。
結合科學與音樂知識,為非科學人 × 非音樂人讀者而寫的專業之作。科學界、音樂界名人連袂推薦:
「唯獨兼具音樂家與神經科學家身份才能擁有的綜觀視野,令人驚異、啟發無限靈感……我尤其偏愛最後一章從演化角度探討音樂的部分。本書無疑是部鉅作。」—— 奧利佛.薩克斯(神經醫學家、《火星上的人類學家》、《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作者)
「儘管本書揭示許多奧祕,卻讓音樂成為更美麗的謎。」—— 大衛.拜恩(Talking Heads主唱)
「為協助理解音樂而生的著作,堪稱藝術與科學美麗的集成。」—— 麥可.波斯納(著名認知神經學家)
「我要向這位膽敢同時挑戰雷蒙斯樂團、披頭四與貝多芬第六號交響曲的仁兄脫帽致敬!丹尼爾以其洞察力、同理心及幽默感回應了『音樂之於人類生存處境扮演何等要角』這古老的問題,卻不損及音樂最神祕的溝通與感知之魔力。」—— 麥特.海默維茲(大提琴家、芝加哥交響樂團獨奏者)
「列維廷博士解釋科學知識的本領嫻熟出眾,信手拈來皆是科學趣聞。」——《紐約時報》
「充分展現專業而不失可親,即使是對神經科學與腦部醫學一竅不通的普通讀者也會大為驚豔。」——《波士頓環球報》
「流利的文筆與輕鬆的寫作方式充滿信服力,讓讀者以全新的角度思考自己的隨身播放器裡裝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法寶。」——《出版人周刊》
「……對心智與旋律的連結提供了敏銳的觀點。」——《科學人圖書俱樂部》
名人推薦:
媒體推薦:史旻玠 配樂家、2012金鐘獎得主
沈鴻元 爵士樂評人、廣播人
陳德政 作家
蘇重 爵士樂評人
Cicada 新銳樂團,一致推薦。
結合科學與音樂知識,為非科學人 × 非音樂人讀者而寫的專業之作。科學界、音樂界名人連袂推薦:
「唯獨兼具音樂家與神經科學家身份才能擁有的綜觀視野,令人驚異、啟發無限靈感……我尤其偏愛最後一章從演化角度探討音樂的部分。本書無疑是部鉅作。」—— 奧利佛.薩克斯(神經醫學家、《火星上的人類學家》、《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作者)
「儘管本書揭示許多奧祕,卻讓音樂成...
章節試閱
第三章 簾幕之後 音樂與心智機器(摘錄)
人類的大腦分為四葉,分別是額葉、顳葉、頂葉和枕葉,外加小腦。我們可對這些部位的功能做粗略的歸納,但事實上,人的行為是很複雜的,無法輕易化約成簡單的分布圖。額葉與規畫能力及自制有關,也具有從感覺系統接收的龐雜訊號中抽繹意義的能力,這正是完形心理學家所說的知覺組織(perceptual organization)。顳葉與聽覺和記憶有關,額葉後區與運動能力有關,枕葉則與視覺有關。小腦與情緒和整體動作協調有關,許多動物(例如爬行類)缺少功能較高級的大腦皮質,但都有小腦。切下額葉內的前額葉皮質,使之與視丘分離的手術稱作前額葉切割術。雷蒙斯樂團(Ramones)有首歌叫〈青少年前額葉切割術〉(Teenage Lobotomy),歌詞內容如下「如今我得告訴他們/我沒有小腦」由解剖學看來並不正確,但考慮到藝術表現的自由,以及他們創作出了搖滾樂史上偉大的歌詞韻腳份上,讓人很難不給他們掌聲。
音樂活動牽涉目前已知的近乎全部腦區,也涵蓋將近所有周圍神經系統。音樂的各種要素分別由不同神經處理,亦即大腦會以各個不同功能的分區來處理音樂,並運用偵測系統分析音樂訊號的音高、速度、音色等各種要素。處理音樂訊息的部分過程與分析其他聲音的方式具有共通性,例如接收他人的話語時,需把聲音切分成字詞、句子和片語,我們才能理解話語的言外之意,如諷刺意味(這點就不那麼有趣了)等,而樂音也可分作數個層面來分析,通常牽涉數種「類獨立神經過程」(quasi-independent neural processes),分析結果也需要經過整合,才能使樂音形成完整的心智表徵。腦部對音樂的反應由皮質下結構(包括耳蝸神經核、腦幹和小腦)開始,然後移至大腦兩側的聽覺皮質。聆聽熟知的樂曲或音樂類型,例如巴洛克音樂或藍調音樂,則會動用大腦中更多區域,包括記憶中樞的海馬迴及部分額葉(特別是下額葉皮質,這個部位在額葉的最下方)。隨著音樂打拍子時,無論是否結合肢體動作,都會牽涉小腦的計時迴路。演奏音樂(無論演奏何種樂器,或是哼唱、指揮音樂)則會再度動用額葉,以規畫肢體行為,同時結合位於額葉後方、靠近頭頂的運動皮質,當你按下琴鍵,或依心中所想地揮動指揮棒時,感覺皮質便會提供觸覺回饋。閱讀樂譜則會使用頭部後方、位於枕葉的視覺皮質。聆聽或回想歌詞則需運用語言中樞,包括布羅卡區(額下迴)和維尼克區,以及位於顳葉和額葉的其他語言中樞。
接著我們來看大腦更深層的運作,音樂所引發的情緒來自杏仁核,以及深藏在原始爬蟲類腦內的小腦蚓部(verebellar vermis)。前者是大腦皮質的情緒中樞。整體來看,大腦各區域的功能專一性十分明顯,但各功能分區間的互補原則也能發揮效用。大腦是高度平行運作的裝置,各種運作過程牽涉腦中諸多區域。大腦沒有單一的語言中樞,也沒有單一的音樂中樞,而是由許多區域分別處理,另有一些區域負責協調訊息的統整程序。直到最近,我們終於發現大腦具有遠超乎想像的重組能力,稱為神經可塑性(neuroplasticity)。這項能力意味著大腦中部分區域的功能專一性是暫時的,當個體遭受創傷或腦部受創,處理重要心智功能的中樞便會轉移至大腦其他區域。
由於描述腦部運作所需的數字實在太過龐大,完全超出日常經驗(除非你是宇宙學家)的水準,因此一般人難以體會大腦的複雜程度。大腦平均由一千億個神經元組成,若將神經元比作一元硬幣,而你站在街角,要以最快的速度把這些硬幣遞給路過的人。假設你每秒遞出一元,一天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地遞出硬幣,那麼從耶穌出生起算至今,你也才遞出全部的三分之二。就算一秒可以遞出一百個硬幣,也要花費三十二年才能全部送出。神經元的數目確實十分龐大,不過大腦與思想真正的能力與複雜度,乃是來自神經元之間的連結。神經元之間會互相連結,一個神經元所能連結的數量從一千個到一萬個不等。區區四個神經元就有六十三種連結方式,總共產生六十四種連結。一旦神經元數目增加,連結數更會呈指數成長:
n 個神經元會產生2(n*(n-1)/2) 種連結
兩個神經元會產生兩種連結
三個神經元會產生八種連結
四個神經元會產生六十四種連結
五個神經元會產生一、○二四種連結
六個神經元會產生三二、七六八種連結
由於數字實在太龐大,我們幾乎不可能知道大腦內所有神經元共有多少種連結方式,也無從得知這些連結所代表的意義。連結的數量代表可能產生的思想數量,或者大腦狀態,而這數目遠遠超過宇宙中的已知粒子數。
第四章 預期 我們對李斯特和路達克里斯有何預期?(摘錄)
參加婚禮時,最能使我熱淚盈眶的,並非新人站在親朋好友面前,懷抱著滿滿的希望與愛迎向未來人生的情景。我往往在婚禮音樂響起的那一刻就落下淚來。觀賞電影時,當劇中佳偶歷經重重考驗後終於再度團圓,這時的背景音樂也會觸動我,將我的情緒推至感性的臨界點。
如先前所述,音樂是有組織的聲音,但這組織應包含某些令人無法預期的元素,在情感上才不會顯得平淡而呆板。對音樂的鑑賞能力,取決於理解音樂結構(如同語言或手語的語法)的能力,能否對樂曲的發展做出預期也同等重要。作曲家要為音樂注入情感,須能了解聽者對音樂的預期,然後巧妙地操作樂曲走向,決定何時滿足這份預期,何時則否。我們之所以為音樂而興奮、顫慄甚至感動落淚,往往是因為熟練的作曲家以及負責詮釋的音樂家,能夠高明地操控我們的預期之故。
西方古典音樂中,紀錄最豐富的錯覺(或說應酬伎倆),稱為「假終止式」。終止式是一段和弦序列,令聽者對樂曲走向產生清楚的預期後走向結束,通常會以能夠滿足聽者預期的「解決」(resolution)作結。在假終止式中,作曲家則會再三重複同一段和弦序列,令聽者確信自己預期的結果即將來臨,然而就在最後一刻,作曲家會丟出一個意想不到的和弦,不是走調,而是一個未完全解決,告知樂曲尚未結束的和弦。海頓經常運用這種假終止式,簡直有點像是著了魔。庫克比之為魔術戲法:魔術師先製造一些預期,再加以推翻,而你完全無法得知他們將如何、何時推翻你的預期。作曲家也會玩同樣的把戲,如披頭四的歌曲〈不為誰〉結束於五級和弦(音階的第五音級),聽者所期待的解決並未出現(至少不在這首),而同張專輯的下一首曲目,竟是從聽者所期待的解決降下一個全音級(降七級音)開始奏起,形成半終止式,令人又是驚訝,又覺鬆了口氣。建立預期然後操控,這正是音樂的核心,而且有無數種方式可達到目的。史提利丹樂團(Steely Dan)的做法是以藍調形式演奏歌曲(運用藍調的結構與和弦進行),並為和弦加上一些特殊的和聲,使之聽來非常不像藍調音樂,如〈廉價威士忌〉(Chain Lightning)便是採用這樣的作法。邁爾斯.戴維斯和約翰.柯川(John Coltrane)之所以能在爵士樂壇享有崇高地位,正是因為他們為藍調音樂重配和聲,創造出揉合舊曲新聲的全新樂曲。史提利丹樂團的唐諾.費根(Donald Fagen)曾單飛出輯《螳螂》(Kamakiriad),其中一首歌開頭帶有藍調和放克的節奏,使我們預期該曲將有標準的藍調和弦進行,然而這首歌開頭的一分半之內只用了一個和弦,而且不曾離開同一個的把位。艾瑞莎.弗蘭克林(Aretha Franklin)的歌曲〈一群傻子〉(Chain of Fools)則更徹底,整首歌只用了一個和弦。披頭四的〈昨日〉(Yesterday)主旋律樂句長達七個小節,顛覆了流行音樂的基本假設,即樂句應以四小節或八小節為一單位(幾乎所有流行與搖滾歌曲都是以這樣長度的樂句組成)。另一首歌〈我要你(她是如此重要)〉(I Want You 〔She's So Heavy〕)則顛覆了另一項預期,開頭是如催眠般不斷重複,彷彿永遠不會結束的終止曲式,而根據以往聆聽搖滾樂的經驗,我們以為這首歌會以逐漸降低音量,即典型的淡出結尾,相反地,這首歌卻戞然而止,甚至不是停在樂句的結束,而是中間的某個音!
木匠兄妹合唱團(Carpenters)則以音色顛覆我們的預期。他們應該是樂迷心目中最不可能運用電吉他破音音效的合唱團體,然而在〈請等一下,郵差先生〉(Please Mr. Postman)等歌曲中,這樣的假設遭到了推翻。滾石樂團堪稱世上最激烈的硬式搖滾樂團,前幾年卻反其道而行,甚至在〈淚水流逝〉(As Tears Go By)等曲目中使用了小提琴。范海倫樂團還是新起之秀時,便做了一件讓樂迷驚訝不已的事:他們把奇想樂團(The Kinks)一首不那麼時髦的老歌〈迷上了妳〉改編成重金屬搖滾版本。對節奏的預期更是經常遭到顛覆。電子藍調中的標準手法是讓樂團先醞釀情緒後中止演奏,留下歌手或主奏吉他手繼續唱奏,這種手法可見於史提夫.雷.范(Stevie Ray Vaughan)的歌曲〈驕傲與快樂〉(Pride and Joy)、貓王的〈獵犬〉(Hound Dog),或者歐曼兄弟樂團(Allman Brothers)的〈別無他路〉(One Way Out)。電子藍調歌曲典型的結尾也是一例,曲子以穩定的拍子進行二至三分鐘,然後⋯⋯重重一擊!當和弦暗示著樂曲即將結束,樂團卻開始用原先的一半速度演奏。還有雙重打擊。清水樂團在〈看好我的後門〉(Lookin' Out My Back Door)的結尾逐漸放慢速度(這在當時已是常見手法),然後顛覆我們的預期,拉回原本的速度演奏真正的結尾。
警察合唱團也以顛覆節奏預期而聞名。搖滾樂標準的節奏模式是強拍落在第一和第三拍(即低音鼓的落點),小鼓則敲在第二和第四拍(反拍)。雷鬼音樂聽來速度彷彿只有搖滾樂的一半(巴布.馬利的音樂是最明顯的例子),因為低音鼓和小鼓在樂句中的敲擊次數只有搖滾樂的一半。雷鬼音樂的基本拍子是吉他彈在「上拍」(或稱弱拍),也就是說,吉他彈在主要拍子之間的空檔,例如:1 AND-A 2 AND 3 AND-A 4 AND 。這種「只有一半速度」的感覺,使得雷鬼音樂表現出慵懶的特質,然而弱拍則傳遞一種動感,將音樂往前推進。警察樂團結合雷鬼音樂與搖滾樂,創造出一種新曲風,既顛覆也滿足我們對節奏的某些預期。主唱史汀經常以嶄新的方式彈奏貝斯,避開搖滾樂總是彈在強拍或與低音鼓同拍的慣用手法。正如頂尖錄音室貝斯手蘭迪.傑克森(Randy Jackson)所告訴我的(我們曾於一九八○年代共用錄音室的辦公室),史汀的貝斯聲線與眾不同,甚至無法用於任何其他人的歌曲中。警察樂團的專輯《機器裡的幽靈》(Ghost in the Machine)中一首〈物質世界裡的幽魂〉(Spirits in the Material World),便將其獨特的節奏手法發揮得淋漓盡致,聽者幾乎無法分辨曲中的強拍落在何處。
荀白克等現代音樂作曲家同樣將預期拋諸腦後。他們所用的音階完全剝除我們對和弦中的解決與根音以及音樂的「家」(home)的概念,製造出沒有家的錯覺,產生一種漂流無依的音樂,也許這正是二十世紀存在主義式的隱喻(又或許只是想標新立異)。如今我們仍可在電影配樂聽到這類音階,用來搭配夢境一般的場景,襯托劇中人漂浮無依、潛入水中或身處太空失重狀態的情境。
第五章 我們如何分類音樂? 你知道我的名字, 自己去查號碼吧(摘錄)
我對音樂最早的記憶來自三歲時,我的母親彈著家中的平台式鋼琴,我則躺在鋼琴下一塊毛茸茸的綠色羊毛地毯上。平台式鋼琴就在我頭上,只見母親的腿不斷上下踩著踏板,我彷彿被鋼琴的聲音淹沒。琴音充塞四面八方,那振動穿透地板和我的身體,我感覺低音就在身體右方,高音則在左方。貝多芬的和弦響亮而緊密;蕭邦的音符如雜耍般舞動,如風雪吹拂;舒曼的節奏嚴整如行軍,他和母親同樣是德國人──這一切構成我對音樂最早的記憶,那聲音令我完全入迷,將我帶往未曾體驗的感官世界。當音樂持續演奏,時間彷彿靜止。
音樂的記憶與其他記憶有何不同?為何音樂似乎能觸動深藏心底或已然流逝的回憶?音樂的預期如何使我們體驗音樂中的情感?我們又是如何認出以往聽過的歌曲?辨認曲調牽涉不少複雜的神經運算,並且與記憶息息相關。當我們專注於樂曲中多次演奏都未曾改變的特徵時,大腦則須忽略其他某些特徵,如此才能擷取出歌曲中不變的特質。也就是說,大腦的運算系統必須將歌曲的各個部分獨立開來,留下每次聆聽經驗中相同的部分,剔除每次都有所變化的部分,或某次的獨特詮釋。如果大腦不這麼做,只要一首歌以不同音量播放,你就會以為自己聽到的是一首全新的歌!而音量並非唯一即使大幅度改變也不影響我們辨識歌曲的參數。演奏用的樂器、速度和音高也都不影響歌曲的辨識基準。也就是說,在擷取能夠辨識歌曲的特徵時,這類特徵即使有任何變化,我們也都不予理會。
辨識歌曲大幅增加了神經系統處理音樂的複雜性。從各種變化中擷取歌曲不變的特徵,可說是件浩大的運算工程。一九九○年代末期,我曾在一家網路公司工作,該公司正在發展辨識MP3 檔案的軟體。很多人的電腦都存有聲音檔,但那些檔案往往不是檔名錯誤,就是根本沒有檔名。沒有人願意逐一檢查所有檔案、修正像「Etlon John」這樣的拼字錯誤,或者把艾維斯.卡斯提洛(Elvis Costello)的〈我是認真的〉(My Aim Is True)更名為〈艾莉森〉(Alison,「我是認真的」是副歌中一句歌詞,而非歌名)。
自動命名的問題其實不難解決,因為每首歌都有數位指紋,我們只須學會如何在包含五十萬首歌曲的資料庫中有效率地搜尋,以正確地指認歌曲。電腦科學家稱之為「查找表」(lookup table)。當你查詢社會安全號碼資料庫時,輸入你的名字和出生日期,資料庫應該只會顯示一組社會安全號碼。同樣地,查詢歌曲資料庫時,輸入某首歌的某個特定版本之數位值,應該只會得到一首相應的歌曲。查找程式看似運作得完美無瑕,但還是有其限制,它無法找出資料庫中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假設我的硬碟內存有八種版本的〈沙人〉(Mr. Sandman),當我輸入吉他大師查特.亞金斯(Chet Atkins)的演奏,並要求程式依此找出電吉他手吉姆.坎皮隆戈(Jim Campilongo),或和聲女音四重唱(The Chordettes)演唱的版本時,電腦就無法做到了。這是因為MP3 檔案開頭的數值串需經過轉譯才會成為旋律、節奏或響度等要素,而我們還不知道如何進行轉譯。查找程式必須能夠辨識相對不變的旋律與節奏,並忽略因不同表演而生的差異,才可能建立版本的連結。以目前的電腦設備,連起步都有困難,而人腦卻能輕鬆地做到這點。
電腦和人腦在這方面有不同的能力,正與我們對人類記憶的本質與功能所進行的討論有關。近來針對音樂記憶所做的實驗,恰好為釐清真相提供了確切的線索。過去一百多年來,記憶理論學者激烈地爭辯著:人與動物的記憶是相對的,抑或絕對的?主張相對的學派認為,我們的記憶系統儲存的是事物與想法之間的關係,無需記住事物本身的細節。這派論點也稱為構成主義觀點,意指即使缺乏感知細節,我們依然能根據感知之間的關係,立即自行填補或重建細節,建構對現實的記憶表徵。構成主義者認為記憶的功能是忽略不相關的細節,只保留「要點」。與之相對的是「紀錄保存理論」(record-keeping theory),其擁護者認為記憶就像錄音機或數位錄影機,精確記錄我們的全數或多數體驗,並以近乎完美的水準忠實再現。音樂也是論辯主題之一,因為如同一百多年前的完形心理學家所言,旋律是由音高之間的關係所決定(這是構成主義觀點),卻也由確切的音高所組成(這是紀錄保存觀點,但前提是音高會儲存在記憶裡)。兩派論點都累積了大量的證據。持構成主義觀點的實驗研究者請受試者聆聽講詞(聽覺記憶)或閱讀文章(視覺記憶),然後說出他們聽到或讀到些什麼。一般來說,人們不太能逐字重述內容,他們能記住大意,但記不住特定的用詞。
許多研究也指出記憶具有可塑性。小小的干擾也可能會對記憶提取造成重大影響。華盛頓大學的伊莉莎白.羅夫塔斯(Elizabeth F. Loftus)做了一系列重要研究,她對法庭上證人講述證詞的精確度非常感興趣。羅夫塔斯讓受試者觀看錄影帶,然後針對影片內容提出誘導式的提問。當錄影帶中兩輛汽車幾乎發生擦撞時,她會問一組受試者:「兩車發生擦撞時,雙方車速多少?」
然後問另一組受試者:「兩車猛烈撞擊時,雙方車速多少?」結果光是用詞上的差異,就讓兩組受試者估計的車速相差十萬八千里。接著,羅夫塔斯會在一段時間之後(有時長達一星期之久),再次邀請受試者來到實驗室,然後問他們:「你看見幾片玻璃破裂?」(事實上沒有任何玻璃破裂。)當時接收到「猛烈撞擊」字眼的受試者,有較高比例的人「記得」影片中有玻璃破裂。這群受試者其實是根據一週前的提問,重新建構了自己的記憶。
第三章 簾幕之後 音樂與心智機器(摘錄)
人類的大腦分為四葉,分別是額葉、顳葉、頂葉和枕葉,外加小腦。我們可對這些部位的功能做粗略的歸納,但事實上,人的行為是很複雜的,無法輕易化約成簡單的分布圖。額葉與規畫能力及自制有關,也具有從感覺系統接收的龐雜訊號中抽繹意義的能力,這正是完形心理學家所說的知覺組織(perceptual organization)。顳葉與聽覺和記憶有關,額葉後區與運動能力有關,枕葉則與視覺有關。小腦與情緒和整體動作協調有關,許多動物(例如爬行類)缺少功能較高級的大腦皮質,但都有小腦。切下額葉內的...
作者序
前言
我愛音樂,也愛科學──但為何要將兩者結合在一起?
我愛科學,而想到有這麼多人害怕科學,或認為選擇科學就代表不能保有同情心、感受藝術或敬畏大自然,便讓我覺得痛苦。科學的意義不在於驅除一切神祕,而是重新創造、活絡神祕的面貌。──摘自《為什麼斑馬不會得胃潰瘍?》,薩波斯基著
一九六九年夏天,當時我十一歲,在住家附近的音響店買了一套音響設備,總價約一百美元。那是我在春天以時薪七十五美分的代價幫鄰居割草賺來的。自此之後,每天下午我都在房間內待上長長的時間,聆聽一張又一張唱片:奶油樂團(Cream)、滾石樂團、芝加哥樂團、賽門與葛芬柯(Simon and Garfunkel)、法國作曲家比才、俄國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爵士鋼琴家喬治.雪林(George Shearing),以及薩克斯風樂手布茲.藍道夫(Boots Randolph)。我沒有將音樂放得特別大聲(至少不像大學時代那樣,將音量開得太大,竟讓喇叭起火燃燒),但當時的音量顯然已吵到我父母。我母親是小說家,每天窩在走廊盡處的小房間奮力寫作,晚餐前則會彈上一小時鋼琴;我父親則是生意人,每週工作八十小時,其中四十小時是晚上和週末在家中的辦公室完成。父親以生意人的口吻向我提出協議:他願意買副耳機給我,只要我答應當他在家中時,聽音樂都得戴上耳機。從此以後,耳機改變了我聽音樂的方式。
當時我正在聆聽一些新崛起的音樂人,他們都開始初步嘗試立體聲混音效果。我花一百元買來的套裝式音響,性能不甚良好,直到戴上耳機之前,我都不曾聽出音樂裡的聲音層次,也就是空間內從左到右、自前至後的樂器配置(即回響)。對我而言,唱片不再只是一首首歌曲,更包含了各種聲音。耳機開啟了一個充滿聲音色彩的世界,彷彿布滿微妙聲音細節的調色盤,超越了和弦、旋律、歌詞或某位歌手的歌聲。無論是清水合唱團(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以美國南方軟膩唱腔吟出的〈綠河〉(Green River)、披頭四樂團充滿田園牧歌空靈美感的〈慈母之子〉(Mother Nature's Son),或是貝多芬第六號交響曲(由卡拉揚指揮)的雙簧管樂音在木石教堂的廣大空間內低吟迴盪,種種聲音將我團團包圍。戴上耳機時,音樂彷彿突然從我腦中冒出,而非來自外界,像是我個人所獨有。就是這種個人的連結感,最終使我成為錄音師與製作人。
多年後,歌手保羅.賽門(Paul Simon)告訴我,聲音是他永恆追尋的目標。「我聽自己的唱片,都是為了聆聽聲音。不是為了和弦,也不是為了歌詞。我得到的第一印象,必然是整體的聲音。」
大學宿舍內的喇叭起火事件後,我決定休學,加入搖滾樂團。我們唱得還不錯,有幸到加州某間擁有二十四軌錄音設備的錄音室錄音,錄音師是才華洋溢的馬克.尼德罕(Mark Needham),他後來參與了一些暢銷專輯的錄音,包括藍調歌手克里斯.艾塞克(Chris Isaak)、蛋糕樂團(Cake)和佛利伍麥克樂團(Fleetwood Mac)。馬克很喜歡我,可能因為只有我有興趣進控制室聆聽錄音結果,而其他人只想在兩次錄音之間保持亢奮。馬克視我為樂團的製作人,雖然當時我並不知道製作人要做什麼。他問我,我們希望樂團呈現什麼樣的風格。他讓我了解麥克風能讓聲音產生多大的區別,放在不同位置又會有何等影響。剛開始,我其實無法完全聽出他所說的差異,但他告訴我該聽些什麼。「注意聽,當我讓這支麥克風靠近吉他的音箱,聲音聽起來會比較飽滿、圓潤、平均。若兩者距離較遠,麥克風會收到房間裡的一些聲音,變得比較有空間感,不過這樣會喪失一些中頻。」
我們樂團在舊金山漸漸打開知名度,當地搖滾電台也播放我們的音樂。樂團解散後(因為吉他手不時鬧自殺,主唱則有吸笑氣和用剃刀自殘的惡習),我開始擔任其他樂團的製作人。我學習聆聽一些過去從未注意的部分,像是不同麥克風甚至不同品牌錄音帶所造成的差異,例如Ampex 456盤帶在低頻範圍有種特別的「碰碰」聲,Scotch 250的高頻特別輕脆,而Agfa 467的中頻部分很亮。知道該聽些什麼後,我能輕易分辨用Ampex、Scotch或Agfa盤帶錄製的音樂,就像分辨蘋果、梨子和橘子一樣簡單。我也進一步和其他優秀錄音師一起工作,例如蕾絲莉.安.瓊斯( Leslie Ann Jones,曾與法蘭克辛納屈和巴比.麥克菲林合作)、弗瑞德.卡特羅(Fred Catero,曾與芝加哥合唱團以及珍妮絲.賈普林合作),還有傑佛瑞.諾曼(Jeffrey Norman,曾與約翰.佛格堤以及死之華樂團合作)。雖然我是製作人(也就是負責錄音大小事的人),卻依然為這些人的風采所折服。有些錄音師會讓我進錄音間和大牌音樂人坐在一起,像是紅心樂團(Heart)、旅行者樂團(Journey)、山塔那(Santana)、惠妮休斯頓和艾瑞莎.弗蘭克林。看著那些錄音師和音樂人互動、談論某段吉他演奏所表現的細微差異、某段唱腔表達得如何等等,我終生受用無窮。他們會討論一句歌詞的某些音節,然後從十段不同的錄音中選出一種,展現出驚人的聽力。他們究竟是如何訓練自己的耳朵,才能聽出一般人無法分辨的差異?
當時我也和一些沒沒無聞的小型樂團合作,認識了不少錄音室經理和錄音師,他們帶領我逐步精進工作技巧。有一天,一位錄音師沒來,我就幫山塔納剪輯錄音磁帶;另一次,在藍牡蠣樂團(Blue Öyster Cult)的製作期間,傑出製作人皮爾曼(Sandy Pearlman)外出吃午餐,留我一人處理完合聲部分。就這樣,案子接踵而至,結果我在加州製作了十年的唱片,也有幸和許多知名音樂家共事。我也曾和不少籍籍無名的音樂人一起工作,他們才華洋溢,只是終究未能成名。這讓我感到很好奇,為何有些音樂人變得家喻戶曉,其他人卻埋沒終生?我也想知道,為何音樂對某些人來說輕而易舉,對其他人則否?創造力從何而來?為何有些歌曲令人感動,有些卻難以親近?此外,傑出音樂人和錄音師擁有神奇的能力,可以聽出音色的細微差異,而大多數人卻沒有,人的感知能力在聽覺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
這些問題促使我回到學校尋找答案。當我仍在擔任唱片製作人時,每週會和皮爾曼開車到史丹佛大學二次,聆聽心理學教授卡爾.皮布姆(Karl Pribram)的神經心理學講座,我發現心理學恰能解答我心中不少疑問,這些問題包括記憶、知覺、創造力,以及造就這一切能力的共同來源:大腦。然而問題還沒找到解答,卻衍生了更多問題,這是研究科學常有的情形。每個新問題都開啟了內心的一扇窗,讓我更能欣賞音樂與整個世界,乃至人類經驗的複雜性。正如哲學家保羅.丘奇蘭(Paul Churchland)所言,人類努力透過歷史紀錄來了解這世界。過去短短兩百年間,我們的好奇心揭露了大自然隱藏的諸多祕密,像是時空的脈絡、物質的組成、能量的多種形式、宇宙的起源、DNA隱含的生命本質,甚至完成了人類基因組圖譜。然而有個謎團尚未解開,即人類大腦的奧祕,以及大腦如何產生思想、感覺、希望、欲望、愛和美的感受,甚至舞蹈、視覺藝術、文學和音樂。
****
音樂是什麼?從何而來?為何某些連串的聲響令人深深感動,而其他聲響(例如狗吠或汽車噪音)卻令人感到不快?對某些研究者而言,這類問題占據了研究生涯的極大部分;其他人則認為,以這種方式來解析音樂,豈不像是解析哥雅畫作的化學成分,而不去欣賞其努力創造的藝術?牛津大學歷史學家馬丁.坎普(Martin Kemp)指出藝術家和科學家的相似性:多數藝術家描述自己的作品時,聽起來就像在描述科學實驗──他們透過一系列嘗試,探討大眾關切的某項議題,或建立某種觀點。我的好友兼同行威廉.湯普森(William Forde Thompson)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音樂認知科學家兼作曲家,他也指出,科學家和藝術家的工作有相似的進展:先是創造與探索的「腦力激盪」階段,接著是測試和逐步推敲,通常這時會應用固定的工作程序,但有時也會發現更富創造力的方法而能解決問題。藝術家的工作室和科學家的實驗室也有諸多相似之處,例如一口氣進行許多計畫,且計畫都處於不同階段。兩者都需要專業器材,並把成果開放給各方去詮釋,而不像建築吊橋那樣會有個最終定案,或者銀行帳戶必須於營業日結束時結算金額。藝術家和科學家還具備一種共同的能力:能夠接受隨時有人對自己的作品提出詮釋及再詮釋。藝術家和科學家皆全心追求真理,但兩者都知道真理的核心本質是變動的,是有情境的,是取決於觀點的,因此今日的真理到了明日也可能會被證實為假說,或變成為人所忘的藝術品。只要看看幾位著名心理學家,如皮亞傑、佛洛伊德和史金納就知道,曾經席捲世界的理論,到頭來也會遭到推翻(或至少是嚴厲的重新評估)。音樂界有好幾個樂團太快受到肯定,例如廉價把戲樂團(Cheap Trick)曾被捧成新一代的披頭四,滾石雜誌出版的《搖滾百科全書》(The Rolling Stone Encyclopedia of Rock & Roll)給亞當和螞蟻樂團(Adam & The Ants)的篇幅就跟U2一樣多。有段時間人們也無法想像,有一天這世界將會遺忘保羅.史圖基 、克里斯多夫.克羅斯 和瑪麗.福特 。對藝術家來說,繪畫與作曲的目的並非表現狹義的真實,而是傳達普世的真理,因此只要作品成功,即使時代背景、社會與文化有所改變,依然能夠觸動人們的心靈。對科學家來說,建構理論的目標是傳遞「當下的真理」,以取代舊時的真理,而今日的真理有朝一日也將受「新的真理」所取代,因為科學就是以此方式向前推進。
音樂既無所不在,又非常古老,因此在人類活動中顯得異常突出。在任何有史可考的過去或現存的人類文化中,音樂都不曾缺席。我們在人類或原始人的考古遺址發現的器具中,有些最古老的製品便是樂器,例如骨笛,或以獸皮覆於樹樁上繃成皮鼓。只要有人類聚集的地方就有音樂,像是婚禮、葬禮、大學畢業典禮、行軍、體育盛事、城鎮夜間集會、祈禱、浪漫晚餐、母親輕搖嬰兒入睡、大學生一同念書時播放的音樂等。而比起現代西方社會,非工業化國家的文化更是充斥著音樂,無論過去或現在,音樂都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遲至大約五百年前,人類社會才出現「音樂演奏者」和「音樂聆聽者」的分類。放眼全世界與人類歷史,「生產音樂」本來就像呼吸、走路一樣自然,所有人都能參與,至於專供音樂表演的音樂廳,事實上直到近幾個世紀才出現。
我和人類學教授吉姆.佛格森(Jim Ferguson)從高中時代就相識,他聰明又幽默,卻非常害羞,真不知道他要如何授課。他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曾前往賴索托進行田野調查,那是一個非洲小國,被南非共和國四面包圍。佛格森在那裡做研究、與村民互動,也耐心贏得大家的信任,直到有一天他獲邀加入村民的吟唱。當索托族的村民邀請他一同歌唱時,他以一貫的溫和語氣說:「我不會唱歌。」這倒是真的,我們高中時代曾一起參加樂團,他很擅長吹雙簧管,卻是個走音大王。他的拒絕讓村民大惑不解,對他們來說,唱歌是再普通不過的日常活動,索托人不分男女老幼都會唱歌,這從來不是限定少數人參加的活動。
我們的文化及語言將專業表演者(像是鋼琴家魯賓斯坦、爵士女伶艾拉.費茲傑羅、歌手保羅.麥卡尼)歸為截然不同的另一類人。一般人付費聆聽專家表演,藉此得到娛樂。佛格森知道自己不擅長唱歌跳舞,對他來說,若在公眾面前唱歌跳舞,就表示他自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村民們盯著他看,說道:「你說不會唱歌是什麼意思?你會說話啊!」後來佛格森對我說:「對他們來說,那是很奇怪的,就好像我說我不會走路或跳舞,可是我明明就有兩條腿啊。」在索托人的生活中,唱歌跳舞是再自然不過的活動,渾然天成,任何人都可以從事。索托語指稱「唱歌」的動詞是「ho bina」,這個詞也表示跳舞,兩者之間沒有分別,而世界上有許多語言也都是如此,因為唱歌原本就包含肢體律動。
在好幾代以前,還沒有電視的時候,許多家庭經常圍坐一圈,彈奏音樂自娛。今日的人則十分強調技術與技巧,也在意某位音樂家是否「夠格」演奏給其他人聽。曾幾何時,在我們的文化中,音樂生產已成為專業活動,其他人只要負責聆賞就好。如今音樂工業已是美國最大型的產業之一,相關從業人員高達數十萬人,每年光是專輯銷售便帶來三百億美元,而這還不包括演唱會門票收入、每週五晚間數千個樂團在北美各地酒館、餐廳的演出,或者透過點對點傳輸免費下載的三百億首歌曲(以二○○五年為例)。美國人花在音樂上的錢多過性愛或處方藥,既然有這麼大量的消費,我敢說,大多數美國人已經夠格當專業的音樂欣賞者。多數人都能夠聽出走音、找到自己喜歡的音樂、記得數百首歌曲,也能跟隨音樂用腳打出正確的拍子,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能夠判斷節拍,過程非常複雜,連大多數電腦都做不到。那麼,我們為何聽音樂,又為何願意花這麼多錢聆聽音樂?兩張演唱會門票的價格往往相當於一個四口之家一星期的伙食費,一張CD的價錢也相當於一件T恤、八條土司或一個月的電話費。若能了解人們為何喜歡聽音樂,什麼原因使我們受到音樂吸引,就等於開啟了一扇窗,讓我們更加了解人類的天性。
****
對人類共同的基本能力提出疑問,就等於是間接對演化提出問題。為了適應所處的環境,動物會演化出某些構造形態,其中對求偶有利的特質會透過基因傳給下一代。
達爾文的演化理論有個很微妙的論點,即生物會與自然世界共同演化。換句話說,生物會因應這個世界而變,這世界也會因生物而發生改變。舉例來說,當某物種發展出某種機制來躲避特定的捕食者,捕食者便面臨了演化壓力,解決之道是發展出破解該種防禦機制的方法,或者另覓別種食物來源。自然界的天擇可說是一場軍備競賽,誰都想在身體形態的變化上趕上對方。
有個頗新的科學領域稱為「演化心理學」,將演化的想法從實體延伸至心理領域。我在史丹佛大學唸書時,曾受教於心理學家羅傑.薛帕(Roger Shepard),他便指出,我們的身體甚至心智,都是數百萬年演化的產物,舉凡思考模式、以特定方法解決問題的傾向,甚至感覺系統,例如看見顏色(及辨別特定顏色)的能力,全都透過演化而得來。薛帕德進一步延伸這個觀點:我們的心智會與自然界共同演化,會因應不斷變化的環境而改變。薛帕德有三名學生成為該領域的佼佼者,即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莉妲.科斯米蒂絲(Leda Cosmides)和約翰.托比(John Tooby),以及新墨西哥大學的傑佛瑞.米勒(Geoffrey Miller)。研究人員相信,研究心智演化的方式,有助於深入了解人類的行為模式。而音樂在人類演化與發展中,發揮了什麼樣的功能呢?可以肯定的是,五萬年、十萬年前的音樂,絕對與貝多芬、范海倫合唱團(Van Halen)或阿姆(Eminem)的音樂大不相同。大腦不斷演化,我們喜歡的音樂、想要聽到的音樂也隨之而變。那麼,我們的大腦是否有特定的區域或路徑,專門用來生產與聆聽音樂?
過去認為藝術和音樂都是由右腦來處理,語言和數學則由左腦負責,但這種簡化的想法已然過時,近來我的實驗室和其他同行的研究結果顯示,處理音樂的部位遍布整個大腦。我們透過腦部傷患的研究案例,發現有些病人失去閱讀報紙的能力,卻仍能聽懂音樂,或者有些人可以彈鋼琴,但缺乏扣鈕扣的動作協調能力。聆聽、演奏音樂和作曲則會使用到近乎我們所知的大腦全部區域,也幾乎與所有神經子系統有關。基於這項事實,我們是否可以說,聽音樂能夠鍛鍊心智的其他面向?每天花二十分鐘聽莫札特的音樂會不會使我們變聰明?
音樂能夠觸動我們的情緒,這份力量早已被廣告製作人、電影工作者、軍隊指揮官和母親運用得爐火純青。廣告商利用音樂,讓某個牌子的飲料、啤酒、慢跑鞋或汽車看起來比競爭對手更棒。導演用音樂告訴我們在某場可能會很曖昧的戲中該有什麼情緒,或加強我們對特定情節的感受。不妨想想某部動作片的經典追逐橋段,或者女演員在漆黑的老房子裡孤身攀爬樓梯的配樂──音樂被用來操控我們的情緒,而我們往往也接受這股力量,願意透過音樂去體會各種感受,即使不全然樂在其中。無論在多麼久遠的時代,世界各地的母親都能用輕柔的歌聲哄孩子入睡,或令孩子忘卻那些使他們哭泣的事物。
許多人愛好音樂,卻坦承自己對音樂一竅不通。我也發現,許多同事雖然研究的是神經化學或精神藥理學這類艱深複雜的主題,面對「音樂的神經科學」卻不知該如何著手,但沒人能怪他們,因為音樂理論家制訂了一堆神祕難解、難以捉摸的術語和規則,幾乎和數學中最艱深的領域同樣晦澀。在一般人眼裡,音樂記譜法上的一堆豆芽菜,看來就和數學集合理論的記號沒兩樣,談到音調、節拍、轉調和移調,更是令人頭痛不已。
我的同事雖被這些「行話」搞得暈頭轉向,仍能說出自己喜歡的音樂類型。我的朋友諾曼.懷特(Norman White)是鼠類腦部海馬迴的世界權威,研究鼠類如何記住自己去過的地方。他也是重度的爵士音樂迷,講起喜愛的爵士樂手總是滔滔不絕。他能憑樂聲立即分辨出艾靈頓公爵和貝西伯爵,甚至分得出路易斯.阿姆斯壯早期與晚期的音樂。懷特對音樂技術一無所知,他能告訴我他喜歡哪首歌,但說不出歌曲所用的和弦名稱,不過他十分清楚自己喜歡什麼。當然,這並不罕見,對於自己喜好的事物,不少人都能掌握一些實用知識,且無需專業的技術知識,也能毫無阻礙地交流彼此的喜好。例如我常去一家餐廳,我知道自己很喜歡吃那裡的巧克力蛋糕,喜歡的程度遠超過住家附近咖啡店的同款蛋糕,然而只有廚師才會去分析蛋糕,詳細描述麵粉、起酥油以及巧克力的差異,將味道拆解成各種成分。
許多人都被音樂家、音樂理論家和認知科學家的行話搞得暈頭轉向,實在有點可惜。任何領域都有專業術語,你不妨試著請醫師向你解釋血液分析報告的全部內容。而就音樂這方面,其實音樂專家和科學家大可多用點心,讓他們做的事情更容易被理解,這正是我寫作此書的目的。事實上,不但「演奏音樂的人」和「聆聽音樂的人」之間出現了不自然的隔閡,就連「純粹愛好音樂的人」(以及喜歡談論音樂的人)和「研究音樂如何發揮作用的人」之間也有類似的鴻溝。
這些年來,我的學生經常向我吐露,他們熱愛生活與生命中的神祕事物,卻擔心學得太多會剝奪生活中的簡單樂趣。神經科學家薩波斯基的學生大概也曾向他表達相同的感受,其實我自己在一九七九年移居波士頓就讀伯克利音樂學院(Berklee College of Music)時也有同樣的焦慮:如果我以學術角度來研究、分析音樂,解開了箇中奧妙,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一旦擁有廣博的音樂知識,我會不會再也無法從中得到樂趣?
結果我依然能盡情享受音樂帶來的樂趣,就與當年那個用著廉價高傳真音響和耳機的我沒有兩樣。我對音樂與科學鑽研得愈多,這兩者就變得愈加迷人,我甚至更有能力欣賞音樂和科學界的真正傑出人士。經過這些年,我敢肯定地說,音樂和科學研究一樣,都是精采的大探險,為每天的生活帶來不同的驚奇。科學及音樂都持續給我驚喜和滿足,原來把兩者結合起來,結果也還不差嘛!
這本書談的是音樂的科學,從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切入(認知神經科學結合了心理學和神經學)。我會談到我與其他研究者的一些最新研究,牽涉的領域包括音樂、音樂的意義及音樂所帶來的樂趣。這些研究為一些深刻的問題闢出了嶄新的視野。舉例來說,假使每個人喜歡的音樂不同,為何某些音樂就是能打動多數人的心,如韓德爾的彌賽亞,或者唐.麥克林(Don Mclean)的〈梵谷之歌〉(Vincent [Starry Starry Night])?另一方面,如果我們都以相同方式聆聽音樂,為何人的愛好如此天差地別?為何某人偏愛莫札特,另一人卻獨鍾瑪丹娜?
近年來,由於神經科學出現突破性進展,心理學也發展出全新研究方法,包括新的腦部顯影技術、以藥物操控多巴胺和血清素等神經傳導物質分泌,加上從過去延續至今的科學研究,我們的心智已向我們透露許多奧祕。另有一些優異的進展較不為人所知,即我們已建立神經系統的運作模型。電腦科技持續變革,使我們逐漸了解腦部的運算系統,這是過去難以企及的成果。如今看來,語言似乎會在腦中形成確切的實體線路,就連意識也是從實體的系統中突現,不再籠罩於令人望而興嘆的迷霧中。然而,至今還沒有人能統合這些新研究,以闡述所有令人類著迷的事物中我所認為最美麗的一種:音樂。了解大腦如何理解音樂,能夠為我們解答人類本質中最難解的謎團,這也是我撰寫此書的目的。本書的目標讀者並非我的專家同事,而是一般大眾,所以我盡可能簡化各個主題,卻不至於過度簡化。本書提及的所有研究都經過同行審查,也曾刊登在學界認可的期刊上,詳細資料請見書末的注解。
透過理解音樂的本質與由來,我們得以更加認識自己的動機、恐懼、欲望、記憶,甚至了解「溝通」最廣義的形式。聆聽音樂是否是為了滿足身體的需求,就像人為了解飢而進食?或者比較類似觀看美麗的夕陽與接受背部按摩,能夠觸動腦中產生愉悅感受的系統?為何人們隨著年紀增長,似乎便愈發執著於固有的音樂品味,不再嘗試新的音樂類型?本書旨在探討大腦與音樂如何共同演化,讓音樂帶領我們認識大腦、讓大腦教導我們認識音樂,並結合兩者,使我們更加認識自己。
前言
我愛音樂,也愛科學──但為何要將兩者結合在一起?
我愛科學,而想到有這麼多人害怕科學,或認為選擇科學就代表不能保有同情心、感受藝術或敬畏大自然,便讓我覺得痛苦。科學的意義不在於驅除一切神祕,而是重新創造、活絡神祕的面貌。──摘自《為什麼斑馬不會得胃潰瘍?》,薩波斯基著
一九六九年夏天,當時我十一歲,在住家附近的音響店買了一套音響設備,總價約一百美元。那是我在春天以時薪七十五美分的代價幫鄰居割草賺來的。自此之後,每天下午我都在房間內待上長長的時間,聆聽一張又一張唱片:奶油樂團(Cream)、滾石樂...
目錄
序言 我愛音樂,也愛科學──但為何要將兩者結合在一起?
第一章 什麼是音樂? 從音高到音色
第二章 跟著音樂打拍子 認識節奏、音量與和聲
第三章 簾幕之後 音樂與心智機器
第四章 預期 我們對李斯特和路達克里斯有何預期?
第五章 我們如何分類音樂 You Know My Name, Look up The Number
第六章 音樂、情感及爬蟲類腦 偶然得見克里克
第七章 音樂家的條件 何謂音樂細胞
第八章 我們為何愛上某些音樂? My Favorite Things
第九章 音樂本能 演化排行榜第一名
附錄
序言 我愛音樂,也愛科學──但為何要將兩者結合在一起?
第一章 什麼是音樂? 從音高到音色
第二章 跟著音樂打拍子 認識節奏、音量與和聲
第三章 簾幕之後 音樂與心智機器
第四章 預期 我們對李斯特和路達克里斯有何預期?
第五章 我們如何分類音樂 You Know My Name, Look up The Number
第六章 音樂、情感及爬蟲類腦 偶然得見克里克
第七章 音樂家的條件 何謂音樂細胞
第八章 我們為何愛上某些音樂? My Favorite Things
第九章 音樂本能 演化排行榜第一名
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