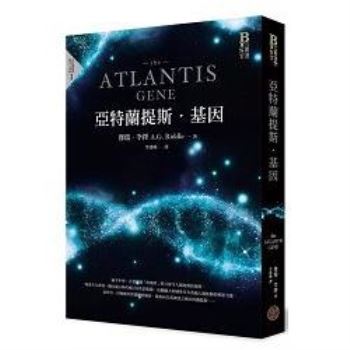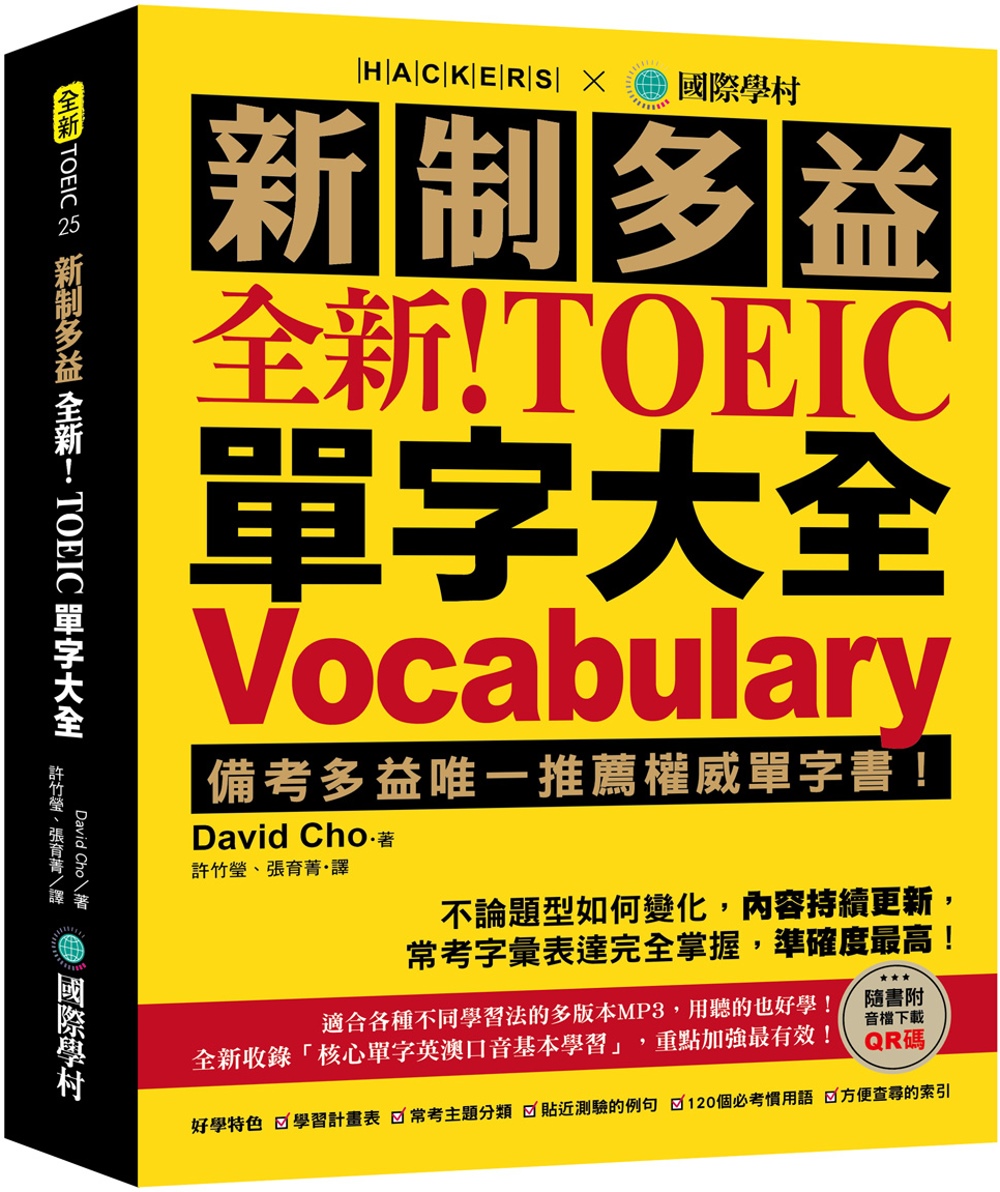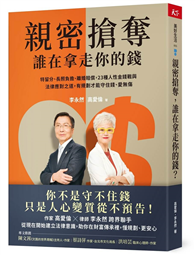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異鄉人(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5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336 |
文學小說 |
$ 379 |
中文書 |
$ 379 |
小說 |
$ 379 |
小說/文學 |
$ 422 |
奇幻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在監獄裡的夜晚,我就想到我愛妳的時候,妳發出的那些溫柔細微的聲音。這讓我感覺,黑暗中,妳就在我身邊。
她在兩段婚姻之間痛苦拉扯,
更在與他的身體發生劇烈、疼痛又歡愉衝撞之後,
發現了她未曾發現的真相。
他為了守護所愛之人亡命天涯,
而累累傷痕的背後,是龍騎士隊長的殘酷,
更是隊長祕而不宣的慾望。
當她有機會回到安全舒適的二十世紀,
她會選擇回去,還是留在戰火一觸即發的古蘇格蘭,共度危難?
當他被迫在愛情和屈辱之間擇一
他會放棄一切來守護她,還是誓死保有自我和家族名譽?
作者簡介
1988年,黛安娜‧蓋伯頓(Diana Gabaldon)為了「練習」,而開始寫小說。不料一寫就寫出RITA年度最佳小說作家獎、浪漫時代生涯成就獎(Romantic Times Career Achievement Award)、「鵝毛筆獎」(科幻/奇幻/驚悚類),寫出這套全球長銷二十年不墜,在美、英、加、澳、德多國名列暢銷冠軍的《Outlander異鄉人》系列。
《Outlander異鄉人》系列的成就,還在於跨足奇幻、推理、愛情、羅曼史、歷史,在各領域都獲得極高評價。從《Outlander異鄉人》系列中「約翰伯爵」一角延伸而出的歷史推理小說系列,如今也已出版九本。
《Outlander異鄉人》這部以20及18世紀蘇格蘭高地為背景的歷史愛情奇書,以細膩的人物刻劃、獨到的幽默感擄獲全球讀者的心。書中翔實的歷史細節不禁會使你以為是出自托爾金的手筆,而細膩的人物心理描寫也可媲美娥蘇拉.勒瑰恩。
黛安娜‧蓋伯頓確實學識淵博,感情也如筆下人物細膩,但她的另一個身分在愛情小說一片家庭主婦作者中絕對屬於異數:她是北亞利桑那大學海洋生態學博士與榮譽人文學博士,曾在大學教授解剖學,更是多本科技、電腦期刊的撰稿、評論人。
蓋伯頓的寫作熱情與她筆下建構的蘇格蘭高地傳奇,在全球奇幻、羅曼史論壇已持續發光二十年,中文讀者現在認識她也還不晚。
譯者簡介
郭虹均
台大外文系畢業,就讀師大翻譯所,現為譯者。
第一次翻譯羅曼史,就顛覆了我對羅曼史的既定印象;故事中元素混雜,傳統與現代思維並陳,男性與女性角色不時出現衝撞和置換。翻譯過程中,豐富的語言和文化的內涵是極大挑戰,也是極大享受。還有許多讓人不禁屏氣凝神和頭皮發麻的情節,更使得這場翻譯之旅高潮迭起。有幸和主角一起穿越時空、漫遊高地,完成一場愛的冒險,愉快之至。
歡迎來信指教:k.hungchu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