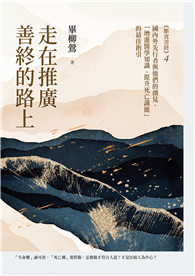◎紅袖添香「第二屆華語言情小說」決賽入圍作品!
◎「古代言情婉約派掌門人」三月暮雪傾情奉獻!
◎看溫柔小女人如何征服兩位王者的心靈,顛覆兩個國家的命運!
◎本書姐妹作《胭脂絕代之 ~ 禁宮柳》將在近期上市!
與生俱來生就的一雙娉婷小足,彷彿是龔穿針注定的宿命!
她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雙溫潤白玉似的小腳也走不快,
不僅家人不見容於她,就連未婚夫家也嫌棄她,早早退了婚!
直到在廟會上,穿針邂逅了俊朗卻神祕的白衣公子夜秋睿,
兩人不但因同拜佛前結緣,他更在她遇險時挺身相救,
那一瞬間的溫暖,讓她對他難以忘懷。
但讓穿針意想不到的是,因為長了一雙與離世王妃一樣的小足,
皇帝竟欽點她入晉王府,作為侍奉王爺蕭彥的侍姬!
這個孑然不同的新身分,硬生生斬斷了穿針的一切念想,
她自此淡漠如水,亟欲忘了從前種種,只求安身立命!
只是妃子們的挑釁、晉王的冷絕、王府裡避諱不談的離世王妃,
這一切就像謎團,一再撩撥起穿針好不容易平靜下來的心。
而此時,夜秋睿竟也因夜探王府,意外負傷逃進了她的房中!
穿針沒料到兩人竟還能重逢,但他,是為了什麼而來?……
作者簡介
三月暮雪
生於陽春三月,江南名城寧波人。古言婉約派掌門,清新系人氣作家。盛大文學十二釵之一。平素喜讀旖旎字眼,相信用溫婉的筆觸能夠書寫一處心靈的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