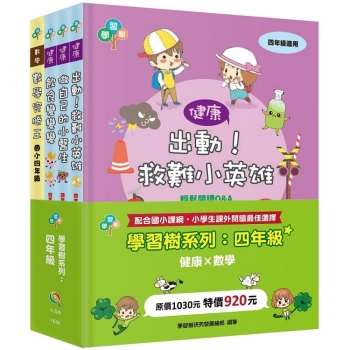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紅袖添香「第二屆華語言情小說」決賽入圍作品!
◎「古代言情婉約派掌門人」三月暮雪傾情奉獻!
◎看溫柔小女人如何征服兩位王者的心靈,顛覆兩個國家的命運!
◎本書姐妹作《胭脂絕代之 ~ 禁宮柳》將在近期上市!
初入晉王府生活,種種猜忌、冷漠不只讓穿針疲於應付,
妹妹引線對她的敵意與對晉王若有似無的媚惑挑勾,
也將穿針推入了更痛苦的無邊深淵!
還記得錦褥床榻前,晉王褪去了冷漠,溫柔得讓她心動,
還記得他眼裡殘留的痛楚,脆弱得讓她心疼,
穿針一步步陷進晉王為她編織的情愛裡,但為何一轉眼,
映入他眼中的,卻是引線巧笑倩兮的絕色容顏?
忽略掉心頭的那股酸澀,穿針將心思全放在夜秋睿身上,
因她承諾過,會幫忙尋找他落在王府裡的一塊家傳玉帛!
但玉帛還沒找著,引線卻在此時傳出了有孕的消息!
引線淚眼婆娑,不願說出與她歡好的男人究竟是誰,
可所有證據卻都讓穿針不得不相信,晉王是唯一的可能!
心痛到極致,能夠更痛嗎?她交付出的真心,又還能收回嗎?……
作者簡介
三月暮雪
生於陽春三月,江南名城寧波人。古言婉約派掌門,清新系人氣作家。盛大文學十二釵之一。平素喜讀旖旎字眼,相信用溫婉的筆觸能夠書寫一處心靈的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