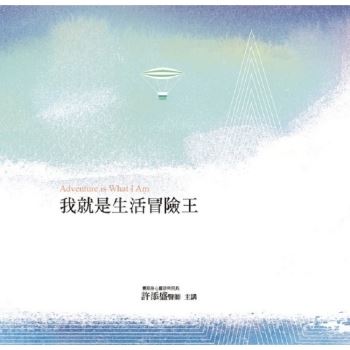楔子
一輪明月如鏡,高懸中天。
庭下空明,花影幽幽,唯聞隱約蟲語,若斷若續。
靜得不能再靜的夜。
一陣微風掠過,一團黑影如驚鴻一現,瞬即消逝。
大宅中的一間房,忽然亮起了燈。
「誰?」睜開惺忪睡眼的老爺,以手遮眼,不勝厭煩地問。
「勾魂使者。」
簡單的四個字從唇齒間擠出,語調雖然平平,卻冷入骨髓,令人戰慄。
老爺一驚,睡意全消,忽然雙眼劇痛,仰倒在床。兩條血線自他眼中緩緩流下。
又一陣風起,吹動了大門上的紅燈籠,兩個「郭」字在黑夜中輕輕搖晃。
第一章
花海蝶舞,柳浪鶯啼,正是江南好風光。
一幢茅草小屋坐落在清溪畔,碧山前,山明水秀,清幽怡人。不過,這是此地夜半才有的景象。這半個月來,草屋四周總是人聲雜沓,絡繹不絕的人潮把這兒弄得像市集似的。
「余大嬸,您的腰痛好點兒了嗎?」
「張爺爺,您的眼睛有沒有改善?」
「王婆婆,您的膝蓋有方便一些嗎?」
「小柱子,你的腿還是要多休息,不要到處跑來跑去。」
……
清脆的話聲不時從草屋中傳出,光聽聲音就可知道,這是間醫館;而且,是間簡陋的醫館;而且,還是間沒掛牌的簡陋醫館。
一間沒掛牌的簡陋醫館能弄得門庭若市,大概也印證了「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這句話吧!
不過,醫館的主持人可不是什麼享譽杏林的大師,也不是什麼活人無數的神醫;相反的,醫館的主持人是個才十七歲的小姑娘,名叫姚清繡。
雖然每天上門求醫的人從來沒少過,可是,連姚清繡自己都搞不清楚怎麼會弄到今天的局面。
她不過是在大街閒逛的時候,以幾根針幫一位常年不良於行的老婆婆暫時站立起來,她就成了眾人口中的「神醫」。
雖然助人為快樂之本,但弄到自己連正事都得丟在一旁,恐怕師父知道了也會頭痛。
可是,她就是沒辦法拒絕那些上門求助的人啊!
而且,最近她又多了一個新的頭銜,叫「神繡姑娘」,這又是那些好心的村民幫她取的名號。她不過是繡了一些小東西,送給那些害怕針灸的小朋友,她就又多了這個響亮的名號。
雖然在她心中,「神繡」只有她師父當得,不過打出「神繡」的名號,對她將做的事也許有些幫助吧!
這天她一如既往,開始她的密醫生涯。未料開張不久,小屋就湧進幾個壯漢。
這些人各個身強體壯,身穿同一服色,看來不像是有病痛的樣子。這些人一到,原來屋裡屋外滿滿的人群全都一哄而散。
「怎麼回事啊?」她連忙抓住一個大嬸問。
「官差呀!」說完,就忙不迭地逃跑了。就連原來不良於行的老人,跟著大人前來玩耍的孩童,連同屋前屋後的飛禽走獸,全都走了個精光。
忽然之間,整座茅屋裡就只剩下她一個人。
「會不會太誇張啦?」她自言自語。「哪來的凶神惡煞?」
姚清繡正疑惑間,幾名壯漢忽然自動分站成兩排,一人越眾而出,直接走到她面前,將一塊牌子亮在她眼前。
「江南郡衙卓翊,奉令查案。」
姚清繡大眼圓睜,死死地盯著看,不過她看的不是那塊牌子,而是這位姓卓的男子的臉。
「哇!長得真好……」幾乎到目不轉睛的程度。
「大膽,竟敢死盯著總捕頭看,卓大是有名的鐵面神捕,妳這女嫌犯等下就會知道他的厲害。」一名捕快喝道。
「鐵面神捕?我看該叫玉面神捕才對。」姚清繡自言自語,忽然──「等一下,你說女嫌犯?」姚清繡這才回過神來。無牌行醫要被抓嗎?那她一定立刻認錯。
難怪他們一來,滿屋求診的人都走得乾乾淨淨,姚清繡暗中祈禱,希望村民們能跑快一點,不要被她連累。雖然她是義診,但她不希望村民因為貪小便宜這小小的人性弱點就吃上牢飯。
「程亮,不要嚇到姚姑娘。」卓翊走了過來。話聲雖溫和,臉上卻無笑意。
「姚姑娘,」卓翊開口道,「在下有幾個問題想請教。」
「請說,卓──嗯……大哥?」
姚清繡努力在腦中搜索適當詞彙來稱呼眼前的男人,他絕對不是「大叔」、「爺爺」之輩的,那她想得到的只有「大哥」,誰教她過去的生活中,從來沒有這一類人出現?
「不要亂攀關係!」程亮又氣急敗壞地叫:「叫『大人』!」
卓翊只回頭看了程亮一眼,程亮就噤了聲,不過臉上猶有餘忿。
「姚姑娘,」卓翊開口道,「請問妳是何時來到清水縣的?」
「大約一個月前。」姚清繡邊答,邊望著卓翊「漂亮」的臉,從眉到眼到鼻到唇,用眼睛將他勾勒了個遍。長得真好!她在心中連連讚賞。
「敢問姑娘為何來到清水縣?」
「因為有事。」卓翊的問題將她拉回了現實,她忙收斂心神,這才發現這個重要的問題,自己偏答得含糊之至。
「敢問何事?」
「私事。」這兩個字她說得極小聲,幾乎是在囁嚅,她只希望卓大人別再追問,她不擅說謊啊!
女嫌犯明顯不合作的態度,幾乎要引起公憤,姚清繡從眾捕快眼中看得出來。如果不是卓翊在,只怕他們要將她生吞活剝了。
「卓……大人,」這兩個字叫得極不順口,姚清繡試著習慣。「你可不可以先告訴我,我到底身犯何案?是因為我替人看病嗎?」
卓翊一聲冷笑,轉身不答,換上一名捕快,「江南郡副總捕丁春山……」
突見副總捕那張黝黑的面龐,沉浸在卓翊丰采中的姚清繡忽然清醒過來,這才發現自己剛才有些昏頭昏腦的。其實副總捕不醜,堪稱英氣逼人,可是接在卓翊之後出場,難免吃了點虧。姚清繡暗暗替他可惜。
「前天夜裡清水縣富商郭進寶被殺之時,妳在哪裡?」
「我大約戌時就寢,所以應該是在床上。」姚清繡想了想回道。
「為何說『應該』?」丁春山逼問。
「說『應該』,是因為我每晚都是上了床睡的,可是醒來後卻常常在床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何時滾下床的。所以你說的那個時辰,我實在也不清楚我是在床上還是在床下。」姚清繡有些不好意思。
眾捕快面面相覷。
丁春山又道:「所以妳的意思是說,妳在睡覺?」
「是。」這次答得很肯定。
「有證人嗎?」
「沒有。」姚清繡想了想,「不過如果有證人,那才奇怪啊!不是顯得處心積慮了嗎?」
這小姑娘倒也不笨。丁春山又問:「妳一個女孩子住在這荒山野嶺中,不會害怕嗎?」
「不會啊!我以前一直住在山上,從小就習慣了。而且這兒環境清幽,免繳房錢,山光水色看不盡……」
「妳到清水縣來,不會只為了欣賞山光水色吧?」丁春山忍住「藝高人膽大」這句話。
「不然呢?副總捕的意思是?」
「這是妳繡的吧?」丁春山拿出一塊白色方巾,方巾的左下角繡有一隻小狗,繡工精緻,狗毛色澤隨著光影變幻,乍看就像活的一般。
「啊!這是我送給小柱子的,」姚清繡接過帕子,說道:「小柱子的小黃狗被馬車撞了,小柱子也傷了腿,不能走動,我答應他,他若乖乖休息,就送他隻新的小黃狗。」摸了摸狗的舌頭,「可惜前幾天絳色絲線供貨不全,只買得到三種紅色,不然小黃的舌頭也能靈活些。」
眾捕快暗暗驚異,這塊被視為間接證物的方巾,他們都看過,當時就對精巧的繡工嘖嘖稱奇,沒想到這小姑娘竟還覺得不滿意。
「所以,村民口中的『神繡姑娘』,指的就是妳了?」
「那是大家抬愛,我要學的還多著呢!」說到這兒,不禁眼望卓翊,心想造物神奇,創造出這般人物,即使自己再勤勉,也終難奪天工,不禁嘆了一口氣。
「針灸、刺繡,與針有關的妳都在行,是嗎?」
「應該是吧!」這麼說有點自誇,不過如果否認,可有點對不起師父。師父的絕技,她就只學了這麼兩樣啊!
「那麼,妳就施展一下放飛針的功夫,讓大家開開眼界吧!」
丁春山話聲一落,幾名捕快立時分散,將姚清繡圍在中心。
聽聞「飛針」二字,姚清繡面色一變,雖然只是一瞬間,這細微的變化已入了卓翊的眼。
只聽姚清繡道:「我會飛針技法,但不會放飛針……」
話聲未畢,卓翊已欺進,姚清繡右肩甫動,卓翊已按住她右掌,姚清繡只覺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向自己推來,胸口氣血翻湧,心想莫非今日將斃命於此?師父的慈愛、教誨、期望霎時閃過腦中。
不過只一瞬,那股力量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原來卓翊已撤回掌力,抱拳道:「得罪了。」
姚清繡立足不穩,差點摔倒,卓翊扶住她,從腰間取出一只藥瓶,傾出一顆藥丸。
「快服下,我幫妳推宮過血。」
「不要。」剛剛他害自己起了「死」的念頭,姚清繡還沒原諒他,不願受他恩惠。她取出針包攤開,拿出一根銀針,伸出手臂,往郄門穴扎下。這一針又快又準。
眾捕快又是面面相覷,眼望卓翊,卓翊以目示意,大家臉上都有訕訕之色。
姚清繡當著眾捕快的面不給卓翊面子,尤其令卓翊尷尬。因為怕她傷及弟兄,卓翊才親自出手相試,沒想到她竟如此不堪一擊,這也間接證實她不是郭進寶一案的兇手。
要將細小的金針擲入雙眼,直沒至腦,需要深厚的內力才做得到,而姚清繡顯然沒有這個本事。
真相已明,該是離開的時候,可是卓翊卻感到為難,把人家好好一個姑娘弄成這樣卻撒手不管,不是有些缺德嗎?卓翊不走,其他人更不敢動,一時之間形成一群大男人必恭必敬圍著一個小姑娘的奇異景象。
「還有什麼話要問嗎?」姚清繡冷冷地道。「還是要把我左手也折了才走?」
「姑娘說哪兒話!今天的事純粹是一場誤會,誤會!妳好好休息,我們就不煩妳了。」丁春山忙出來打圓場,幫著姚清繡捲好針包。針包一入手,丁春山才發現原來有兩層,上層是針灸所用,其下一層,則排著女紅所用的各式縫衣針、繡花針,長短色澤不一,但其中一排令卓翊一瞥就再也移不開目光。
那是與從郭進寶腦中取出的,一模一樣的金針!
* * *
「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這是姚清繡對今天白天遭遇的總結。
遭受無妄之災也就罷了,更慘的是,師父曾叮嚀她,千萬別與官府打交道,今天卻被官差找上,不知能否脫身?
還有那個卓翊,長得那麼完美,卻有副蛇蠍心腸,一出手就把她弄個半死不活,真是人不可貌相。
天一黑,姚清繡就決定上床睡覺,這樣可以早點和倒楣的今天說再見。
不知睡了多久,一種對危險的本能感應,使姚清繡忽然醒來。奇蹟似的,她還睡在床上,可是她的床前卻站了一個人,一個黑衣人。
「妳不該來這兒。」黑衣人的雙眼閃著異光,姚清繡再次感到死亡的威脅,立即翻身下床。
她確實不會武功,可是她會輕功;她不能傷人,可是她能避免被人傷害。
茅屋很小,姚清繡一邊騰挪移動,一邊想逃出屋外。她相信黑衣人就是放飛針的人,也是她要找的人,可是黑衣人絕不會給她說話的機會。
所以她只能不停地躲。
不知為何,黑衣人並沒有對她放飛針,也因為如此,姚清繡才能勉強支持。
忽然,黑衣人踢碎桌椅,姚清繡一開始以為他是因為追不上她,才拿桌椅出氣;然而很快地她發現,地上雜物越多,對她越不利,只要一個不小心,她就會被絆倒。
當她明白這一點的時候,她已經摔倒在地。
匕首的寒光在她眼前閃爍,她的皮膚甚至可以感覺到匕首的森冷。原來她大限已到,即使睡了一覺,霉運仍跟著她……腦中再一次閃過師父的臉,而除了師父之外,又多了一張臉,就是那個心如蛇蠍的卓翊。
忽然,該刺進心臟的匕首卻偏了幾寸,只劃過姚清繡的肩膀,原來有人手執長劍,以攻勢逼得黑衣人回招自救,所以匕首失了準頭。
姚清繡定睛看去,那人竟是卓翊。
月光下,卓翊已與黑衣人鬥在一起,卓翊長劍翻飛靈動,黑衣人在兵器上吃了虧,漸落下風。不過他身形飄忽,總在危急之時以鬼魅般的身法避過。兩人鬥得激烈,姚清繡忘了臂傷疼痛,走近窗邊觀看。
忽然,一陣細微的勁風劈面而來,然後是細碎的金屬撞擊聲,幾乎同時,卓翊已經到了窗邊,而黑衣人趁隙脫走。
只一眨眼,姚清繡已到鬼門關外繞了一圈。
原來黑衣人明知打不過卓翊,危急中向姚清繡射出金針,這是圍魏救趙之法,卓翊不會不知,可是他還是選擇了救人。
「妳被針射到了嗎?」卓翊隔著窗戶問。
「沒有。」
「那就好。」卓翊放下心來,露出笑容。
第一次看到卓翊的笑,姚清繡雙眼一亮,這真是太美了!心中卻又有些慚愧,剛剛卓翊在與黑衣人過招的時候,她竟暗暗希望黑衣人贏,至少不要被卓翊擒下;可是卓翊,卻是因為關心她的安危,才讓黑衣人逃走。自己這麼想,是不是有些忘恩負義呢?
「好吧!我原諒你了。」姚清繡說。
卓翊愣了一下,才意會到她說的是白天的事,不禁笑了起來,說道:「那很好,不枉我在這裡守了大半夜。」
「你守了大半夜?」姚清繡坐回桌前,卓翊從窗外跳進來,幫她點亮了燈。
「這點也要跟妳抱歉了。」卓翊邊看她的傷口邊說。還好沒傷到筋骨,他拿出金創藥,倒在姚清繡的傷口上,又取出隨身布條為她紮好傷口。
「因為妳針包中的金針,與被害人身上取出的一模一樣,所以……」
「所以,你留下來監視我?」姚清繡覺得頭痛,這些當差的,怎麼這麼鍥而不捨啊!
「說監視也太難聽了。不過,如果妳覺得不高興,我跟妳道歉。職責所在,總是不能大意。」
姚清繡點了點頭,只要他知道錯就好。而且,他畢竟救了自己,光就這一點來說,也算功過相抵了。
「那現在,我的嫌疑是否『完全』排除了呢?」
「我相信,妳和郭宅凶案沒有直接關係。」卓翊笑了笑,忽道:「兇手,妳認識吧!」
「我怎麼……你……」姚清繡急著否認,無奈心虛令她口齒不靈便,略停一停,順了順氣,才道:「如果我認識他,他怎麼會來殺我!」
「正因為妳認識他,所以才要殺妳滅口。」看姚清繡漲紅了臉,又笑道:「我沒別的意思,只是依常理推斷。查案子查了這些年,總有些心得。」
姚清繡翻了翻白眼,不想再跟他說話。這人太精明,自己一不小心就會露出馬腳。
「你可以走了。」這是姚清繡今天第二次對他下逐客令。
「如果妳休息夠了,那我們就走吧!」
「我們?」姚清繡又吃了一驚。「難道你還要監視我?」
「不是監視,是保護。」
姚清繡又漲紅了臉,氣道:「今晚我已經被殺過了,而兇手也已經被你這個大神捕趕跑了,根據你辦案多年的心得,你認為兇手會不知死活地再來自投羅網?」
「根據我辦案多年的心得,殺人未遂去而復返的情況總是經常發生。」卓翊又笑了。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郎君太禍害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67 |
羅曼史 |
$ 323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郎君太禍害
蝦米?她有沒有聽錯?
眼前這個帥得很禍害的捕快大人,竟說她是謀害富商的重大嫌犯?
她只不過是擅長使針,幫街坊繡繡方巾,手藝巧奪天工了點,
怎麼就變成他口中的飛針殺手?!
她擅於刺繡並不表示她就會用金針殺人好嗎……
直到她被真正的兇手偷襲,才終於證明了自己的清白;
以為他不會再來勾勾纏,
可他卻又用「保護」的名義要她去衙門小住,實則想調查她的身分,
雖然她一點都不想被關在衙門裡保護,
不過看在他如此可口的分上,她就勉為其難去「作客」一下好了!
而在相處的過程中,她才發現他這位神捕表面冷漠,內心體貼,
總是在她傷心時靜靜陪伴她身旁,給她依靠與安慰,
這樣溫柔的他,加上他足以迷死男女的俏臉皮,教她情不自禁的丟了心,
兩人的情感也如野火燎原般急速竄升,
只是他們的幸福,似乎來得猛、去得也快……
章節試閱
楔子
一輪明月如鏡,高懸中天。
庭下空明,花影幽幽,唯聞隱約蟲語,若斷若續。
靜得不能再靜的夜。
一陣微風掠過,一團黑影如驚鴻一現,瞬即消逝。
大宅中的一間房,忽然亮起了燈。
「誰?」睜開惺忪睡眼的老爺,以手遮眼,不勝厭煩地問。
「勾魂使者。」
簡單的四個字從唇齒間擠出,語調雖然平平,卻冷入骨髓,令人戰慄。
老爺一驚,睡意全消,忽然雙眼劇痛,仰倒在床。兩條血線自他眼中緩緩流下。
又一陣風起,吹動了大門上的紅燈籠,兩個「郭」字在黑夜中輕輕搖晃。
第一章
花海蝶舞,柳浪鶯啼,正是江南好風光。
一幢茅草小屋坐落...
一輪明月如鏡,高懸中天。
庭下空明,花影幽幽,唯聞隱約蟲語,若斷若續。
靜得不能再靜的夜。
一陣微風掠過,一團黑影如驚鴻一現,瞬即消逝。
大宅中的一間房,忽然亮起了燈。
「誰?」睜開惺忪睡眼的老爺,以手遮眼,不勝厭煩地問。
「勾魂使者。」
簡單的四個字從唇齒間擠出,語調雖然平平,卻冷入骨髓,令人戰慄。
老爺一驚,睡意全消,忽然雙眼劇痛,仰倒在床。兩條血線自他眼中緩緩流下。
又一陣風起,吹動了大門上的紅燈籠,兩個「郭」字在黑夜中輕輕搖晃。
第一章
花海蝶舞,柳浪鶯啼,正是江南好風光。
一幢茅草小屋坐落...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元珊
- 出版社: 龍吟ROSE 出版日期:2010-12-08 ISBN/ISSN:986621389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