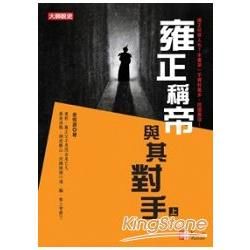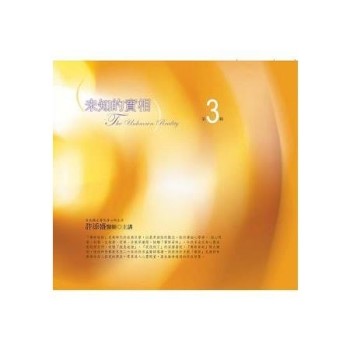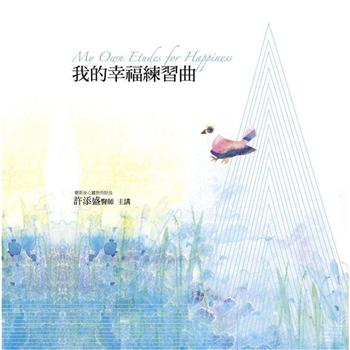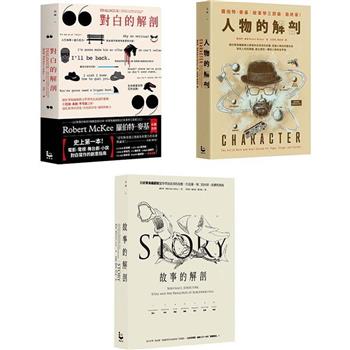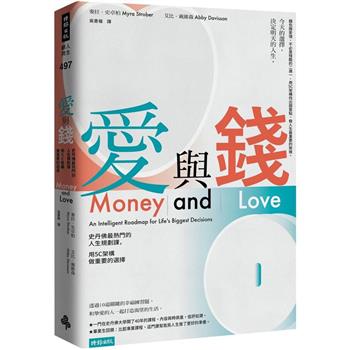【前言摘錄】
康熙是一位政治家,他對皇位繼承人這件大事,若有暗示,決不會只僅暗示一次,必會暗示多次,並且必會預先在授其權力、樹其威望、壯其力量、錘煉其能力等諸多方面作出一連串動作。這些舉動又必是公開的、大張旗鼓地進行,決不會只在暗中無聲無息地進行,更不會連所選接班人胤禛本人及眾多皇子、大臣都長期被蒙在鼓裡,這是不符合歷史邏輯的。
因此,對於康熙為甚麼令胤禛南郊祭天,究竟是暗示要其繼位,還是因當時某些其它重要原因非要將其從宮中調出,對其採取防範、控制? 就值得重新認真研究。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如果南郊祭天果真是暗示要其繼位,康熙病重時召胤禛“速至”就是要傳位給他,胤禛是個精明之人,理應跑得最快、也理應“速至”才對,為甚麼胤禛竟然要抗旨、拖延八個多小時不去? 這些問題要求其真相,就一定要對康熙末年南郊祭天的前前後後、裡裡外外、已經公開的官方史書以及尚未公開的全部過程進行綜合考量,尤其要對照當時康熙、胤禛父子圍繞南郊祭天的全部言行及文檔史料進行綜合考量後,才有可能找到合理答案。
對康熙所說萬年後要選一個“堅固可托之人與爾等作主”,有學者提出,“這個人正是雍正”。查康熙所說原話:“朕萬年後必擇一堅固可托之人與爾等作主,必令爾等傾心悅服,斷不致貽累於爾諸臣也”。這就很清楚,康熙所說的“堅固可托之人”,首先必須是一個能“令爾等傾心悅服”之人。那麼,無論在雍正四十五年漫長的皇子時期,還是康熙去世後雍正稱帝執政的頭八年時期,雍正是一個能“令爾等傾心悅服”之人嗎? 是一個“斷不致貽累於爾諸臣”之人嗎? 大量血腥的歷史事實,包括雍正欽定的官書《大義覺迷錄》、《雍正朝起居註》、《上諭內閣》、《朱批諭旨》等,都已經作出了生動而又客觀的答案。
再則,康熙固然說過“朕萬年後必擇一堅固可托之人與爾等作主”,但康熙要進行選擇、培養、樹立堅固可托之人一事,必將在其生時就要妥善落實解決之,決無可能放到自己萬年之後或奄奄一息時再去解決。萬年之後或奄奄一息之時還能怎麼解決呢? 這本來是一個必然的、無需懷疑或爭議的問題。然恰好本來是一個無需懷疑或爭議的問題,竟又恰好是近幾年來我與某些專家論戰不息的問題。
【內文摘錄之一】
﹝“南郊祭天“拉響父子決戰導火線﹞
南郊祭天”,即皇帝往京城南端的天壇祭天祈穀。由於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已是康熙帝生命中的最後一月,某些專家據此提出,康熙帝臨終前幾日命胤禛去南郊祭天,是以此暗示要用胤禛繼位。這種觀點的前提,似乎康熙帝當時已經知道或者已經預感十一月的下半月將是他個人生命中最後一月。但這個前提事實上並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南郊祭天”之命發生於十一月初九日,與十月初九日命胤禛去京城東郊查勘糧倉,正好是一個月。在康熙末年的最後一個月中,康熙帝兩次將胤禛調出宮外乃至京城之外,並非無意之舉,目的都是不讓胤禛留在他身邊。這與五十六年、五十八年兩次特諭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十一月初七日,康熙帝預先作十一月初七日,康熙帝預先作了任命十二阿哥允祹為鑲黃旗滿洲都統、吳爾占為鑲白旗滿洲都統、並隨即奉命去南郊負責祭天警衛。在以上布置一一落實三天後,又果斷改變了原先的十一月初十日胤禛與隆科多等十人前往暢春園集體請安的原定計劃,改變為初九日單獨召見四阿哥胤禛一人,命其第二天(初十日)即去南郊祭天。
十一月初七日,初八日,初九日三天中事件的發展,是一環扣一環並環環相聯的。康熙取消初十日胤禛、隆科多等十人集體請安、拒絕胤禛留在自己身邊懇求,堅持派胤禛去南郊並置於預先安排的吳爾占的監控之下,當然還不是事情的最後結果。
既然康熙已公開宣布停止奏章的最後期限是十一月十五日,這就預示著康熙、胤禛的父子鬥法在此之前必定會有一個徹底了斷。
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突然蹊蹺死去,而圍繞胤禛繼位的最關鍵又是最反常的活動,又都發生在這個時間界限之前的十一月十三日這一天,這決非偶然。十一月十三日丑刻(凌晨一~三時),康熙召胤禛於南郊齋所,“諭令速至”。按常理,康熙在凌晨丑時緊急召喚四阿哥胤禛,一定有十分緊迫的事情需要交待。
據官書記載,康熙與胤禛見面後,僅告訴他“病勢日臻之故”六個字。……但翻遍《聖祖實錄》或《世宗實錄》,竟都沒有一字一句談及十一月十三日胤禛如何組織御醫搶救康熙的情況。
如果康熙真的病危,胤禛這個人心機極深,理應當如四十八年一樣,與三阿哥、八阿哥等共同悉心料理,以示自己誠孝和清白,何以在康熙病危時始終避開眾兄弟,獨自一人進出寢宮五次? 如果是日寅時康熙宣布胤禛繼位確有其事,則胤禛更完全可名正言順在父皇在父皇未死之前就擔起太子角色,何以在奉召之後長達八~十個小時不露面?
胤禛又為甚麼要抗旨? 胤禛能抗旨,當然意味著康熙帝已對胤禛失控了。
康熙帝是否曾打算用“上疾大漸”、凌晨“諭令速至”急召作為誘捕之計,從當時情形看,這種可能也未可完全排除。但此計未成,反而被胤禛、隆科多識破並以更為有力更為迅速的反撲所控制。也很有可能,康熙帝在召見胤禛後,先向胤禛攤牌,決意立十四阿哥為儲,並以﹁四阿哥人品貴重﹂作高帽子,付托胤禛全心輔政。胤禛長期受壓,此時受托輔政又豈敢深信? 此時康熙帝既已為胤禛所控制,又值康熙帝患病之際,康熙立十四阿哥為儲又決意不肯收回,至此,康熙、胤禛父子的矛盾鬥爭激化成你死我活的地步。
胤禛必會以各種理由向父皇攤牌,或以許以勤政、勵精圖治作為向康熙求得皇冠之保證。但康熙帝的立儲計劃是經多年觀察、培養、考驗後決定的,豈能因胤禛的口頭保證就肯輕易改變? 康熙帝堅持不變,死不鬆口,胤禛也無可奈何。但此時胤禛也已無路可退。他既已經在皇阿瑪康熙帝面前公開暴露出了他的﹁廢立自專﹂的決心,他還可能再讓步嗎? 康熙帝堅持不變立儲主意後,胤禛又不可能作出讓步妥協,形勢已經變得水火不容而又騎虎難下。既然胤禛不可能改變皇阿瑪的立儲計劃,那麼,唯一的辦法就是讓皇阿瑪盡快死去。康熙帝不死,胤禛不僅當不上皇帝,只怕日後連自己性命都無法保住…
【內文摘錄之二】
﹝胤禛幕後的關鍵人物﹞
康熙帝晚年雖在立儲問題上大傷腦筋,但即使對大阿哥、二阿哥這樣罪大惡極、恨之入骨的不孝子,也並沒開殺戒,至其晚年又豈會對四阿哥開殺戒? 隆科多與康熙帝只是君臣關係,康熙帝與胤禛畢竟還有一層父子關係。一旦隆科多將胤禛之事抖出來,到那時,非但自己不可能以此換取顯赫大貴,只怕後半輩子從此就將在高墻、鐵鏈之下打發餘生。
而一旦胤禛成功,不僅永不再有康熙帝的壓力,也將永遠擺脫皇八子黨的奚落和蔑視。在這關鍵時刻,隆科多與胤禛的心態一樣,都是巴不得康熙帝快點死去,越快越好。只要康熙帝一死,一切問題都可解決。但隆科多在康熙帝之死上,不願意背歷史罪名,也不肯自己直接向康熙帝下手,而是採取放任、縱容、支持胤禛得逞的態度。也許,這個態度正是通州勾結時雙方談妥的先決條件。隆科多本來一直躲在幕後,直到康熙帝蹊蹺猝死後才從幕後走到臺前,原因蓋於此。
雍正繼位過程中,隆科多究竟扮演了甚麼角色、起了甚麼作用、起了多大作用?
有人認為,可能是康熙帝將隆科多承襲一等公爵事留中四年,引起隆科多不滿。隆科多為此事心中不滿是很有可能的,但僅僅因為這一不滿就要冒天下之大不諱、發動一場宮廷政變,以隆科多與康熙帝長期來主僕之情誼、加之隆科多為人一向精明謹慎之個性,則其可能性就不會很大了。
有學者提出:“六十一年十月雍正奉命清查糧倉,隆科多為(清查) 成員之一,可能這個時候成了雍正的人。“胤禛奉命清查糧倉,時間為六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始於暢春園,至十一月初六日就在南苑以彙報結束了,前後總共只有二十八天,一個月都不到。而隆科多任康熙帝步軍統領,僅是這一職務,時間就連續長達十一年之久。隆科多與胤禛之間親密往來,充其量不足一個月。隆科多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竟發生了政治上如此翻天覆地之巨大變化,而且要冒殺身、誅連九族的巨大風險,僅此一點,也就值得細細尋味,隆科多究竟是為甚麼?──當時究竟發生了甚麼事、甚麼原因、甚麼理由,才使隆科多這個一向謹慎勤奮的步軍統領,橫下這麼大決心、化這麼大力氣、冒這麼大風險,拼死要將胤禛推上龍座交椅?
學者楊珍先生提出:“隆科多擁戴胤禛的最主要原因,是他於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受到玄燁斥責後,隨即疏遠冷淡胤祀、胤禟等人,為使玄燁徹底改變對自己的看法,隆科多很可能還曾揭發胤祀等反太子的事,以及乃父佟國維、堂兄鄂倫岱等人的罪行。這種反戈一擊的做法,儘管較快贏得玄燁的信任,但也必然招致胤祀、胤禟集團及佟氏家族主要成員的鄙夷,認為他是見風使舵之人,從而使他日益得寵的同時,感到孤立與難堪。所以,玄燁猝死後,隆科多權衡利弊,迅速作出如下判斷:
即使自己擁戴皇十四子胤禎,由於同胤祀、胤禟等人已有積怨,非但不能換取回報,仕途亦不容樂觀;而若擁戴皇四子胤禛,則會是另外一種結果。事實證明了他的判斷,胤禛繼位後,他暫時如願以償,所受榮寵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沒有隆科多的支持,十一月十三日這一天玄燁急召胤禛,胤禛何以能抗旨八~十個小時不去? 玄燁未死之前,胤禛又何以能進見五次、並在玄燁身邊長達十幾個小時? 可見,隆科多對胤禛之功,不僅僅是“玄燁猝死後”。隆科多投靠、支持胤禛,也並非是“玄燁猝死後,隆科多權衡利弊”才決定的,而是早在玄燁未死前一個多月就迅速作出判斷了。否則,胤禛怎麼能從十一月初十起每天不斷多次派遣侍衛進駐暢春園? 胤禛的奪宮又何以能如此周密、迅速、高效? 就是因為胤禛早就暗中得到了步軍統領隆科多的支持。而關鍵時刻隆科多的支持態度並非只是發生於“玄燁猝死後”,而必定是“玄燁猝死前”就同胤禛結盟了。
十一月十三日晚康熙帝去世後,胤禛先是為先帝“更衣”,隨後馬上就悄悄將康熙帝遺體從暢春園秘密運往大內。在這整個過程中,除了胤禛、隆科多和侍衛外,沒有其他大臣、皇子在場。既然沒有其他大臣、皇子在場…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雍正稱帝與其對手(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 238 |
科學科普 |
$ 280 |
歷史人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雍正稱帝與其對手(上)
書籍內容及賣點
雍正稱帝,是一個歷史大謎團。
歷來眾說紛紜,各有著名學者持各種不同資料提出差異甚遠的說法,讀者也跟著眼花撩亂。
本書作者係滿族,愛新覺羅‧玄燁(即康熙帝)第八世孫,主攻:雍正之人物研究。
本書從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的許多宮中檔案抽絲剝繭、以極具邏輯的相互對照方式來
寫本書,十分難能可貴!
從康熙的個性、雍正的個性;康熙的布局、雍正的謀劃;情況的演變、因應的手法──
康熙、雍正這對父子的攻防,真是步步驚心!
雍正用什麼手法借重康熙身邊的重要人物;康熙何等智慧的皇帝為何讓局面失控──以至
逼、騙、奪三管其下,雍正稱帝!若非數十年深刻研究,加上條理分明的筆觸,本書不但好看,
對於喜愛中國歷史的讀者,是值得珍藏的好書!
作者簡介:
金恆源
‧1944年生,籍貫北京市,滿族,愛新覺羅‧玄燁(即康熙帝)第八世孫。
‧清史研究者,主攻:雍正之人物研究。
‧主要論著:《雍正帝篡位說新證》、《論康熙遺詔真偽》、《南郊祭天解疑》、《正本清源說雍
正》、《論康熙帝之死》、《關於雍正研究中的若干誤區》。
章節試閱
【前言摘錄】
康熙是一位政治家,他對皇位繼承人這件大事,若有暗示,決不會只僅暗示一次,必會暗示多次,並且必會預先在授其權力、樹其威望、壯其力量、錘煉其能力等諸多方面作出一連串動作。這些舉動又必是公開的、大張旗鼓地進行,決不會只在暗中無聲無息地進行,更不會連所選接班人胤禛本人及眾多皇子、大臣都長期被蒙在鼓裡,這是不符合歷史邏輯的。
因此,對於康熙為甚麼令胤禛南郊祭天,究竟是暗示要其繼位,還是因當時某些其它重要原因非要將其從宮中調出,對其採取防範、控制? 就值得重新認真研究。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
康熙是一位政治家,他對皇位繼承人這件大事,若有暗示,決不會只僅暗示一次,必會暗示多次,並且必會預先在授其權力、樹其威望、壯其力量、錘煉其能力等諸多方面作出一連串動作。這些舉動又必是公開的、大張旗鼓地進行,決不會只在暗中無聲無息地進行,更不會連所選接班人胤禛本人及眾多皇子、大臣都長期被蒙在鼓裡,這是不符合歷史邏輯的。
因此,對於康熙為甚麼令胤禛南郊祭天,究竟是暗示要其繼位,還是因當時某些其它重要原因非要將其從宮中調出,對其採取防範、控制? 就值得重新認真研究。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
»看全部
目錄
【上】
前言/4
第一章 父子恩怨,由來已久/18
第二章 “南郊祭天”拉響父子決戰導火線/34
第三章 “廢立自專”父敗子勝/124
第四章 木欄圍場與南苑/131
第五章 雍正與年羹堯/140
第六章 雍正與隆科多/186
第七章 雍正與三阿哥、八阿哥/234
第八章 雍正與十二阿哥/246
前言/4
第一章 父子恩怨,由來已久/18
第二章 “南郊祭天”拉響父子決戰導火線/34
第三章 “廢立自專”父敗子勝/124
第四章 木欄圍場與南苑/131
第五章 雍正與年羹堯/140
第六章 雍正與隆科多/186
第七章 雍正與三阿哥、八阿哥/234
第八章 雍正與十二阿哥/246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金恆源
- 出版社: 知本家 出版日期:2012-07-18 ISBN/ISSN:978986622330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64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歷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