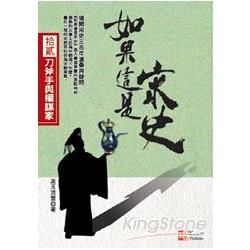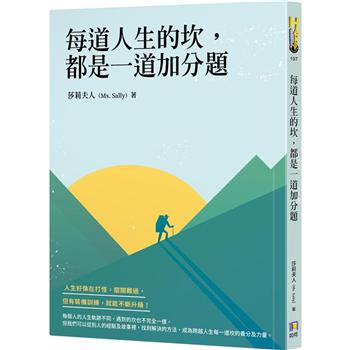宋朝是個非常特殊的朝代:
北宋共有九帝,除了在位超短的英宗(僅五年),各個皇帝都有值得一讀的歷史,本書寫的是宋哲宗,他是個力圖改革的皇帝,深知王安石變法對宋朝的益處及重要性,但他面臨了下面幾項十分嚴峻的挑戰:
九歲即位,垂簾聽政的是他的祖母:嗜權好強的高氏太皇太后,極力要抹平兒子宋神宗的變法,弄得整個朝廷陷入“三黨黨爭”(新、舊、朔黨),國家運轉空耗。
鐵打的朝廷,流水的宰相。這是黨爭直接影響的結果。
內廷雖亂,宋哲宗得到“西線百年第一人”,宋軍得到百年難得的最天才、最有勇略的指揮官章楶,讓不斷向宋朝耍賴搶劫擾邊、百般要錢要東西的西夏徹底改天換地,主動權掌握在宋朝手裡。
曇花一現的賢君,宋哲宗在位僅15年,死時25歲。
一息猶存,但已不能言語的宋哲宗,死前眼睜睜的看見向太后矯旨立新皇帝。
作者簡介
高天流雲
本名劉羽權,沈陽人。
從事宋史研究多年,其出版的歷史著作《如果這是宋史》系列,是目前市場上最為暢銷的白話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