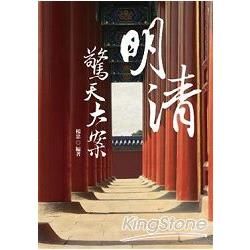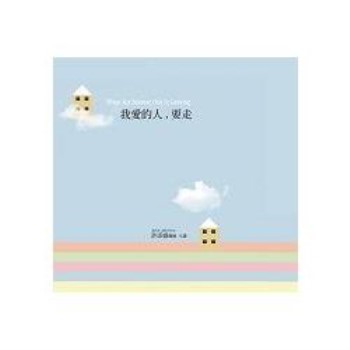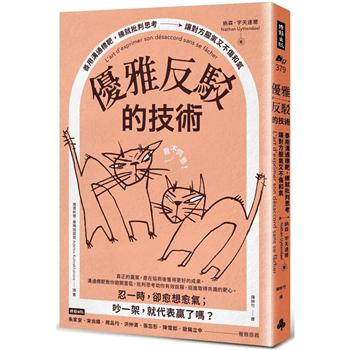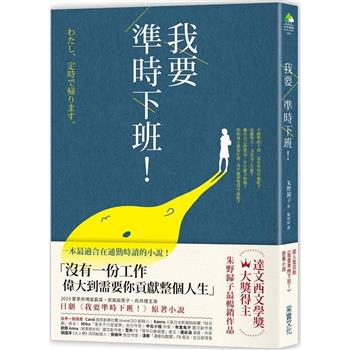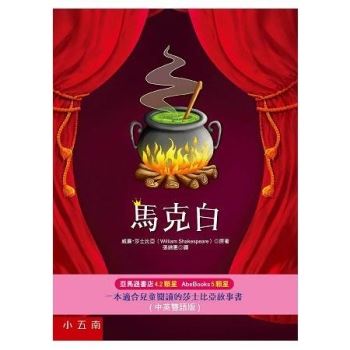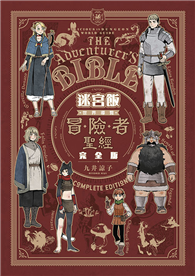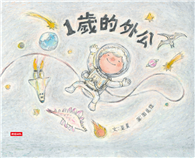解密離奇案件,還原歷史真相!
明朝宮女怎敢斗膽謀害皇帝明世宗?
明末一代名將袁崇煥何以慘死告終?
清朝文字獄背後究竟藏著什麼祕密?
科場舞弊為何牽連一品大學士人頭落地?
楊乃武與小白菜之冤何以驚動慈禧太后?
大清第一宗總督大人刺殺案的真兇是誰?
名角楊月樓與富家女的囍事為何變成悲劇?
清朝第一次步上西方法庭的窘態所為何事?
明清五百多年,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絕唱,其中有許多轟動朝野、錯綜複雜且影響深遠的驚天大案,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廣泛層面,以今日視野看待,依然充滿戲劇性張力,而這也是歷史的迷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