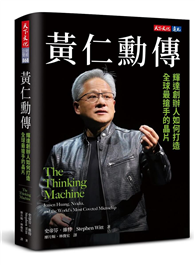故事發生在宋朝,一對江南世家夫婦前往遼國尋找藥引
玉樹臨風的丈夫與美麗的妻子,帶著一個尚在襁褓的女嬰匆匆趕路
路經黑山天池時,卻碰上來意不善的契丹人
先是調虎離山引走丈夫,再趁妻子不備,搶走女嬰
剎那間天地變色,愜意的旅程成了傷心之旅
女嬰的命運繫於老天一端:被契丹人養大或被狼奪去性命
這看似意外卻是計算精密的復仇計畫
幕後陰謀者目的為何?
多年後,江湖上出現一清麗不容逼視的女子,名之為觀音奴
十三年前即渴望親手扶養她長大的藍眼男子
十三年前從狼洞救她出險的契丹少年
十三年後在江南水鄉邂逅的士族公子
愛情,會在他們之間投下何等變數?
作者簡介:
本名朱慧穎,四川新都人,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屬相為蛇,星座雙子。
十六歲時曾休學習武,在中國南端的熱帶島嶼磨練了四個月。瓊海市加積鎮的門山園武術館成為一生夢想的起點,當日師父傳授的套路已然淡忘,惟錚錚武俠一直是心底所愛。
主要作品:《連城脆》、《寒鴉劫》、《牡丹錯》、《十二城記》、《三京畫本》。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盛顏及時挽救了大陸新武俠一把
網路好評不斷,私心鍾愛首選
◎盛顏的作品面世速度當真是慢,卻仍有那麼多讀者一如既往地追隨,我想,她文字之美,應當是一個極大的因素吧。(清霜傲雪)
◎盛顏的筆觸描繪著美妙,即使是樸素的文字也會給人帶來一種撲面而來的幽靜。(舞峰陽)
很沉迷盛顏的文字……有一種難以言語的美,如她那句經典的名句:只可感懷,不可述說。很多句子我都看了一遍又一遍,真的有口齒噙香的感覺。(卓清漣)
◎盛顏的確是慢工出細活,但是作品堪稱經典。(舒亞男)
◎盛顏的作品每部都妙不可言!清新又大氣,婉轉又自然。(janely)
◎盛顏稱得上個真正的才女,文字不錯,人物也寫得很好,故事也好,看上去平淡中又帶著一點浮動。(儆。藍)
◎在經歷了前半年的「新武俠」低潮之後,盛顏及時挽救了大陸新武俠一把。她的劍並不鋒利,但是卻是鍛造許久的。銳氣和厚重,透過層層的黑山白水,撲面而來。(河流如金)
盛顏勾畫愛情的功力,超越金庸
武俠小說編輯&書評人專業推薦
明日工作室「明日武俠」書系主編劉叔慧
如果你愛看武俠,這壯麗的邊城恩仇、深沉的江湖算計,必讓你愛不釋手;如果你不愛看武俠,僅是觀音奴、鐵驪、嘉樹的愛恨情仇,就足令你牽腸掛肚,痴心等待。楊過和小龍女的愛情超越文類,盛顏勾畫愛情的功力,超越金庸。
《今古傳奇》武俠版社長、主編鄭保純
盛顏的稿子,真是不厭其長,但恨其短。與《寒鴉劫》比較,她還在向前走,觀音奴果然是氣象一新,神刀門的武功到後來嘉樹的煉魂術法,說明盛顏武學,亦新亦舊的探索也未停下來。盛顏在北宋地理人文等方面,也下了工夫,使之與江湖的設定結合完美,這個也非常的罕見。
大陸知名武俠作家、《今古傳奇》武俠版前主編鳳歌
盛顏是武俠版作者中很獨特的一個,文史並茂,意興洋洋,行文間既有不讓男兒的蒼茫大氣,又以女性的視角觀照人世,情感細膩柔美,婉約有致。
《今古傳奇》武俠版編輯部主任李逾求
「金堅玉潤,鶴骨龍筋,膏液內足。」用蘇東坡形容沉香的話來形容盛顏的文字,倒是恰如其分。
盛顏對三京之生活風土等進行了極為細緻的描繪,以細微論,幾可媲美于大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可是《三京畫本》又不僅僅局限於一隅,而是以三京為背景,以時代為橫軸,以成長為縱軸,形成一個既具歷史感,又具時代感的恢宏畫卷。觀音奴、蕭鐵驪、耶律嘉樹等在其間上映著喜怒哀樂、悲歡離合。這江湖如此廣大,廣大到縱橫綿延開來,便是人生和世界。這江湖又如此細微,細微到我們可以憑藉歷史的座標,找到其中任何一點。
名人推薦:盛顏及時挽救了大陸新武俠一把
網路好評不斷,私心鍾愛首選
◎盛顏的作品面世速度當真是慢,卻仍有那麼多讀者一如既往地追隨,我想,她文字之美,應當是一個極大的因素吧。(清霜傲雪)
◎盛顏的筆觸描繪著美妙,即使是樸素的文字也會給人帶來一種撲面而來的幽靜。(舞峰陽)
很沉迷盛顏的文字……有一種難以言語的美,如她那句經典的名句:只可感懷,不可述說。很多句子我都看了一遍又一遍,真的有口齒噙香的感覺。(卓清漣)
◎盛顏的確是慢工出細活,但是作品堪稱經典。(舒亞男)
◎盛顏的作品每部都妙不可言!清新又...
章節試閱
第一折 宛轉豔歌行
大興安嶺曼衍北疆,到與燕山交接之處,生出一座挺秀的峰來,契丹人呼作黑山,後世稱為賽汗罕烏拉。傳說黑山是天神居所,契丹人死後,靈魂必定歸於此處,受黑山之神管轄,所以契丹人視黑山為聖地,若非祭祀,不敢近山。
遼國天祚帝乾統七年(一一○七)的夏天,黑山道上,轔轔的車聲碾破了一山寂靜。
車帷挽著,露出一個碧衣女子的側影,鴉鬢雪膚,風致楚楚。車後,兩名男子騎馬相隨,當先一騎白衫素履,神情軒朗如朝霞初舉,光耀幽深山道;殿後的少年著淺藍布袍,身形瘦削,氣質乾淨。
行至半山,車中突然響起嬰兒的啼哭,白衫男子縱馬上前,在車窗邊道:「希茗,夜來醒了麼?我想她是餓了。」
碧衣女正給嬰兒哺乳,聞言笑道:「是餓了呢。今天這孩子倒乖,睡了一路,讓我也悶了一路。逸哥,你唱首歌來解解乏。」
崔逸道睨著她,微笑道:「希茗想聽什麼呢?」他想了想,彈鋏而歌:「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鷂子經天飛,群雀兩向波。」聲音清越,激起群山回應,將一首簡單的北朝民歌唱出單騎入陣、所向披靡的慷慨來。
李希茗抿嘴一樂,逗著懷中嬰兒,「夜來,阿爹沒嚇著你吧?姆媽給你唱一首柔和的。」她曼聲歌道:「月既明,西軒琴複清。寸心鬥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淒以哀。願為星與漢,光影共徘徊。」清冽陽光穿過縹青山林,映著她晶瑩肌膚和淺紅嘴唇,淡到極致反成濃豔。
崔逸道心中一醉,低聲道:「希茗若是星辰,我便是天河,總是陪著你的。」
李希茗不說話,低著頭整理嬰兒襁褓,素白的頸項卻沁出微紅。蜷在錦褥上打瞌睡的小丫鬟玎玲半睜眼睛,偷偷笑起來。
說話間,山道已盡,一條窄徑壁立於前,只堪人行,再容不下車馬了。崔逸道右手攬著李希茗,左手抱著嬰兒,足尖輕點,瞬息間已攀到幾丈外,藍袍少年緊隨其後。
玎玲仰著脖子,悻悻地對車夫崔穆道:「穆叔,阿躬的功夫這樣好了,卻不肯帶我上去,忒也小氣。」
崔穆裝了一鍋煙,美美地吸了一大口,「未必摘下來的金蓮就不是金蓮了,在這裡等著,一樣得見。」
玎玲嚮往地道:「咱們淮南的荷花都是紅白兩色,這深山老嶺裡倒長出金黃的來了,真想不出是怎麼個好看法。」
崔穆嗤地一笑,「那可是太夫人的藥引子,再好看也不能簪到你小丫頭的腦袋上。」
玎玲鼓起腮,「嘁,穆叔別把我當小孩兒取笑。」
黑山如此峭拔,料不到峰頂平坦如砥,方圓足有十餘里。雲煙淡淡,及膝深的草上,冶豔的夏花錦一般鋪開。花海中央的天池,赤金色荷花吐蕊綻放,華麗花光與碧綠水色相映,如夢如幻。
李希茗只覺麗色流轉、花香繚亂,不由讚歎:「逸哥,見到這等景致,一路辛苦都不枉了。」
崔逸道微笑頷首,打量四圍,見遠處有八九個左衽窄袖的契丹人,牽著白馬白羊,抱著白雁,想必是來祭祀山神的。他將嬰兒遞給她:「希茗,我去摘金蓮。」言罷雙臂展開,鷹一般掠過長草。
崔逸道落到天池中的荷葉上時,李希茗身側忽有異動。一名戴著青狼面具的契丹人向她衝來,將草叢分出筆直的一線,其勢如同破竹裂帛,眨眼間已距她七尺。契丹人的長鞭似靈蛇一般鑽到李希茗懷中,勾著嬰兒的襁褓,一回手,竟將嬰兒生生奪了過去。得手之後,契丹人決不耽擱,轉身狂奔而去。
侍立在旁的崔躬應變不及,倉皇中將佩劍當暗器來使,朝那契丹人擲去。長劍破空,釘在契丹人臀上,他踉蹌前撲,卻將手中嬰兒奮力拋向夥伴,另一人接了就跑,如同接力。
李希茗叫著「夜來」,拔步便追,但她不會武功,情急之下一腳踩到裙裾,反而跌進草叢。
變生俄頃,待崔逸道掠回,搶到嬰兒的以敵烈已快奔到山峰邊緣。崔逸道拔劍追去,有如隼擊長空,將攔路的契丹人一個個劈翻在地。劍光雪亮,一蓬蓬血花在草場上綻開,他的身法卻無半點窒礙。
以敵烈流星般向下墜去,身影很快沒於蒼茫林海。
崔逸道放聲長嘯,候在峭壁下的崔穆聽到主人嘯聲,已然警覺,旋即見一個懷抱嬰兒的契丹男子從小徑奔下,鵝黃色襁褓赫然是自家幼主的。
崔穆迎上去,怕傷著孩子,攻的是以敵烈下盤,紫銅煙鍋狠擊在他的髕骨上,火星四濺。
以敵烈只覺一股開碑裂石的大力斫在骨頭上,身子晃了晃,死抱著嬰兒不放手,步伐卻慢下來。
崔穆這一阻,崔逸道便追了上來,踏著雲杉的枝條,風一般卷過山林,躍過以敵烈的頭,落在山道上。崔逸道出劍的速度極快,劍勢夭矯,屈曲盤旋的劍路似一場凍雨般裹住了以敵烈。
以敵烈只覺全身要害都籠罩在他冰冷的劍光下,惶惶不知向何處反擊,忽然耳郭劇痛,漫天劍光斂於一泓碧水,八寶崔氏的碧實劍已削去他一片耳朵,架在他頸上突突跳動的血管旁。
崔逸道見夜來吃了這番驚嚇,竟然不哭,一雙烏溜溜的眼睛瞧著自己,心中頓時安穩,冷冷道:「還我女兒來。」
以敵烈並不退讓,怒視著崔逸道,牙齒咬得格格響。他長得極高大,髡髮空頂,只在兩鬢留了兩股長髮,被耳朵上的兩個金環收束著。此刻少了一片耳朵,頭髮便披散下來,髮梢猶在滴血,樣子極凶。
崔逸道怕他傷著女兒,不敢硬奪,出手點他穴道,卻覺指下一滑,明明點在實處的穴道竟成了虛的。這契丹人並非內家高手,決不可能練成轉移穴道的神技,但崔逸道連試幾處都是如此,不由震駭。
遠遠傳來一個柔媚的聲音:「這位官人,可以放開我的同伴麼?」
崔逸道偏頭一看,臉上忽然沒了表情。來的是個薩滿教中的巫女,抄一把解腕尖刀抵在李希茗心口,後面跟著眼神迷濛的崔躬。
巫女郁里的白衣在風中翻飛,馥郁的香氣像河水一樣漫過。她細腰柔軟,步伐如舞,腕上繫著的金鈴發出叮叮之聲,並不是什麼出色的美人,卻帶著難描難畫的魅惑。
玎玲怔怔地瞧著,只覺脈搏與這巫女行走的節奏漸漸一致,心跳聲似春雷一般在耳邊迴響,極恐懼,卻又極歡喜。連崔穆這樣的老江湖也露出恍惚神色,惟有崔逸道不為所動,冷冷地站在當地。
郁里眼色媚人,道:「你,兩個裡選一個。要娘子,就放我同伴走;要孩子,你娘子就死。」她的漢話頗流暢,只是腔調怪異,像咬著舌頭說話。
崔逸道方才連斃八人,就是為了避免後顧之憂,殊不料這巫女暗中埋伏,竟挾持了李希茗。一邊是傾心相許的妻子,一邊是如珠如寶的女兒,又有哪一邊捨得下?一顆心頓時如煎如沸。
郁里見他不語,手上微微加力,已挑破李希茗的羅衣,霎時鮮血湧出,濕透前襟。李希茗痛得全身發抖,被巫女迷惑的神志卻清明過來,正看到以敵烈卡著女兒的脖子,似掐非掐,表情猙獰一如惡鬼。李希茗顫了一下,果決地道:「逸哥,你不必以我為念,先顧著夜來。」
崔逸道望著她,夫妻對視,仿佛過了良久時間,在旁人來說不過頃刻。崔逸道不再猶豫,沉聲道:「我放他走,你就保我娘子周全?」
李希茗急了,厲聲道:「逸哥,你別糊塗!」
郁里抬手在尖刀上一抹,豎起鮮血淋漓的手掌,「我以血為誓,你讓我的同伴帶了小孩走,我絕不要你娘子性命。如違此誓,叫我血液乾枯而死。」
崔逸道撤劍,喝道:「滾!」
以敵烈沿山道狂奔而去。李希茗聽著孩子尖利的哭聲越來越遠,眼眶一熱,奮力掙扎,卻被郁里牢牢扣住。
崔逸道眼神冰冷,雖是盛夏,郁里卻覺得一股肅殺秋氣直砭肌膚,令寒毛都立了起來。她咬牙苦撐,捱了半個時辰,算著崔逸道再也追不上以敵烈,才挾持著李希茗慢慢挪到崔逸道的馬旁。
崔逸道的明雪駿向來認主,絕不容生人靠近,在郁里面前竟很馴順,低下頭舔著她手上的傷口。郁里輕輕啟齒,婉轉一笑,其媚術之瑰麗,只可用驚心動魄形容,崔穆等自不待言,連崔逸道都有些眩暈。
便當此際,郁里突然發力,將李希茗往山道旁一塊稜角鋒銳的巨石上拋去,自己身子一旋落到明雪駿背上,迅疾拍馬而行。
崔逸道在十步外飛身躍起,挽住李希茗的羅袖。夏衫輕柔,承受不了李希茗的重量,嗤的一聲,只留了半幅袖子在崔逸道手中。幸虧他反應極快,使出汴京紫衣秦家的神通拳,臂膀喀地一響,似突然長了一截,拿住了她的手腕。他攬著李希茗,不由得冷汗涔涔,方才若稍晚一步,她必然重傷。
「要找回你的孩子,到上京來。」郁里卻已逃到二十丈外,遠遠地撂下這話,笑聲灑落一路。
崔逸道恨極,惜乎日行千里的明雪駿被郁里奪走,想追上她卻是萬萬不能了。他低下頭,見妻子白著一張臉,黑色眼睛裡水氣迷濛,忙將她抱進馬車,仔細包紮。
李希茗掙扎著道:「別管我,逸哥,快去把夜來追回來,快啊!」
「已經追不上了。」崔逸道頓了一下,「希茗,當時若不答應那巫女,只怕你已經遭她毒手,這個險,我真的冒不起。」
她咬緊嘴唇,定定地看著他,怒氣鬱結在胸口,卻沒辦法發作出來,只能澀聲道:「我寧肯自己當人質,寧肯自己受磨折,也不願夜來吃一點苦。我的意思,你竟不明白。」
崔逸道心裡並不好受,雖說是安慰妻子,也是在安慰自己:「這些蠻人處心積慮地奪了夜來去,自然是想要脅我什麼,不會為難夜來的。八寶崔家不敢說要什麼有什麼,但凡這世上有的東西,我都會為夜來弄到手,你只管放心。」
他微微仰起頭,「咱們崔家的基業,幾百年來都在淮南,從未伸到北方。這次來遼國求金蓮,卻令你受傷,又失了夜來,這場子我一定要找回來。連妻兒都保護不了,我還算人麼?」
崔逸道另有一層想法,是決計不敢對李希茗提起,倘若夜來是被崔沈兩家放逐到遼國的對頭劫走,情形就不妙了。屈指算來,那被逐走的孩子現在才十五歲,短短三年就能設下這個局,驅使這許多高手來復仇,實在可怕。
李希茗知道夫婿少年得意,是南方武林的第一人,聽他說得這樣有把握,終於鎮定下來:「我並不是怪你……逸哥,我已經失去了阿元,再不能失去夜來了。這些蠻人哪裡會照顧孩子,夜來餓了怎麼辦?傷著怎麼辦?回不來怎麼辦?」她越想越怕,到末一句時難以為繼,哽在了喉嚨裡。
崔逸道低頭吻住她蒼白的嘴唇,不欲她再說下去,那唇涼得他的心微微一顫。他輕聲道:「希茗,我一定會找回夜來,帶你們娘倆平安回家,你安心歇著。」
給李希茗裹上羽緞披風,崔逸道出了馬車,卻見崔穆等人兀自癡癡呆呆,那巫女的攝魂術還真是了得。他出掌擊在三人的玉枕穴上,崔穆、崔躬只覺一股清涼之氣直透腦門,醒了過來;玎玲卻嚶嚀一聲,暈了過去,被崔穆一把托住。
崔逸道伸兩指搭在玎玲脈上,道:「不礙事,放她到車裡陪著夫人。崔穆守在此處,我與崔躬再去查勘一下,隨後趕赴上京。」
上到峰頂,被崔逸道殺死的八名契丹人竟已不見,現場只剩八灘深褐色的污跡,散發出淡淡的腥味。崔逸道歎了口氣,料想是那巫女動的手腳,用秘藥化盡了屍體的衣服血肉。他找不到線索,只得悻悻離開。
遼立國以來,先後建有五京,即上京臨潢府、中京大定府、東京遼陽府、南京析津府與西京大同府。太祖阿保機在臨潢建造的皇都,太宗德光時改稱上京,終遼之世,一直是國家的統治中心。
白石山中淌出的南沙水,在靜穆的草原上流過,水之北是上京的皇城,水之南是上京的漢城。皇城的佈局仿唐都長安之制,然除了宮室官署、貴族宅院,城中也多氈廬,循的卻是契丹舊俗。漢城規模稍小,雜居著漢人、回鶻人、渤海人等,驛館和集市也設在此間,倒比皇城還熱鬧些。
乾統七年的夏天,濕熱不堪,尤勝往年,天祚帝早率百官去了散水原清暑,上京城中一時空了許多,守軍也有些微懈怠。皇城大順門的衛兵站在烈日下,眉梢掛著汗水結成的鹽晶,眼神渙散。驀地,他的表情專注起來,定定地看向對岸。
一名白衣男子隨一輛馬車馳來,長髮在風中揚起,容顏耀眼,令正午的熾烈陽光也為之黯淡。這一騎一車徑直入了漢城北門,衛兵忍不住閉了閉眼睛。
馬車在南橫街的客棧前停下,崔逸道躍下馬,一言不發地托著李希茗往內院去了。店主極會看事,笑嘻嘻地迎上來與崔穆交涉。崔躬茫然地站在當街,被玎玲狠狠擰了一把:「阿躬,你不要時時擺出這種如喪考妣的樣子,惹得公子和夫人更煩。」
崔逸道將李希茗放到客房的床上,正好小二端了新汲的井水來,他便取了巾子為她拭汗。李希茗額上一涼,周身的暑氣散去好些,卻只是懶怠說話,將袖子掩了面,悶悶地躺著。
崔逸道坐在床沿,神情似一把出鞘的劍,離上京越近,鋒芒越利,似乎看一看也能傷了人的眼睛。
李希茗的袖子漸漸濕了,崔逸道拿開她的手,見到不及掩飾的淚痕。玎玲冒冒失失地闖進來,見到這光景想要縮腳,卻來不及了,只得硬著頭皮道:「我和阿躬在街邊買到一種稀罕果子,聽說解暑得很,請公子和夫人品嘗。」將一個碧綠的西瓜往案上一擱,一溜煙去了。
這是西域傳到遼國的水果,中原沒有的。崔逸道瞥了一眼,道:「希茗,我切開來給你嘗嘗。你總不肯吃東西,傷口怎麼復原?」他拿起來在手上掂了掂,一劍斬下,清香四濺,露出漆黑的籽兒鮮紅的瓤。
李希茗瞧著這豔麗水果,頓時想起黑山天池畔的那場殺戮,想女兒落到那些蠻人手中,不知會招致怎樣的報復。她痛苦地喘了一聲,轉過頭去。
崔逸道看在眼裡,走過去握住她的手,緩緩道:「這兩天你總做噩夢,除了擔心夜來,也因為那場血腥吧?黑山是契丹人的聖地,他們敢在那裡動手,是什麼後果都不計了。」他的手突然用力,「我擔心你和夜來,下手就沒留餘地。」
李希茗勉力笑道:「逸哥,我既然嫁了你,就不該懼怕這種局面。就算前路血雨腥風,我也會隨你去,你不必向我解釋什麼。我只是著急,擄走夜來的那些人怎麼一去無消息了?」
「到了上京,那撥人也該現身了。無論如何,我一定會找回夜來,你別急壞了身子。」
事情的發展卻出乎崔逸道的意料,擄走夜來的契丹人再沒現過身。若在淮南,他自有大批人手調度,黑白兩道也都買他的帳;在遼國,他空有一身卓絕武功,卻只有束手等待隱在暗處的敵手。
三日後,崔逸道打發崔穆將製成乾花的金蓮送回淮南,順道聯絡遼東大豪郭服的半山堂,以極昂貴的代價換來半山堂的支持。然而半山堂的人將上京道所轄州縣和部族細細篦了三遍,也沒得到夜來的半點消息。
秋天來臨的時候,崔逸道和李希茗終於絕望,離開了上京。
長空黯淡,連著無邊無際的衰草,空氣裡浸染著淒清的蒼黃。道旁有兩個人目送崔氏車馬隆隆而去,當先的少年突然微笑起來:「八寶崔家的人,不是這麼容易死心的,以後還有文章可做。」
落後一步的是個老年僕婦,聞言躬了躬身:「主人說的是。只可惜郁里和以敵烈兩個蠢材誤事,害主人白白丟了這麼重要的籌碼。」
「丟了也罷。」少年蒼白韶秀的臉上,兩道長得幾乎連在一起的眉微微揚起,深藍的眸子裡閃著凶光,「千丹,讓他們這樣不知生死地牽掛著,這滋味才叫好呢。」
這少年只有十四五歲,說起話來卻陰冷徹骨:「想動搖這些根深葉茂的世家大族,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是我操之過急了。真寂寺才復興就遭此重創,總要好幾年才恢復得過來。以後須更加耐心,慢慢佈局,下好這盤棋。」
注:
《遼史》卷三十二《營衛志中》:「黑山在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蓮。」
第二折 蕭家觀音奴
郁里下黑山,疾馳十三里,在白水之濱追上了以敵烈。
蒼鬱的山掩住了西沉的太陽,淡金的光芒灑滿草原。以敵烈等在約定的側柏林裡,看她自無垠綠野中嫋嫋娜娜地行來。他的眼睛裡迸發出歡喜的光芒,放下嬰兒迎上去,大力抱住她。
郁里的身量只及以敵烈的肩膀,口鼻都被他的胸膛封住,頓時喘不過氣來。她奮力掙脫,嗔道:「你幹什麼?」
以敵烈打量著郁里,再度攬住她,慶幸道:「只是手上有傷。」
郁里摸著他結了血痂的耳根,「可憐的以敵烈啊,沒了耳朵的以敵烈,幸虧我們都活著。那個煞神,殺死了我們帶出來的八個人傀儡。」她猛地想起一事,驚惶地拉開以敵烈衣襟,見他貼身穿的貔貅軟甲上,赫然十幾個指甲大小的圓洞。
兩人相顧駭然,以敵烈吸了口氣,「強弓也射不穿的甲,竟然被他一指戳穿,你家傳了三代的寶物讓我給毀了。」
郁里顫抖著道:「多虧這寶甲,讓那煞神兩頭都顧不到,否則他奪回孩子再來對付我,我們只好一起送命。」她反手勾住他,大叫一聲以敵烈,似是恐懼,又似狂喜。
郁里在以敵烈懷中抖個不停,讓這粗魯漢子感到從未有過的愛憐。她溫暖而馥郁的體香滲進他的每一寸肌膚,於是每一寸都像著了火,古老的渴望猛然蘇醒。
劫後餘生的歡慶,一點火星便可燎原。
她躺在林間空地上,最後的陽光傾瀉一身,蜜色肌膚閃著柔和的金光。他熱切地覆蓋下來,充滿了她。
郁里的頸項向後彎著,彎出一個令他熱血沸騰的弧度。她睜大眼睛,望著夕陽在側柏的樹枝間燃燒,隔著寥廓的草原,是慶州城外的釋迦佛舍利塔。七十三米高的潔白寶塔,秀美無倫地立在草原上。
她注視著玲瓏的塔尖,只覺軀幹化為鄉線菊在青蔥的大地上生長,四肢化為常春藤在湛藍的穹隆上伸展,而世界成為她的花園。
白水奔流不歇,在他們身邊唱著亙古不變的調子。夏夜的暖風裡,一頭大狼悄然接近,叼起嬰兒,輕捷地去了。兩個人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正是意亂情迷之際,渾然不覺。
月亮升起又沉,柔光穿過暗綠的枝葉,仿佛碎的水晶,落在地上有錚錚之聲。
以敵烈的歎息從胸腔裡直透出來,抱著郁里道:「我們搶到這孩子,主人給我再多的賞賜也不要,我只要你。」
她水一般從他懷抱裡滑出來,惡狠狠地道:「呸,我可不是主人的賞賜!」
以敵烈靠著樹幹,愉快地大笑起來。
郁里哼了一聲,轉過頭去,臉上的玫瑰紅突然褪盡,澀聲道:「孩子呢?那孩子哪兒去了?」
以敵烈一躍而起,撲到放孩子的地方,查看四周的足跡,仰起臉在空中嗅了嗅,臉色發暗,「是野狼叼走的,咱們快追。」
郁里反而鎮定下來,「還追什麼?昨天路過涅剌越兀部時,聽說他們族中的獵手射死了狼王的孩子,惹來狼群報復,拖走了好幾個小孩,吃得骨頭都不剩。恐怕這漢人小孩已經到了狼肚子裡。」
以敵烈頹然道:「郁里,這都怪我,讓我來領主人的責罰。」他懊惱地敲著自己的頭,「方才已經把咱們得手的消息傳給主人了。」
郁里打了個寒噤:「主人為了得到這孩子,費了無數心思,我們卻把她送進了狼肚子裡。我不敢去見主人,」她一把握住他的手,「以敵烈,我們快逃走吧。」
以敵烈身體一震,「你想背叛主人?也許那孩子還活著呢,我們應該追上去。」
「若那孩子死了呢?追上去不過是空耗時間。這次帶出來的人傀儡全部折損在那煞神手裡,再空著手回去,只怕主人的懲罰比死還可怕。」郁里笑容惑人,眼神卻悲哀,「以敵烈,你沒想過離開真寂寺嗎?今天我們在黑山做了冒犯山神的事,死後一定會沉進暗黑地獄,永無出頭之日,既然如此,還顧慮什麼呢?快活一天是一天。」
說出逃走的話後,這念頭就像落到乾草堆上的火星,越燒越旺,她怕他不肯,竭力遊說著:「趁主人還沒練成冰原千展炁,我們逃走吧。到主人練成的那天,種在我們體內的烈陽珠就會被冰原千展炁感應到,從此過著縛手縛腳的日子,跟那些吃了千卷惑的人傀儡有什麼差別?」
以敵烈看了她一眼,目光炯炯如閃電,決然道:「好!」
他攔腰抱起她,翻身坐到明雪駿背上,解開韁繩放馬而去。獵獵風聲中,他大喊:「痛快,這煞神的馬比主人所有的馬都跑得快。」
郁里辨著方向,忽然道:「錯了,以敵烈,別走這邊。趁主人還沒發現,我們一直逃到宋人的地方去。」
以敵烈吃了一驚:「什麼?到宋人的地方去。」
「是,有一次主人喝醉了,我親耳聽到他說,他這一生都不能踏進宋國。」
崔逸道那匹萬中選一的神駒越跑越歡,托著兩個逃亡者,四蹄仿佛不沾地一般,溶進如洗的月色裡。
母狼的利爪撥弄著嬰兒。夏天食物充足,牠並不饑餓,只想撕裂人類的小孩,看血肉飛濺,如牠自己的孩子。但這嬰兒與以前叼到的那些不同,不哭不鬧,帶著初涉塵世的新鮮和好奇盯著牠,那樣純淨的眼睛,黑的似星光微微的夏夜,白的如嘉鹿山中的初雪。母狼的爪子慢慢鬆開,她格格地笑,向牠伸出胖乎乎的小手。
也許是餓得狠了,也許是湊巧,嬰兒本能地找到了母狼的乳頭,用力吮吸起來。母狼一激靈,眼中爆出噬血的凶光,又一點點褪去,漸漸溫柔。失去六隻小狼崽後,牠夜夜在草原上遊蕩,尋覓報仇的物件,然而那飽脹到不可宣洩的痛楚,並不是將人類的小孩連皮帶骨地吞下去就能舒緩。
牠側躺下來,讓她可以吃得更舒服。她滿足的咿呀之聲,填平牠失去孩子後的空洞。月光下,十幾雙綠油油的眼睛悄然接近,母狼警覺地站起來,齜著白牙低嘯一聲,身子微微弓起。狼群停住,面面相覷,不明白母狼的敵意從何而來。
頭狼站在離狼群較遠的高處,兇狠地瞪著母狼。頭一次,牠們沒了默契和溝通,頭狼不理解妻子這種異乎尋常的反應。對峙良久,頭狼忽然昂首長嘯,狼群漸漸散開,母狼銜著嬰兒往黑山深處奔去。
昏暗的洞穴裡,母狼撕開嬰兒的襁褓,她頸上掛的磨牙棒亦滑落到浮土中,玉色青翠,寶光瑩然。
母狼將這嬰兒的身體細細舔了兩遍,認定了她。狼群來去如風、四處遊移,母狼只能獨力養育她,而這次牠找到一個更隱蔽的洞穴,絕不讓人再奪走牠的心愛。
母狼粗糙的舌頭在細嫩的嬰兒肌膚上舔過,她放聲啼哭,似乎到此時才知害怕。嬰兒哭得倦了,昏昏沉沉地睡過去,醒來不見父母,小小人兒也不會言語,只是哭,連母狼給她哺乳時也噙著淚。
母狼也不哄她,倒有大半時間在外覓食,回來時還給她帶些新鮮血肉,嚼碎了餵她。可憐四個月大的孩子,哪裡嚥得下去,咳得臉皮紫脹,盡數吐了出來。母狼圍著她轉圈兒,雖然著急,卻是無法。
到半夜,嬰兒更發起熱來,燒得臉蛋通紅,身子滾燙。母狼遍山去找藥草,黎明才回來,在嘴中嚼出汁液,一點點餵給她。如此反覆數日,將母狼折騰得夠戧,她倒慢慢好起來。
失去人間父母的溫柔看顧,嬰兒逐漸適應了母狼的照料,細聲細氣地學著母狼嗥叫,學牠的舉止。
秋風起時,嬰兒長出了門齒,母狼開始教她撕咬血食,並且日日迫她自己爬出狼穴。狼的孩子到這年紀,早已精壯俐落地跟在母親身後到處跑了,似她這樣,實在令母狼憂心。
這狼穴隱在山腹,洞道深而陡,她每次爬到第一個緩坡便骨碌碌滾下來。母狼絕不心疼,低嗥著督促她繼續向上爬。如此過得兩月,她的四肢強壯許多,有一日竟真的爬到了洞口,母狼在她身後一頂,將她推出洞去。
天是冰晶樣的藍,陽光毫無保留地傾瀉下來,造出一個燦爛世界,一草一木,皆生光輝。彼時已是晚秋,黑山的樹大半紅透了,其間綴著金黃淺碧,世間的許多顏色突然向這孩子席捲而來,與她局促洞中時在山縫裡見到的一痕青天,不啻天壤之別,不由開心得手舞足蹈。
自此母狼便常常放她出來玩耍。從遷到此處,已經幾個月不見人跡,母狼的警戒心也就淡了。某日牠出山覓食,走得遠了些,遇上了自己那一群的狼。此時正是狼發情的季節,且頭狼與牠夫妻重逢,分外親熱,到牠離開,也戀戀不捨地跟了去。
兩匹狼一前一後地掠過草原,百米外有個十二歲的男孩,瞇著眼睛,彎弓搭箭朝牠們射去,卻哪裡射得到,只見兩匹青灰的大狼向著金紅的落日奔去,似要奔進太陽一般。男孩身後的羊群潮水般湧來,褐袍老人揚著鞭子,喊道:「鐵驪,羊要歸圈了。」
蕭鐵驪僵直的手臂頹然垂下,「阿剌爺爺,我看見叼走觀音奴的狼了,可惜隔得太遠。」
阿剌嚴肅地道:「是那條缺了左耳的頭狼和牠的母狼?鐵驪,你年紀還小,對付不了牠們。」
蕭鐵驪不服氣,卻也不多話,盯著越來越遠的兩個黑點,嘴唇緊抿著,抿出兩道細長的紋,倔強地劃過下巴。
蕭鐵驪站在黑山的隘口,身體的重心從左腳換到右腳,又從右腳換到左腳,他微微晃動著,心情也搖擺不定。最後,找到狼穴的決心戰勝了對山神的敬畏,男孩悄無聲息地穿過山體投下的巨大陰影,走進這收納所有契丹靈魂的神聖所在。他戰戰兢兢地走著,心裡反覆念誦:「黑山的神啊,我不是故意冒犯你。阿爹的魂啊,請你保佑我。」
月黯星疏,白日裡燦爛至極的一山紅葉都模糊著,整座山便似一塊碩大無朋的雞血石,細潤的黑底子上泛著微微紅暈。蕭鐵驪呼吸急促,除了深入禁地的恐懼,竟還有些興奮。他找到一棵巨大的山檀,爬進牠的樹冠裡藏好。
那天陪阿剌大爺牧羊,見頭狼和母狼一起奔進山中,蕭鐵驪就留了心。這七八日,他都見到母狼銜著食物進這隘口,不禁懷疑族裡的獵手並沒將母狼的孩子全部射死,山裡還藏著母狼的幼崽。
蕭鐵驪空等了一夜,卻不氣餒。等到第三夜,果然見到母狼從山裡出來,只是過隘口時步伐有些遲疑。蕭鐵驪不知牠是否聞出了自己的味道,抱著樹幹,大氣兒不敢透一口。他每次出來,都在白水洗過,衣帽靴襪一概不穿,赤身進山,此刻不由懊惱地想,狼鼻子靈得很,多半瞞不過去。
母狼東張西望了一陣便去了,蕭鐵驪仍然一動不動地伏在樹上。他聽族裡的獵人講,狼性狡猾,既然起了疑,只怕還會折回來。蕭鐵驪等了良久,只覺耐性磨成了一張紙,一捅就要破了。就在他再也忍不住時,母狼的身影在隘口一晃而過,輕巧得沒半點聲音。
瞧著母狼沒進草原的夜色,蕭鐵驪又等了小半個時辰,方才下樹,長吁一口氣,想這回母狼是真的去了。他潛行到山外的一個草窪子旁,穿上衣服,彎指打了個呼哨,一條健碩的大狗便竄了出來。男孩帶著狗直撲母狼頭次現身時的林子,狗低頭在地上嗅著,果決地往山上奔去,在一道山脊上停住,狺狺低吠。
蕭鐵驪見再行幾步便是黑沉沉的山谷,分明找到一條絕路上來,不由詫異。他走到山脊邊緣向下看去,發現山壁上裂著一道大縫,怪石嶙峋,犬牙交錯,仿佛一個上古怪獸踞伏在他腳下,等他掉進張開的大嘴。這怪獸的嘴是俗稱地包天的那種,下唇凸出很多,方圓足有七八丈。
風中飄來淡淡的狼臊味兒,狗先耐不住,一躍而下,對著主人興奮地狂叫。蕭鐵驪做了個噤聲的手勢,慢慢滑下去,在怪獸的「唇」上站定。一直躲在雲層後的月亮恰在此際探出臉,銀練似的光輝瀉下來,令蕭鐵驪看得分明,怪獸的「咽喉」部位有個黑沉沉的洞口。
蕭鐵驪知道狼崽多半在春天出生,長到這時候已不會躲在狼穴裡,但母狼的行蹤證實牠還有幼崽。男孩沒有半點猶豫,喝住躍躍欲試的狗,自己鑽進洞去。他要親手逮到狼崽子,用作引誘整個狼群的餌,給可憐的妹妹報仇。
狼穴很深,一直鑽到盡頭,蕭鐵驪方能直起腰來。洞壁的縫隙透進一線月光,雖然昏暗,但他目力甚好,借著這縷光已瞧見壁角縮著一隻瑟瑟發抖的小獸。
蕭鐵驪鬆開汗濕的刀柄,撲上去逮那小獸,觸手之處滑膩無比,令他大吃一驚,拎到光下看時,哪裡是什麼狼崽,竟是個一歲不到的孩子,雙足亂蹬,嘴裡發出尖利的嗥叫。
蕭鐵驪歡喜得一顆心像要從腔子裡蹦出來。「觀音奴還活著,觀音奴還活著……」他迷糊了一會兒,猛地省起母狼隨時都會回來,連忙脫下短袍,嚴嚴實實地裹好孩子,縛到自己背上。男孩渾身都是勁兒,飛快地爬出狼洞。
直到出了黑山,淌過白水,瞅見部族的營盤,蕭鐵驪懸在半空的心才踏踏實實地歸了位。緊繃的神經一鬆下來,隨即感到頸項疼痛難忍,他伸手一摸,指上帶出淡淡的血痕,卻是背上的孩子咬的,不由低聲道:「觀音奴啊觀音奴,你變得跟狼一樣了,才長出幾顆乳牙呢,咬人就這樣狠。」說著埋怨的話,快樂卻漲滿胸膛,一溜煙地跑向自家氈房。
氈房裡傳出模糊的人聲,蕭鐵驪詫異地停住腳,略一分辨,頓時僵在當地,面孔漲得通紅。
他聽到母親綿軟的聲音:「移剌,你該走了。」
蕭移剌懶洋洋地回答:「鐵驪要回來了,所以趕我走?我來找你是光明正大的事情,為甚要躲著藏著?大哥死了,你自然歸我,連鐵驪都是我的。」他說的是契丹人「報寡嫂」的風俗,哥哥死了,弟弟便可娶嫂子為妻,這是宗族賦予弟弟的權利,同時也是他的責任。
女人長歎一口氣,「你還不明白鐵驪的性子麼?他死也不肯的。」
蕭移剌大聲道:「這可由不得他!」他話音未落,氈房的簾子已被人挑開,清澈的晨光和著微涼的空氣一起湧入,一個男孩逆光而立,怒目瞪著糾纏在一起的男女。耶律歌奴慌忙推開蕭移剌,掩住裸露的前胸。
蕭鐵驪右手握著一把鑌鐵長刀,轉側間刀光雪亮。蕭移剌一驚之下也拔刀而起,兩條腿卻被耶律歌奴死死抱住,不由發急:「放開,放開,你這婆娘到底幫誰?」
耶律歌奴叫道:「你要碰我兒子,除非殺了我。」她轉向男孩,「鐵驪,你想做什麼?這是你親叔叔!我為你阿爹守了一年,現在決心嫁給他了。」
蕭鐵驪見母親伏在男人腳下,神情倉皇,卻有種說不出的嫵媚宛轉,是父親在世時從沒有過的,不由得熱血直衝頭頂,狂怒中舉刀道:「黑山大神作證,我蕭鐵驪只有一個阿爹,決不會再認第二個。我也只有一個阿媽,決不與移剌家的孩子一起奉養。我只聽你一句話,要我還是要他?」
耶律歌奴愕然鬆手,慢慢站起來,心想:果然是他的孩子,一樣的強橫霸道,一樣的不顧惜人不體恤人。多年潛藏的怨恨忽然在這刻洶湧而出,她站得筆直,一字字道:「當年是移剌聘了我,卻被你爹強奪過來。我幾次逃走,都被你爹攔下,後來有了你,我才認命。如今你爹死了,我要嫁自己喜歡的男子,憑你去問天上地下所有的神,看誰說我耶律歌奴不該。」
蕭鐵驪眼中的火苗忽然熄滅,手中長刀無聲無息地落在氈毯上,頭也不回地衝出了氈房。耶律歌奴追了幾步,伸出手去,只挽住了清冷的空氣。鐵驪的名字在她舌尖滾得幾滾,終於未能出口。
蕭移剌攬住她,苦笑道:「歌奴,你既然選了我,就別想留得住鐵驪了。」他疑惑地摸摸頭,「不過,鐵驪背的是什麼東西,軟綿綿的還在動。」
蕭鐵驪僵著脖子走出母親的視線,拔足狂奔起來。呼嘯的風拍打著他的身軀,疼痛中滿含快意。他不知跑了多久,直到腳下一絆,跌進草叢。
他爬起來抹了一把臉,濕漉漉地有汗也有淚,這才清醒些,記起自己還背著狼穴裡撿回來的觀音奴。男孩解開短袍,見髒兮兮的小孩兒蜷成一團,眼睛緊閉著,似乎很畏懼白天的光線。
蕭鐵驪低聲道:「觀音奴啊,阿爹死了,阿媽也不要我們了。你害怕麼,你難過麼?」他問著問著,只覺眼眶一陣發熱,勉力忍住,將那溫暖的小東西貼在自己胸口,「你別怕,哥哥會護著你,再不讓狼把你叼走,不讓任何人欺負你。」
他抱著她沒有目的地亂走,搖搖晃晃地走了許久,來到白水的一條支流旁,男孩忍不住跳了進去。浸在清涼的水裡,他覺得好過很多,小孩卻很抗拒,嗚嗚叫著,使勁撲騰。
「觀音奴,你一身狼味兒,要好好洗洗。」蕭鐵驪嘀咕著,不理她的抓撓撕咬,透徹地將她洗了一遍。
蕭鐵驪站在齊腰深的水裡,舉起洗乾淨的小孩,不由呆住了。秋日的明淨光線裡,孩子極少接觸陽光的皮膚好似新鮮羊乳,潔白晶瑩。他想不到一個人的眉眼能生得這樣好看,而這夢一般的美麗竟托在自己掌心。
他猶豫地伸出手,拍拍她的臉蛋,被她一口逮住,再不鬆開。男孩痛極,卻笑道:「觀音奴餓了麼?哥哥給你找吃的去。」
蕭鐵驪明白她不是自己的妹妹,而是母狼從別家叼來,可這有什麼關係?他丟了一個觀音奴,黑山之神便還了他另一個。從此這高天廣地,他只能與觀音奴一起相依為命了。
注:
《遼史》卷五十三《禮志六》:「黑山在境北,俗謂國人魂魄,其神司之,猶中國之岱宗雲。每歲是日(即冬至日),五京進紙造人馬萬餘事,祭山而焚之。俗甚嚴畏,非祭不敢近山。」
第一折 宛轉豔歌行
大興安嶺曼衍北疆,到與燕山交接之處,生出一座挺秀的峰來,契丹人呼作黑山,後世稱為賽汗罕烏拉。傳說黑山是天神居所,契丹人死後,靈魂必定歸於此處,受黑山之神管轄,所以契丹人視黑山為聖地,若非祭祀,不敢近山。
遼國天祚帝乾統七年(一一○七)的夏天,黑山道上,轔轔的車聲碾破了一山寂靜。
車帷挽著,露出一個碧衣女子的側影,鴉鬢雪膚,風致楚楚。車後,兩名男子騎馬相隨,當先一騎白衫素履,神情軒朗如朝霞初舉,光耀幽深山道;殿後的少年著淺藍布袍,身形瘦削,氣質乾淨。
行至半山,車中突然響起嬰兒...


 2010/07/18
2010/07/18 2010/04/13
2010/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