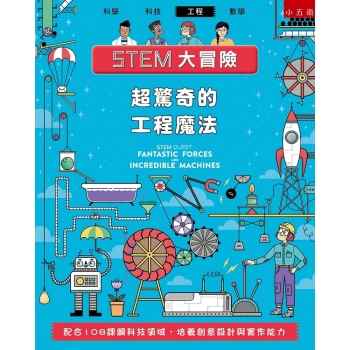第四個月:路殤
我學校有條隱密的黑色小路。
小鎮開荒以後,學校也興建起來。後來曾翻新過一次,但校舍依然不可避免地走向頹敗的局面。滾紅的陽光直落落灑在白亮亮的鐵皮屋,映出赭紅色的耀眼光芒。大雨過後,挾帶雨水而來的泥土顆粒洋洋灑灑滾落屋頂上。殘破簡陋的教室,經過日晒雨淋的侵蝕,斑駁的牆壁縫隙冒出墨綠色青苔;熱帶藤蔓植物攀沿著外牆角往天幕的方向,一路蜿蜒到屋頂。
建校初期,校舍後方有處僻靜地,原是用作師生的廁所。剛搭建好梁柱骨架,卻臨時改換他處建廁所。工程完畢後,工人們似乎忘記將那幾間殘破的廁所拆卸下來,校方為了省錢省事也選擇忽略它的存在,任其廢置。舊廁所四周長滿白花花的野芒草,在紅豔豔的日光下,露出光禿禿的磚柱骨幹,像一座聳立撐起的骨骸。久而久之,那片僻靜地縈繞著詭譎陰森的氛圍。傳說,曾有稚齡小孩掉落某間廁所洞口而死。夜裡經過那附近,會傳出孩童的哭泣聲。我和同學們對並未經過證實的事,產生莫名所以的恐懼。我們刻意避開靠近那鬼魅的地方,但它卻擁有一股強大的魔力,牽引出我們想一窺究竟的衝動。
有天,我走近那兒。
那天放學後,我隨人潮緩慢步出教室,抬起頭仰望蔚藍似大海的天空,暑熱的日光蒸散了天際的白雲,無風,顆粒狀的塵埃飄浮在凝滯的空氣中。氣溫持續沸騰,我腦袋昏沉沉,耳邊突然響起一陣淒厲的狗吠聲,我嚇了一大跳,馬上彈開。我朦朧恍惚中,不小心踩到狗尾巴。那隻毛髮髒兮兮的小狗原本趴在路邊午睡,被我驚醒後,聳起身,拖著瘸腿拐往校舍後方的小路,牠用渾濁的黑褐色眼瞳回望我,無力地搖晃剛被我踩著的尾巴,轉身繼續瘸行。我看著那可憐的小狗,不知道牠要去哪裡,我好奇地尾隨牠。
我的步伐不知不覺遠離教室和學校範圍,來到荒廢的校園盡頭。廢棄的廁所孤伶伶矗立在草叢中,陽光拂照著空蕩蕩的屋殼,彷彿有幾抹幽魂飄遊其間。那瞬間,我豎起全身汗毛,想逃離此處。倏地,那隻瘸狗朝我吠了數聲,勾回我的思緒,也穩定了我的心魂。我搜尋牠的蹤影,只見牠停駐在長長的籬笆邊。我瞧了瞧周圍的景緻。萬簇的紫色牽牛花叢纏繞在生鏽的圍籬上,破舊的鐵閘門虛掩,小狗慢慢鑽入閘門空隙,來到籬笆外頭。牠停下來看了看我,哀怨地吠了一聲,似乎在等待我,接著低頭緩慢地走向前方小路。我不由自主跟上去,使出吃奶的力氣才推開閘門一點點的距離,我微微喘氣,側著身子從半開的閘門溜出去。
我離開了學校的區域和嘈雜的街市,彷彿進入一個迥異的世界。我目光飄忽,搜尋引我前來的小狗。終於,我在一個女子的身邊發現了牠的蹤影。那女子是蘇瑪,她站在分岔路口,晃動的身影似乎猶豫著要走往哪條小路,她腳邊的小狗汪汪叫起來,搖晃乏力的尾巴望著她。
※ ※ ※
人們開始留意蘇瑪的存在,是源於她發瘋。
與我同年齡的孩子,見她出現在大街上,興致就來了。大伙圍擠上來,頂著熟透的紅日頭,緊跟隨她顛簸的身影,沿著零亂、鬧烘烘的大路漫走下去。他們嗤笑她遲鈍、笨拙的神態和舉止。有時,蘇瑪不慎跌跤,不喊痛,蹲下身,雙腳敞開,默默擦掉那些乾炙的沙子,傻笑著,無意中露出她泛黃的高腰內褲,他們就爆笑不止,交頭接耳。每天,他們等待她出現,然後跟在她背後,圍繞她,期待她做出滑稽的事,當作一天的樂趣。
關於她的發瘋,在口訛相傳間,聽過幾種說法。有說某個寂靜的夜晚,人們沉陷在睡夢中,長屋裡忽然傳出悽愴的哭喊,尖銳的女聲劃破長空。那天過後,她連續在夜裡就寢時間痛哭出聲,接著變本加厲,天色近黃昏時默默哭泣,甚至在屋子裡狂亂蹦跳,胡言亂語,擁有比平時強大的力氣,沒人敢親近她。大家都說她中了可怕的降頭。另一種說法是她孩子病死的事實徹底痛擊她。聽媽媽提過,她的孩子大約我這年紀,有天肚子劇烈疼痛,那孩子洗澡後,過不久開始發高燒。有人說他得了毛丹,蘇瑪馬上用雞毛浸過溫水清洗孩子的身體,取來雞蛋來回搓揉他全身。撥開蛋殼一看,全是黑色的羽毛。情況沒有好轉,她的孩子高燒一天一夜後,身軀發黑致死。還有說她的丈夫無故失蹤的那天起,她漸漸變得神智不清,時常遊蕩在大街路和舊街,徘徊於各家商店走廊、碼頭、大樹林邊緣,想尋找丈夫的蹤影。
蘇瑪身材矮小,黝黑的膚色發亮如珍珠,深邃的五官蘊含一絲野氣。她是名卡達山族女子。她爸爸曾是我們東林店的勞工,前幾年,她還和家人住在我爸爸提供的員工長屋宿舍裡,直到她和一名菲律賓的非法外勞發生感情,在她父母的反對下漏夜私奔到鄰近的斗湖市。她爸爸為此事忿怒,數天後在凌晨暴斃,她未回來奔喪,鎮上的人紛紛譴責她。後來再看到蘇瑪是在她媽媽的喪禮上,我剛讀小學一年級。年老的女祭司在為她媽媽的靈體吟誦、祝禱的時候,她攜她丈夫前來長屋奔喪。圍觀的人群一陣嘩然,私底下議論紛紛,一度中斷了祭祀的儀式。她看起來憔悴許多,身軀乾癟得像一尾風乾的鹹魚,皮膚暗淡,失去光澤。她閃動著迷茫的眼神,蹣跚地走向她媽媽的靈柩,緩慢跪下來,輕輕啜泣,氣若游絲地細語。人們拉起耳廓,唇齒碰撞,掀起一陣騷動。她這趟回來,決定長住下來。爸媽輾轉聽說她的丈夫在斗湖市丟了工作,又欠下一屁股債務,走投無路下逃回古納鎮避難。
蘇瑪發瘋以後,變成小鎮的守護者。每天大清早,曦光灑落在坑洞處處的路上,光影忽明忽滅的時候,她恍惚出現在學校的校門前,經過我身邊,露出兩排黃牙,對我傻笑,好像認得我,似乎又不是。她頂著蓬鬆的亂髮,手裡抱著骯髒的假娃娃,嘴裡念道:「寶寶乖,不痛喔,媽媽幫妳秀秀。」耐著性子等到放學,我飛也似地奔向大街,發現她流連在路旁、商店的五角基,似乎沒有什麼人理睬她。她宛若孩童,睜大幼稚的眼眸,貪婪地凝視那些琳琅滿目的物品,忍不住觸碰,招來店家嫌惡的眼神,厲聲叱罵她,催趕她離開。她痴笑走開,繼續走向舊街、馬來甘榜、蔭翳的樹林區。日落前,東林店打烊了,爸媽帶我回家,蘇瑪靜默地從碼頭漫步回返,環繞完小鎮一圈。日復一日,從白晝到黑夜,她不停歇地遊走在鎮上。
起初,大人們對於她這番奇特的舉動不以為意,只當作他們茶餘飯後偶爾談論的話題。蘇瑪像是一幅流動的風景,供小孩子觀賞的餘興節目。不知從何時開始,她的身邊圍聚著一群孩子,有的比我還小,尚未讀書;有的一放了學,不顧身上穿著校服,揹著書包,馬上混跡其中。他們膚色有深有淺,有男有女,毫不在意她全身隱隱散發的腐臭味,加入這遊行隊伍,嬉鬧蘇瑪來消解苦悶無聊的孩童生活。一伙人放肆走在路上,漸漸驚動大人們。有一次,我蹲在東林店的門廊邊,雙手托起下巴,無精打采地打起盹。不遠處傳來嬉笑怒罵聲,我驚醒過來,面露狐疑,抬眼望去,那群孩子推擠著蘇瑪前進,拉扯她的衣角,把她當有趣的玩具耍弄。他們太過分了!怎麼可以欺負她?我忿怒地站起身,感到手足無措時,突然,幾位身材臃腫、肥胖的婦女奔走過來,滿臉怒容地對著自己的孩子咆哮起來。她們將孩子從蘇瑪身邊拖離,對著她嘶吼:「滾開!」有一人把她推落在地。那些孩子嚇壞了,有的大哭起來,有的低頭靜默,不敢出聲。「聽著,以後不許靠近她!」有一位婦女瞪視她那滿身髒兮兮的孩子,叱罵道:「髒死了,快回家洗澡,聽到了沒?」然後拼命拉著她孩子離去。
突如其來的騷動纏繞了路人的目光。他們湧上來,七嘴八舌交談著,有的人遠遠觀望著看好戲。我趕快跑去叫爸媽。爸爸知情後,闖進人群,媽媽把我拉到身後,不讓我靠近混亂的現場。我從縫隙偷窺,爸爸扶起跌坐路旁的蘇瑪,她傻楞楞瞅著他,不知周遭發生什麼事,歪斜著腦袋,緊攫住手中的假娃娃。爸爸輕拍她的肩膀,安撫她,斡旋於那幾位婦女間,向她們講道理、解釋,才平息這場糾紛。沒戲唱了,人群鳥獸散,舊街恢復原本漠然的景象,頃刻間,天色早已暗去。
婦女們嚴禁那群孩子追隨蘇瑪遊街後,她又孤伶伶了。我默默留意她,發現她已不如前幾年豐腴,現在的她骨瘦如柴。我懷疑她是否有吃三餐,常常見她徘徊在大街上,撿餐廳的剩餘飯菜;向路人乞討,惹來嫌棄;翻找路邊垃圾堆腐爛的殘渣糊口。我爸爸感念她父親曾是員工的情分,不忍心她這模樣,經常派我拿些飯菜給她。久了,她似乎有點認得我,每次我出現在她面前,她的嘴角就不自覺彎起來,湊著我痴痴笑。
謠言越演越烈,鋪天蓋地傳遍小鎮。那些婦女忿怒不平,向她們的丈夫咬耳朵,閒言閒語散播的速度比光速還迅猛。大人們搬出蘇瑪的過往經歷,關於她父母、丈夫和小孩的事,透過不同的人口中不斷轉述,像螫人的大黃蜂慌亂竄飛,一切都變了調。
幾天以後的下午,天氣異常炙熱,火焰般的太陽像頭暴怒的猛獸,兇狠地踐踏街道,熱風吹得粒粒沙子熨過大路,空氣渾濁難耐。街上路人稀少,幾名衣衫襤褸的乞丐徘徊在亞答屋和路邊。我在東林店悶得發慌,取得媽媽的允許後,我從舊街一路遊蕩,不消一會兒背部就汗涔涔。我不知不覺來到亞都茶餐室,裡頭的喧囂景況吸引我的目光,我冒然闖進去。茶餐室裡鬧烘烘,空氣的溫度隨著沸騰的喧譁聲掀湧上升,大人們閒來無事,有的一屁股挨坐下來,還有的倚著別人的肩膊斜站在旁,甚至有人蹲踞在梁柱邊,全圍聚於此,我閃避簇擁的人群,躡手躡腳躲坐在僻暗角落。
沒有人注意我,我隱身在暗處,睜大烏黑的眼瞳,毫無顧忌地注視他們。店裡那個又矮又瘦,長相有點猥瑣的小伙子嘴裡嚼著煙草,手中拿塊抹布,手腳俐落,迅速抹淨餐桌,搬弄油膩膩的嘴皮子,周旋於人客間,招呼他們入座、點餐,扯開沙啞的嗓門,朝廚房和茶水間嘶喊。耐不住性子的粗魯男子揮掌拍桌,嚷叫何時上菜,端菜的妙齡女子匆匆在廚房和餐桌廊上鑽進鑽出,杯盤相互碰擊,瑩亮的水光迸濺,男女人聲忽起忽落,聲光游離。我聽不清男人們在談論什麼話題,他們的聲音相互疊合,像交纏打鬥的人體,誰也不想輸了陣腳,被另一人拽下來。我勾起濃濃的好奇心,豎起雙耳,凝神掃過每一張表情靈動、興味高昂的臉孔,滔滔不絕笑鬧開來。
我的前方坐了七八名流裡流氣的莽漢。他們目光閃爍不定,不曉得懷著什麼肚臍眼鬼計,壓低嗓子交談。
欸,你的意思是──你那晚看見了……
沒錯!她丈夫往那條黑色的路走去……鬼鬼祟祟的……
呿!別騙肖了!你當我毛頭小子啊!
信不信由你!
哈,話說回來,你怎麼能確定是他?
哼!有興趣了吧!
對啦,大爺您說明白點吧!小的洗耳恭聽。
這還差不多!
有人擠身過來,我聽得模模糊糊,周圍的嘈雜聲不絕於耳,我頓覺腦袋轟轟響,耳畔嚶嚶嗡嗡迴盪。短暫的閃神,使我錯過他們之間的對話,我回過神,屏氣凝視坐在我對面,帶頭敘述的男子。他眉宇間蘊含邪氣,嘴角歪斜,左下巴上芝麻大小的黑痣在他講話時不停微微抖動,顯得滑稽又礙眼。我端詳了一會兒,暗自心想,那不是林瀚嗎?
男人們顯得不耐煩,鼓噪著,滿臉狐疑望向林瀚,弓起身子往前傾。
別急,聽我說!
少賣關子,有屁快放!
我這不就講了!
林瀚歪著身子,一副吊兒郎當的模樣。我盯著他瞧,他彷彿意識到有人注視,朝我的方向瞥了一眼,我渾身不自覺起疙瘩。他微低垂頭,攬著其他人的肩膀和脖子,怪聲怪調繼續往下說,我豎起雙耳傾聽──那晚天色漸黯淡下來,這時候人煙稀少,那條路附近也不會有人經過。我當時走在樹林邊緣,忽然聽見窸窣的聲響,我馬上警覺起來,還以為會是野山豬或大蜥蜴之類的。雖然內心有點恐懼,但我又覺得好奇,就小心翼翼躲在一棵大樹後窺視。那時樹林邊緣和附近的紅泥路一片暗濛濛,我屏息瞅著,哪有什麼野獸,只是個路人剛好闖入這一帶。那人鬼祟地閃現路口,踉踉蹌蹌走在黑色小路上,朝樹林方向的前路行去。這麼晚了還有人經過此地,我心生疑惑,就多看兩眼,赫然發現那人是蘇瑪的丈夫!我怎會如此肯定?你們別忘了,他曾在市集中為了一把獵槍和我起爭執,當晚他手裡就是握著那把獵槍,更何況他那張像極老鼠的尖酸臉龐,化成灰,我也認得!我靜靜躲著,不想讓他逮著我,你們要知道,我和他可是結下梁子,如果他牢記那場爭吵,看我不對盤,突然擦槍走火什麼的,一發子彈就能將我斃命,我早已升天啦!哼,你們太瞧不起我了!我藏得可好呢!
太奇怪了!這麼晚了,他拿著把獵槍,是要幹嘛?
該不會是從山林打獵回來吧?
要是這樣的話,我可沒看到他打了什麼野豬野兔的啦!
那一定是他的狩獵技術奇差無比!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弔詭的是,那晚之後,沒過幾天,傳出他失蹤啦,不久蘇瑪就變得瘋瘋癲癲了!
你講這話是什麼意思啊?說明白點!
我懷疑那晚他走那條路逃走啦!
喔……
喔什麼喔,給點反應行不行?
哎呀,為什麼要逃走啊?
鬼才知道,哈哈!
……
他們談到後來沒有理出正經的結論,嬉笑怒罵地結束蘇瑪和她丈夫的八卦。那一桌有人轉移了話題,開始聊到最近這起周老闆的命案。他們刻意壓低嗓門,臉色凝重地交談,我聽得模模糊糊,眼皮頻眨,空氣悶熱,撩得我昏昏欲睡,最後索性離開嘈鬧的茶餐室,走回東林店找媽媽,天黑前一起回家。
流言曝光後,像海浪,一波接著一波,迅速散佈到鎮上人們的耳中。平時麻木的人們眼神開始變得熱烈起來,他們熱切談論蘇瑪丈夫失蹤的原因,互問對方是否曾在那天夜晚見過蘇瑪的丈夫,探聽一切可疑的線索。他們紛紛懷疑這起無故失蹤事件和周老闆的死亡是否有關聯。人們之間掀起相互猜忌和揣度的小風波。鎮上的人都知道,周老闆雇用大量的非法外勞為他做許多粗重的勞動工作。他們不分晝夜被分配在魚市場碼頭和海鮮批發店工作。為了牟利,周老闆不斷壓榨他們的工資,甚至賒欠工資不還。有一陣子還引起靜默抗議的事件,但此事沒有張揚到政府單位,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假裝沒這回事。我耳裡充塞著大人們粗暴和巨大的歧異聲音:學校裡,從幾位師長身邊走過;貌似流氓的兩三名莽漢半蹲在臭氣熏天的垃圾堆邊,嘴裡叼著香菸,粗聲粗氣交談著;平房前閒話家常的婦女們,看顧小孩的同時,也交換著鎮上每日的八卦訊息;沒客人上門時,商家無聊地在門廊前觀望,和隔壁店家閒聊上幾句;路人漫談著穿越街道;遊走在喧騰的市集販攤之中。這些紛雜的聲響化成畫面、氣味穿梭於我的感官,在我日常生活裡不斷繁衍成一隻可怕暴怒的猛獸,伺機襲擊我。
※ ※ ※
我溜出學校後門,踩在黑色小路上,是那隻小狗冥冥中引領我遇見了蘇瑪。我站在圍籬外,筆直且遠長的小路往前方綿延開展,兩旁蔓生繁茂的矮樹叢,枝葉和根芽的芬香氣味直竄入鼻子。我望向矮樹叢的盡頭,蘇瑪佝僂著身子站在分岔路口,腳邊的狗兒倏然吠起來,像是催促她前行,她嚇了一大跳。我好奇她竟出現在這隱密的林間,難道她每天環繞小鎮的路線也包括這裡嗎?我疑惑不解,邁開輕緩的步履,跟上去,不讓她發現我。媽媽曾說,這幽祕的黑色小路是條人工路,戰後的發展商為了方便伐木工作和開發種植園區,將原本的小溪填平,墾出這蜿蜒漫長的路徑,直通向大樹林深處。黑褐色的泥土散發著濃郁的腐爛物晒乾後的氣味。路面上坑坑窪窪、凹陷不平,隆起的小黑蟻丘向四面八方蔓延,暴烈的陽光下,蟻群黑壓壓一片,摻雜在黑土裡。我感覺雙腳麻麻的,手抹去一看,是噬血肉的黑螞蟻,我不停擺手揮落,跺腳踩葉,想甩開牠們。而且,似乎有什麼東西在我的腳踝處輕輕蠕動,我俯身探看,嚇呆了!那……不是螞蝗嗎?臃肥的環肚黏吸著腳踝,爸爸曾在大森林裡被這類可怕的螞蝗吮吸手臂的血,那時他還翻閱熱帶雨林的昆蟲圖鑑,指著牠給我看!我驚慌得下意識撿起壤土上的枯葉,死命用枯葉撥除腳上的螞蝗,再將牠往遠處扔擲。我摸索腳踝,幸好還沒被吸噬,沒留下傷口,我鬆了一口氣,不想一個人留在原地,只好迅速跑上前,追隨蘇瑪。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母墟的圖書 |
 |
母墟 作者:黃瑋霜 出版社: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9-2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7 |
二手中文書 |
$ 205 |
中文書 |
$ 205 |
中文現代文學 |
$ 221 |
小說/文學 |
$ 229 |
小說 |
$ 234 |
美國文學 |
$ 234 |
現代小說 |
$ 23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母墟
◎東華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培育作家又一波!
◎東華創英所曾珍珍教授 專文推薦!
◎馬華文學最受矚目的後起之秀黃瑋霜,首部長篇小說!
就在那天夜裡,我的影子決定離家出走……
透過一個小女孩的安靜凝視,折射出喧譁的人世叢林
小說版《神隱少女》
一場蠻荒而奇幻的雨林漫遊!
「妳終究要回到生命的最初。」影子說。
媽媽點燃蠟燭,照亮昏暗的客廳。燭光搖曳不定,照著她乾裂的嘴唇,一張臉泛著黃光。她在屋子裡來回踱步,她的影子妖媚地映照在牆壁上。我看著牆上飄移的影子,發現其中沒有我的影子,我不能用雙手變化出各種動物的影子了。
漫遊,是為了能再次找到回家的路
承襲馬來西亞作家的濃厚熱帶文學風格,《母墟》是馬華新秀黃瑋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她以懷胎九月的時程為骨架,以童年印記為血肉,似虛若實地鋪展出一長串失落與追尋的故事。就如《神隱少女》裡的千尋,小舞在沒有父母庇護之時,憑著孩童那不可思議的本能和直覺,四處冒險闖蕩。一個瘋婆子與一個十歲小女孩,以及一隻野狗,就這樣在廣大無邊的雨林和橡膠園中穿梭流連。
黃瑋霜以純真不造作之筆,層層剝開鄉野小鎮的內裡,透過小舞敏感不安的雙眼,我們看到作者筆下的魔幻熱帶風情背後,愈顯狂野、赤裸的人心騷動……
作者簡介:
黃瑋霜
一九八一年出生於馬來西亞。中學畢業後赴台就學。國立政治大學金融學系兼中文輔系畢業。由於嚮往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坊的創作環境,後赴花蓮的國立東華大學,就讀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獲藝術碩士。
作品曾獲國立政治大學道南文學獎散文首獎和小說佳作、新加坡國際華文散文優勝獎、馬來西亞星雲文學獎散文優秀獎等。曾獲馬來西亞南大小說出版基金、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彈奏第六級文憑和樂理第五級文憑。著有合輯《偷窺》(東華創作所文集I)。目前從事文字工作。
章節試閱
第四個月:路殤我學校有條隱密的黑色小路。小鎮開荒以後,學校也興建起來。後來曾翻新過一次,但校舍依然不可避免地走向頹敗的局面。滾紅的陽光直落落灑在白亮亮的鐵皮屋,映出赭紅色的耀眼光芒。大雨過後,挾帶雨水而來的泥土顆粒洋洋灑灑滾落屋頂上。殘破簡陋的教室,經過日晒雨淋的侵蝕,斑駁的牆壁縫隙冒出墨綠色青苔;熱帶藤蔓植物攀沿著外牆角往天幕的方向,一路蜿蜒到屋頂。建校初期,校舍後方有處僻靜地,原是用作師生的廁所。剛搭建好梁柱骨架,卻臨時改換他處建廁所。工程完畢後,工人們似乎忘記將那幾間殘破的廁所拆卸下來,校...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黃瑋霜
- 出版社: 寶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9-20 ISBN/ISSN:978986624960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