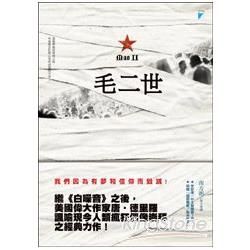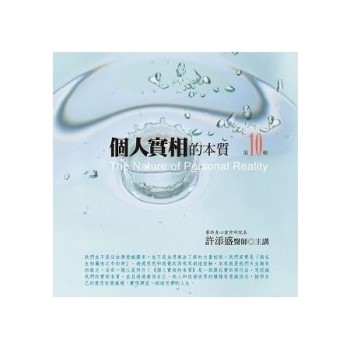導讀
唐.德里羅不安的眼神!
一九八五年,美國當代主要作家唐.德里羅出版了他的第八本小說《白噪音》,該書獲得當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入選「時代雜誌一百大小說」,並被評論界譽為是後現代主義小說的經典之作,該書也很快進入了大學的文學研究講堂,其中文譯本也於二○○九年於台灣上市。
繼《白噪音》之後,一九九一年唐.德里羅出版了他的第十本創作《毛二世》。這部作品一出,同樣驚動了各方,不但為他獲得了「國際筆會福克納獎」,而且隨著國際社會的演變,極權及恐怖主義蔓延,而這些都是《毛二世》的主題之一。於是使得該書更長期被討論,譽之為對時代心靈有著見微知著的異稟。現在這本著作的中譯本也開始和大家見面。
首先,《毛二世》的書名,它乃取材自普普藝術家安迪.沃荷(Andy Warhol, 一九二八-一九八七。)的同名絲印畫。安迪.沃荷的藝術,乃是透過攝影複製的風格,將藝術作品以商品複製的形式瓦解其獨特性。將毛澤東、瑪麗蓮.夢露,甚或可口可樂罐裝圖畫以這種複製的方式呈現,一方面用商業顛覆了藝術,另方面也等於用庸俗顛覆了政治的擬神聖性。唐.德里羅以毛澤東的這幅絲印畫題目為書名,可以想像得到他是要把毛澤東這種偶像式的人物,透過反諷、嘲謔、複製等方式,將他的偶像性抹除,使它成為歷史過程中的一則笑談。他的《毛二世》從書名開始,即顯露出他那種「塗抹」的後現代風格。「塗抹」是把從前過度渲染,因而蓋住別的頁面的油彩抹消抹掉,其他被蓋掉的才可重見天日。
但如果人們讀了《毛二世》,即可發現唐.德里羅做為當今後現代主義的寫作大師,他其實並沒有如此狹窄,而且有關毛澤東這個題材只不過是書中的一部分而已,甚至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當代美國主要文學理論家之一──杜克大學教授林特濟查(Frank Lentricchia)乃是唐.德里羅權威學者,他即指出,如果讀者只是想在他的作品裡尋找容易辨認的道德中心,那就一定會覺得很受挫折,因為他的作品實在太易讀太難懂了:
「他是對這個讓我們快樂不起來的世界做著文化解剖,而同時這個解剖家又對語言中的句子和詞彙深深愛好,當他在描述不同的聲音時顯露出極大的睿智,並且有真正的蓬勃活力。他的作品除了實況的景象外,還有一種文學的愉悅感。因此作品最後的視野是既可怕又美的。」「他的作品代表了美國文學上的一種罕有成就。小說家的想像和文化批判有了完美的混合。」
因此,唐.德里羅的作品乃是當代難懂的典型代表。他的作品當然有大的主題,但他的主題並非單一的題旨,而是在這個主題下將各種相關的現象揉合在一起,而後將這些現象做出夾敘夾議的發抒。唐.德里羅最特殊之處,乃是他在夾敘夾議的敘述中,展現出他罕有的文化觀察與文化批判思維能力。他總是能在現象的辯陳間找到可以落斧鑿之處,而嵌入他那種懷疑、嘲諷、深度的憂慮。由於他的語言之斧從不針對單一的題旨而發,因此讀者就很容易掉進他的情節編織和語言串聯中,彷彿進入了迷宮一樣。就敘述而言,他所營造的效果,彷佛有如一個封閉的「迴路」(Loop),在兜了一大圈之後,似乎仍找不到清晰的出口。
就以《毛二世》為例,他的維京出版公司主編,本身也是作家的格拉罕(Nan Graham)就說過:「在唐.德里羅寫作之前,他就告訴過我,他存了兩個資料卷宗,一個標明是『藝術』,一個標明是『恐怖』。這顯示出藝術家的本質處境,以及人類的恐怖主義問題早就進入了他的思想之中。」而《毛二世》這部作品中所碰觸到的作家及恐怖性的群眾議題,其實早已進入了他的心靈時間表。由於關心藝術家(作家)和恐怖群眾的課題,他才會注意到安迪沃荷的絲印畫「毛二世」、伊朗何梅尼對《魔鬼詩篇》作者魯西迪(Salman Rushdie)發布死亡追殺令等問題,並將這些故事轉化成他在《毛二世》書裡的元素。
《毛二世》這部作品從韓國統一教教主文鮮明在紐約洋基球場所辦的一場一萬三千人集團結婚開場。統一教乃是以領袖崇拜為動力而形成的宗教團體。他的青少年信眾成員都視文教主為父,沒有自我。這些沒有個性,只有群性的信徒,甚至由文教主代他們決定配偶。一個美國中產少女凱倫.詹尼,就受命和一個才剛見過面的韓國男子金中樸結為永久配偶,而該男子立刻就要被派去外國傳教。《毛二世》以統一教的信眾行為開場,其實已將極端權威、極端群眾、甚至極端到沒有自己的面目的小社會景象做了展開。
而統一教的群眾其實只是《毛二世》的序奏。接著它就開始了本書的正文:
一個名叫比爾.格雷的隱居作家。唐.德里羅設定這個角色,多少是以前輩作家沙林傑(J. D. Salinger)、湯瑪斯,品瓊(Thomas Pynchon)、威廉.嘉底士(William Gaddis)等為原型。這些作家早年皆沒沒無名,後來名氣漸盛,盛名後皆長期隱居,自外於讀者群眾。這個比爾.格雷成名後也隱居埋名,只是在拖拖拉拉寫著他並無意願出版的新著。他把寫作視為非常純粹的自我行為:再度出版新書,又要被推上台前,就會把真正的自我摧毀。比爾.格雷有個崇拜者轉成的祕書助手史考特,而凱倫.珍妮這個前述的統一教女信徒,則是史考特的夥伴。史考特在她徬徨無措的時候將她救回到人間。她形同史考特的夥伴兼助手。
而就在這時,比爾接受了一個外國籍報導攝影女記者布麗塔的採訪要求,做為生命中的最後留痕。在攝影時他和布麗塔有過對話,他認為在以前是作家提出改變時代的見解,但到了現在,這已經陳舊過時,真正改變人們意識的角色反而從作家讓位給了恐怖主義群眾。在採訪結束後,比爾託她傳話給紐約一家大出版公司的主管查理.埃弗森。查理乃是比爾以前作品的出版人,他也是比爾的舊友。比爾顯然已有意安排他新作的出版事宜。接著他們兩人在紐約聯絡上,而就在這時,一個瑞士調查黎巴嫩貝魯特難民營健康衛生狀況的瑞士人在貝魯特被恐怖組織綁架,由於查理乃是一個國際支持言論自由的組織之負責人,又由於那個人質曾以法文寫過一些詩作,查理遂邀比爾一同前往倫敦,準備舉行作家聲援作家的援救記者會。但到了倫敦後,他們的記者會受到恐怖份子的威脅而沒開成,反倒是比爾碰到了一次炸彈案,被震波掃到受傷。而在倫敦,比爾也被介紹認識了該綁架人質的組織代表喬治.哈達德,於是比爾決定自行前往黎巴嫩。他由倫敦假道塞普勒斯。在塞普勒斯候船的期間,稍早一班的渡輪遭到不知何方的恐怖攻擊,因此比爾的行程遭到拖延,而他在此時也被一輛車子撞到,雖然表面沒事,但其實卻已肝臟或脾臟受創。最後他搭上了前往黎巴嫩的渡輪,但在睡著後卻再也沒有醒來,他的護照和身份辨識證件也被別人順手拿走,這意味著比爾的遺體最後一定被視為不明人物而被草草掩埋處理。一個擁有一點知名度的作家,在這個恐怖主義群眾無所不在的時代,就這樣徹底的從世間蒸發消失。
比爾的作家之死是個值得深思的課題。在許多社會,甚至於直到不久前的現在,作家都是種危險的人物。他們的發聲會搖晃甚至顛覆整個社會的基礎,他們是原有秩序統治者恐懼的對象,難免遭到被視為某種程度的恐怖份子而遭到壓迫。他們也是既有秩序裡漂泊的異鄉人:時時可能遭遇到不可測的命運。作家的命運有如屠格涅夫的《羅亭》,可能滿腔不可能的壯志並為此而苦,但最後卻被不知從哪裡跑出來的一顆子彈了卻生命。一個有意隱居和隱藏自己的作家,最後真的被蒸發隱藏,這不正是坐實了作家的脆弱。寫作在個人主義的世界已成了葬送人生的手段。
現在的時代變了,個人主義的作家時代已經結束,代之而起的乃是集體主義的群眾瘋狂甚至恐怖主義。在《毛二世》裡,有關這部分的敘述乃是比爾這個作家的。它藉著何梅尼死亡時群眾瘋狂的場景畫面、毛澤東發動群眾的盛大場景,以及黎巴嫩那個綁架人質的毛派小組織頭目的表現,呈現出另一個宏大歷史的走向:現在的歷史這個鐘擺,已往群眾這邊擺動。群眾不只是人多,群眾是一種意識,恐怖主義的綁架人質,只不過封閉群眾型國家的一種微型預演而已。唐.德里羅在《毛二世》裡,一方面討論個人主義的沒落及邊緣化,另方面則談到集體主義這邊被操弄的群眾瘋狂開始興起,他為什麼從早年開始就一直關心「藝術」和「恐怖」這兩個問題,並對這兩個問題保留了兩個檔案夾,他的心情之沉重已不言自明。
唐.德里羅在當代作家裡,乃是修辭之斧運用得最細膩周密的翹楚,近代的文學敘述已愈來愈清楚的知道,一個述句由於概念和語法的推論,該句子本身在表達出來之後,它就如囚籠般限定了作者的意識,因此對於不想被述句限定的作者,他們總會在語言的辯限中,諸如雙關、歧義、內涵及外延的含混處,尋找可以落斧之處,使述句的內容複雜化,俾能承載更多的意義。唐.德里羅的這種敘述修辭模式,乃是他的作品雖然早已在文學圈內享有盛名,但普通讀者的接受卻較遲的原因。這也就是說他的述句有如一個個意義的迴路,透過夾敘夾議的筆法而正反相續,拉
而除了敘述修辭有如意義的迴路外,在《毛二世》裡人們還可注意到在這部作品裡,它在整個敘事的大結構上也具有這種迴路的特性。《毛二世》的序幕以統一教主文鮮明舉辦萬人集體結婚開場,來見證集權主義已侵入到了群眾最私密的婚姻與性這個領域。現在這個時代,「自我」對許多人已成了巨大的負擔,寧願將「自我」捨棄,託庇於威權的教主一人:教主所宣稱的「末日審判」其實尚未到來,但「自我」的「末日」卻早已開始了。而這種「末日」也就是盲目群眾時代的開始。由何梅尼之死的瘋狂,由毛澤東偶像崇拜的瘋狂,由黎巴嫩那個毛派暴力綁架組織,都印證了群眾時代的到來。但這種群眾時代的終極結果又如何?在這本著作裡,攝影師布麗塔倒是親眼目睹了一場黎巴嫩的荒誕婚禮。婚禮的道具是一輛老舊的俄製T-三四戰車。戰車後面是二十個大人和此數一半的小孩。這是個婚禮的迎娶隊伍,新郎新娘手持香檳杯子,一些小孩手持火花燦麗的仙女棒,這是個滑稽歡樂,但也荒誕的場景,隊伍的最後則是駕著無後座力輕機槍的吉普車。這部作品以婚禮始,以婚禮終,第一個統一教婚禮是群眾式集體主義儀式,後一個婚禮則是在暴力群眾政治當道的地方,它反而產生了個人主義的婚禮歡樂。只是這種歡樂以槍砲戰車為道具,總難免給人一種荒誕悲傷的感覺。這也顯示出,在群眾創造歷史的這個時代,歷史究將何去何從的令人迷惘不安。唐.德里羅不意圖告訴人們任何簡單的答案,只是用他那還算清明的眼神,不安的看著這個世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