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平凡的生活裡,
真正的危險並非來自那些我們可以意會、預想的事物,
而是我們自己。
瑞蒙‧卡佛創作生涯巔峰之作!◇ 《君子雜誌》評譽:卡佛作品為「男人必讀之書」首選!
◇ 郭強生(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專文推薦
◇ 12篇經典之作,首次完整譯介,在台灣問世!
◇ 《大教堂》為眾所公認卡佛寫作生涯中最成熟的作品!
◇《大教堂》所收錄短篇小說〈一件很小、很美的事〉獲美國「歐.亨利文學獎」!
卡佛曾自述:「《大教堂》中的小說,與我過去的小說相比,更加豐滿,文字更慷慨,也更積極了一些。」的確,這本被譽為卡佛巔峰之作的《大教堂》,所收錄的十二篇短篇小說裡,我們可見到卡佛以一貫的犀利極簡筆觸,描繪出無情瓦解的日常生活,同樣矛盾而充滿妙趣的對話,同樣的平凡無奇小人物,卻多了人性的溫度與光輝。
〈一件很小、很美的事〉描寫一位母親為兒子訂了生日蛋糕,但兒子卻在生日當天車禍,隨即昏迷不醒。當她與丈夫守在醫院時,早把蛋糕的事情忘得精光,而不知內情的蛋糕師傅也不斷打電話給她們,並被當成惡意的騷擾者。誤會越積越深,孩子最終不幸過世,當夫婦倆猛然意識到騷擾者的真實身分後,憤而決定報復……
〈大教堂〉呈現人與人之間一種微妙而凌駕感官之上的聯繫:一位男子的太太表示將邀請與她通信多年的盲人朋友前來作客,半出於嫉妒,半出於對殘障人士的排拒,男子對此頗感不是滋味,客人來訪當晚,他更從太太與盲人的交談中隱隱感覺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然而當妻子睡著後,在客廳無事可做的盲人和男子,竟透過一種奇特的遊戲,找到彼此心靈相通的片刻……
相較於卡佛的早期作品集結《能不能請你安靜點?》,《大教堂》所刻畫的現實雖依舊荒謬崩解,但不同的是,這一次,卻讓我們看見了人與人之間最隱藏難察的善意與希望。沒有偉大的結局或不切實際的救贖,卻能讓人在掩卷之後,不經意地一再想起。
作者簡介:
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1938-1988)
美國短篇小說家,詩人。
被譽為自海明威以降,最具有影響力的美國短篇小說家。
《倫敦時報》推崇他是「美國的契訶夫」。
1938年,出生於俄勒崗州,19歲高中畢業後,即奉子成婚。他曾做過鋸木工人、門房、送貨員、圖書館助理維生,但生活仍難以為繼。卡佛人生的前半部分,在失業、酗酒、破產中度過,妻離子散,貧困潦倒,但始終懷抱著作家夢,堅持創作。
他的寫作功力是苦學而來,直至四十歲,即70年代後期,才逐漸在文壇嶄露鋒頭,而後在1983年獲米爾德瑞─哈洛斯特勞斯生活年金獎;1985年獲《詩歌》雜誌萊文森獎;1988年被提名為美國藝術文學院院士,並獲哈特福德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同時獲布蘭德斯小說獎。然而,卡佛享受成名的滋味並無太久,只活到五十歲就過世了。他所留下的作品並不多,主要有《能不能請你安靜點?》、《大教堂》、《憤怒的季節》等短篇小說集和詩集。作品亦被改編成《銀色.性.男女》等電影。
儘管卡佛一生創作並不豐,對後世作家的影響卻相當巨大,尤以村上春樹為著。這位日本當代名家,曾譯過卡佛許多作品,為他做過很多評註,更直接透露自己在寫作上受到卡佛很大的影響,卡佛是他最景仰的美國偉大作家。學界亦常以兩者的文本做比較。村上說:「我的寫作,多數來自瑞蒙‧卡佛的啟發。」
卡佛的文字向來被歸為極簡主義,他作品中快樂的成分不多,大都是讓人想笑又笑不出來的黑色幽默;而他所描寫的,大多來自生活物品與細節,以及再平凡不過的小人物:舉凡情人、夫妻、母子、同事等,或是電話、電視、咖啡,都成為卡佛書寫的對象。他的小說沒有災難劇情的表相,卻有最波動、最無奈的人生際遇與寫照,就如他所言:「對大多數人而言,人生不是什麼冒險,而是一股莫之能禦的洪流。」
瑞蒙.卡佛的作品之所以能夠跨越世紀,三十年來持續被全球廣大的讀者拜讀,影響後世作家,或許正在於他不為任何「偉大」的目的而書寫,雖不經意,卻深刻地為我們鑿斧出最偉大動人的生命之書。
譯者簡介:
余國芳
中興大學合作學系畢業,曾任出版社主編,目前是自由譯者,有《大魚老爸》、《在地圖結束的地方》、《爆醒惡夢的第一聲號角》、《屠夫男孩》、《冥王星早餐》、《慾望的盛宴》、《輝丁頓傳奇》、《外出偷馬》、《能不能請你安靜點?》等超過四十部文學與非文學譯作。
章節試閱
一件很小、很美的事
星期六下午她開車到購物中心的麵包店。在看過貼在活頁紙上的蛋糕圖片之後,她訂了巧克力口味,這是孩子的最愛。她選的蛋糕上裝飾著一艘太空船,發射台上空撒著白色的小星星,另外一頭是一顆用紅色糖衣做的星球。他的名字,史考帝,要用綠色的字體寫在這顆星球底下。那個脖子很粗、有點年紀的麵包師傅不發一語的聽她說話,她告訴他小孩子下週一滿八歲。麵包師傅穿著類似工作服的白圍裙。圍裙的帶子從胳臂底下繞到背後再回到前面,牢靠的綁在厚實的腰圍底下。他用心聽著,兩手擦著圍裙,眼睛看著那些照片,由著她講。他不催促她。他才剛到班,這一整晚他都會在這兒,烘麵包烤麵包,他一點也不急。
她告訴麵包師傅她的名字,安妮.魏斯,還有電話號碼。蛋糕會在星期一早上出爐,那天下午孩子的生日派對絕對趕得及,時間很充裕。麵包師傅不苟言笑。他們兩人之間沒有一點歡樂的互動,只有幾句最基本的對話,交換一些必要的資料。他讓她覺得很不自在,她不喜歡這樣。他在櫃台上拿起筆彎下腰的時候,她打量著他粗俗的面貌,心裡狐疑著,不知道他這一生除了當麵包師傅以外還有沒有做過別的事。她是一個母親,三十三歲,在她眼裡的每個人,尤其像這個麵包師傅的年紀――一個老到足以做她爸爸的男人――肯定都會有兒女,也肯定經歷過這一段有著蛋糕和生日派對的特別日子。他們之間應該會有這些共通的地方才對,她想著。他對她太「硬」了――不是沒禮貌,而是生硬。她不想再跟他攀什麼交情。她朝著麵包店裡面張望,望見一張厚重的木頭長桌,桌子一頭堆著鋁製的派餅鍋,旁邊一個金屬容器裡裝滿了空的框架。還有一只大到驚人的烤箱。收音機裡播放著西部鄉村樂曲。
麵包師傅在訂貨卡上填好資料闔上活頁簿,看著她說,「星期一上午。」她道謝之後,就開車回家了。
星期一上午,這位生日男孩跟另外一個小男孩一起走路上學。兩個人把一包薯條傳來傳去的吃著,生日男孩想要知道今天下午他的朋友會送他什麼樣的生日禮物。生日男孩沒注意看路,在十字路口,一腳剛跨出路邊,立刻被一輛車子撞到了。他側身摔倒,腦袋歪向水溝,兩腿伸在路面。他的眼睛閉著,兩條腿卻前前後後的動著,好像要爬上什麼東西似的。他的朋友扔了薯條開始大哭。那車往前開了一百多呎在路中央停住。駕駛座上的人轉過頭往後看。他等到男孩東倒西歪的站起來。男孩有些站不穩,一副暈頭轉向的樣子,好在沒什麼大礙。那名駕駛發動引擎開走了。
生日男孩沒有哭,也沒說話。他朋友問他被車撞的感覺,他也不回答。他往家裡走,他的朋友繼續往學校走。生日男孩一到家,就把這事告訴了媽媽――她陪他坐在沙發上,握住他的手擱在她腿上,嘴裡說著,「史考帝,你真的覺得還好嗎,寶貝?」心裡想著無論如何要撥個電話給醫生的時候――他忽然倒在沙發上,閉起眼睛,整個人癱軟了。她發現怎麼叫都叫不醒他,趕緊打電話找正在上班的丈夫。霍華要她保持冷靜,千萬保持冷靜,他為孩子叫了救護車,自己也立刻趕去醫院。
當然,生日派對取消了。孩子住進了醫院,輕微腦震盪加上休克。有嘔吐的情形,而且肺部積水,當天下午就得抽除。現在他似乎睡得很沉很沉――但並不是昏迷,法蘭西斯醫生看見這對父母驚恐的眼神,特別強調,絕對不是昏迷。當晚十一點,孩子在經過一連串X光檢查和各種檢驗之後,顯得安穩多了,等他清醒過來恢復知覺頂多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霍華便離開了醫院。那個下午,他和安妮一直待在醫院陪著孩子,他想回家沖個澡換套衣服。「我一個鐘頭就回來,」他說。她點點頭。「沒關係,」她說。
「這裡有我。」他親親她的額頭,兩個人拉了拉手。她坐在病床邊的椅子上看著孩子。
她要等他清醒,等他好轉,她才能放下心。
霍華從醫院開車回家。他在潮濕黑暗的街道上開得飛快,忽然驚覺不對,慢慢減低了速度。到現在為止,他的人生一直走得很順很快意――大學,完婚,再多讀一年大學,取得了高階的商管學位,成為一家投資公司的小股東。還當了父親。他很幸福,應該說,很幸運――這一點他很清楚。他的父母健在,他的兄弟姐妹都過得不錯,他大學裡的那些朋友在業界也都有各自的地位。到目前為止,他沒有經過太大的風浪,順利的避開了那些存在著的惡質力量――如果運氣不好,如果情勢忽然轉變,就會碰上它,把人整個拖垮。他轉上車道,停下車,覺得左腿在抖。他在車上坐了一會兒,努力叫自己用理智的態度面對眼前的狀況。史考帝被車撞了,住進了醫院,不過他不會有事,他會好起來的。霍華閉起眼睛,用手抹了把臉。他下車走向前門。屋裡的狗在吠,電話響個不停,他開了門鎖,摸索著電燈開關。他不應該離開醫院的,不應該。「糟糕!」他說。他抓起電話說,「我剛進門!」
「這裡有個蛋糕還沒來提走,」電話那一頭的聲音說。
「你在說什麼?」霍華問。
「一個蛋糕,」那聲音說,「一個十六塊錢的蛋糕。」
霍華把話筒緊貼著耳朵,完全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我不知道什麼蛋糕,」他說。「天哪,你在說些什麼啊?」
「別跟我玩這套啊,」那聲音說。
霍華掛斷電話,走進廚房給自己倒了杯威士忌。他撥電話到醫院。孩子的情況還是照舊;還是在睡,沒有任何變化。浴缸裡放了水,霍華在臉上塗抹泡沫刮鬍子。他剛剛躺進浴缸,閉上眼,電話又響了。他吃力的爬出來,抓了條毛巾,急急忙忙衝過房間,一路的說,「笨哪,真是笨哪,」他恨自己幹嘛離開醫院。他接起電話大嚷,「喂!」電話那頭沒有半點聲音。對方掛斷了。
他回到醫院的時候剛過午夜。安妮仍舊坐在床邊的椅子上。她抬頭看了看霍華,再看回到孩子身上。孩子的眼睛還是閉著,頭上也還是紮著繃帶。他的呼吸平靜均勻。一瓶葡萄糖液吊在病床上方的儀器上,一條管子從瓶子延伸到孩子的手臂。
「他怎麼樣?」霍華問。「這些東西是幹嘛的?」他指指那瓶葡萄糖和管子。
「法蘭西斯醫生交代的,」她說。「他需要補充營養,需要保持體力。他怎麼還不醒過來呢,霍華?我不懂,如果沒事怎麼不醒呢?」
霍華伸手摸著她的後腦勺,手指順著她的頭髮。「他會好的,再過一會兒就會醒的。法蘭西斯醫生很清楚病情的。」
過了半晌,他說,「不如妳先回去休息一下,這兒有我。只是別去理會那個老打電話來的傢伙,馬上掛斷就是了。」
「誰老打電話來?」她問。
「我不知道誰,還不就那些喜歡隨便撥電話的無聊人嘛。妳走吧。」
她搖搖頭。「不了,」她說,「我可以。」
「聽話,」他說。「回去歇一會兒,早上再來跟我換班。不會有事的。法蘭西斯醫生怎麼說的?他說史考帝會好起來的。我們不必擔心。現在他只是在睡覺罷了,不會怎樣。」
一個護士推開門,向他們點個頭走到病床邊。她把孩子的左手從被子底下拿出來,用手指搭著他的手腕,看著手錶,幫他把脈。過一會兒,她把孩子的手臂放回被子底下,再轉到床尾,在掛在那裡的一塊板子上寫了些東西。
「他怎麼樣了?」安妮說。霍華的一隻手按著她的肩膀。她感覺得出他手指的壓力。
「他很穩定,」護士說。接著她又說,「醫生一會兒就會過來。醫生回醫院了,正在查房。」
「我剛才跟她說要她回家去休息,」霍華說。「現在還是等醫生來過了再走吧,」他說。
「她可以回去,沒問題的,」護士說。「如果兩位想回去休息,都沒問題。」護士是一個金髮大個子的斯堪地那維亞女人,說話帶著一絲特別的口音。
「我們先聽聽醫生怎麼說吧,」安妮說。「我想跟醫生談一談。我覺得他不應該老是這麼睡著,這不是好現象。」她一手舉到眼睛上面,頭微微的向前傾。霍華握住她肩膀的力道加重了,他的手慢慢移到她的脖子,手指揉捏著她脖子上的肌肉。
「法蘭西斯醫生過幾分鐘就會來了,」護士說著,離開了病房。
霍華注視著兒子,小小的胸膛在被子底下輕輕的起伏著。從這天下午安妮打電話到他辦公室找他開始,過了那驚嚇爆點的幾分鐘之後,現在是頭一次,他全身上下感受到了真正的恐懼。他拚命搖頭。史考帝沒事,他只是換了個地方睡覺,不在家裡自己的床上,而是睡在醫院的病床,頭上裹著繃帶,手臂插著管子而已。目前他就需要這個救助。
法蘭西斯醫生進來了,他跟霍華握握手,其實兩人在幾小時前已經見過面。安妮從椅子上站起來。「醫生?」
「安妮,」醫生點點頭。「我們先看看他現在情況如何,」醫生說。他走到病床邊,把把孩子的脈搏。翻開孩子的眼皮,看完一隻再看另一隻。霍華和安妮站在醫生旁邊看著。醫生把被子拉開,用聽診器聽過孩子的心和肺。他用手指在孩子的腹部這裡那裡的按著。忙完之後,他走到床尾,查看那份表格,然後望著霍華和安妮。
「醫生,他怎麼樣?」霍華說。「他究竟怎麼回事?」
「他為什麼不醒過來?」安妮說。
醫生是個寬肩膀的俊男,有著一張健康黝黑的臉孔。他穿了三件式的藍色西裝,打著條紋領帶,戴一副象牙白的袖釦。一頭灰髮整齊的往後梳著,看起來就像剛聽完一場音樂會回來的樣子。「他沒事,」醫生說。「沒什麼太大的問題,我覺得,情況應該更好才對。不過他真的沒事。我也希望他能夠醒過來,應該快了吧。」醫生再看一次那孩子。「再過幾個小時,等一些檢驗報告出來之後,我們對病情就會更清楚了。不過他現在真的沒事,相信我,除了頭蓋骨有些細微的裂縫。這點很確定。」
「天哪,」安妮說。
「還有些腦震盪,之前我也說過。當然,你們知道他休克了,」醫生說。「在休克的病例裡有時候就會這樣。嗜睡。」
「他脫離危險了嗎?」霍華說。「之前你說他沒有昏迷。現在你也不認為這叫做昏迷―― 是嗎,醫生?」霍華等著答案。他注視著醫生。
「對,這不能算是昏迷,」醫生邊說又再看了孩子一遍。「他只是處在一種深度的睡眠當中。這是身體採取自我復元的一種方式。他當然脫離危險了,這點我可以非常肯定。不過等他醒過來,等到那些檢驗報告出來之後,我們就可以掌握得更清楚了,」醫生說。
「這還是昏迷吧,」安妮說,「在某種程度上。」
「還不算,不算是真正的昏迷,」醫生說。「我不認為這叫昏迷,現在還不到這個程度。他休克了。在休克的案例裡面,這種反應很平常;這只是一種身體受到創傷後的暫時性反應。至於昏迷。昏迷是一種深度的、持續性的無意識,這種情況可以持續好幾天,甚至好幾個禮拜。史考帝不屬於那個範圍,就目前來說。我相信他的情況到明天早上一定會有明顯的改善。我敢打包票。等他醒了,狀況就會更清楚,就快了。當然,兩位想要留在醫院或者回家休息,都可以。離開一會兒絕對沒有問題。對兩位來說這真的很難熬,我知道。」醫生再次看著男孩,觀察他,然後轉過頭對著安妮說,「妳盡量放寬心,年輕的小媽媽。相信我,該做的我們都做了。現在就只剩再多等一點時間的問題了。」他向她點個頭,跟霍華再握一次手,離開了病房。
安妮把手放在孩子的額頭上。「還好他沒發燒,」她說。一會兒她又說,「天哪,他怎麼那麼冷。霍華?他應該這樣的嗎?你來摸摸他的頭。」
霍華摸了摸孩子的太陽穴,他的呼吸也變慢了。「應該就是這樣吧,」他說。「他休克了,記得吧?醫生說過的。醫生剛才來過。要是史考帝情況不好,他早就會表示了。」
安妮咬著嘴唇站了一會兒,坐回到椅子上。
霍華坐入她身旁的那張椅子,兩個人對望著。他很想說兩句安慰她的話,可是他自己也在害怕。他握住她的手放在他的腿上,有她的手在他腿上的感覺令他踏實許多。他拿起她的手用力的捏著擠著。兩個人就這樣手握手的坐著,守著孩子,什麼話也不說。他不時的用力捏一下她的手。最後,她把手抽開了。
「我在做禱告,」她說。
他點點頭。
她說,「我以為我已經忘記怎麼禱告,現在全都想起來了。其實只要閉上眼睛說,『上帝,請幫助我們――幫助史考帝。』剩下的就很容易了。說詞都是現成的。或許你也可以試試,」她對他說。
「我禱告過了,」他說。「就在今天下午――是昨天下午,我說的是――就在妳打電話給我之後,我一直在禱告,」他說。
「太好了,」她說。到現在為止,她第一次有兩個人一起攜手共度難關的感覺。她驚訝的發現,在這一刻之前,這件大事似乎只跟她和史考帝有關係。她始終沒有讓霍華參與,雖然他一直在這裡,一直不可少。她很高興,她為自己能夠作為他的妻子而感到高興。之前的那個護士又進來幫孩子測脈搏,檢查掛在床頭的點滴瓶。
過了一個小時,另外一個醫生進來。他說他的名字叫帕森,從放射科來的。他蓄著落腮鬍,穿著便鞋、牛仔襯衫、牛仔褲。
「我們帶他下樓去照幾張片子,」他對他們說。「我們需要再多照幾張,還要做一次掃描。」
「什麼?」安妮說。「掃描?」她站在醫生和病床的中間。「X光片你們不是都已經照過了?」
「恐怕還需要再照幾張,」他說。「不必擔心。我們只是多照兩張片子,再做一次腦部掃描。」
「我的天哪,」安妮說。
「像這類的病例,這些都是完全正常的程序,」這個新來的醫生說。「我們只是想正確的查出他不醒過來的原因。這是正常的醫療程序,真的一點都不用擔心。過一會兒我們就來帶他下去,」醫生說。
不到一會兒,兩名護工推著輪床進來病房。兩個都是黑頭髮、黑皮膚的男性,穿著白色的制服,他們互相用外國話交談了幾句,接著把孩子手臂上的管子解開,再把他從原來的病床移到輪床上,推出病房。霍華和安妮跟著一起進了電梯。安妮注視著孩子。電梯往下降的時候,她閉起了眼睛。兩名護工各站在輪床的一頭,都不說話,只有一次,其中一個用他們的語言對另外一個說了一句什麼,而另外那個只是用微微的點頭作為答覆。
那天早上稍後,當X光科候診室的窗戶開始出現陽光的時候,他們把孩子推出來了,推回到原來的病房。霍華和安妮又一次跟著他一起搭電梯,又一次站回到原來病床邊的位置。
他們等候了一整天,孩子仍然沒有醒。偶爾一下下,夫妻倆當中的一個會離開病房到樓下咖啡廳喝杯咖啡,然後,像是忽然覺得有罪惡感似的,又趕緊離開餐桌奔回病房。法蘭西斯醫生那天下午又來查看孩子一次,還是告訴他們說他的情況不錯,隨時都有醒來的可能,之後就離開了。一些護士,跟前一晚不同的護士,不斷的進進出出。然後一個化驗室來的年輕女子敲門進來病房。她穿著鬆垮的白長褲和白上衣,拿著一小盤東西,她把小托盤放在病床旁邊。沒跟他們說一句話,就往孩子的手臂上抽血。那女的在孩子手臂上找著了正確的位置,一針扎下去的時候,霍華閉起了眼睛。
「我不明白這是做什麼,」安妮對那女的說。
「醫生交代的,」年輕女子說。「我都聽醫生的。他們說抽這個,我就抽這個。他怎麼了?」她說。「他好可愛。」
「他被車撞了,」霍華說。「是肇事逃逸,撞了人就跑了。」年輕女子搖搖頭,再看看男孩,便端起托盤離開病房。
「他怎麼就是不醒呢?」安妮說。「霍華?我要這些人給我個答案。」
霍華什麼話也沒說。他再度坐回椅子,一條腿架在另一條腿上。他搓著臉,看了看兒子,再靠回座椅,閉上眼,睡了。
安妮走到窗前,望著窗外的停車場。入夜了,車子亮著頭燈在停車場上進進出出。她站在窗口兩手緊扣著窗台,她心裡有數,他們出事了,而且事情非常嚴重。她很害怕,牙齒直打顫,非得緊緊咬住牙關才能止住。她看見一輛大車停在醫院前面,有個人,一個穿長大衣的女人,鑽進車子裡。她真希望她是那個女人,也會有個人,任誰都行,開了車來接她,接她離開這裡去到別的地方,去到一個下了車就能看見史考帝在等候著她的地方,等著叫她媽媽,等著要她抱在懷裡。
過了一會兒,霍華醒了。他又看看孩子,然後從椅子上站起來,伸個懶腰,走到窗口站在她身邊。兩個人一起凝視著停車場,彼此都不說話。在這一刻他們似乎心靈相通,彷彿這份隱憂使得他們倆自然而然的透明起來。
病房門開了,法蘭西斯醫生走了進來。這次他換了一套不同的西裝和領帶。他的灰髮仍舊梳理得服服貼貼,看上去好像剛剛刮過鬍子。他直接走到床邊查看孩子。「他現在應該要醒了,實在沒道理不醒,」他說。「不過我可以明確的告訴兩位,他不會有任何危險。現在只要他醒過來,那就更好了。真的沒有理由,一點理由也沒有,搞不懂他為什麼還不醒過來。一定快了。啊,他醒過來的時候頭會很痛,這是肯定會的。他所有的跡象都很好,都很正常。」
「那,這就是昏迷囉?」安妮說。
醫生揉了揉他光滑的臉頰。「在他醒過來之前,我們暫時可以這麼說。兩位一定都累壞了,這很辛苦,我知道這很辛苦。隨便出去走走,吃點東西吧,」他說。「那對你們有好處。只要兩位有這個意願,我會安排護士進來。真的,去吃點東西吧。」
「我什麼也吃不下,」安妮說。
「當然,一切都看你們的意思,」醫生說。「總之,我還是這句話,所有的跡象都很好,檢驗結果都是陰性,沒有任何狀況,只要他醒過來,就沒事了。」
「謝謝你,醫生,」霍華說。他再跟醫生握一次手。醫生拍拍霍華的肩膀,走了出去。
(未完)
一件很小、很美的事
星期六下午她開車到購物中心的麵包店。在看過貼在活頁紙上的蛋糕圖片之後,她訂了巧克力口味,這是孩子的最愛。她選的蛋糕上裝飾著一艘太空船,發射台上空撒著白色的小星星,另外一頭是一顆用紅色糖衣做的星球。他的名字,史考帝,要用綠色的字體寫在這顆星球底下。那個脖子很粗、有點年紀的麵包師傅不發一語的聽她說話,她告訴他小孩子下週一滿八歲。麵包師傅穿著類似工作服的白圍裙。圍裙的帶子從胳臂底下繞到背後再回到前面,牢靠的綁在厚實的腰圍底下。他用心聽著,兩手擦著圍裙,眼睛看著那些照片,由著她講。他...
推薦序
我拿起一本瑞蒙.卡佛
郭強生/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
我拿起一本瑞蒙.卡佛。那是我剛到美國唸書的時候,他已經死了。我在書店看到他的照片。在書封底,黑白的,一個粗眉毛的白人男子。我翻回書正面,它的書 ──都是短篇小說集──每個封面都是風格相近水彩畫。畫的是床上抽煙的女人,或是男人喝酒的背影。他已經死了。早死的作家,都讓我發生興趣。
要來談瑞蒙.卡佛,很難。因為是談他,我的句子就不可以那麼複雜。他是我看過最會用簡單過去式的英語作家。用中文寫作的我,一直很好奇能不能也這樣寫,整篇小說都不用形容詞或者副詞。除非必要。例如:「他走進來坐下。她看著他。旁邊有人說話。他說。她說,他又說。她點點頭。」
我寫沒幾句就開始心不在焉──不,應該也不可以用成語。我沒寫幾句就開始抽煙。我把煙捻熄。我在想,為什麼?
為什麼他要這麼寫?我試著學他。我的句子都太長了。可是我把句子改短也成不了瑞蒙.卡佛。因為,他的小說開頭都是這樣的:「星期天,她開車去購物中心的糕餅店」、「這個瞎子,他是我太太的老朋友,正在路上要來過夜」、「我這個同事,巴德,邀請我和芙蘭去他家晚餐」。
我如果說,「一個平靜典型的星期天,她開著車,正要去一家位於鄰近購物中心的糕餅店」,那就不對勁了。老瑞蒙只是敘述,這個女人某天去了一個地方。他並不是打開錄影機,讓我們看到這個女人在開車,而且這一天到底平不平靜,天曉得!但是第二個例子卻又是有一個瞎子「正在路上」,為什麼不是「有一天,這個瞎子,他是我太太的老朋友,來我家過了一夜」?第三個例子,為什麼不是這麼說:「我和芙蘭正要去我的同事巴德家晚餐」?
為什麼?老瑞蒙這樣開頭應該有他的理由。我最早讀他的作品,因為是英文,我特別注意這種文法問題。也許,我猜,故事的發生,都有不同的起點。
我不能學瑞蒙.卡佛。不是因為我不用英文寫小說。用他這種方式開頭,我就要發起呆了。(我就發呆?我發呆了?我通常就會像呆子一樣不知道該怎麼往下寫?)「星期天,她開車去購物中心的糕餅店」,有太多種可能──什麼事都有可能。也可能什麼事都沒有。
什麼事都有可能。也可能什麼事都沒有。他的小說讀多了,就會覺得他在重複這句話。這會讓人很沮喪。活著就是像這樣。來說一個這樣的故事,關於活著,句子不可以太複雜。因為活著已經是很複雜的事。
沙特很不滿意所謂的寫實主義小說。他說,那種故事裡,「不管走去哪裡,草都不會生長。」因為事件過去了,小說裡的世界是死掉的。我想他應該來讀一點瑞蒙.卡佛。沒錯,就是一個死掉的世界。統統都變成了簡單過去式。但是老瑞蒙就是對這個死掉的世界很有興趣。就像我對他的簡單過去式也很感興趣,因為中文裡沒有。我從老瑞蒙的小說裡聽到一種聲音。是死人的聲音,但是很溫暖。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有毛病?
「一件很小、很美的事」。那到底是什麼?
可以是幾根羽毛,也可以是一座宏偉的大教堂。我讀完那篇〈大教堂〉的時候,有一種溫暖激動的感覺。我不知道大教堂應該是什麼樣子,我也不知道幸福是什麼樣子,或是死亡是什麼樣子。我一天一天過下去,希望有一天會知道,但是也許永遠不會。我想,老瑞蒙會這麼跟我說,所以要寫下來啊!那個瞎子,讓自己的手「搭乘」著說故事的人的手,隨著繪出的線條在紙上走。他撫摸線條在紙上透出的凸痕。我也搭乘老瑞蒙的聲音,往人的心中走。他的短句子在我心上留下凸痕。瞎子真的不知道大教堂是什麼嗎?或許他才是那個繪出真正大教堂的人。很多人花很久的時間蓋的房子,那就是大教堂。我們後來都住在裡頭,但是我們繪不出教堂的樣子。
我第一次讀到瑞蒙.卡佛的時候,他已經死了。以前,我從來不知道,每一個故事中的每一個句子,都可以是一個祕密。
世界很大。我在我自己的生命裡,跟這個世界無關,又好像有關。老瑞蒙把世界變得很小,卻是一個充滿不可知的世界。每個人都知道那個世界是什麼,就像以為知道道德是什麼,愛情是什麼。我們都是拼圖中的一塊,每一塊拼圖有一定的形狀,一定的位置才能擺得進去。每一塊拼圖一定連著其他好幾塊,沒有一塊拼圖只有它自己。沒有人知道圖拼完會是什麼樣子。
之前;以後;然後;那時;這時;最後;終於;現在……我拿起一本瑞蒙.卡佛。
我開始拼圖,試著寫下一句簡單過去式。
我拿起一本瑞蒙.卡佛
郭強生/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
我拿起一本瑞蒙.卡佛。那是我剛到美國唸書的時候,他已經死了。我在書店看到他的照片。在書封底,黑白的,一個粗眉毛的白人男子。我翻回書正面,它的書 ──都是短篇小說集──每個封面都是風格相近水彩畫。畫的是床上抽煙的女人,或是男人喝酒的背影。他已經死了。早死的作家,都讓我發生興趣。
要來談瑞蒙.卡佛,很難。因為是談他,我的句子就不可以那麼複雜。他是我看過最會用簡單過去式的英語作家。用中文寫作的我,一直很好奇能不能也這樣寫,整篇小說都不用形容詞或...
目錄
1.羽毛
2.謝夫的房子
3.保鮮
4.包廂
5.一件很小、很美的事
6.維他命
7. 小心
8. 我在這裡打電話
9. 火車
10. 發燒
11. 馬勒
12. 大教堂
1.羽毛
2.謝夫的房子
3.保鮮
4.包廂
5.一件很小、很美的事
6.維他命
7. 小心
8. 我在這裡打電話
9. 火車
10. 發燒
11. 馬勒
12. 大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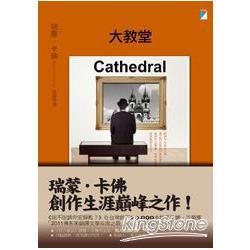

 2012/05/31
2012/0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