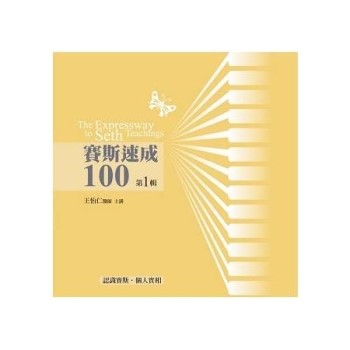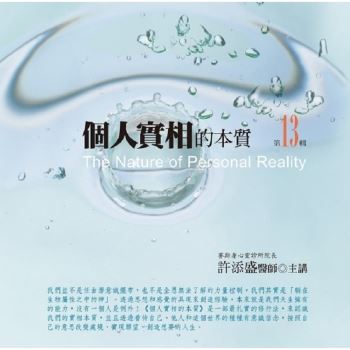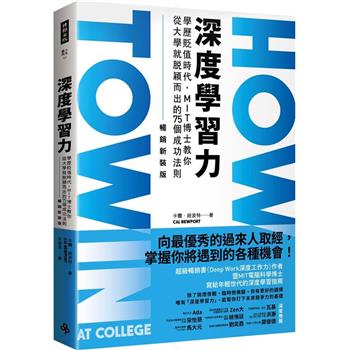這世代──火文學
寫作是殺死自己,讓別人守靈!
寶瓶文化與重慶出版集團共同策劃出版,兩岸同步發行!
我們表達恨的時候是天才,到了愛面前卻如此平庸。
他將人世間不共戴天的仇恨釋放,寫活了凡夫俗子最微小的愛!
他擊敗大江健三郎,奪得「曼氏亞洲文學獎」,
被評委譽為當代的契訶夫!
畢飛宇部分作品已譯為英、德、法、日、荷,韓等多國文字!
同時推薦:盛可以《道德頌》、魏微《十月五日之風雨大作》
徐則臣《夜火車》、李洱《遺忘》
他的小說是挾風帶雨,愛恨計算皆無可閃避;
是人欲傾軋排山倒海而來,
真實而又傳奇。
他藉一枝筆,將人世間不共戴天的仇恨釋放,
更寫活了茫茫紅塵的凡夫俗子,最微小的愛。
他是畢飛宇。
畢飛宇擅長刻劃親痛仇快的欲望傾軋,揭示權力鬥爭下最不堪的赤裸人性,他文字鋒利無比,句句見骨見血,面對他的小說,我們毫無閃躲之力,只能被牢牢攫住。在這集子裡,收錄了畢飛宇極為傑出的十三篇短篇,且看他以細膩得近乎苛刻的敘述,展現驚人的敘事功力,無論是整個時代的蒼涼跌宕,滄海一粟的人世冷暖,盡皆凝聚於此,主題更是橫跨了世代、性別與地域,小說技藝爐火純青。
作者簡介:
畢飛宇
1964年生於江蘇興化,畢業於江蘇揚州師範學院。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創作,作品譯有英、德、法、荷、日、韓等多國文字,享譽海外。
畢飛宇在大陸文壇地位不容忽視,代表作品之一《青衣》翻拍為電視劇後,轟動一時;張藝謀知名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劇本亦出自他手。他曾接連獲得中國五大文學獎中的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及其他重要獎項,《哺乳期的女人》拿下首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後,《玉米》又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並於2011年奪得第四屆曼氏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成為繼姜戎、蘇童之後,第三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作家。他於2008年推出的長篇小說《推拿》不但與莫言並列 2011年茅盾文學獎得主,同時也拿下《當代》長篇小說年度獎和《人民文學》優秀長篇小說獎、中國當代文學學院獎和小說雙年獎等。代表作品包括《畢飛宇文集》、短篇小說集《是誰在深夜說話》、《哺乳期的女人》、長篇小說《玉米》、《青衣》、《平原》、《上海往事》、《推拿》等。
《推拿》繁體中文版亦榮獲「2009開卷好書獎‧十大好書」。
章節試閱
如果我不能做
我想做的事情
那麼我的工作就是
不做我不想做的
事情
這不是同一回事
但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
事情
……
——尼基.喬萬里《雨天的棉花糖》
一
七月三日,那個狗舌頭一樣炎熱的午後,紅豆嚥下了最後一口氣。紅豆死在家裡的木床上。陽光從北向的窗子裡穿照進來,陳舊的方木欞窗格斜映在白牆上,次第放大成多種不規則的幾何圖形。死亡在這個時刻急遽地降臨。紅豆平靜地睜開眼睛,紅豆的目光在房間裡的所有地方轉了一圈,而後安然地閉好。我站在紅豆的床前。我聽見紅豆的喉嚨裡發出很古怪的聲響,類似於秋季枯葉在風中的相互摩擦。隨後紅豆左手的指頭向外張了一下,幅度很小,這時紅豆就死掉了。紅豆的生命是從他的手指尖上跑走的,他死去的指頭指著那把蛇皮蒙成的二胡,紅豆生前靠那把二胡反覆搓揉他心中的往事。
紅豆的母親、姐姐站在我的身邊。她們沒有號哭。周圍顯示出盛夏應有的安靜。他的父親不在身旁。等待紅豆的死亡我們已經等得太久了。我向外走了兩步,一屁股坐進舊籐椅中,舊籐椅的吱呀聲翻起了無限哀怨。我的腦子裡空洞如風,紅豆活著時長什麼樣,我怎麼也弄不清了。我只能借助於屍體勾勒出紅豆活著時的大概輪廓。他的手指在我的印象裡頑固地堅持死亡的姿勢,指責也可以說渴望那把二胡。
紅豆死的時候二十八歲。紅豆死在一個男人的生命走到第二十八年的這個關頭。紅豆死時窗外是夏季,狗的舌頭一樣蒼茫炎熱。
少年紅豆女孩子一樣如花似玉。所有老師都喜歡這個愛臉紅、愛忸怩的假丫頭片子。紅豆曾為此苦悶。紅豆的苦悶絕對不是男孩的驕傲受到了傷害的那種。恰恰相反。紅豆非常喜歡或者說非常希望做一個乾淨的女孩,安安穩穩嬌嬌羞羞地長成姑娘。他拒絕了他的父親為他特製的木質手槍、彈弓,以及一切具有原始意味的進攻性武器。姐姐亞男留著兩隻羊角辮為他成功地扮演了哥哥,而紅豆則臉蛋紅紅的、嘴唇紅紅地做起了妹妹。但紅豆清醒地知道自己不是妹妹,他長著女孩子萬萬長不得的東西。那時我們剛剛踩進青春期,身體的地形越長越複雜。有機會總要比試襠部初生的雜草,這算得上青春期的男子性心理的第一次稱雄。紅豆當時的模樣猶如昨日。紅豆雙手捂緊褲帶滿臉通紅,望著我不停地說,不,我不。我說算了,大龍,算了吧。大龍這傢伙硬是把紅豆給扒了。扒開之後我們狂笑不已,紅豆的關鍵部位如古老的玉門關一樣春風不度。大龍指著紅豆的不毛之地說:「上甘嶺!」紅豆傷心地哭了。
生命這東西有時真的開不得玩笑。我堅信兒時的某些細節將是未來生命的隱含性徵兆。一個人的綽號有時帶有極其刻毒的隱喻性質。小女孩一樣的紅豆背上了「上甘嶺」這個硝煙瀰漫的綽號,最終真的走上了戰場,戰爭這東西照理和紅豆扯不上邊的,戰爭應該屬於熱衷於光榮與夢想的男人,不屬於紅豆。從小和我一起同唱「長大要當解放軍」的,不少成了明星、老闆或大師。愛臉紅、愛歌唱、愛無窮無盡揉兩根二胡弦的紅豆,最終恰恰扛上了武器。這真的不可理喻,只能說是命。
紅豆參軍的那年我已經進了大學。我整天坐在圖書館裡對付數不清的新鮮玩意。那年月的漢語語彙經歷了一個戰國時代,「主義」和「問題」螞蟻一樣繁殖問題與主義。「只要你一個小時不看書,」我的一位前輩同學在演講會上伸出一個指頭告誡說,「歷史的車輪將從你的脊椎上隆隆駛過。把你輾成一張煎餅!」
圖書館通往食堂的梧桐樹蔭下我得到了紅豆當兵的消息。這條筆直的大道使圖書館與食堂產生了妙不可言的透視效果。班裡的收發員拿著紅豆的信件對我神祕地唊眼。這個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小子極其熱衷旁人的隱私,為了收集第一手資料,他拚死拚活從一個與黑人兄弟談戀愛的女生手裡爭取到了信箱鑰匙。收發員走到我的面前,說,請客。我接過信。認出了紅豆聽話安分的女性筆跡。後來全班都知道了,我交了一個女朋友,名字起得情意纏綿。紅豆用還沒有漲價的八分錢郵件告訴我,他當兵去了。聽上去詩情畫意。
紅豆熟悉大米的腸胃還沒來得及適應饅頭與麵條,就在一個下雨的子夜靜悄悄地鑽進了南下的列車。他走進了熱帶雨林。他聽到了槍聲,真實的槍聲。在槍聲裡頭生命像夏天裡的雪糕,紅豆在一個夜間對我說,看不見有人碰你,你自己就會慢慢化掉。你總覺得你的背後有一支槍口如獨眼瞎一樣緊盯著你,掐你的生辰八字。
紅豆的部隊在濕漉漉的瘴氣世界裡不算很長。我一直沒有紅豆的消息。戰爭結束後戰鬥英雄們來到了我們學校,我突然想起紅豆的確有一陣子不給我來信了。英模們的報告結束後我決定到後臺打聽紅豆。宣傳部穿中山裝的一位幹事用巴掌擋住了我:「英雄們有傷,不能簽名。」我說我不是求簽名,是打聽一個人。穿中山裝的幹事換出了另一隻巴掌:「英雄們很虛弱,不能接待。」我看見我們的英模們由我們的校領導攙扶著走下階梯,心中充滿了對他們的敬意。但我沒能打聽到紅豆。回寢室的路上已是黃昏,說不出的不祥感覺如黃昏時分的昆蟲,在夕陽餘暉中吃力地飄動並且閃爍。
噩耗傳來已是接近春節的那個雪天。紛揚的雪花與設想中的死亡氣息完全吻合。紅豆家的老式小瓦屋頂斑斑駁駁地積了一些雪,民政廳的幾位領導在雪中從巷口的那端走向紅豆家的舊式瓦房。他們證實了紅豆犧牲的消息。紅豆的母親側過臉讓來人又說了一遍,隨後坍倒了下去。紅豆的父親莊重地用左手從領導手中接過一堆紅色與金色的東西,他的右手被美國人的炮彈留在了一九五二年的朝鮮。紅豆父親接過紅色與金色的東西時,覺得今天與一九五二年只有一隻斷臂一樣長。一伸手就能從這頭摸到那頭。民政廳的領導把紅豆的骨灰放在日立牌黑白電視機前,說:「烈士的遺體已經難以辨認了,不過,根據烈士戰友的分析,除了是烈士,不可能是別的人。」民政廳領導所說的烈士也就是紅豆。紅豆的名字現在就是烈士了。
二
我們都在努力,試圖從記憶中抹去紅豆。那個漂亮的愛臉紅的小夥子正在黑框的玻璃後面,用女性氣很濃的眉眼以四十五度的視角微笑著審視人間。紅豆的母親把紅豆那把二胡擱在遺像的左側。紅豆的母親每天都要用乾淨的白布擦拭一塵不染的鏡框玻璃。玻璃明亮得如紅豆十八歲那年的目光一樣清澈剔透。但那把二胡紅豆的母親從來不碰,兩根琴弦因日積的粉塵顯得臃腫。紅豆的母親說,這孩子的魂全在那兩根弦上了,碰不得,一碰就是聲音。
小學五年級紅豆買回了這把二胡。紅豆的父親相當生氣甚至是相當絕望:紅豆用十七元人民幣買回了這把需要坐著玩的東西。這位光榮的殘廢軍人盼望龍門出虎子,他的兒子能夠威風八面。紅豆令他絕望。紅豆卻從一個算命的瞎老頭那裡得到了二胡演奏的啟蒙。蛇皮裡沙啞的聲音讓紅豆癡迷,一聽到目光就呆了。紅豆不認識樂譜。樂譜完全是視覺世界裡的阿拉伯數字,不是流動好聽的音符。紅豆依靠瘦長指尖的耐心撫摩使琴弦動了惻隱之心。胡琴把所有的心思全都傾訴給紅豆了。兩根琴弦很聽紅豆的話,就像紅豆聽所有人的話一樣。紅豆放學後拿一張竹凳放在巷口,一巷子都塞滿橫秋老氣。不滿一年紅豆學會了許多電影插曲。紅豆的音樂記憶與生俱來,他母親把它與紅豆一同生下來了。紅豆聽完了樂曲就回家到胡琴上尋找,多難的曲子紅豆都能找到,多貴重的曲子胡琴也總是願意給他。看完了「英雄兒女」,紅豆開始迷戀那些英雄讚歌,那些無限抒情的曲子成了紅豆每日練習的壓臺戲。巷子裡的人們很快聽出來了,任何一首歌曲都能被紅豆弄出傷心來,優美得走了調樣。即使是革命歌曲也總是要哀婉淒迷的。那一回學校演出,紅豆正在彩排〈英雄讚歌〉,校長走了過來。校長說,停。校長指著紅豆說:「你傷心什麼?」紅豆怯生生地抬起頭,兩眼汪了兩朵淚:「王成叔叔死了。」「不是死了,是犧牲!」校長拿了一根鼓槌,「要拉得勇敢、自豪,要拉得有力量!是犧牲。不是死!」在鼓槌的威脅下紅豆的演出果然一反常態,變得雄壯豪邁。但回到小巷口不久紅豆就又把自己還給自己了。老太太們聽著紅豆的琴聲時常背著紅豆的母親議論:「這孩子,命不那麼硬。」話裡頭有了擔憂。
紅豆這孩子現在什麼也不是了。只是一把灰。放在一只精製的木盒子裡。那把灰被人們稱作烈士。
畢業之後我令人陶醉地從高等學府返回故里,走進了機關大院。我對我的父母說,過些年我就會做官的。我一點也不臉紅,一點也不。讀書而做官本來就是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我既不是智者也不是仁者,我不做官誰做?我不做官做什麼?我們不能讓歷史從我們這代人身上斷了香火。我心安理得地走進了機關大院宣傳部,端坐在淡黃色「機宣0748」號辦公桌前,等待微笑與恭維話登門拜訪。
這一天風和日麗。風和太陽都像婚後第十七天的新娘,美麗而又疲憊。天上地下都是平安無事的樣子。我坐在辦公室裡盼望出點什麼事,但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安靜得讓人沮喪。我泡了茶,開始起草部長讓我起草的講演報告。
事情發生在我寫到「取得了偉大勝利」之後。這個我記得相當清楚。一般說,講演報告中不能缺少「偉大勝利」這樣營養豐富的詞彙,但在這樣的大補過後必須是一個減肥過程。減肥是困難的。這是常識。不能太膩了,卻又不能傷了筋骨。我點上了一根菸,「取得了偉大勝利」之後時常令我大傷腦筋。
這時候走進來了一個人。逕直走到我的「機宣0748」號辦公桌前。左手的指關節敲擊我的辦公桌面。我很不情願地抬起頭。是一個男人。滿臉胡茬。我打量這個沒帶微笑與恭維話的陌生男人,只一秒鐘,我手上的菸就掉下來了。我掛下了下巴腦袋裡頭轟地就一下。「你不用怕,」他說,「很對不起,我是紅豆。」我笨拙地站起身,我認出了那雙韭菜葉子一樣寬的雙眼皮和那種永遠都是二十攝氏度的眼神。這種眼神習慣於後退與尋求諒解。「實在對不起,紅豆。」我說,我感覺到我說「紅豆」時有一種特別異樣的感覺,不像漢語。紅豆對我笑笑:「我沒有死,我還活著。」紅豆這樣說。他的樣子很怪,笑容短促而又渺茫,好像費了吃奶的勁才從玻璃鏡框中掙脫出來。我握過他的手,他的手也像玻璃那樣冰冷,是另一個世界的陰涼。
三
我告訴弦清,紅豆他回來了。弦清放下手裡的塑膠葡萄,不高興地說,你胡說什麼。弦清在馬尾的尾部創造性地燙了幾道波浪,興高采烈地籌辦我們的婚事。我說我不是胡說,是真的。弦清轉過身研究了我好大一會兒,才說,是真的?我說是真的。弦清沒有出現我期待的大喜過望。不是說紅豆犧牲了嗎?弦清說。沒有,我對她說,還活著,蝦子一樣活蹦亂跳!弦清用小拇指漫不經心地捋頭髮,手指在耳墜那裡停住。紅豆他又回來了?弦清這樣自語。她的冷淡讓我失望。女人一到結婚的前沿就變得愚蠢和殘酷,就只知道買塑膠水果和變更髮型。
我請來了「上甘嶺」時的幾位朋友,為紅豆接風。朋友這東西就這樣,鬧了一大圈,到後來又回到了兒時的一圈中來了。弦清把天井掃得很乾淨,灑了水。說是吃晚飯,下午兩點多鐘人就齊全了。我買了很多菜,我自己也弄不清為什麼要買那麼多,就好像賭了天大的怨氣,就好像明天不活了。花錢時我有一種說不出的仇恨與痛快。今晚得把紅豆灌醉。我進了機關從來沒醉過。不敢醉。今晚誰要不醉我讓他鑽褲襠。
幾位朋友帶來的女士或小姐在弦清的調度下忙菜。我們五六個乾坐了一會兒,後來紅豆很寂寥地打開了九英寸黑白電視。一個呆頭呆腦的男人講述會計。別的頻道清一色是雪花。隨著紅豆手腕的轉動,民政廳的同志就迎著雪花向紅豆的舊式瓦房款款而至了。令人心碎的瞬間在紅豆的手指間切換,紅豆當然渾然不知。我發了一圈香菸。我注意到他們幾個今天約好了似的不提紅豆。紅豆的臉上一直掛著很多餘的客套性微笑。這使他看上去很累。我不知道他對我為什麼要這樣。我拿出兩副紙牌,關上電視,說,打牌,這東西有什麼看頭。
紅豆說,你們玩,我玩不好。大家讓了一回,後來他們幾個玩起了八十分。利用這個美好的時刻我和紅豆坐在一角談起了過去的一些時光。人生中美好的時光總是由懷舊開始。紅豆夾著菸,夾菸的樣子很笨拙,菸在手上彷彿是長錯了位置的手指頭。紅豆的記憶力好得驚人。許多過去的時光能被他十分細膩地抓回來,紅豆的存在使你堅信生活這東西從來就不會「過去」。紅豆的歸來讓我覺得生活一下子美好如初,如青春期的新鮮感覺桃紅柳綠地漫山遍野。好極了。真他媽想哭。
我很快注意到紅豆的講述時常在「曹美琴」周圍閃閃爍爍。他不只一次地提及曹美琴,說起時又彷彿是淡忘了,總是說成「那個曹什麼什麼的」。紅豆能叫出所有人的名字,對這個漂亮風騷的文娛委員反而陌生。紅豆在我面前這麼躲藏讓我覺著生分、難過。紅豆那時候一定經歷過無限傷痛的單戀,如烈日下的芭蕉吃力地瘋狂與妖嬈,卻從來錯過了花季,年復一年地枯萎而不能表達。紅豆歷來就是這樣的男人,愛上一回便災難一次。曹美琴是我們班第一個勇敢地挺著兩個小乳頭走路的女生。這個小騷貨把她的鳳眼均勻地播給每一個和她對視的男人,包括我們的校長和班主任。我和曹美琴有過一次驚心動魄的見面。這次會晤發生在夢中。醒來時我驚奇地發現老子已經是男人了。曹美琴這刻早就成了老闆娘了,她的財富如她的腰圍一樣每況愈上。好幾次我想對紅豆說,「她結婚了」,看他茫然的樣子,又總是沒說。
弦清在天井裡喊,該殺雞了。我和紅豆走進天井。我從弦清手裡接過菜刀,遞給紅豆。「紅豆,玩一玩,你來殺。」弦清怨我胡鬧,怎麼能叫客人殺雞。我說沒什麼,紅豆便接過了刀。我去拿碗接雞血。
從廚房出來紅豆呆愣愣地站在天井中央。右手提刀,左手上卻淨是血。這傢伙當了幾年兵雞都殺不好。我回頭看了一眼,雞卻好好的,圓圓的眼睛一愣一愣地對我眨巴,而紅豆的手掌卻鮮血如注。「怎麼了,紅豆?」
紅豆盯著我。紅豆的目光幾秒鐘內徹底改變了形式與內容。紅豆的眼睛發出了類似於崩潰的死光,滾出了許多不規則幾何體,如兩支引而待發的卡賓槍口,發出藍幽幽的色澤。
「不……」紅豆怔怔地說。
「怎麼回事?」
「我不殺。」紅豆這樣說。菜刀響亮地墜地,在水泥地上砸出一道白色印跡。
這時的紅豆已經完全不對勁了。我撲上去抱緊了紅豆。
「我不殺。」紅豆在我懷抱裡掙扎。所有的眼睛都瞪大了,默不作聲地面面相覷。
「紅豆。」
「我不殺。」
「紅豆!」
「我不殺。我絕對不殺。」
如果我不能做
我想做的事情
那麼我的工作就是
不做我不想做的
事情
這不是同一回事
但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
事情
……
——尼基.喬萬里《雨天的棉花糖》
一
七月三日,那個狗舌頭一樣炎熱的午後,紅豆嚥下了最後一口氣。紅豆死在家裡的木床上。陽光從北向的窗子裡穿照進來,陳舊的方木欞窗格斜映在白牆上,次第放大成多種不規則的幾何圖形。死亡在這個時刻急遽地降臨。紅豆平靜地睜開眼睛,紅豆的目光在房間裡的所有地方轉了一圈,而後安然地閉好。我站在紅豆的床前。我聽見紅豆的喉嚨裡發出很古怪的聲響,類似於秋季枯葉在風中的相互摩...
推薦序
台灣火作家:紀大偉、甘耀明、鍾文音,郝譽翔。
大陸火作家:盛可以、畢飛宇、魏微、徐則臣,李洱。
施戰軍(著名評論家、《人民文學》雜誌社主編)特別撰序推薦
台灣火作家:紀大偉、甘耀明、鍾文音,郝譽翔。
大陸火作家:盛可以、畢飛宇、魏微、徐則臣,李洱。
施戰軍(著名評論家、《人民文學》雜誌社主編)特別撰序推薦
目錄
《祖宗》 《雨天的棉花糖》
《是誰在深夜說話》 《嬸娘的彌留之際》
《男人還剩下什麼》 《武松打虎》
《受傷的貓頭鷹》 《寫字》
《好的故事》 《蛐蛐,蛐蛐》
《地球上的王家莊》 《家事》
《相愛的日子》
《祖宗》 《雨天的棉花糖》
《是誰在深夜說話》 《嬸娘的彌留之際》
《男人還剩下什麼》 《武松打虎》
《受傷的貓頭鷹》 《寫字》
《好的故事》 《蛐蛐,蛐蛐》
《地球上的王家莊》 《家事》
《相愛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