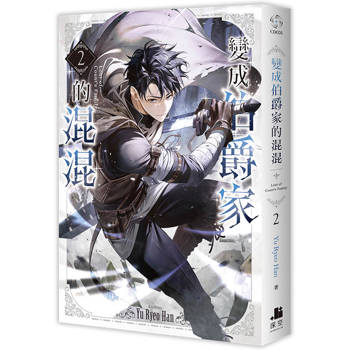後記
獻給這空茫混沌之「在」的一曲長歌
我本無意在此談論道德問題,關於《道德頌》這部小說,我所關心的是,盛可以如何講述,以及她為何如此講述?
在我們即將傾聽的這個故事中,未婚女子旨邑遇到了一個已婚男人:水荊秋。故事由此開始,接下來,我們看到愛慾、愛慾反覆經歷侵蝕和修復、愛慾的頹敗和消散。總之,如果不考慮當事人的感受,我們可以把它直接稱為不幸的婚外戀故事──實際上,也幾乎沒有幸福的婚外戀故事,因為當婚外戀被書寫時,書寫者站在起點,目光已經看到了終點:那裡必是一片廢墟。不僅是因為道德,書寫者們並非都是婚姻制度的維護者,他們只是看到了人類激情的自然限度,時光和庸常的生活必將它磨損得面目全非。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爾斯泰以一句如此世故的格言開始他關於婚姻和非法激情的偉大故事,這不僅是解說安娜和卡列寧,也是對安娜和渥倫斯基做出的預言──幾乎就是一句詛咒。這詛咒並無惡意,托爾斯泰筆下那無名的敘述者發出的是老謀深算的生活的聲音。
生活並不站在當事人一邊,如果將此類故事的敘述權交給無名的、見多識廣的「生活」,那麼,一切必將歸於虛妄。所以,在這個關於非法激情的故事中,爭奪敘述權力的鬥爭至關重要:故事由誰講?由誰作證由誰起訴由誰審判?誰可以將自身從虛妄中拯救出來?
所以,如果《道德頌》的聲音完全歸於旨邑我將毫不意外,盛可以當然會這麼幹,她將塑造一個女性主義戰士,傷痕累累,孤絕而驕傲,堅守著她的堡壘。
但情況並不如此簡單,《道德頌》視點游移,雖然是緩慢的,常常難以察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敘述追隨旨邑,但仔細看就能看出縫隙和破綻,至少有幾處,視點轉向原碧和謝不周,有時敘述者甚至不慎暴露面目,他或她站在那裡,自稱「我們」。
一個小小的,但在我看來至關重要的問題是:這個「我們」是誰?究竟出於什麼意圖,盛可以引入了「我們」?這個「我們」又為什麼如此羞澀和閃縮?
簡單的答案是,這基本上是技術上的權宜之計,作為書寫者的盛可以任性、不守紀律,她無意遵守自己定下的規矩,她粗暴地破壞規矩以應對規矩所帶來的困難。鑑於在我的印象中,小說家盛可以的美德並不包括守紀律,鑑於《道德頌》中視點的游移確實缺乏清晰的形式感,「權宜之計」的判斷未始不能成立。
然而,盛可以其實有更為簡捷明快的解決辦法,她可以採用徹底的「我」,她也可以採用堂堂正正的「我們」,無論前者還是後者,敘述的難度都不會比現在更高,都會使局面清晰、穩定,使我們明確地領會作者的意圖和立場。但現在,她似乎是猶豫著,模稜兩可,把情況弄得曖昧複雜──就一部小說而言,作者未曾寫出的與她已經寫出的同等重要,作者猶豫的、含混的地方比她信心十足之處更為重要,她的真正關切和焦慮,她向自己、向小說中的世界提出的真正問題,可能就隱藏在這一片她最終未能驅散的陰翳之中。
所以,我傾向於認為,《道德頌》的視點游移並非權宜之計,它是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複雜考量之間競爭與妥協的結果。
有一件事顯而易見,盛可以明確地屏棄了「我」。這部分是出於對「自傳性」的警覺,書寫者避自傳性之嫌,不想讓人們產生聯想──在作為小說敘述者的「我」和書寫者的「我」之間,當他們的經驗和觀點和身分發生某種重合或具有重合的可能性時,都會由此生出一個曖昧的區域,在這個區域裡,讀者受到鼓勵和誘惑,在兩個「我」之間建立聯繫,進而穿透文本去指認那個作者的「我」。
每當此時,小說家面對的都是一個倫理難局:她要嘛承認小說中的「我」就是我,要嘛斷然否認,前者虛榮,她像個急於出風頭的「星媽」,她濫用作者權利,有意毀壞小說的邊界,以牟取小說人物並未期待的利益,後者至少是看上去不誠實,至少是冒犯了讀者對她的書寫的信任。
盛可以很可能考慮了這一問題,她排除了「我」,她無意訴諸自傳性幻覺,她所寫的不是「我」而是那個名叫旨邑的女人,她在最低限度上維持旨邑的客觀性,在旨邑與寫作者之間保持一道縫隙:一個寫作者得以脫身,由旨邑自己承擔責任的縫隙。
儘管如此,盛可以並不想掩飾她對旨邑的喜愛,盡人皆知,作者認同這個人物,書寫在絕大部分時間裡追隨著她,跟著她疼痛和歌哭,常常的,書寫者直接進入旨邑內部,她和她接近於完全重合。
很好,盛可以原可以徹底地維持旨邑的視角,當然她也應該能想出辦法克服由此帶來的不便,但我的感覺是,她對旨邑強勁的、覆蓋性的聲音隱約感到不安,似乎有一種衝動在焦慮地低語: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聽從這種直覺,她幾乎是任意地要「破」,破開旨邑的聲音,她要打斷她,她要壓制她對小說世界的壟斷。
這種衝動由何而來?我認為,盛可以必是意識到,徹底地認同旨邑隱含著某種危險,將在可能根本上誤導這部小說的主題方向。
這就涉及到這部小說的主題──「道德」,我不得不談論這個如此複雜和困難的問題──我知道很多人並不認為「道德」這個問題有什麼困難之處,他們認為「道德」是一塊磐石,正好可讓他站在上面,看人們如何頭破血流。
但我認為,道德肯定不是磐石,它經受著人類無盡的反思和求證。《道德頌》的題記引用了尼采的話:「沒有道德現象這個東西,只有對現象的道德解釋」,──恕我寡陋,不知這話出自何處,僅就字面意義而言,我以為這話就是表明,道德並非一個自然事實,它不能自我呈現,它有賴於人的體驗和論證。或者說,對上帝而言──如果他在的話──道德才是「現象」,而當上帝不在時,道德就只能依賴人的「解釋」。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拒絕解釋的「道德」是僭妄和悖謬的,它將自身封為自然之物,它不再關乎人的境遇和體驗,它獨斷、不可爭辯,在極端狀態下,它反對人的選擇和自由、取消人自證道德的可能。
在這裡,一個微妙的悖論是,旨邑的全部鬥爭就是要從「天經地義」之處取回道德,她力求在自己的境遇中做出解釋,但就這部小說而言,徹底的獨一視角至少在邏輯上是有自我封閉的危險──人可能在與物件的鬥爭中將自己凝固起來,變成一塊同樣僵硬的磐石。
我必須強調,旨邑本身並非磐石,她的聲音中最令人難忘的就是她自身的複雜、矛盾和變化、發展。旨邑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盛可以在她的身上做了高難度的試驗:將近乎女學究的思想興趣與經驗、直覺、激情融為一體,她有身體,也有頭腦,她的身體和身體、頭腦和頭腦、身體和頭腦激烈地對話爭執;當然,盛可以的才華依然在於強悍的直覺,當旨邑像個知識分子一樣思考時,我常常覺得她更像一個背書的高手,但當旨邑作為一個女人、一個情人、一個可能的但最終毀棄了自己胎兒的母親時,小說寫得華彩紛披、步步精確,常常是剝皮見骨、直指本心。
但旨邑那一重女知識分子的聲音並非全然無效,它豐富了旨邑的精神維度,在她的內部,這是一重轟鳴的背景音,低沈、笨重、自我干擾,它使旨邑的經驗和生命變得嚴重、闊大,這個身處庸常激情故事中的女人最終竟大於她的自身,成為一個你不得不嚴肅對待的道德形象。
──是的,這部書確實就是《道德頌》,而旨邑,她是這個時代的小說所刻劃的最道德的人之一,她徹底自覺地追求道德,她當然不是循規蹈矩、謹小慎微,她從未期待人群的稱頌,她之道德不是出於畏懼和虛榮,而是出於絕對認真、絕對嚴肅的生命意志,她真的在自己的內心深處體驗到道德之艱難,她絕不僅僅是攻擊婚姻制度所憑依的道德律條──她不僅是個冒犯者,她的真正問題是:她決意做個善好之人,為此她不僅要與他人鬥爭,更要與自己鬥爭。
在這個意義上,《道德頌》是迄今為止小說對我們這個時代人的道德境遇和道德體驗的最為有力的表達和探索。
儘管如此,盛可以的疑慮揮之不去。道德問題的複雜性在於,關於何為善好,人類的觀點和體驗極為殊異。正如善與惡也許只有一線之隔,徹底的道德相對主義也幾乎就是旨邑的敵人:道德絕對主義──每一個「我」都自我封授為「上帝」。這種危險大概就潛存於盛可以的書寫過程的底部,被她極力壓制。我甚至妄猜,旨邑為什麼叫「旨邑」?是「旨意」嗎?或者是「脂邑」──《聖經》中的奶與蜜之地?
可見,道德是一個多麼複雜的迷宮,稍失警覺,人就可能千辛萬苦地走回了出發之地。因此,在道德問題上,個人的生命體驗必應敞開:「我」要走向他人,我的境遇要與他人的境遇交換,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說的此事。《道德頌》的道德敏感也就在於此,盛可以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或者說,每當她忽然意識到這個問題時,她就忍不住將旨邑的聲音破開──她是矛盾的,她如此強悍地在「我」的邊界內申說道德,但是她也意識到,在任何真正的道德體驗中,「我」必須擴展為「我們」。
但誰是「我們」?是由「我」所選定的人們嗎?那麼這個「我們」就與「我」並無區別;這其中包括「你們」嗎?那些境遇不同,對何為善好有著完全不同的體認的人們?看起來,在這個問題上,盛可以極為猶豫。
這種猶豫反映在小說中,就是那個似有若無的敘述人稱──「我們」,盛可以必是認為它應該在,但對它究竟是誰、它能夠說什麼、它的觀點和態度全無把握,結果,這個「我們」就像現在這樣,站在小說的高處,模糊微弱地閃動。
──類似星空,但是星空晦暗。康得將道德律與天上的星空並提,既是說人類良知之神祕,也是說,道德終究關乎星空,所有的「解釋」並非絕對自足,它要指向解釋者之外的某個地方──那裡也許坐著個上帝,也許正是一片蒼茫。
正是在這一點上,《道德頌》中那個微弱的「我們」表露著這個時代精神之病的真正要害:它應該在,但它破碎、微弱、難以確認,而《道德頌》就是獻給這空茫混沌之「在」的一曲長歌。
◎李敬澤(著名評論家、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