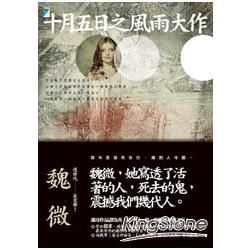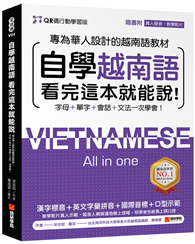這世代--火文學
寫作是殺死自己,讓別人守靈!
寶瓶文化與重慶出版集團共同策劃出版,兩岸同步發行!
魏微,她寫透了活著的人,死去的鬼,
震撼我們幾代人。
部分作品已譯為英、法、日、韓、波蘭等多國文字!
◎擊敗韓寒,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年度小說家獎」,被譽為最具潛力的國際性年輕作家!
最美好的,我們終將失去,
那比火焰更冷,比冰塊更燙,
一熱便要熄滅……
她的小說,筆下的人物個個有血有肉,
有點無奈,有點輕狂,有點脆弱,有點奔放,
她的文字如一把弦,沉靜而又不張揚,
她寫盡每個微不足道的片刻。
她書寫生命的暖溫和寒意,
她書寫那些蘊含著遺憾、後悔、狂喜、孤獨、哀愁的臉孔,
她是魏微。
魏微是個心性很高、同時又保有對未知世界高度著迷的作家。她擅寫人情百態,不刻意,不造作,她幾筆輕輕帶過,形神兼具,每一次都出手不凡,可媲美張愛玲的荒涼寡淡,蕭紅的細膩入微。
本書收錄魏微極為優秀的短篇小說,10篇故事,10種人生。面對她的小說,我們得以窺見眾生相的老到滄桑,及其悲歡聚散。她,寫盡人們的生之燦爛,死之寂滅,大時代的小人物在她的筆下,幽微的、縹緲的、無以名狀的美好與愴痛,化成一束束流麗綻放的煙火,半明半暗,在我們心上燦爛乍響,回頭看,生活仍有著,一切不同了……
作者簡介
魏微
1970年生於江蘇,作品構思新穎,文筆細膩動人,刻寫日常生活的人事入木三分,小說曾登1998年、2001年、2003年、2004年中國小說排行榜。作品曾獲《人民文學》獎、《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中國小說學會獎等多個國家級文學大獎,部分作品被翻譯成英、法、日、韓、波蘭等多國文字。
魏微從24歲開始寫作,27歲開始在《小說界》發表作品,迄今已在《花城》、《人民文學》、《收穫》、《作家》等刊物發表小說、隨筆近一百萬字。她自認熱愛寫作,認為活著是一件迷人的事情,即便瑣碎,平凡,可是生之燦爛。假如不寫作,就是個簡單的日常女人。
細讀魏微的故事後,令人驚嘆能從中看到張愛玲的依稀背影,能給予一個閱讀者足夠的魅惑;另外,在2010年的年度小說家獎的評選上,魏微曾擊敗排在提名名單第一位的韓寒,獲得了「第九屆華語文學傳媒年度小說家獎」。已出版長篇小說《拐彎的夏天》、《流年》、《一個人的微湖閘》;小說集《越來越遙遠》、《情感一種》;散文集《你不留下陪我嗎》、《到遠方去》、《既曖昧又溫存》。
《拐彎的夏天》、《一個人的微湖閘》中文繁體版由寶瓶文化出版。